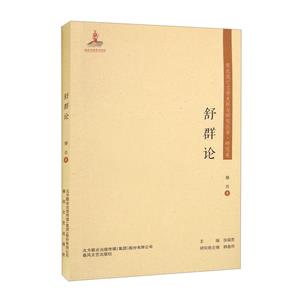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東北流亡文學史料與研究叢書:舒群論 版權信息
- ISBN:9787531361527
- 條形碼:9787531361527 ; 978-7-5313-6152-7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東北流亡文學史料與研究叢書:舒群論 內容簡介
舒群(1913-1989),現代著名作家,一般被視為“東北流亡作家”之一,自成名作《沒有祖國的孩子》發表以后,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一直活躍于左翼文壇,新中國成立后雖然政務纏身,也陸陸續續有作品發表。縱觀舒群一生,發表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共計一百多萬字,雖不是著作等身,作品質量參差不齊,但就主要作品的數量與風格而言,也足以自成一家,因而,對舒群做專門論述是可行的。
東北流亡文學史料與研究叢書:舒群論 目錄
第二章 舒群小說的人物群像與題材選擇
第三章 舒群小說的思想特質
第四章 舒群小說藝術風格論
第五章 舒群小說的敘事、倫理與人性的糾纏:以《秘密的故事》為例
第六章 轉變后的舒群創作
參考文獻
附錄:舒群創作系年
東北流亡文學史料與研究叢書:舒群論 節選
再考察1949年以后、特別是“十七年”時期的紅色經典,我們會發現,民族革命戰爭背景下的女性又成了另一種模式——“女戰士”模式,即將女性徹底男性化,成為革命/戰爭中的槍桿,比如《野火春風斗古城》里的金環、銀環,《鐵道游擊隊》里的芳林嫂,《新兒女英雄傳》里的楊小梅,等等。這些作品與人物都較為簡單,對女性做“減法”,將女性人物簡化到*低限度,與男性戰士/革命者差堪比擬。 在這些作品中,戰士/革命者的身份是具有優位性、排他性的,其他身份相較之下必然是微不足道。這不僅表現在它比其他身份更重要,更表現在對其他身份的徹底摒棄。于是,犧牲一己私利乃至自己、愛人或親人的性命以維護革命利益也就勢所必然。這些作品一定不遺余力地將選擇時的誘惑、痛苦、短暫的猶疑以及*終忍痛后的斬截無限放大,不吝以*動人的筆觸渲染其間的張力。也正因此,這些小說基本看到開頭便能猜到結尾,呈現出模式化的面貌。這樣的模式化,也正是意識形態宣傳所需要的。 不過,女性本應有著多重身份,比如母親、妻子、朋友、情人、國民、革命者等,也因此注定會有多種情感和人性的向度,她會愛孩子、愛丈夫或者情人,也會愛國、獻身于革命。但為了意識形態宣傳的需要,文本難容多重話語的共存,私人話語因為宏觀話語的鼓蕩而被芟減凈盡。在1949年以后,民族主義話語的正當性當然不容置疑,作品也只需突出表現女戰士,表現其愛國熱情與能征善戰,其他的人性向度早就可有可無,遑論女性獨有的向度。戰爭中的女性形象也便單一化、模式化。如此想象戰爭中的女性、如此呈現人性向度顯然太過簡單。 但是,在《秘密的故事》中,小說至少為我們展示了民族革命背景下女性的四個維度:情人性、妻性、母性、暴力。借用路德維希“克婁巴特拉傳”的標題,可以概括為:情人、母親、戰士、妻子①: 一、情人。袁倪對青子的眷戀無時或已,一俟重逢,更顯熾烈。與此同時,青子卻對袁倪早已失去興趣,只是心系抗日大業,因利用袁倪對抗日仍有所幫助,才與之虛與委蛇。袁倪對此并無感知,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袁倪的一廂情愿和青子的周旋不已形成張力,成為小說主要的推動力。行禮如儀的夫妻之情當然不能有此偉力,唯有逾越倫常的虐戀情深才能成為摧枯拉朽的洪流,席卷著袁倪拋妻棄母,一路忘我狂奔。這虐戀正如青子給他的一吻:“然后她吻住了我一面的臉頰,許久,不肯放開我,好像要從我臉上吻下一塊肉,才是終了。”夾雜著快意和痛苦的詭異感覺,使袁倪既害怕又沉迷不已。 二、妻子。青子在小說中扮演著妻子的角色。小說對青子和她丈夫之間的情況交代很少,我們卻可從不多的文字中略窺一二。青子當年嫁給丈夫后,便隨他一起投身民族革命。兩人同為義勇軍戰士,不得不服從大局,因而聚少離多,根本難以顧及家庭的經營,青子因此對于自身妻子的角色和身份投入甚少。兩人之間雖然感情平淡,但也有夫妻之情,這從送別時的細節不難看出,只不過,兩人其實更近于并肩作戰的同志關系,夫妻之情被民族主義倫理整合進了自身的邏輯,實際上已被湮沒、銷蝕。 另一方面,小說對敘事人袁倪的妻子苓子著墨甚多,并將她的賢惠寫到極致。與青子不同的是,苓子扮演了典型的“妻子”角色,這一身份幾乎占據了她的整個生命。詭異的是,越是鋪陳她的賢惠,越是反襯出她作為妻子的無力。苓子日復一日、無怨無悔的付出,抵不上青子的一個小動作、一句軟語溫言,數年來日積月累的夫妻之情,也抵不上年湮代遠的舊愛。或許,我們從中并不能讀出袁倪對青子有多深的情意,反倒看出“妻性”在“情人性”面前的全面潰敗。試想,若是當年青子與袁倪成婚,她的一言一行還能如此魅惑? 三、母親。相對于“五四”小說對母愛的極力歌頌,這一小說則要復雜、曖昧許多。小說中,青子和丈夫育有一女一子。起初,作為母親的青子對孩子的情感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因為難以從民族革命中抽身:并未盡到母親的責任,兩個孩子長期無人看顧,她為此飽受煎熬。丈夫死后,隨著她對革命的越發狂熱,革命已然成為絕對律令,病子又成了拖累,她必須結束這一兩難的局面,而殺子后的狂笑正印證了她內心的痛苦——她對孩子有著太多不舍,只不過,對民族主義倫理的偏執已使她喪失理性,逼得她親手絞殺了親情倫理。 袁倪與其母親的關系也耐人尋味。母親愛袁倪,但這其中有無私,也有自私,她也傷害了袁倪,有主觀導致的,也有無意為之的,因而,袁倪對母親也是愛憎交加。小說一開始,“我”便交代,自己愛著母親。可是,當母親為了讓“我”斷絕舊愛,藏起了僅存的青子舊照,苦尋無果后,“我”竟這樣描述母親:“‘你找什么?’母親問我,她的聲調,很不自然,仿佛有些慚愧,有些虛偽,有些憤恨。”“我”向苓子提出離婚,母親不允,并說除非在她死后。于是,當深夜街上乞討者的手風琴聲聲入窗,“我”竟起了詭異的念頭:“‘要在我死后!’這句話引起了我一種幻想——想象那琴聲是母親的葬曲了。”對情感的各個隱秘面、陰暗面的鉤沉,造就了這一小說的曖昧與深度。 四、戰士。有革命倫理打底,暴力的使用也便獲致了正當性,“暴力革命”本是偏正詞組,卻幾乎成了人們習以為常的同義反復。不暴力,怎么能蕩滌舊跡,通向未來?人們不會有阿倫特的洞見:“革命”一詞雖由來已久,本指英國式的“光榮革命”,直至法國大革命以后才染上了血與火的雄渾色彩。這一偏至背后,可能是目的和手段的倒錯。①當女性成了女戰士,怎能不暴力甚至嗜血。舒群不動聲色、詳細入微地描述了青子殺子的暴力場景,看似冷靜客觀,不加評論,立場卻隱然由敘事人之口托出。 ……
- >
自卑與超越
- >
有舍有得是人生
- >
姑媽的寶刀
- >
中國歷史的瞬間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朝花夕拾
- >
我與地壇
- >
羅庸西南聯大授課錄
- >
朝聞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