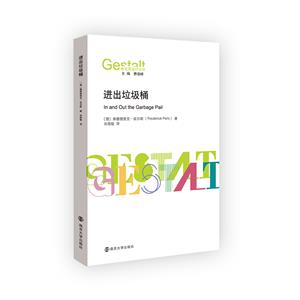-
>
妙相梵容
-
>
基立爾蒙文:蒙文
-
>
我的石頭記
-
>
心靈元氣社
-
>
女性生存戰爭
-
>
縣中的孩子 中國縣域教育生態
-
>
(精)人類的明天(八品)
進出垃圾桶 內容簡介
本書為德國著名心理學家、格式塔治療之父弗雷德里克·皮爾斯的一部獨特的自傳,首次出版于1969年12月。作者應用了他聚焦于覺察的理論,寫下了“想要寫下的任何東西”,全面審視并深刻剖析了自己過往的生活與當下的狀態。本書文體特別,集反思、回憶、理論、詩句和討論于一體,部分文字采用了詩歌體裁,有時候卻又是高度理論化的;文中充滿了各種文字游戲,寫作風格活潑,非常自然,極具個人特色。這些風格獨特的文字,既展示了皮爾斯格式塔治療的形成與發展,也讓我們感嘆于這一療法的驚人效果。
進出垃圾桶 目錄
從書序一
從書序二
正文
譯名對照表
進出垃圾桶 相關資料
這一次我打算寫寫我自己。毋庸置疑,任何一個打算寫自傳的人,或多或少地,都帶有主觀色彩。當然你可以說書寫的是所謂的客觀觀察或者概念和理論,但是觀察者終究是這些觀察的一部分。或者他會選擇所觀察的內容,又或者他遵循老師的指令,這種情況下他自己的卷入可能減到很小程度,但是仍然存在。
因此,我再說一遍。難免武斷——永遠不要說:“我的觀點是……”
我的名字是弗里德里希·薩洛蒙·皮爾斯(Friedrich Salomon Perls),美式寫法是弗雷德里克·S. 皮爾斯(Frederick S. Perls),通常被人稱為弗里茨或者弗里茨·皮爾斯,有時候是弗里茨博士——寫這些的時候我感覺多少有點輕巧和官方化。我也在想,我是寫給誰看呢,而且最要緊的是,我能有多真誠。哦,我也知道,我并不指望做真情告白,但是我希望我對自己是誠實的。那我會面臨什么風險呢?
我成了一個公眾人物。從默默無聞的中下層猶太男孩成為一個平庸的精神分析師,最后成為一種“新”療法和一種能夠給人類帶來幫助的新哲學的擁護者。
這是否意味著我是個大善人或者我希望為人類服務呢?實際上,我問出這個問題就表明了我的懷疑。我相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我自己,為了我解決問題的興趣,更多的是為了我的虛榮心。
當我能夠成為主角,炫耀快速觸及一個人的本質和困境的特技時,我感覺無比良好。然而,我一定還有另外一面。無論何時,當有真實的事情發生的時候,我都深深地被觸動,當我與一個患者在深層相遇的時候,我完全忘記了我的觀眾和他們可能的贊美,我那時是全然在那里的。
我可以做到這樣。我可以完全“忘記”我自己。比如1917年,我們駐扎在一個火車站附近。當這座火車站被炸毀的時候,兩輛載有彈藥的火車相撞,在炮彈紛飛中,我毫無恐懼地奔向那里,也顧不上我的皮肉,趕到傷員身邊。
看,我又來了,吹噓。炫耀。也許我夸大或者編造了這件事?一個人幻想的限制是什么?就如尼采所說:記憶和驕傲在打仗。記憶說:“是那樣的。”驕傲說:“不可能是那樣的!”然后記憶屈服了。
我感覺到防御。我的營長是一個反猶太者。他曾經因此感到壓力,但是當他要為我寫推薦信的時候,壓力就落到我頭上了。
我在做什么?凝視一個自我折磨的游戲?還是在炫耀。看,我多么誠實!
歐內斯特·瓊斯曾經叫我展示者,不帶惡意。他性格溫和,也喜歡我。
這一次我打算寫寫我自己。毋庸置疑,任何一個打算寫自傳的人,或多或少地,都帶有主觀色彩。當然你可以說書寫的是所謂的客觀觀察或者概念和理論,但是觀察者終究是這些觀察的一部分。或者他會選擇所觀察的內容,又或者他遵循老師的指令,這種情況下他自己的卷入可能減到很小程度,但是仍然存在。
因此,我再說一遍。難免武斷——永遠不要說:“我的觀點是……”
我的名字是弗里德里希·薩洛蒙·皮爾斯(Friedrich Salomon Perls),美式寫法是弗雷德里克·S. 皮爾斯(Frederick S. Perls),通常被人稱為弗里茨或者弗里茨·皮爾斯,有時候是弗里茨博士——寫這些的時候我感覺多少有點輕巧和官方化。我也在想,我是寫給誰看呢,而且最要緊的是,我能有多真誠。哦,我也知道,我并不指望做真情告白,但是我希望我對自己是誠實的。那我會面臨什么風險呢?
我成了一個公眾人物。從默默無聞的中下層猶太男孩成為一個平庸的精神分析師,最后成為一種“新”療法和一種能夠給人類帶來幫助的新哲學的擁護者。
這是否意味著我是個大善人或者我希望為人類服務呢?實際上,我問出這個問題就表明了我的懷疑。我相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我自己,為了我解決問題的興趣,更多的是為了我的虛榮心。
當我能夠成為主角,炫耀快速觸及一個人的本質和困境的特技時,我感覺無比良好。然而,我一定還有另外一面。無論何時,當有真實的事情發生的時候,我都深深地被觸動,當我與一個患者在深層相遇的時候,我完全忘記了我的觀眾和他們可能的贊美,我那時是全然在那里的。
我可以做到這樣。我可以完全“忘記”我自己。比如1917年,我們駐扎在一個火車站附近。當這座火車站被炸毀的時候,兩輛載有彈藥的火車相撞,在炮彈紛飛中,我毫無恐懼地奔向那里,也顧不上我的皮肉,趕到傷員身邊。
看,我又來了,吹噓。炫耀。也許我夸大或者編造了這件事?一個人幻想的限制是什么?就如尼采所說:記憶和驕傲在打仗。記憶說:“是那樣的。”驕傲說:“不可能是那樣的!”然后記憶屈服了。
我感覺到防御。我的營長是一個反猶太者。他曾經因此感到壓力,但是當他要為我寫推薦信的時候,壓力就落到我頭上了。
我在做什么?凝視一個自我折磨的游戲?還是在炫耀。看,我多么誠實!
歐內斯特·瓊斯曾經叫我展示者,不帶惡意。他性格溫和,也喜歡我。
的確,我具有一些自我展示的傾向——甚至在性方面——但是窺探的興趣總是更大。更進一步講,我不相信我想要炫耀的需要可以被簡單地解釋為性變態。
盡管我有這么多的自吹自擂,但是我不太想著自己,這一點我很確定。
我的中間名字是薩洛蒙。英明的薩洛蒙大帝宣稱:“虛榮,盡是虛榮!”
我甚至不能吹噓我特別虛榮。然而,我確信,大多數的炫耀是出于過度補償。不僅僅是補償我的不確定,而且是過度地補償,好對你催眠,讓你相信我真的天賦異稟。而且不容置疑!
我和我的妻子很多年來都在玩這樣一個游戲:“你一定是被我吸引了吧?你能否認嗎?”直到我意識到我總是被壓制,我壓根兒贏不了。那個時候我仍然對人類愚蠢的游戲感興趣——認為贏是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
歸根結底都落到自尊、自愛和自體意象的問題上。
自尊和其他任何一個心理現象一樣,也存在極性問題。與高自尊、自豪、榮耀、自覺高人一等相對的是:感覺低下、無價值、卑微、渺小。就像英雄與寒士。
…………
這帶領我們進入存在主義哲學的領域。關于存在性議題的澄清,我相信相當程度上聚焦于虛榮和真誠的存在,甚至可能為我們的社會和生物存在之間的分裂提供解藥。
作為生物性個體,我們是動物;作為社會性存在,我們扮演各種角色,上演各出戲。作為動物,我們為生存而殺戮;作為社會性存在,我們為了榮耀、貪婪和復仇而殺戮。作為生物性存在,我們過著一種與自然息息相關的生活;作為社會性存在,我們實行一種“仿佛”性存在(費英格:《“仿佛”的哲學》),這種存在充斥著大量的現實、幻想和假裝的混淆。
對于現代人來講,這個問題可以歸結為通常不兼容的兩個方面,自體實現與自體概念,或者自體意象的實現。
1926年我成為庫爾特·戈爾德施泰因的助手,治療腦損傷士兵。之后我會多談一下他。現在我只想提一下,他曾經使用過“自體實現”這個詞,我那時并不理解。25年后,當我從馬斯洛的嘴里聽到這個詞的時候,除了覺得它聽起來是個好東西外,還不是很理解,它的意思就像是你要真誠地表達自己,但是又要刻意去做。這相當于一個項目、一個概念。
很多年之后,我才從格特魯德·斯坦的“玫瑰是玫瑰就是玫瑰”的意義上理解了自體實現的本質。
自體概念的實現就如弗洛伊德所說的理想自我。然而,弗洛伊德像變戲法似的交替使用“超我”和“理想自我”的概念。它們絕對是不同的現象。超我是道德性的,具有控制的功能,只有百分之百渴望服從的自我才稱它(超我)是理想的。弗洛伊德在理解自體這點上從來沒有說到點子上。他卡在自我上了。母語是英語的人在理解弗洛伊德的邏輯方面還有另外一個困難。在德語中,“自我”和“我”是同義詞。在英語中,“自我”的含義接近自尊系統。我們可以把“我想要認可”翻譯為“我的自我需要認可”,但是“我想要一片面包”不能翻譯為“我的自我需要一片面包”。這樣說聽起來很荒謬。
“自體實現”是一個現代詞語。它已經被嬉皮士、藝術家,還有心理學家——抱歉這樣說——美化、扭曲了。它已經成了一個項目和成就。這就是物化的結果,一種把過程變成物的需要。這種情況下,這甚至意味著神化和美化一個位點,自體僅僅顯示發生事情的“位置”,自體需要和他者性做對比才有意義。
自體是一種指示燈,“我自己做”僅僅表明沒有其他人做,必須用小寫字母。一旦把它寫成首字母大寫的“Self”,很容易就把一部分——一個非常特別的部分——當成整個有機體。它近似于陳舊的靈魂概念或者哲學本質的概念,被當成有機體的“本源”。
相反的是潛能和自體實現。小麥的種子具有成為一株植物的潛能,小麥植株就是它的自體實現。
注意:自體實現意味著小麥種子會實現成為小麥植株而不是黑麥植株。
…………
最近我找到一種更具有建設性的方式對付我的無聊:坐下來寫作。如果沒有無聊的感覺,我可能也不會坐下來,在紙上寫字。
這聽上去是我在精神病院經常做的事情的反過程:也就是說,無聊是阻礙真正興趣的結果。
現在我是否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美化自己是我生活的真正興趣,我奴役并動用它來服務于偉大的弗里茨·皮爾斯形象?也就是說我沒有實現我的自體,而是實現一種自體概念?
突然之間,這點對我來講非常貼切,“應該主義”也是。自體概念實現是一種罪。我是否正在變成清教徒?
再回到自體實現的“美德”和自體實現的現實。
讓我們把小麥和黑麥種子的例子推到極致。
很明顯,老鷹通過在天空翱翔、捕食小動物、筑巢來實現自己的潛能。
很明顯,大象的潛能在體型、力量和笨重方面得到體現。
沒有老鷹想要成為大象,也沒有大象想要成為老鷹。它們“接受”自己,它們接受它們的“自體”。不對,它們甚至無所謂接受不接受,因為接受意味著存在拒絕的可能性。它們理所當然地接受自己。不對,它們甚至也無所謂理所當然,因為理所當然意味著還有其他的可能性。它們就是如此。它們就是它們的天性使然的存在。
如果它們像人類一樣,具有幻想、不滿和自欺,該多么荒謬!如果大象厭倦了在陸地上行走,想要飛翔,想吃兔子,還會下蛋,那是多么荒謬。如果老鷹想擁有野獸的力量和厚厚的皮肉,那是多么荒謬。
把這些都留給人類吧——想要變成別的樣子——懷揣不能觸及的理想,被完美主義詛咒,只有完美才能免于被批評,經受無窮無盡的心理折磨。
一邊是一個人的潛能及其實現,另一邊是對這種真實的扭曲,二者之間的差距已顯而易見。“應該主義”抬起了丑陋的頭。我們“應該”消除、否認、壓抑、忽略很多真實的特征和源頭,而增添、假裝,以及扮演和發展不被我們的生命沖力支持的角色,制造了不同程度的虛假行為。不同于真實的人的整體性,我們是片段化的、沖突的、帶著麻木絕望的紙人。
內穩態這個自體調節和有機體自體控制的精妙機制,被一個外部的強加的控制狂取代,一個人和物種的生存價值被削弱。軀體化癥狀、沮喪、厭倦和強迫性行為取代了生活樂趣。
心與身的二分法,是深植于我們文化的最深層的分裂,而且被當成理所當然:這種迷信認為具有兩種分離又彼此依賴的物質,即心靈和身體。數不清的哲學家提出了各自的假說,要么斷定思想、精神或心靈創造了身體,要么從物質主義角度出發,認為這些現象或者副現象是物質的結果或者超級結構。
以上兩種都不對。我們就是有機體,我們(指的是神秘的第一人稱“我”)不擁有有機體。我們就是一種整體的單位,但是我們具有從這個整體中抽象出很多部分的自由。是抽象,不是減去,不是分裂。我們可以根據我們的興趣,有機體的行為、社會功能或者生理狀態,解剖學,或者這個、那個方面進行抽象,但是我們需要保持警覺,不要把任何抽象出來的東西當成整體有機體的某個“部分”。興趣和抽象概念,以及部分和格式塔浮現之間的關系,我以前已經寫過了。我們可以具有抽象概念的組合,我們可以趨近了解一個人或者一個東西,但是我們永遠不可能具有對物自體全部的覺察(用康德的話來說)。
我現在是不是太哲學化了?畢竟,我們太需要一種新的定向、一個新的視角了。對于定向的需要是有機體的功能。我們有眼睛和耳朵等,讓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定向,我們的本體感受神經幫助我們知道皮膚內發生了什么。哲學化意味著重新在一個人的世界中定向。信仰是一種哲學,一種不言自明的參照系統。
哲學化是我們智力游戲的一個極端例子。它尤其符合“符合”的游戲。
也許還有其他游戲,但是我看到兩種主導我們大部分定向和行為的游戲。比較的游戲和符合的游戲。抽象是有機體的功能,但是一旦我們從情境中抽象后,就把它們變成了符號和數字,然后它們就成了游戲的材料。拿雙關和繞口令來講,就可以說明我們可以讓抽象概念離原始情境有多遠。
進出垃圾桶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弗雷德里克·皮爾斯(Frederick Perls,1893—1970),德國著名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師、心理治療師,格式塔治療之父。代表作有《自我、饑餓與攻擊》《格式塔治療實錄》《進出垃圾桶》《格式塔取向與見證治療》《格式塔治療:人格中的興奮與成長》(合著)等。
譯者簡介
吳艷敏,心理學碩士,中國心理學會注冊系統注冊心理師,心理平臺簽約成熟咨詢師、督導師。具有豐富的心理學口譯和筆譯經驗,譯有《弗里茨·皮爾斯:格式塔治療之父》《格式塔治療實錄》等。格式塔自媒體“歌詩道心理”負責人,開放、形成中未定型的格式塔治療學習者和實踐者。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裝共3冊
- >
莉莉和章魚
- >
中國歷史的瞬間
- >
【精裝繪本】畫給孩子的中國神話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伯納黛特,你要去哪(2021新版)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朝花夕拾
- >
羅曼·羅蘭讀書隨筆-精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