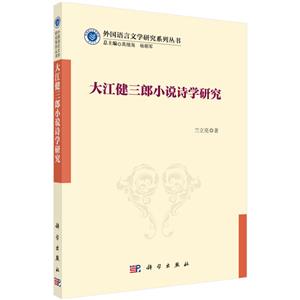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大江健三郎小說詩學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696540
- 條形碼:9787030696540 ; 978-7-03-069654-0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大江健三郎小說詩學研究 本書特色
蘭立亮同志在對大江小說文本進行詳細考察的基礎上總結了大江小說詩學的總體特征。本書對大江“文學理論家”地位的認同,可以說基于蘭立亮同志對大江小說理論的全面理解和對大江創作實踐的綿密考察,高度概括了大江小說的詩學特征。
大江健三郎小說詩學研究 內容簡介
《大江健三郎小說詩學研究》嘗試從文本細讀入手,考察日本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大江健三郎幾部長篇小說代表作在小說形式審美層面的詩學實踐,探討大江的小說形式實驗與小說主題建構、倫理訴求的關聯,并結合大江的文學理論著作、文藝隨筆、演講、訪談等反映大江文藝思想的理論文獻深入挖掘大江小說詩學所體現的濃厚的社會文化意蘊和強烈的現實關懷,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對大江小說詩學特征進行宏觀把握。
大江健三郎小說詩學研究 目錄
叢書序
序
緒論 1
**章 《感化院少年》的創傷敘事與主體建構 4
**節 自我與他者:凝視與反凝視 4
第二節 作為烏托邦/異托邦的空間二重性 7
第三節 空間的逃離:創傷書寫與倫理訴求 11
小結 14
第二章 《個人的體驗》的鏡像敘事與身份認同 16
**節 自我欺瞞的空間:“非洲”和“多元宇宙” 17
第二節 動物比喻、鏡像與身份認同 23
第三節 從逃避現實到回歸家庭的倫理敘事 29
小結 33
第三章 《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的時空敘事與身份認同 34
**節 歷史時間與心理時間 35
第二節 地理空間與精神空間 39
第三節 歷史記憶與身份認同 43
小結 47
第四章 《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的個體記憶與歷史書寫 49
**節 父子關系的隱喻:從家庭到國家 50
第二節 內部暴力呈現與身份認同焦慮 53
第三節 真實與虛構:搖擺的“同時代史” 56
小結 59
第五章 《別了,我的書!》的互文性敘事與晚期風格 61
**節 雙重敘事結構與元小說技法 61
第二節 互文性敘事與小說主題建構 66
第三節 “奇怪的二人組合”與“晚期風格” 70
小結 75
第六章 《優美的安娜貝爾 李寒徹顫栗早逝去》的跨界敘事與身份認同 77
**節 現在時技法與影像敘事 78
第二節 翻譯與改編:身份認同的探尋和建構 81
第三節 紀實與虛構:私小說敘事中的元小說技法 85
小結 89
第七章 《水死》的戲劇敘事與倫理訴求 91
**節 戲劇元素與人物形象塑造 92
第二節 戲劇化特征與小說主題生成 98
第三節 戲劇敘事與晚期風格 104
小結 112
結語 113
參考文獻 116
附錄一 中日兩國大江健三郎小說詩學研究概論 139
附錄二 日本期刊大江健三郎研究論文文獻輯錄 168
后記 209
大江健三郎小說詩學研究 節選
緒論 鮑里斯 托馬舍夫斯基在《詩學的定義》中指出,“詩學的任務(換言之即語文學或文學理論的任務)是研究文學作品的結構方式。有藝術價值的文學是詩學的研究對象。研究的方法就是對現象進行描述、分類和解釋”。作為一個文學理論概念,小說詩學是對小說創作風格和敘事結構進行研究的一項審美策略。雖然,當前的小說詩學已超越了研究小說文體、結構、創作技巧等形式的傳統研究領域,進入了通過對文學文本和文學現象的文化解析來提倡人文關懷和詩意追求的“文化詩學”領域,但對審美形式的探索仍然是小說詩學研究的基本內容。 大江健三郎是一位對小說形式極為關注的作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歇爾 耶思普瑪基在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中切中肯綮地指出了大江文學的顯著特征。“大江說他的眼睛并不盯著世界的聽眾,只對日本的讀者說話。但是,其中存在著超越語言與文化的契機、嶄新的見解、充滿凝練形象的詩這種‘變異的現實主義’。讓他回歸自我主題的強烈迷戀消除了(語言等)障礙。” 的確,大江文學具有濃厚的社會文化意蘊和強烈的現實關懷,這一點與日本當代社會文化語境息息相關。“變異現實主義”這一大江文學特征,如果脫離了其小說形式就成為空洞的評價。大江小說的文學訴求與作家的形式創新緊密結合,使形式本身具有了主題建構的重要意義。在這個意義上,大江的小說詩學無疑會為中國作家的小說創作提供重要的借鑒。在大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中國和日本的研究者重新開始審視大江的小說詩學,出現了一些頗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詳見附錄一),但從整體來看,這一領域的研究尚需進一步拓展和深入。之所以如此,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在于大江小說創作數量龐大且風格多樣,而且不斷在對舊作題材、主題的重新書寫中推陳出新,這就要求研究者要持續關注大江的小說創作,同時,對大江的文學理論著作、文藝隨筆、演講、訪談等與大江文藝思想密切相關的內容也需要深入研讀,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把握大江小說詩學的發展脈絡和思想精髓。 大江既是作家,又是文學理論家,其小說詩學毫無疑問包含了“理論”和“實踐”兩個向度,二者互相闡釋,共同構成了大江小說詩學不可分割的部分。由于大江的小說創作在文學界影響深遠,在某種程度上遮蔽了其文學理論家的光芒,造成許多研究忽略了其文學理論在其小說詩學中的重要作用,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因此,學界需要一種將二者結合起來的整體性思路來拓展大江小說詩學研究領域。本書嘗試將小說理論和小說個案考察緊密結合起來,探究文本所反映的大江的思想文化來源,真正分析并歸納出大江小說詩學的主要內涵及其總體特征。大江對世界文學、現代思想發展狀況極其關注,同時在電影、音樂、繪畫等藝術領域造詣頗深,這使其小說詩學具有了廣闊的世界文學、文化背景和明顯的跨媒介特征。因此,比較文學的跨界視野為將大江小說詩學置于世界文學、文化背景及當代日本社會文化語境中給予重新觀照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可以說,只有將宏觀理論研究和微觀文本分析結合起來,將比較文學、文化視野導入大江小說詩學研究,才能真正理清大江在小說結構、技法和思想表達方面對西方文藝理論、現代思想的吸收、借鑒,以及對日本傳統敘事文學批判繼承的創作脈絡,真正把大江小說詩學研究推向深入。 大江健三郎小說詩學研究一直是筆者研究的對象。為了更為全面地考察大江小說詩學的整體特征,本書選取大江早期、中期和晚期的長篇小說作為研究對象。其中,《感化院少年》為大江**部長篇小說,在其早期創作中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個人的體驗》為第11屆“新潮文學獎”獲獎作品,是大江“與殘疾兒共生”主題系列的扛鼎之作;《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為第3屆“谷崎潤一郎獎”獲獎作品,是一部將歷史、現實共時再現,蘊含著之后大江小說諸多創作主題萌芽的巔峰之作;《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在小說敘事上極具實驗性,為大江反天皇制主題小說的代表作;《別了,我的書!》是晚期三部曲“奇怪的二人組合”*后一部,集中體現了大江的“晚期風格”;《優美的安娜貝爾 李寒徹顫栗早逝去》是中國“21世紀年度*佳外國小說(2008)微山湖獎”獲獎作品,充分體現了大江小說創作的跨界思維;《水死》為2016年度國際布克獎長名單入圍作品,是一部采用戲劇表現手法,對《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優美的安娜貝爾 李寒徹顫栗早逝去》等舊作進行改寫,明確體現大江“重寫”這一晚期創作風格的恢宏之作。以上小說無論是發表后的社會反響,還是在大江創作中的地位,都可以說代表了大江某一時期小說詩學的集大成之作,很好地體現了大江小說詩學的發展脈絡和總體特征。本書試圖從小說敘事入手,考察大江小說形式實驗的先鋒色彩,探討小說形式實驗與小說主題表達、倫理訴求的關聯,深入挖掘大江小說詩學所體現的對日本和世界文學、文化思潮的認識和接受,以期對中國讀者深入理解日本當代文學,對中國的當代文學創作提供有益的借鑒。 **章 《感化院少年》的創傷敘事與主體建構 《感化院少年》的創傷敘事與主體建構 《感化院少年》(『芽むしり仔撃ち』1958)是大江健三郎**部長篇小說。該小說講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為躲避敵軍轟炸,一群感化院少年被疏散至一個位于山谷中的小村莊后發生的故事。由于村里發生瘟疫,他們被村民拋棄,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建立了自己的共同體。但是,這一共同體*終在村民歸來后被迫解體,成員屈從村民的淫威而集體沉默,而堅貞不屈的“我”不得不在村民的驅逐下朝村外逃亡。小說以悲劇告終,但大江卻認為,通過創作這部小說,自己能夠以直率的形式將少年時期無論是甜美還是心酸的記憶在小說的意象中釋放出來,直言“對我來說是*令我感到幸福的作品”。也就是說,《感化院少年》直面慘淡的人生,生動地呈現了戰時日本人的精神生態,是一部源于大江戰時生活體驗的激情之作。在敘事上,別具一格的邊緣人物視角、意味深長的空間設置、哀婉凄楚的敘事格調,使這部小說所體現的戰爭反思和主體性叩問主題綻放出了璀璨奪目的人性之光。 **節自我與他者:凝視與反凝視 劉小楓指出,現代的敘事倫理包含著人民倫理的大敘事和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人民倫理的大敘事的教化是動員、是規范個人的生命感覺,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的教化是抱慰、是伸展個人的生命感覺”。《感化院少年》就是一部講述曾為不良少年的“我”在戰后這一時代語境中講述的自己的生命故事。 感化院是對失足少年進行改造的地方,對“我”來說,這一空間本身就意味著對人身自由的禁錮。感化院的高墻構成了文本中具體有形的“墻”,意指被囚禁之人與外部自由世界的隔離。疏散地“山谷村莊”雖然不同于感化院的高墻,但取而代之的卻是一種更深的禁錮。村民和感化院少年之間的隔閡使山谷村莊無論是在地理上還是在精神上都成為一個封閉的空間。在這一空間中,“我們”成了被凝視的他者。 我們這一群像被獵獲的怪獸一樣的異國人在眾人盯視的眼皮下,*安全的辦法就是變得像花草木石一樣,沒有眼睛、沒有感情,成為只供人觀賞的一件物品。正因為弟弟執拗地反盯著村里人,他的面頰有時就要遭受村婦卷著黃褐色的大舌尖啐出來的唾液,有時還要挨小孩子的石頭。 在此,“我”的弟弟在小說**章暫時成為**人稱回顧性敘述的視點人物,因為“我們”被物化,只能通過弟弟的眼光來呈現“我們”所處的境況。因為弟弟與“我們”不同,他并非因為犯罪,而是為了躲避美軍對城市的轟炸被父親送至感化院的,所以并沒有受到過感化院的規訓和懲罰,尚未習慣他人的凝視。“它(凝視—筆者注)通常是視覺中心主義的產物,觀者被權力賦予‘看’的特權,通過‘看’確立自己的主體位置,被觀者在淪為‘看’的對象的同時,體會到觀者眼光帶來的權力壓力,通過內化觀者的價值判斷進行自我物化。”在村民壓迫性的凝視下,“我們”這些感化院少年被剝奪了主體性,將自我物化為“只供人觀賞的一件物品”。天真無邪的弟弟“執拗地反盯著村里人”,顯然被村民視為挑戰他們的權威,勢必會遭受來自村婦和村里孩子的暴力。通過被凝視者被塑造為他者這一權力運作結果,大江揭示了凝視背后的權力規訓和壓迫。“我們”都無法擺脫代表國家權力的村民帶有歧視色彩的凝視對自我的控制,但對自由的向往又促使“我們”反凝視,這充分體現在南這一人物對南方的向往和多次逃跑這一行為上。小說**至第三章全面采用了“我們”這一非自然敘事形式,與村民(“他們”)涇渭分明地區分開來,本身就具有與山谷村莊村民共同體對抗的性質。“在絕大多數現代敘事作品中,正是敘事視點創造了興趣、沖突、懸念、乃至情節本身。”“我們”這一**人稱復數敘事,由于其所指人數模糊不定,從而具有較大的靈活性。“我們”一開始僅指感化院少年,之后,弟弟、朝鮮少年李、逃兵、少女等分屬不同群體的人陸續加入了進來,*后形成了與村民對立的少年共同體。石原千秋指出,小說敘事在“我們”與“我”之間自由穿行,“這使《感化院少年》的視點結構不穩定,‘我’的實質幾乎沒有涉及,這一點象征著只要‘我們’包含‘我’就行了”。的確,從表層看來,**人稱復數敘述屬于一種想象的集體身份,是講述少年共同體集體記憶的敘事裝置。或許可以說,使用**人稱復數敘事就是為了強化感化院少年這一群體與村民這一群體的對立,是一種反凝視的表現形式。“就意識再現(即對人類意識的映射—筆者注)而言,**人稱復數敘述顯然把作為個體的‘我’的意識與作為集體的‘我們’的意識推到了關注的*前沿。鑒于**人稱復數敘述者指稱范疇的模糊性,由此導致了其‘意識’再現的潛在沖突性。”從邏輯上看,在**章“抵達”和第二章“**次勞動”中,由于“我們”這一復數敘事形式的大量使用,“我們”的聲音與意識壓制了**人稱單數敘述者“我”的聲音和意識。但從第三章“傳染病流行和村民逃難”開始,隨著村民躲避瘟疫從村莊撤出,“我”開始從權力的規訓眼光中解脫出來,主體意識開始覺醒,獲得了觀察和講述的個人主體性,逐漸從“我們”這一群體敘事視點中解放出來,“我們”這一群體視點敘事也開始轉為**人稱單數“我”的個體敘事。 在村民撤離后,擺脫了村民凝視的個人主體性開始萌芽,與外界隔絕的山谷村莊這一封閉空間為文本中人物肉體和精神的歷練提供了廣闊的舞臺,成為少年們獲得個體成長的自由天地。第七章“捕鳥和雪節”描寫了相當于少年們成人儀式的狩獵活動。弟弟因捉到一只漂亮的野雞而獲得了同伴的贊嘆,“一邊大笑一邊不厭其煩地講述他的歷險記”。在朝鮮少年李的提議下,“我們”舉行了村
大江健三郎小說詩學研究 作者簡介
蘭立亮,河南南陽市人,河南大學外語學院日語系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河南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人員,主要從事日本近現代文學、文藝學研究。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2項、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面上項目1項,在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項。在科學出版社、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重慶出版社等出版專著2部和譯著多部。在《外國文學》《國外文學》《外語研究》《外國語文》《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日語學習與研究》《東北亞外語研究》《外文研究》《外語教育研究》等專業期刊發表論文20余篇。曾獲第八屆“孫平化日本學學術獎勵基金”三等獎、河南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特等獎、河南省社科聯優秀調研成果獎一等獎等。
- >
詩經-先民的歌唱
- >
巴金-再思錄
- >
我與地壇
- >
自卑與超越
- >
二體千字文
- >
中國歷史的瞬間
- >
新文學天穹兩巨星--魯迅與胡適/紅燭學術叢書(紅燭學術叢書)
- >
山海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