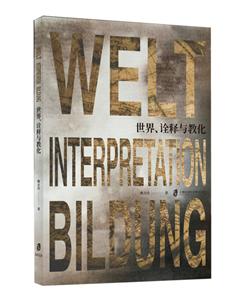預估到手價是按參與促銷活動、以最優惠的購買方案計算出的價格(不含優惠券部分),僅供參考,未必等同于實際到手價。
-
>
道德經說什么
-
>
電商勇氣三部曲:被討厭的勇氣+幸福的勇氣+不完美的勇氣2
-
>
新時期宗教工作與管理
-
>
帛書道德經
-
>
傳習錄
-
>
齊奧朗作品·苦論
-
>
無障礙閱讀典藏版:莊子全書
世界、詮釋與教化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2020519
- 條形碼:9787552020519 ; 978-7-5520-2051-9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世界、詮釋與教化 內容簡介
本書的追索之旅從千年流變的“世界”概念的詮釋開始, 對漢語哲學史開端的“心”“物”“德”“經典”概念以及相關喻象做了深入的詮釋, 還對西方源遠流長的經典詮釋和教化傳統作了系統的梳理分析。
世界、詮釋與教化 目錄
上篇 世界
**章 “世界”概念的緣起
第二章 “世界”概念的詮釋: 早期佛教與玄學合流之情勢
**節 loka的源始涵義
第二節 三千大千世界的佛教宇宙觀
第三節 大道而察:佛玄合流的世界圖景
第三章 天下—世界:從概念變遷看近代東亞世界圖景之變更
**節 中國古代“天圓地方”的“天下”圖景
第二節 漢傳佛教“多元多重”的“世界”圖景
第三節 “世界”還是“天下”:近代東亞世界圖景之變更
第四章 共在、同居和世界
中篇 詮釋
第五章 “傾聽哲學”與“觀的哲學”:兩種不同的詮釋學取向
第六章 水道與經典:儒家經典詮釋場域的形成及其核心特質
**節 “哲學的突破”與儒家經典體系的形成
第二節 “貫通水道”:儒家經典詮釋與注疏理念的形成
第七章 開放而收斂的水域:儒家經典詮釋的隱喻
**節 儒家經典詮釋理念的形成
第二節 開放而收斂的水域:儒家經典詮釋場域的特性
第三節 經典詮釋與思想創造
第八章 “物”的多重面相
**節 “物”之三訓
第二節 生生物化
第三節 “物”之成、序、位、格
第四節 與物同體
第九章 “直心為德”及其意象考釋
第十章 種“德”者必養其“心”
**節 王陽明經典詮釋思想的價值維度
第二節 “種德養心”和“下學上達”:王陽明的經典詮釋觀
第三節 朱王經典詮釋思想之異同
第十一章 孟莊“心”學殊異考
**節 孟子論心:“谷”之實達
第二節 莊子論心:“鏡”之虛靈
第三節 圣人之異:“養心”和“游心”
第四節 “心”之正負功夫
下篇 教化
第十二章 馴養、教化和自然
**節 musar:馴養與訓育
第二節 παιδεiα:轉化與教化
第三節wσι:生長與技藝
第十三章 成形與教化:愛克哈特論“神人合一”
**節 永恒沸騰的靈魂火花
第二節 流溢回返的教化循環
第三節 神人合一的純化之路
第十四章 “內在形式”:沙夫茨伯里的新自然神論
**節 內在形式和活的自然
第二節 情感教化和紳士理想
第三節 神圣秩序與和諧宇宙
第十五章 情感與教化:沙夫茨伯里道德哲學與審美話語辨析
**節 自然和教化
第二節 道德和情感
第三節 審美和秩序
第十六章 沙夫茨伯里對德國教化觀念的影響
**節 “內在形式”:從柏拉圖到沙夫茨伯里
第二節 “內在教化”:從萊布尼茨到厄廷格爾
第三節 “普遍的人”:德國古典教化觀念的核心
第十七章 內在之路:從神的肖像到自我教化
**節 教化觀念的源起
第二節 德意志運動與教化觀念的普遍化
第三節 自我教化:德意志運動的內在精神之路
附錄:被卷入難民危機里的“康德”
參考文獻
世界、詮釋與教化 節選
“傾聽哲學”與“觀的哲學”:兩種不同的詮釋學取向 “傾聽哲學”(philosophy of hearing)與“觀的哲學”(philosophy of observation)分屬于中、西兩種不同的詮釋傳統,前者立足于西方“語音中心論”(phonocentricism),后者則建立在中國“文字中心論”(writtencentricism)的基礎之上。語音中心論乃基于拼音文字的文本閱讀經驗,強調言說的語言,認為邏各斯與言語具有一種原始本質的聯系。伽達默爾堅持西方語音中心論傳統,認為理解與傾聽不可分割,沒有理解的傾聽是不存在的,也不存在某種沒有傾聽的理解。他將閱讀過程視為在相互傾聽中的對話過程,由此而奠定了“傾聽哲學”的基礎。 與之不同,德里達旗幟鮮明地提出了與傳統詮釋學觀念相對立的“文字中心論”的主張,以期能擺脫當代西方詮釋學發展所面臨的困境。但是要注意,他所講的文字是一種神秘的、先于書寫的“原初文字”(archiecriture),它所指向的是思維中交替顯、隱的思想軌跡(trace)。就此而言,他所倡導的“文字中心論”之本旨在于“書寫”,即文字被書寫的過程。他的基本觀點以及在此基礎上對“語音中心論”的批判,對于反思西方的詮釋傳統、進而建構中國詮釋學具有深刻的啟迪意義。我們的思考起點是對漢字的考察。根據潘德榮在《語音中心論與文字中心論》一文中所作的解釋,我們所講的“文字中心論”的解釋傳統立足于字形分析字義和文義,注重的是文字本身,在這個意義上,“觀”對于漢字這種形意文字,意義正猶如“聽”對于拼音文字。由此,成中英認為中國知識論可被稱為“觀的哲學”,即假定在“觀”的過程中,能看得見并感覺得到事物的本質,從而得到對事物、對世界的直接理解。這種獲取知識的模式使獲取知識成為對事物的本質的內在和直接的經驗,而不像西方知識論那樣經常把對事物的知識下降到感覺經驗或是上升到抽象的概念。 德里達的解構主義與成中英建立本體詮釋學卓有成效的嘗試,使我們更清醒地看到了發源于西方邏各斯中心論傳統中的詮釋學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建立中國詮釋學的重要意義。 德里達在《文字學》中把語音中心論等同于迄今一直主導西方文明的“邏各斯中心論”(logocentricism)。它以為“聲音與存在、聲音與存在的意義以及聲音與意義的理想性絕對近似”,認為心靈是思想、意義之源,而思維則追隨著理性與邏輯。這種邏各斯中心論可追溯到柏拉圖。柏拉圖認為文字既不明晰、也不可靠,像圖畫一樣,僵硬與死板的文字不懂如何“因材施教”,一旦出現誤解,只能束手無策坐待作者救援。在他看來,寫作只是保留了信息,卻不能保留邏各斯,因為邏各斯是書寫在靈魂之中的。正因為如此,柏拉圖將以寫作為生“混淆人心”的詩人逐出理想國。而亞里士多德則明確提出,口語是心靈的符號,文字則是口語的符號。作為崇尚視覺優先性的古希臘人在此陷入了一個悖論: 一方面,他們注重的是自然時空,特別是空間的自然真實性(當然他們的空間意識是雕塑式的立體意識);另一方面,他們給口語以優先地位,強調邏各斯中心說使“說”與“聽”的地位極為重要,而說與聽卻是一個不斷流逝的線性時間過程。正如羅蘭·巴特所言,聽覺的“時間”的符號就其特征而言,傾向于象征,視覺的“空間”的符號特征傾向于圖像。這樣一來,希臘人得以極大地發展了抽象能力,但與此同時,書寫能賦予語言以言語所不具備的空間—物理存在,這點卻被古希臘人忽略了。由此造成的結果就是,古希臘人不得不采取空間的方式來理解時間,聽、說造成的線性時間流程被空間化了。這種僵硬的缺乏時間內在節奏統領的空間觀,甚至影響到近代西方人采取了深邃無盡單向縱深的空間意識,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了牛頓的力學時空。但是“在此力學時空中,作為生命體驗的時間難以在場”。 在完成了語言學轉向后,海德格爾對語言本質(das Sprachewesen)、語言之本質(das Wesen der Sprache)與本質的語言(die Sprache des Wesens)在本體論上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海德格爾寫道:“文字顯示聲音,聲音顯示心靈的體驗。心靈的體驗顯示心靈所關涉的事情。”“惟有詞語才讓一物成其為物。”“詞語本身即是關系,因為詞語把一切物保持并且留存在存在之中。”“自希臘以來,存在者便一直被經驗為在場者。只要語言存在,那么語言,即時時存在著的說,就是一種在場者。人們從說方面,著眼于分音節的聲音和涵義的載體來表象語言。說乃是一種人類活動。”所以,“這種自身不拒絕只能以下訴方式說話,即它說:‘它是(Es sei)。’從此以后,詞語便是物之造化(Bedingnis)”。從中不難看出,海德格爾對“說”的強調,是深深地植根于語言與邏各斯的同一之觀念中的。就如上帝用語詞造物一樣,詞與物同時產生。這種邏各斯中心主義正是西方那種本質與現象二分的形而上學所賴以存在的根基。人們以為,自然界的一切東西只要能被命名就能被認識、理解、把握、征服。海德格爾對語言進行的本體論探討并未擺脫西方傳統形而上學的陰影,它實際上是由西方自古希臘以來就始終追求“在場”證明的強烈沖動所導致的。 海德格爾在向古希臘哲學尋找“在”的源頭時,發現了原始語言的內在矛盾性及融匯時空于一體所蘊藏的豐富性。正如麥克斯·繆勒所說的,“在創造神話的那個時代,每個詞,無論是名詞還是動詞,都有其充分的原生作用。每個詞都是笨重和復雜的,它們的內涵都非常豐富,遠遠超過它們應說的東西。所以,我們對于神話與語言中的千奇百怪,只能理解為會話的自然生長過程”。海德格爾指出:“現實語言的生命在于多義性,活生生、游移不定的詞轉化為單義的、機械僵硬的符號系列,乃是語言的死亡,此在的凍結與荒蕪。”這種認識使他能夠回歸古希臘充滿生命力的mythos精神傳統之中,但另一方面他還是無法擺脫語音中心論的束縛,有一種強烈的在場的“說”的沖動,而語言的本質恰恰是不可說的。這特別體現在他與日本學者手冢富雄教授的對話之中所持的那種對語言本質謹慎的沉默。他發現語言本質實質上是無法命名的,而只有選擇沉默的“寂靜之音”(das Gelut der Stille),即靜觀,這實際上預示著他已達到了詮釋學作為生命世界現象學的真正核心,即以生命為本體的詮釋學要致力于意義的不斷生長,正確的道路是只有回歸源初語言的豐富與混沌性中,在本體論上持靜觀的態度,體察到在“文字”的“書寫”中時間與空間的生命節奏是如何得到擴展的,同時在方法論層次上則是在“說”的基礎上進一步展開“傾聽”與“對話”。 在對語言的本體論探討上,伽達默爾同樣堅持語音中心論,而將語言視為照亮了晦暗不明的自然界的“光”(這種光的隱喻在西方文化中是源遠流長的,如近代西方形而上學建基于其上的理性之“光”)。不過,他獨特的哲學風貌更多地源于他在方法論上對海德格爾思想的發展。在海德格爾那里,對語言本質的認識可見之于他轉引的亞里士多德在《解釋篇》中的話:“有聲的表達(聲音)是心靈的體驗的符號,而文字則是聲音的符號。而且,正如文字在所有的人那里并不相同,說話的聲音對所有的人來說也是不同的。但它們(聲音與文字)首先是符號(Zeichen,海德格爾又將其譯為“顯示”Zeigen),這對所有的人來說都是心靈的相同體驗,而且,與這些體驗相應的表現的內容,對一切人來說也是相同的。”海德格爾進而將作為有聲表達的語言所具有的結構概括為,字母乃是聲音的符號,聲音乃是心靈體驗的符號,心靈的體驗乃是事物的符號,符號關系構成了這個結構的支柱。 但他往往停留于人類語言本質的同一性及對其不可說性保持一種神圣的沉默,而未意識到,在生活世界中人類要相互傾聽與對話才能達到溝通與理解。伽達默爾將閱讀理解為傾聽,正是對海德格爾哲學在方法論層次上的繼續發展。他曾坦言:“我的闡述是以這種與‘觀’的觀點相反的論點為基礎的。我試圖從中找出視覺與聲音的對立。”伽達默爾對語音中心論即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堅持,使他更深地陷入了海德格爾所意識到的困境,即我們如何解決詮釋學作為生命世界現象學的生命本體問題,在邏各斯中心論中生長出來的西方詮釋學能否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詮釋學作為一種生命世界的現象學,無論是面對生活世界還是面對生命本身,都不能忽視直觀的“觀照”。晚年的伽達默爾已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棄單純強調傾聽的立場,轉而提出:“必須學會觀看。” 德里達則開辟了另一條詮釋學之路。他對海德格爾所持有的時間觀、語音中心論及潛意識里將語言視為照亮自然界萬事萬物之光的觀念進行了批評,由此改變了西方自柏拉圖以來根深蒂固的以邏輯、理性、人類為中心的這種“光”的傳統。他改造“差異”(différence)而創造了“延異”(différance)的概念,他說,“a是被寫的和被讀的,但是不能被聽”。 “被寫的和被讀的”,是寫作的空間性要素,“被聽的”則是時間性要素。在“延異”概念中,隱含著一個空間化的時間意象,即“差異”和“延宕”,前者是符號活動,也就是痕跡的空間化,后者則是其時間化。德里達的“延異”和“差異”概念的區別與聯系,標明了他的文字學與傳統的語言學和海德格爾此在本體論的不同之處,就是力圖用空間化的寫作來拆解傳統寫作中的線性時間秩序。他指出,“字母,通過展開、屈伸、部署、伸展而從它那里獲取這種空間化,如今必須得到反思、沉思,并重新追溯其圖案”。這種空間化寫作,是德里達稱之為“靜默寫作”(mute writing)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寫作。他雖然不刻意反對拼音文字,但他認為“書寫”文字之于“意義”對于語音更為重要。他借用弗洛伊德的“本源—痕跡”(architrace)的概念,將“文字”擴展到了“延異”本身,這使他的“靜默寫作”伸展到了極為廣泛的領域,也更加接近詮釋學中生命意義上的本體。
世界、詮釋與教化 作者簡介
鮑永玲,安徽黃山人,華東師范大學哲學博士,復旦大學和洪堡大學博士后,中國CSC留學基金訪問學者,德國DAAD基金訪問學者,現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歐洲思想史、詮釋學和政治哲學。著有《“種子”與“靈光”:王陽明心學喻象體系通論》(2012年)、《德國早期教化觀念史研究》(2018年)等,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博士后特別資助項目、博士后國際學術交流計劃派出項目、上海市社科基金項目等十余項,在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論文、譯文七十余篇。
- >
經典常談
- >
羅庸西南聯大授課錄
- >
巴金-再思錄
- >
羅曼·羅蘭讀書隨筆-精裝
- >
【精裝繪本】畫給孩子的中國神話
- >
自卑與超越
- >
二體千字文
- >
山海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