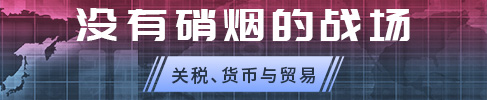包郵 無(wú)用的文學(xué)(卡夫卡與中國(guó))(精)
-
>
百年孤獨(dú)(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guó)”系列(珍藏版全四冊(cè))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jiǎn)⒊視?shū)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guó)大家筆下的父母
無(wú)用的文學(xué)(卡夫卡與中國(guó))(精) 版權(quán)信息
- ISBN:9787559801029
- 條形碼:9787559801029 ; 978-7-5598-0102-9
- 裝幀:簡(jiǎn)裝本
- 冊(cè)數(shù):暫無(wú)
- 重量:暫無(wú)
- 所屬分類(lèi):>
無(wú)用的文學(xué)(卡夫卡與中國(guó))(精) 本書(shū)特色
1.“如果要舉出一位當(dāng)代*能和但丁、莎士比亞、歌德相提并論的藝術(shù)家,卡夫卡是**人。”書(shū)中分八段破解卡夫卡斷片式寫(xiě)作的語(yǔ)言藝術(shù),及其文本碎片中隱藏的罪愆、苦難、希望與真途,為讀者呈現(xiàn)一代文化偶像。既是哲學(xué)書(shū),也可作為文學(xué)評(píng)論讀本。
2.直擊現(xiàn)代人的精神困境。本書(shū)關(guān)于卡夫卡與中國(guó)文化尤其是老莊哲學(xué)的關(guān)系之研究,但根本上是為了從中國(guó)道家思想的路徑解析卡夫卡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的中國(guó)意象,以回應(yīng)現(xiàn)代性的危機(jī),回應(yīng)現(xiàn)代人之精神困局。
3.哲學(xué)原創(chuàng)思想。夏可君將“無(wú)用”的概念帶到世界哲學(xué)論壇,同時(shí)打開(kāi)比較哲學(xué)與比較文學(xué)的一個(gè)新方向。其哲學(xué)文章創(chuàng)作多于說(shuō)理,富有個(gè)人色彩。
無(wú)用的文學(xué)(卡夫卡與中國(guó))(精) 內(nèi)容簡(jiǎn)介
為什么,卡夫卡說(shuō)“從根本上我就是中國(guó)人,并且正在回家”?
為什么,卡夫卡要把他的生命枝嫁接到中國(guó)文化的生命樹(shù)上?
文學(xué)目前很驚人的時(shí)刻出現(xiàn)了。
夏可君以十個(gè)獨(dú)特的閱讀法則,深入卡夫卡的文本,在“無(wú)用”的重新思考中,以卡夫卡、本雅明所隱含著的新助力,“以中國(guó)為方法”“以中國(guó)為道路”的新原理,讓西方人通過(guò)中國(guó)來(lái)認(rèn)識(shí)自身,讓進(jìn)入現(xiàn)代性的中國(guó)人去反思自身。
無(wú)用的文學(xué)(卡夫卡與中國(guó))(精) 目錄
楔子 閱讀卡夫卡:多余的十誡
切片 卡夫卡與中國(guó):無(wú)關(guān)之聯(lián)與空無(wú)之道
**段 助手們的無(wú)用工夫論:虛無(wú)主義的三重解釋學(xué)
1.1 《鄰村》:你說(shuō)這是誰(shuí)家的村子呢?
1.2 桑丘:這家伙是一個(gè)道家或者就是莊子?
1.3 虛無(wú)的解釋學(xué):瘋狂默化的工夫論
第二段 多重譬喻的吊詭:卡夫卡式的腹語(yǔ)術(shù)或雙簧戲 2.1 走過(guò)去:這是走到中國(guó)?
2.2 譬喻與卮言:相互的轉(zhuǎn)化
2.3 許多聲音:從拉比的解釋學(xué)到無(wú)用的解釋學(xué)
第三段 “奧德拉德克式”的姿勢(shì)詩(shī)學(xué): 同時(shí)表演三個(gè)人的“樣子”
3.1 奧德拉德克:如此多變的樣子
3.2 一分為三:“天敵”或“死皮”
3.3 “第五維度”:一種新的自由科學(xué)
第四段 卡夫卡需要的中國(guó)鏡像:仙道式助手打開(kāi)的小門(mén)
4.1 本雅明與道家:生命的相似性
4.2 中國(guó)鏡子:卡夫卡的困惑
4.3 “前世界”:發(fā)明仙道式的助手
第五段 卡夫卡的“猶太式法西斯主義 ”?無(wú)用之樹(shù)與生命之樹(shù)
5.1 捕鼠器,捕鼠器:卡夫卡的“猶太式法西斯主義”?
5.2 布萊希特的教諭詩(shī):“彌賽亞之道家化”的歡樂(lè)
5.3 依然位于“關(guān)口”:魯迅與中國(guó)
第六段 《中國(guó)長(zhǎng)城建造時(shí)》:成為一個(gè)無(wú)用的民族
6.1 沒(méi)有教訓(xùn):中國(guó)人所處的兩難絕境
6.2 《中國(guó)長(zhǎng)城建造時(shí)》:“墻文化”的形式語(yǔ)言
6.3 形式本身的重構(gòu):自然的彌賽亞化
6.4 無(wú)用的民族:時(shí)間的加速度與折疊的拓?fù)鋵W(xué)
第七段 總是來(lái)得太晚:皇帝的圣旨
7.1 看似不必要的文本還原
7.2 寄喻:不可能的寫(xiě)作
7.3 無(wú)限的中國(guó)卻沒(méi)有時(shí)間
7.4 吊詭的工作:認(rèn)真做某物,又空無(wú)所成
7.5 不可摧毀之物與彌賽亞性
第八段 卡夫卡式的吊詭寫(xiě)作:從未抵達(dá)與早已結(jié)束
8.1 句法組織的不可能性
8.2 聚集時(shí)間的音樂(lè)
8.3 吊詭的模態(tài)
8.4 如何解咒
殘段或余論 走向一種無(wú)用的文學(xué)
附錄 無(wú)用文學(xué)的三個(gè)斷片
禪教劇:兩個(gè)中國(guó)“猶太拉比”的深夜交談
這是個(gè)壞世界?不,是糟糕!不,是還不夠糟糕!
刺客庖丁謠傳
參考文獻(xiàn)
無(wú)用的文學(xué)(卡夫卡與中國(guó))(精) 節(jié)選
殘段或余論
走向一種無(wú)用的文學(xué) 卡夫卡與中國(guó)。
首要的問(wèn)題還是:為什么我們要在當(dāng)下再次閱讀卡夫卡?
1938年的歷史危機(jī)時(shí)刻,在寫(xiě)給自己的猶太朋友肖勒姆的書(shū)信中(1938 年 6 月 12 日,巴黎),本雅明首先援引了卡夫卡的朋友勃羅德的觀點(diǎn),認(rèn)為卡夫卡和布伯一脈相承,這就像在網(wǎng)里捕蝴蝶,其實(shí)翩翩飛舞的蝴蝶在網(wǎng)里投下的只是影子。把卡夫卡與布伯相關(guān)聯(lián),無(wú)疑還因?yàn)椴疾抢锨f與中國(guó)文學(xué)的翻譯者,卡夫卡的中國(guó)動(dòng)機(jī)無(wú)疑深受布伯影響,蝴蝶的比喻甚至也與莊子的蝴蝶夢(mèng)相關(guān)。
本雅明把卡夫卡的寫(xiě)作描繪為一個(gè)橢圓式的結(jié)構(gòu),這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嚴(yán)格管制的機(jī)器體系與彌賽亞神秘主義隱晦傳統(tǒng)—這兩個(gè)遙遙相隔的焦點(diǎn)上,彌賽亞救世主可能的來(lái)臨給予了卡夫卡觀照嚴(yán)酷現(xiàn)實(shí)的獨(dú)特目光,其*新的感悟與寓意才顯得如此特別。但如此的觀照方式,需要我們有著猶太教神秘主義彌賽亞的回眸目光(還并非基督教與諾斯替主義)?!如果沒(méi)有,又如何可能明白卡夫卡寫(xiě)作的寓意?本雅明繼續(xù)說(shuō),卡夫卡生活在一個(gè)需要補(bǔ)充的世界,他的小說(shuō)試圖去發(fā)現(xiàn)這個(gè)虛無(wú)世界的某種“補(bǔ)充物”。
本雅明接著指出, 所幸還有著少許歡快的余地(der herrliche Spielraum),并未被災(zāi)禍波及, 這有利于卡夫卡做出驚恐的舉止。盡管卡夫卡費(fèi)勁在聽(tīng),但其實(shí)傳統(tǒng)已經(jīng)沒(méi)有什么秘密可以傳遞,世界歷史處于徹底虛無(wú)主義時(shí)代,由此卡夫卡的寫(xiě)作只是對(duì)世界已無(wú)真理可言的“譬喻”(如同莊子在古代中國(guó)認(rèn)識(shí)到時(shí)代的徹底無(wú)正義而開(kāi)始卮言式寫(xiě)作),這也是為何卡夫卡作品中只有“謠言”和“愚蠢”這兩種奇怪的遺產(chǎn),只有支離破碎的智慧。
或者說(shuō),只有智慧的無(wú)用與無(wú)用的智慧。但愚蠢也非一無(wú)是處,可能那些笨拙的助手,他們勤勤懇懇工作的傻勁,如同桑丘牽引著堂吉訶德,也許有著某種奇特的輔助作用,看似無(wú)用,其實(shí)有著大用。
但這個(gè)補(bǔ)充物,尚未完成的補(bǔ)充,其輔助式的工作,不可能來(lái)自西方自身的傳統(tǒng)。本雅明認(rèn)為卡夫卡肯定了傻子幫助的必要性,比如像堂吉訶德的仆人桑丘那樣的人物,而本雅明在他1934年左右研究卡夫卡卻一直被后人所忽視了的筆記中指出,在卡夫卡道家化的無(wú)用論中,這個(gè)桑丘已經(jīng)不是仆人,而是成為一個(gè)老莊式的道家主義者(給桑丘所戴上的這頂奇怪的“帽子”式戲法,西方?jīng)]有任何學(xué)者對(duì)此有所研究!),桑丘,這個(gè)一無(wú)所用、無(wú)所作為的家伙,這個(gè)變戲法的家伙,變出了堂吉訶德,讓世界得以在敗壞與污泥中,還有著少許的歡樂(lè)。
這樣一來(lái),堂吉訶德不過(guò)是桑丘的木偶,自然主義或者道家無(wú)用化的“侏儒”桑丘,才是彌賽亞救贖者這個(gè)“木偶”的操作者,針對(duì)資本主義拜物教批判的歷史唯物主義與喀巴拉神 秘主義傳統(tǒng)的彌賽亞主義,這二者之間的關(guān)系,因?yàn)榭ǚ蚩ǖ纳G鸬兰一膶?xiě), 將全然不同, 不再只是 1940 年《論歷史的概念》中的唯物主義木偶與神秘主義彌賽亞侏儒的彼此操縱關(guān)系。
卡夫卡與中國(guó),中國(guó)與卡夫卡,在未完成中,相互促成,這也是相互的借鑒與啟發(fā),相互的助力與協(xié)助,相互的錘打與擊碎,這將讓我們更好地看到現(xiàn)代性的困難。
卡夫卡的小說(shuō)世界也照亮了一個(gè)事實(shí)—我們中國(guó)人依然生活在卡夫卡的世界里:
一方面,卡夫卡的世界*好地暗示了中國(guó)社會(huì)的處境,喪失了外在絕對(duì)超越參照的中華帝國(guó),就是一個(gè)自身封閉的圓圈,一個(gè)看似可以?xún)?nèi)在無(wú)休止自轉(zhuǎn)的太極圖,如同萬(wàn)里長(zhǎng)城“墻文化”的自我封閉性,是無(wú)論如何也走不出去的,無(wú)論接受多少西方現(xiàn)代性的產(chǎn)品與技術(shù),也只是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自身的封閉而已,并沒(méi)有走出自身,也并沒(méi)有從根本上達(dá)到人性的改善與自由的解放。一旦此資本拜物教還與現(xiàn)代官僚統(tǒng)治機(jī)器合謀,所有生命都將成為被資本征用的“多余生命”,*終導(dǎo)致內(nèi)部的塌陷與毀滅。
另一方面,卡夫卡也認(rèn)識(shí)到猶太人的外在超越,在世俗歷史之外,也無(wú)法進(jìn)入世界,尤其是當(dāng)世界越來(lái)越世俗自足時(shí),彌賽亞的救贖越來(lái)越多余,越來(lái)越無(wú)用。但中國(guó)道家文化的自然觀已經(jīng)在儒家自然化的倫理化政治禮儀秩序之外,打開(kāi)了一個(gè)世界,彌賽亞進(jìn)入這個(gè)自然化的世界,也許可以由此“迂回”,而再度“進(jìn)入”世界?
卡夫卡不是沒(méi)有認(rèn)識(shí)到“我們中國(guó)人”:在思想方法上清晰與不清晰的同時(shí)存在,漠然的同時(shí)卻并沒(méi)有悖論感。卡夫卡的寫(xiě)作對(duì)此生存悖論的徹底無(wú)感及其詭異有著深刻的洞見(jiàn):
在當(dāng)年建筑長(zhǎng)城期間和自那以后直至今天,我?guī)缀跬耆铝τ诒容^民族史的研究, —有一些問(wèn)題可以說(shuō)非用這個(gè)方法搞不透徹—并且發(fā)現(xiàn),我們中國(guó)有某些民間的和國(guó)家的機(jī)構(gòu),有些純?nèi)坏那逦行┯旨內(nèi)坏牟磺逦?
——我們中國(guó),其行事的方式,有著純?nèi)坏那逦旨內(nèi)坏牟磺逦恕般U摰臒o(wú)感”才是中國(guó)人的“麻木”或“自欺”之根源, 才是“虛假的吊詭”—毋寧說(shuō)是“詭詐的操弄”, 一切看似清楚明白,有著規(guī)則與禮儀秩序,但一切似乎都并沒(méi)有什么用處,可以隨時(shí)取消。越是對(duì)偉大的無(wú)用之物著迷,越是對(duì)其實(shí)現(xiàn)手段毫無(wú)建樹(shù)。更為奇妙與可笑的則是,此兩種 狀態(tài)同時(shí)并存而毫不相悖。
如何感知到此無(wú)感狀態(tài)?只有進(jìn)入“非真理”狀態(tài),或者進(jìn)入帝國(guó)危機(jī)滅亡的時(shí)刻,或者在殘局中體驗(yàn)僵局的可怕之處。一旦中國(guó)人無(wú)法對(duì)此“無(wú)感”有所感之時(shí),就只有借助于外力,此外力之助來(lái)自哪里?如同阿多諾所言,只能來(lái)自彌賽亞救贖的目光:
走向終結(jié)。—哲學(xué),唯一還負(fù)責(zé)任的哲學(xué),乃是在面對(duì)絕望,尋求去思考一切事物時(shí),應(yīng)該從救贖的立場(chǎng)來(lái)思考事物將如何呈現(xiàn)自身。如此的認(rèn)識(shí),將沒(méi)有其他的光照,唯有救贖之光能照亮世界:其他的一切都不過(guò)是復(fù)建和保持為技術(shù)的片段而已。如此的視點(diǎn)必須建構(gòu)出來(lái),相似于這個(gè)世界并使之變得陌生,并顯示出其中所有的裂痕與罅隙,如同它們?cè)?jīng)作為貧乏與扭曲的樣子,而讓它們?cè)趶涃悂喌墓庹障碌靡燥@現(xiàn)。沒(méi)有任何的任意與暴力全然從如此對(duì)立的視點(diǎn)中超越出來(lái),去贏獲一個(gè)視點(diǎn),思想只能從此而來(lái)?
甚至,齋戒高貴的饑餓表演藝術(shù)也是無(wú)用的了,這種無(wú)用,對(duì)于卡夫卡而言,也是小說(shuō)本身的無(wú)用—小說(shuō)并不傳達(dá)什么真理,盡管一再要講不是故事的故事(元敘事),但現(xiàn)實(shí)生活的荒誕勝過(guò)了所有的故事。 小說(shuō)家要掄起錘子, 錘打語(yǔ)詞,更加講究,認(rèn)真地錘打我們的心臟,但立刻同時(shí)要認(rèn)識(shí)到,這是無(wú)用的,這是無(wú)用的技藝。甚至也是信仰的無(wú)用,因?yàn)檫@是練習(xí)空寂,是對(duì)缺席之物的期待。據(jù)說(shuō),卡夫卡的寫(xiě)作過(guò)程本身也是如此,卡夫卡經(jīng)常保持一頁(yè)紙的空白,這是他寫(xiě)作經(jīng)常被打斷的征候,好回頭再來(lái)書(shū)寫(xiě),如同那高處的表演者總是被一座在高處的吊桿懸吊著。
這是雙重的無(wú)用,或者有用與無(wú)用的疊加:一方面,饑餓表演,確實(shí)一個(gè)人在“表演”現(xiàn)實(shí)肉體的絕食,但已經(jīng)無(wú)用了,人們不再關(guān)注這門(mén)表演藝術(shù),本來(lái)表演饑餓就不是一門(mén)藝術(shù),其本身已經(jīng)無(wú)用;但另一方面,如此的表演,乃是對(duì)無(wú)用的表演,是對(duì)小說(shuō)本身或信仰本身的無(wú)用之暗示,即饑餓表演所顯現(xiàn)的那種至高的激情已經(jīng)無(wú)用了。
而且,我們中國(guó)人似乎也遺忘了自身思想中來(lái)自無(wú)用的化解力量。
但到底何謂道家的無(wú)用論?這是來(lái)自老莊對(duì)于“無(wú)”與“用”,無(wú)用之為大用的思考。簡(jiǎn)而言之,這是在有與無(wú)的對(duì)立之外,以虛為用:“天地之間,其猶橐龠乎!虛而不屈,動(dòng)而愈出。”(《道德經(jīng)》第五章)以及:“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莊子·人間世》)這也是“以無(wú)為用”與“讓無(wú)來(lái)為”:老子的“無(wú)為而無(wú)不為”,“予能有無(wú)矣,而未能無(wú)無(wú)也”(《莊子·知北游》),“今子有大樹(shù),患其無(wú)用,何不樹(shù)之于無(wú)何有之鄉(xiāng),廣莫之野,彷徨乎無(wú)為其側(cè),逍遙乎寢臥其下。 不夭斤斧, 物無(wú)害者, 無(wú)所可用, 安所困苦哉!”(《莊子·逍遙游》)以及“以明”的態(tài)度:“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樞始得其環(huán)中, 以應(yīng)無(wú)窮。 是亦一無(wú)窮, 非亦一無(wú)窮也。故曰莫若以明。”(《莊子·齊物論》)尤其是莊周夢(mèng)蝶,既是作為人類(lèi)的莊周夢(mèng)為**自然的蝴蝶,也是**自然的蝴蝶重新夢(mèng)為或生成為新的人性或新的第二自然,是自然生命的再生與轉(zhuǎn)化。
進(jìn)入現(xiàn)代性,此無(wú)用之思,卻被現(xiàn)代性的發(fā)展進(jìn)化觀所擠壓與排斥,被一種整體的實(shí)用主義所徹底遮蔽,道家的無(wú)用之思有待于面對(duì)現(xiàn)代性困難,與西方唯一神論思想對(duì)話(huà)后,重新激活。
卡夫卡與中國(guó),既是猶太思想對(duì)中國(guó)道家的想象,反過(guò)來(lái),對(duì)于中國(guó)思想,這也是對(duì)自身思想資源的再理解,如此的自身理解,經(jīng)過(guò)了變異,“無(wú)用”成為“教義”,無(wú)用的文學(xué)乃是一種新現(xiàn)代性重寫(xiě)的虛托邦想象。
卡夫卡的小說(shuō)就并非僅僅是少數(shù)人或小民族的“少數(shù)的文學(xué)”, 而是屬于所有人或無(wú)用之人的“無(wú)用的文學(xué)”!確實(shí),卡夫卡曾經(jīng)在日記中思考了《論小化文學(xué)》的特點(diǎn),但其 中,在“輕松性”的要求下,寫(xiě)出了“無(wú)用的廢物”(Abfall der Unfaehigen)這個(gè)題目, 也許這才是卡夫卡寫(xiě)作的核心秘密?無(wú)用的藝術(shù)乃是另一種切割術(shù)?另一種割禮標(biāo)記?
饑餓表演,這失敗了的表演,這無(wú)用的技藝與心齋之術(shù),可能是我們穿越熙熙攘攘的廣場(chǎng)時(shí),唯一要停下目光的時(shí)刻。
哪些文學(xué)寫(xiě)作已經(jīng)是無(wú)用的文學(xué)?卡夫卡那些與中國(guó)文化關(guān)的雜文式書(shū)寫(xiě)已經(jīng)是嘗試中的無(wú)用文學(xué)。也許德國(guó)早期浪漫派大量未完成的斷片寫(xiě)作,如同布朗肖所繼承的寫(xiě)作方式(大量的小說(shuō)以及文論,尤其是《從卡夫卡到卡夫卡》以及無(wú)盡的交談中對(duì)于“無(wú)作”與“無(wú)用”的非功效的討論),克萊斯特的寫(xiě)作,荷爾德林未完成的戲劇作品以及瘋狂之前的哀歌與祖國(guó)頌歌,還有尼采的格言式寫(xiě)作,超現(xiàn)實(shí)主義的一些作品,阿爾托的殘酷戲劇,昆德拉的某些小說(shuō),策蘭的詩(shī)歌,梅爾維爾的《書(shū)記員巴特雷比》, 布萊希特關(guān)于墨子的寫(xiě)作,等等,也可以從無(wú)用來(lái)解讀。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中魯迅的《野草》,也是無(wú)用文學(xué)的代表作。
當(dāng)然,莊子的自然化也只是一種協(xié)助,西方的彌賽亞需要幫助:西方唯一神論之間的沖突——上帝主權(quán)的天敵導(dǎo)致無(wú)盡的暴力,資本主義拜物教——人類(lèi)欲望之虛無(wú)的深淵誘惑也是天敵,法西斯主義或民粹主義的興起——自然本能叢林法則的天敵,如此三重的天敵一旦結(jié)合,人類(lèi)不可能從此天敵中獲救。因此,需要莊子的幫助,莊子自然的虛化,回到混沌,可以不斷激活自然的再生性潛能,讓彌賽亞自然化,也許是一種出路。
同時(shí),莊子的自然化也需要彌賽亞性的協(xié)助,自然化需要彌賽亞化的幫助:從本雅明“微弱的彌賽亞力量”,到德里達(dá)“沒(méi)有彌賽亞主義的彌賽亞性”(尤其是與 chora 虛位的結(jié)合),再到晚期海德格爾與卡夫卡的“彌賽亞的無(wú)用化”,直到重新喚醒本雅明“彌賽亞的自然化”,再次激活莊子的自然,讓“自然彌賽亞化”。
如此的跨文化對(duì)話(huà),或相向而行,或彼此的相互協(xié)助,可以化解當(dāng)下的世界危機(jī)?
我們依然生活在卡夫卡所虛構(gòu)的現(xiàn)實(shí)世界里,天敵們無(wú)所不在, 這看起來(lái)如此詭異, 卻又如此真實(shí)。卡夫卡與本雅明的文本中所隱含著的“以中國(guó)為方法”或“以中國(guó)為道路”的 新原理或新助力,既讓西方人通過(guò)中國(guó)來(lái)認(rèn)識(shí)自身,也讓中國(guó)人——進(jìn)入現(xiàn)代性的中國(guó)人——去反思自身,這是一個(gè)雙面鏡。
而一個(gè)來(lái)自《道德經(jīng)》“為無(wú)為”與莊子“無(wú)用之用”的方法或道路,可以化解猶太人乃至整個(gè)現(xiàn)代性的危機(jī)嗎?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道路,也是西方尚未思考的方法,盡管曾有過(guò)“歐洲道家化”的謠言(如同斯洛特戴克的思考),但在卡夫卡與本雅明的寫(xiě)作中,這種西方或彌賽亞的道家化,或者1945年左右海德格爾所施行的亞洲或“東亞轉(zhuǎn)向”其實(shí)已經(jīng)發(fā)生了,只是因?yàn)槎?zhàn)與冷戰(zhàn),因?yàn)椤?·11”事件與恐怖主義盛行,這條打開(kāi)的道路被不斷遮蔽著。
如今重新揭示出此無(wú)用的教義, 其實(shí)也只是再次的“接力”與“借力”,不只是顯示西方曾經(jīng)有過(guò)的“借力”,還是我們中國(guó)人需要借助于卡夫卡—既然我們依然生活在這個(gè)卡夫卡的現(xiàn)實(shí)世界,這個(gè)并無(wú)真理可言的世界——再次“借力”來(lái)反思我們自己的道路,我們得再次成為學(xué)生與助手,不僅僅是中國(guó)文化古老教義的助手,還是異質(zhì)性猶太教思想的學(xué)生, 如同我們一直都是德國(guó)哲學(xué)的勤奮研究者。
卡夫卡與中國(guó),卡夫卡隱秘地改寫(xiě)著道家的思想,當(dāng)然也是為了改寫(xiě)?yīng)q太人自身的命運(yùn)。
卡夫卡與中國(guó),閱讀這些改自道家的語(yǔ)句,其中有什么改寫(xiě)的秘密可以發(fā)現(xiàn)?這就是猶太人的彌賽亞精神,竟然要通過(guò)老莊無(wú)用之思的迂回與過(guò)渡,才可能在塵世間施行出來(lái),猶 太人才有獲救的機(jī)會(huì), 這不再是基督教的“道成肉身”(上帝成為某個(gè)人的肉身),而是彌賽亞“救贖的自然化”(認(rèn)同卡夫卡看到自然風(fēng)景時(shí)的渴望,讓自己成為一個(gè)與自然風(fēng)景同在的中國(guó)人)。這也是猶太人在回應(yīng)現(xiàn)代性的根本危機(jī):如果集中營(yíng)大屠殺或者現(xiàn)代性的災(zāi)變必然發(fā)生,如果這也是現(xiàn)代人的普遍命運(yùn),不只是猶太人,猶太人只是體現(xiàn)了如此的征候,是對(duì)這災(zāi)難的殘酷見(jiàn)證,其實(shí)也是對(duì)整個(gè)人性本身死亡的見(jiàn)證,那么,如何避免此不可逃避的災(zāi)難?這是生存的絕對(duì)困境,也許,先知性的卡夫卡與本雅明事先已經(jīng)預(yù)感到這一災(zāi)難,似乎在隱秘地尋找一條不可能的道路來(lái)避免這種不可避免的命運(yùn)。
這就是:彌賽亞的道家化,彌賽亞的無(wú)用化,彌賽亞的自然化。彌賽亞的救贖既然不與世界相關(guān),彌賽亞又不可能如同基督教那樣道成肉身,彌賽亞找不到與世界的關(guān)聯(lián)點(diǎn),那就只有通過(guò)此道家式道路的迂回與轉(zhuǎn)化。借由此“無(wú)關(guān)之聯(lián)”,猶太人才可能不重復(fù)之前被放逐的命運(yùn),以及被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排斥的命運(yùn),此彌賽亞的道家化與喀巴拉神秘主義的道家化是西方從未走過(guò)的道路。
這是一次大膽的改寫(xiě)、一次隱秘的改寫(xiě),在歷史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但從未被讀出來(lái):這是彌賽亞的自然道家化,也是自然道家的彌賽亞化。這是西方思想迄今從未明確的連接,從未發(fā)現(xiàn)的關(guān)聯(lián),不是陶伯斯指明的猶太教神學(xué)政治傳統(tǒng),也不是齊澤克的左派式暴力革命,也不是阿甘本結(jié)合彌賽亞主義與保羅革命神學(xué)的身體無(wú)用論。
阿甘本認(rèn)為保羅神學(xué)的復(fù)興有待于通過(guò)本雅明的“彌賽亞式馬克思主義”, 但在我們看來(lái), 通過(guò)本雅明的卡夫卡研究,則不再僅僅是保羅基督教化的彌賽亞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轉(zhuǎn)化(或者它還必須首先經(jīng)過(guò)南希的基督教自身解構(gòu)),也非齊澤克的保羅與列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同盟(它無(wú)法化解無(wú)產(chǎn)階級(jí)專(zhuān)政導(dǎo)致的巨大暴力), 也非巴迪歐的保羅式基督教普遍主義(作為剩余與余外的猶太性恰好是反對(duì)基督教式普遍主義的),也非肖勒姆純粹猶太教的神秘主義與虛無(wú)主義的彌賽亞性(上帝回縮后的空間一直沒(méi)有找到革命的主體),當(dāng)然也非施米特的天主教的彌賽亞主權(quán)(神權(quán)政治的世俗化導(dǎo)致的暴力模仿無(wú)法自我解決),也非海德格爾存在歷史命運(yùn)的“詩(shī)性彌賽亞主義”(民族的詩(shī)性神話(huà)回歸并沒(méi)有打開(kāi)新的開(kāi)端),也非德里達(dá)的沒(méi)有彌賽亞主義的彌賽亞性(此彌賽亞性還是過(guò)于依賴(lài)技術(shù)化或者假器化的上帝), 此彌賽亞性還需要再次與柏拉圖的 chora 聯(lián)系起來(lái)重新思考,這就可能走向自然化或道家化的彌賽亞性。
此“彌賽亞式的道家”(Messianic Daoism)或“彌賽亞的自然主義”(Messianic Naturalism), 也并非上帝死亡的神學(xué), 而是走向無(wú)用的神學(xué)與文學(xué),是救贖之為第五維度“非時(shí)間性”,與自然的再自然化生命條件,二者結(jié)合的節(jié)奏,伴隨對(duì)于社會(huì)歷史事件的懸置,這是新的時(shí)間整合所形成的事件性,不同于之前對(duì)于事件的革命暴力思考。或者,它有待于重新理解布伯開(kāi)啟的方向、后期海德格爾的讓予姿態(tài)、德里達(dá)與薩里斯對(duì) chora 的重新思考、伊利格瑞等人的女權(quán)主義神學(xué),等等。這些細(xì)微的差別,有待于一本專(zhuān)著來(lái)展開(kāi)研究。
反倒是本雅明在 1920 年左右所寫(xiě)的《神學(xué)-政治學(xué)殘篇》中所言的“彌賽亞式自然的節(jié)奏”開(kāi)啟了思想之新的可能性:彌賽亞的自然化—自然的彌賽亞化,彌賽亞的無(wú)用化—無(wú)用的彌賽亞化,這是一個(gè)中國(guó)研究者可以發(fā)現(xiàn)的關(guān)聯(lián)?這依然是一個(gè)無(wú)關(guān)之聯(lián),抑或這是一個(gè)有待于發(fā)生的事件?這是從未寫(xiě)出之物,卻有待于發(fā)生的真理性事件?一個(gè)無(wú)用的新教義還有待寫(xiě)出。
卡夫卡與中國(guó),二者之間其實(shí)只有一道非常窄的橋,因?yàn)檫@是一個(gè)并沒(méi)有真理可言的世界,其與真理對(duì)立的“非真理”(Unwahrheit)也不啟示反面的真理性。
我們已經(jīng)處身于時(shí)間意識(shí)中的“地獄”。我們并非在等待彌賽亞的來(lái)臨,我們可能只是在等待一個(gè)巨大的“整體危機(jī)”的來(lái)臨,不是例外狀態(tài),既然世界一直處于余外狀態(tài)與僵局之中,此狀態(tài)也就成為多余的,借用漢語(yǔ)的“字思維”的內(nèi)在觸及,那就只能在總體化的無(wú)余狀態(tài)時(shí)刻,我們所生活的殘局世界才可能被終結(jié)。
無(wú)用的文學(xué)(卡夫卡與中國(guó))(精) 作者簡(jiǎn)介
夏可君,哲學(xué)家,評(píng)論家與策展人。
武漢大學(xué)哲學(xué)博士,曾留學(xué)于德國(guó)弗萊堡大學(xué)與法國(guó)斯特拉斯堡大學(xué),現(xiàn)為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著述十余部,從“無(wú)用”出發(fā),撰有《虛薄:杜尚與莊子》《庖丁解牛》《一個(gè)等待與無(wú)用的民族:莊子與海德格爾的第二次轉(zhuǎn)向》,以及英文著作Chinese Philosophy and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Unthought of Empty。夏可君嘗試讓“無(wú)用”“虛化”以及“余讓”的中國(guó)范疇,生成為當(dāng)代世界哲學(xué)的核心概念。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推拿
- >
朝聞道
- >
伊索寓言-世界文學(xué)名著典藏-全譯本
- >
中國(guó)人在烏蘇里邊疆區(qū):歷史與人類(lèi)學(xué)概述
- >
月亮與六便士
- >
我從未如此眷戀人間
- >
莉莉和章魚(y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