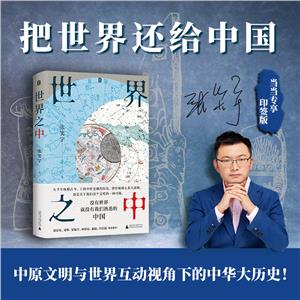-
>
清通鑒(全四冊)(精裝)
-
>
明通鑒(全三冊)(精裝)
-
>
跨太平洋的華人改良與革命 1898-1918
-
>
天有二日(簽名鈐印特裝本)
-
>
歐洲至暗時刻(1878-1923):一戰為何爆發及戰后如何重建
-
>
(精裝)奧托·馮· 俾斯麥與德意志帝國建立
-
>
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世界之中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9879530
- 條形碼:9787559879530 ; 978-7-5598-7953-0
- 裝幀:平裝-膠訂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世界之中 本書特色
★中原文明與世界互動視角下的中華大歷史;一部特別視角的五千年發展史
這是一部關于中華文明五千年的發展史。從堯舜時代到清末民初,揭示我們成長歷程中的偉大、神奇、彷徨與遺憾。
這是一次關于中外交融的深刻思考。古代的我們并不像想象的那樣隔離于世界。歐亞大草原、云貴高原、東海、南洋都是我們聯通世界的橋梁。世界從未離開過我們的歷史,只是我們很容易忽略它。把世界還給中國,才會在世界向我們襲來時,從容自信。
★秦制國家與財政國家的成長博弈。
秦制國家的特點:土地國有、編戶制度、農業稅收為主、服徭役兵役。漢與匈奴,唐與高句麗、中亞,在地緣政治引發的沖突中,邊疆民族或秦制化,與中原王朝此消彼長,或對中原王朝造成沉重的負擔,甚至成為改朝換代的誘因。
財政國家的特點:非農業稅收為主,利用金錢進行資源配置。宋代曾經歷非農業稅收占財政收入主體的時期,王安石變法、蔡京的財政政策都是宋代財政國家化的重要標志,也積累了大量貴金屬。不過,蒙元的征服又造成了中原的貧困。明初,中國又不得不走秦制國家的老路。雖然明后期出現了短暫的資本主義萌芽,但終因全球化的周期變化,遇上白銀循環的終結,*終造成了大明的崩潰。
★本書充滿想象的張力和驚喜,十段被人忽略的歷史,探尋中華文明更多的可能性。
陶寺因成功測量天象而成為遠古東方科技*發達的文明,他們締造了“中”這個概念,中國由此稱為“中國”。
亞歷山大遠征,在中亞留下了巴克特里亞,中國開始與希臘文明有了交集,皇帝的神格被確定下來。
西南地區的古彝族為道教傳遞了西方宗教的彌賽亞,土生土長的道教也有自己的救世主。
秦制國家的變化周期造就了兩漢與匈奴間的此消彼長。
因為沒有西域小國那樣的地緣優勢,高句麗成為北朝隋唐在東北亞*大的困擾。
號稱“絲綢之路上的猶太人”的粟特人曾是唐朝重要的軍事力量。
★中原文明與世界互動視角下的中華大歷史;一部特別視角的五千年發展史
這是一部關于中華文明五千年的發展史。從堯舜時代到清末民初,揭示我們成長歷程中的偉大、神奇、彷徨與遺憾。
這是一次關于中外交融的深刻思考。古代的我們并不像想象的那樣隔離于世界。歐亞大草原、云貴高原、東海、南洋都是我們聯通世界的橋梁。世界從未離開過我們的歷史,只是我們很容易忽略它。把世界還給中國,才會在世界向我們襲來時,從容自信。
★秦制國家與財政國家的成長博弈。
秦制國家的特點:土地國有、編戶制度、農業稅收為主、服徭役兵役。漢與匈奴,唐與高句麗、中亞,在地緣政治引發的沖突中,邊疆民族或秦制化,與中原王朝此消彼長,或對中原王朝造成沉重的負擔,甚至成為改朝換代的誘因。
財政國家的特點:非農業稅收為主,利用金錢進行資源配置。宋代曾經歷非農業稅收占財政收入主體的時期,王安石變法、蔡京的財政政策都是宋代財政國家化的重要標志,也積累了大量貴金屬。不過,蒙元的征服又造成了中原的貧困。明初,中國又不得不走秦制國家的老路。雖然明后期出現了短暫的資本主義萌芽,但終因全球化的周期變化,遇上白銀循環的終結,*終造成了大明的崩潰。
★本書充滿想象的張力和驚喜,十段被人忽略的歷史,探尋中華文明更多的可能性。
陶寺因成功測量天象而成為遠古東方科技*發達的文明,他們締造了“中”這個概念,中國由此稱為“中國”。
亞歷山大遠征,在中亞留下了巴克特里亞,中國開始與希臘文明有了交集,皇帝的神格被確定下來。
西南地區的古彝族為道教傳遞了西方宗教的彌賽亞,土生土長的道教也有自己的救世主。
秦制國家的變化周期造就了兩漢與匈奴間的此消彼長。
因為沒有西域小國那樣的地緣優勢,高句麗成為北朝隋唐在東北亞*大的困擾。
號稱“絲綢之路上的猶太人”的粟特人曾是唐朝重要的軍事力量。
兩宋曾是*接近財政國家的時代,終因蒙元的改朝換代而煙消云散。
一條鞭法得益于地理大發現帶來的白銀循環,但全球化的周期退潮也給大明帶來了崩潰的結局。只可惜,大明的精英既不知道當初他們為什么成功,更不知道他們為什么敗落。
鄭成功、蘭芳公司、陳嘉庚,歷史上的南洋華人曾在各個時代為祖國作出過卓越貢獻。
孫中山的老師、香港啟德機場中的“啟”(何啟)曾主張建立現代財政國家;而清王朝覆滅的序幕——保路運動,也緣于清末的財政改革。
★打破刻板印象,篩選重構浩瀚史料,還原豐富無限的歷史真相。
我們很多人對很多國家、民族都容易形成刻板印象,但讀多了歷史,你就會發現,許多刻板印象并不是“自古以來”便是如此,它們形成的時間其實都相當短暫。滄海桑田,世殊事異,誰說是什么就一定是什么?只有那些永遠不擁抱變化的民族,才無法甩去他人對其自身*消極的刻板印象。
史料不會憑空增多,但視角可以隨時變換。我們的歷史觀取得進步,往往不是因為發現了新的史料,而是因為我們用全新的視角去看待自己的過去。
如果我們認為中國人長于道德討論而弱于科技研發,那么這本書會告訴你,中國之所以名為“中國”,就是因為我們曾經是科技*先進的古文明。如果我們認為中國與世隔絕,那么這本書會告訴你,中國從來不曾遠離世界,也不可能遠離世界。如果我們認為游牧與農耕勢不兩立,那么這本書會告訴你,從事游牧的中國人對中國歷史的塑造,或許比農耕者更深刻。
我們理解中國歷史的視角越是不同尋常和豐富,我們就越可能接近我們從何而來的真相。
★何懷宏、劉擎、劉蘇里、羅振宇、施展、許紀霖特別推薦!
這是一部極具想象力的作品。它融史實、史功、史識、史思于一體,真誠坦蕩,喚起了一個文明的自我認同與自我覺醒。
世界之中 內容簡介
對我們每個人來說,“中國”這個詞可以無比熟悉,也可以感到陌生。因為中國的幅員太遼闊,歷史太悠久,多元一體的豐富性太五彩繽紛,而每一次盛世和每一次劇變中,中原、邊疆乃至歐亞大陸的古老民族都曾扮演過關鍵性角色。你能否想象,“中國”這一名字的由來,乃是因為這片土地曾是科技*先進的地方?你能否想象,秦制或許與波斯和匈奴都有巨大關聯?你能否想象,絲綢之路的主角之一可能是默默無聞的粟特人?你能否想象,華人也曾在南洋建立起共和國?從中國的遠古時代到清末,本書摘取了十個鮮為人知又影響深遠的歷史片段,希望向讀者呈現這樣一個事實:中國是被世界多元力量共同塑造之中國。本書視野宏大,視角獨特,觀點精奇,論述得當,并將政治學、經濟學、國際關系學、考古學等眾多理論融會貫通,縱橫上下五千年,為我們展示了許多曾被忽略又不得不嘆為觀止的歷史畫面。
世界之中 目錄
**章 中國為什么叫中國
第二章 秦始皇崇拜亞歷山大大帝嗎?
第三章 道教是一種“彌賽亞”宗教?
第四章 匈漢原來是一家
第五章 慕容復的真正仇家是高句麗
第六章 粟特人與唐帝國的歷史轉向
第七章 阿拉伯商人與宋代的財政國家進程
第八章 沒有地理大發現就沒有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改革?
第九章 海外華人也曾“走向共和”?
第十章 孫中山的老師主張建立現代財政國家
結語 “我們是誰”與“我們本可以”
世界之中 相關資料
另類中國史的一部杰作。其獨特之處一是從全球文明看中國,二是方法上大膽想象、小心求證。并非敘述中華歷史文明的主流、但卻揭示了一些“本可以”的其他可能性。——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何懷宏 這里的故事,或許關乎我們這個文明的一種可能;農耕中原與游牧北方,編戶賦役與商貿財政,當中國歷史中的往復與博弈被置于世界之中時,仿佛一切又有了新的解讀。弘闊精深的視野,真誠坦蕩的筆觸,十段鮮為人知的記憶,喚起了一個文明的自我認同與自我覺醒。——華東師范大學紫江特聘教授 劉擎自序
據說在短視頻時代,書是越來越難賣了。以前像我們這樣的非虛構作者,都是憑喜好寫書的。你喜歡哲學,他喜歡歷史,那么就寫本關于哲學或歷史的書,掙點文字搬磚工的勞動報酬。但現在感謝互聯網的壓力,我們寫一本書,得先想想能不能熱賣,尤其是按照很多平臺的成功經驗,好像還得販賣一下焦慮,才能賣得好。
所以一位對中國出版行業非常理解的編輯告訴我,你寫歷史題材,得抓住當代中國人的知識焦慮。這其中最大的一個焦慮,就是關于身份認同的。翻譯成白話就是中國人憑什么成了中國人,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意味著什么。
我說這可是中國啊,真有那么多人關心身份政治嗎?他說當然了,你想男人三大愛好,兩性、足球、政治。兩性不讓談,足球談了就生氣,那就只剩下政治了。現實政治紅線太多,那最適合談的當然就是身份政治。民族、國家、歷史,都是身份政治的一部分。
我覺得這個分析當然是很一針見血的,但我們作研究的人最不擅長的就是迎合身份政治,因為我們在學校里學到的內容就是:當你沒別的可炫耀的時候,你就只能炫耀你的身份,這就是身份政治為什么有那么多擁躉的原因。
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北大畢業生默認的一句人生箴言,就是畢業十年后別提你是北大的。因為如果這么做,那就意味著你畢業十年后取得的成就都沒能超過這個成就。
個人是這個道理,國家好像也是這個道理。這就是為什么塞繆爾·約翰遜博士說:“愛國主義是無賴最后的避難所。”因為無賴除了彰顯他的身份之外,好像沒別的成就可以提。
有段時間知識分子都是拿這句話來批判過激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似乎一個落后又愚昧的民族才會靠身份政治打雞血獲取自豪感。但“活久見”的是,這屆美國大選之后,我們發現美國人好像也開始搞“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了。至少他們好像確實不太愿意有人打個飛機過去生孩子就能變成美國人,哪怕這是他們憲法里已經寫進去的事實。
這可能就是為什么大家都在感嘆文科已死。我們上課時學關于身份政治的內容基本都是反面教材,到了政治家那里反而成指導手冊了,我們這些做題家還是學生思維,活該做不了官也賺不到錢。
言歸正傳,我們要吃飯,所以要賣書。要賣書,好像是得迎合一下身份焦慮。所以據說替中國回答“終極三問”,也就是中國是什么、從哪兒來、到哪兒去的書,都能賣得好。
自序
據說在短視頻時代,書是越來越難賣了。以前像我們這樣的非虛構作者,都是憑喜好寫書的。你喜歡哲學,他喜歡歷史,那么就寫本關于哲學或歷史的書,掙點文字搬磚工的勞動報酬。但現在感謝互聯網的壓力,我們寫一本書,得先想想能不能熱賣,尤其是按照很多平臺的成功經驗,好像還得販賣一下焦慮,才能賣得好。
所以一位對中國出版行業非常理解的編輯告訴我,你寫歷史題材,得抓住當代中國人的知識焦慮。這其中最大的一個焦慮,就是關于身份認同的。翻譯成白話就是中國人憑什么成了中國人,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意味著什么。
我說這可是中國啊,真有那么多人關心身份政治嗎?他說當然了,你想男人三大愛好,兩性、足球、政治。兩性不讓談,足球談了就生氣,那就只剩下政治了。現實政治紅線太多,那最適合談的當然就是身份政治。民族、國家、歷史,都是身份政治的一部分。
我覺得這個分析當然是很一針見血的,但我們作研究的人最不擅長的就是迎合身份政治,因為我們在學校里學到的內容就是:當你沒別的可炫耀的時候,你就只能炫耀你的身份,這就是身份政治為什么有那么多擁躉的原因。
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北大畢業生默認的一句人生箴言,就是畢業十年后別提你是北大的。因為如果這么做,那就意味著你畢業十年后取得的成就都沒能超過這個成就。
個人是這個道理,國家好像也是這個道理。這就是為什么塞繆爾·約翰遜博士說:“愛國主義是無賴最后的避難所。”因為無賴除了彰顯他的身份之外,好像沒別的成就可以提。
有段時間知識分子都是拿這句話來批判過激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似乎一個落后又愚昧的民族才會靠身份政治打雞血獲取自豪感。但“活久見”的是,這屆美國大選之后,我們發現美國人好像也開始搞“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了。至少他們好像確實不太愿意有人打個飛機過去生孩子就能變成美國人,哪怕這是他們憲法里已經寫進去的事實。
這可能就是為什么大家都在感嘆文科已死。我們上課時學關于身份政治的內容基本都是反面教材,到了政治家那里反而成指導手冊了,我們這些做題家還是學生思維,活該做不了官也賺不到錢。
言歸正傳,我們要吃飯,所以要賣書。要賣書,好像是得迎合一下身份焦慮。所以據說替中國回答“終極三問”,也就是中國是什么、從哪兒來、到哪兒去的書,都能賣得好。
其實在這片土地上寫這類書,就好像在日本寫《名偵探柯南》一樣,結論是給定的:柯南一定把案子給破了,你要關心的只是他怎么破。同樣的道理,你讀這類書,要關心的就是中國過去為什么行,將來為什么還能行,這就夠了。
但是我們知識分子有個壞毛病,腿腳有問題,又老想站著還把錢掙了。這就像我有一次參加某個企業家交流會,有人慷慨激昂:我們只能相信中國經濟好,因為我們別無選擇。我當時就在想,你老婆孩子好像拿的是澳洲護照吧,你也不是沒選擇啊。如果你用沒選擇來論證你對一個事情有信心,那你講這個話的客觀作用好像只能是打擊我對這個事的信心啊。
我作為一個熱愛這片土地和這片土地上同胞的三好青年,著實不想掙這種錢。但是市場規律是要遵循的,焦慮是要販賣的,身份政治是要回應的。所以我思來想去,只能找到一個似乎略顯刁鉆的角度。
現在擺在你面前的這本書,聊的還是關于中國為什么成為中國的歷史。但是我想聊的不是你自己怎么成了你自己,而是在這個過程中,別人怎么幫你成了你自己。用學術術語來說,就是域外的世界力量是怎么塑造中國成為我們今天熟悉的這個中國的。
我本來給這本書起的名字叫“把世界還給中國”,意思是說,塑造我們中國成為中國的有很多來自世界的力量。有北方游牧民族的,有中亞波斯印度的,有南洋大航海探險的,當然也有西方的政治理論。沒有這些力量的塑造,就沒有我們熟悉的秦漢唐宋元明清。假設我們覺得中國過去行,我們得看到這些力量的作用。假設我們希望中國將來行,我們就還要繼續期待這些力量發揮作用。
但是后來編輯說這個名字不妥,這意思好像是說世界過去是中國的所有物,后來被奪走,現在要歸還中國對世界的合法所有權,你可不能這樣表態,啊。“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意思不是世界上除了中國沒有別的國家了。
我一想也對,只好商量改成現在這個題目,叫作“世界之中”,意思是中國不光是中國人的中國,也是全世界的中國。
這個道理乍看起來好像有點唐突,但仔細想一想,邏輯也很簡單。這就像上海不光是上海人的上海,而且是中國的上海;深圳不光是深圳人的深圳,而且是中國的深圳。你能這么叫證明你本身的優秀性超越了地域性。像我的老家山東省日照市嵐山區高興鎮厲家湖村,就沒資格叫中國的厲家湖,因為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愿意為厲家湖這片熱土添磚加瓦的,肯定比不上愿意為上海和深圳添磚加瓦的。
你能夠用你域外的上位概念來指稱你,這是一種光榮和責任,這意味著來自域外的力量愿意來你這里發光發熱,而你也愿意接納他們,讓你成為他們一種更好的選擇。
這就是我們熱愛這片土地和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理由。不是因為我們沒的選擇,而是因為它一直在提供著不一樣的選擇。
是為序。
結語(選):
我們很多人對很多民族都容易形成刻板印象,但讀多了歷史,你就會發現,許多刻板印象并不是“自古以來”,它們形成的時間其實都相當短暫。
今天的瑞士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富庶、進步和“永久中立”,但在1848年以前,此地多屬農村,又在阿爾卑斯山間,窮鄉僻壤,是環境惡劣的“四戰之地”。瑞士雇傭兵曾因驍勇善戰著稱,曾于1499年擊敗施瓦比聯盟,但也在1515年敗給法軍。此后他們雖然很少從事對外戰爭,卻因為宗教改革經常爆發內戰(1656年的維爾梅根戰爭,1712年的托根堡戰爭,1798年被法軍占領,1847年獨立同盟戰爭)和農民起義。今天富庶的瑞士,是工業化之后才誕生的。
今天人們普遍認為法蘭西的軍隊軟弱而德意志的軍隊強悍,然而在兩百年前,人們對這兩個民族的印象是相反的。托爾斯泰的小說《戰爭與和平》創作于1865—1867年,描寫的是拿破侖戰爭時代的事。那里面安德烈公爵的父親老博爾孔斯基對拿破侖的評價是:“波拿巴(即拿破侖)生來有福分。他的士兵很精銳,而且他先向德國人進攻,只有懶人才不打德國人。自從宇宙存在以來,大家都打德國人。他們打不贏任何人。他們只曉得互相殺戮。他就是憑這一手聞名于世的。”這便是當年德國人給歐洲其他民族留下的印象。德國人扭轉這個印象,也不過是最近一百五十年的事。
今天日本給人的印象是干凈、整潔、秩序井然,福利制度全面且貧富差距不大。然而在1910年日本作家長冢節的小說《土》中,盡管日本已經開始了成功的工業化,但農村婦女因為醫療條件差而死亡,兒童普遍挨餓,女孩被送到慘無人道的黑心工廠去工作,每天十二個小時輪班,宿舍骯臟至極無法入眠,大城市周邊貧民窟無處不在。即便在“二戰”前,日本的工業建設也不過就是那個樣子,而日本人扭轉這個印象,也用了三十年的時間。
今天許多中國企業家在“出海”時,計算越南、印度尼西亞、墨西哥、埃塞俄比亞或蘇丹的勞動力性價比,認為那些地方工人懶惰、愚昧、教育水平低下,不如中國人勤勞勇敢、聰明刻苦。然而倒退回20世紀80年代,日本、新加坡、中國香港或中國臺灣的企業家看大陸,其實也帶有類似的偏見。大陸人扭轉這種刻板印象,也用了一代人的時間。
滄海桑田,世殊事異,誰說是什么就一定是什么?過去的失敗不代表將來會一直失敗,過去的輝煌也不代表將來會一直輝煌。只有那些永遠不擁抱變化的民族,才無法甩去他人對自身最消極的刻板印象。
歷史學里有一個說法:我們的歷史觀取得進步,往往不是因為發現了新的史料,而是因為我們用全新的視角看待自己的過去。19世紀中葉的德意志民族用“懶惰”定義自己嗎?并不是這樣。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發現,德意志人從中世紀開始就是精于商貿和探索的民族,他們有輝煌的漢薩同盟,而今德意志人要復現這種傳統。19世紀中葉的日本民族用“閉關鎖國”定義自己嗎?并不是這樣。吉田松陰開塾授課,所講的內容也不過是《論語》《孟子》《孝經》《禮記》《莊子》《孫子兵法》《史記》《資治通鑒》《三國志》《后漢書》《新論》和《日本書紀》《古事記傳》等中日經典著作,然而維新派就是可以從中開出變法自強的新道。
一百年前,有不少絕頂聰明的才學之士討論過國民性問題,他們討論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不外乎要重新樹立中國人的驕傲。然而張之洞寫《勸學篇》,以“教忠”“明綱”為先,似乎不感念大清之愛民,不以三綱五常為本,便不配做中國人。至于倭仁論“以忠信為甲胄、禮儀為干櫓”,似乎連搞了洋務運動、學了洋槍洋炮的,都不配做中國人。至于19世紀中葉政府收購了洋人修筑的鐵路,再行拆毀,那意思是坐火車都不配做中國人了。
為什么定義“中國人是誰”要以限制某種可能性為前提呢?
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欽佩的是梁啟超、何啟這樣的人。有人說中國人的民族性格中無武勇,梁啟超便挖掘中國歷史上的武士精神,說中國人也可以做武士;有人說中國人的民族性格中不開拓,梁啟超便挖掘中國歷史上的殖民英雄,說中國人也可以大航海;有人說新學舊學勢同水火,何啟便寫文章說,孔孟之道與西人講自由、民權殊途同歸,中國人不必限制自己的可能性。
在我看來,這才叫知識分子里的真英雄。
亞里士多德有一種關于事物變化的學說,叫作“潛能與現實”理論。
所謂“潛能”,就是事物可能呈現的樣子。譬如一塊木頭,它可以成為一只碗,也可以成為一張桌子,也可以成為一尊精美的神像。它成為什么,這要看在雕刻它的木匠眼中,它可以成為什么。如果這位木匠一輩子只會做碗,那么再好的木頭,也只能變成一只碗。木匠頭腦中束縛自己的框架,就成了木頭的桎梏。
而這個“現實”,在哲學界前輩的文獻中,有一個非常浪漫且優美的譯法,叫作“隱德來希”。這既是對拉丁語entelecheia的音譯,也是對它的意譯:“隱在事物中之德如何能按我們的希望到來。”這便是“現實”。其實我倒以為,這個詞可以有一個更地道的中文翻譯:成全。在諸多可能性中,把最好的那個帶出來,便是成全。
被局限的頭腦想要的成全,其實往往不是成全。鄭淵潔以前有篇童話,說上帝想讓大灰狼羅克成為第一個攻克癌癥的人,所以賦予他喜愛觀察生物的天賦。但羅克的父母想要培養他做鋼琴家,于是砸鍋賣鐵給他請鋼琴老師。上帝希望糾正他們的做法,便讓鋼琴出故障,而羅克的父母賣血也要讓羅克學鋼琴。上帝沒有辦法,只能把人類攻克癌癥的時間推遲一百年。
被局限的成全不是成全,只有讓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社會意識到在自己體內本來具有無限的可能性,由此催生出那種積極昂揚感,才有可能鍛造真正的成全。
在這本書里,我想寫的故事,曾經被那么多人忽略,卻是關于我們這個文明的可能性。
其實所有的歷史寫作,本質上都是篩選。同一個時代有億萬生靈、億萬個故事,其中因為個體本身的成就和故事本身的精彩而得以被記錄、保留,或者被口頭傳頌從而誕生的一手史料,本就篩選去了百分之九十九,余下百分之一。而當時的歷史記錄者可能為了刻畫時代的風氣與精神,又會按照自己頭腦中對時代的理解,再從這些一手史料中篩選剩下的百分之一,把它們綴連起來,錄入史籍。后世的歷史學家如果寫一部通史,就只能從這些史籍中再篩出百分之一,讓它構成對這個時代的記憶。而如果諸位讀者不想費心力去讀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或者威爾·杜蘭的《世界文明史》那些大部頭的通史著作,只愿意從我們這些“二道販子”手里擇些東西淺嘗輒止,則又要經歷一道百分之一。
連續四個百分之一的篩選,就只剩億分之一。這就是真相:人類社會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所閱讀到的歷史,可能只是原始歷史資料的億分之一。而這從億到一的篩選中,如果有任意兩到三步是被記錄者或者寫作者頭腦中的框架所束縛,那么你能獲得的,就只是世代積累的刻板印象的加總,距真正豐富無限的歷史,可謂遠矣。
當然,沒有人能還原那“億分之億”的歷史真相,但是我們有另外一種辦法,那就是,以不同的標準進行篩選。譬如,如果過去我們以為中國人長于道德討論而弱于科技研發,那么我就想告訴你,中國之所以名為“中國”,就是因為我們曾經是科技最先進的古文明。如果過去我們以為中國與世隔絕,那么我就想告訴你,中國歷來不曾遠離世界,也不可能遠離世界。如果過去我們以為游牧與農耕勢不兩立,那么我就想告訴你,也有從事游牧的中國人,他們對中國歷史的塑造,或許比農耕者更深刻。如果過去我們以為中國人錯過了大航海時代,那么我就想告訴你,也有在大航海時代雄霸一方的中國人,有共和立國的中國人,有身兼中西之長的中國人,有跟萊特兄弟同時造出飛機的中國人。
世界之中,也可以說是把世界還給中國,就是把這樣一些可能性還給我們自己。我們明明可以好好說話,明明可以好好擁抱這個世界,明明可以在科技、商業和文化領域拔得頭籌,為什么要封閉自己,不去睜眼,看看別人所思所想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我們流俗的民粹主義意見中表達的那些東西?為什么我們的先輩都能夠正視這個世界,正視我們自身不可或缺的世界性,而我們有些人卻不能?高鐵、5G、移動互聯網,這些進步中哪一項能夠缺少與世界的健康交流,但為什么還有那么多人只是用這些成就來助長另一些人的驕傲自大、固步自封?
我相信再優秀的人,他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東西,他自己也可能只懂其中的十分之一。而對其余事物的理解,很可能是被某些并不優秀也不專業的人塑造的。這剩下的十分之九中,歷史理解與歷史記憶也許占到很大的比重,因為我們多數人都不會選擇成為歷史學家,但多數人愿意從歷史閱讀中汲取智慧與力量。不過,如果我們的歷史記憶是被那些固步自封的想法篩選掉的,甚至這種篩選將我們定義得越來越窄小,那將對我們所有人造成不可磨滅的傷害。因為世間最大的遺憾,并不是我們“做不到”,而是我們“本可以”。
我想在這本書中送給你的,就是歷史上我們曾經做到的那些事,和它們可能啟迪我們在這個時代應該做到的那些“本可以”。
世界之中 作者簡介
張笑宇,山東人,畢業于北京大學,后赴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現為華東師范大學世界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上海世界觀察研究院研究員,兼任寬資本產業研究顧問、騰訊騰云智庫成員。著有“文明三部曲”(《技術與文明》《商貿與文明》《產業與文明》)。2021年第一屆亞洲圖書獎得主(《技術與文明》),是中國大陸知識界第五位,也是最年輕的獲獎者。
- >
山海經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羅庸西南聯大授課錄
- >
企鵝口袋書系列·偉大的思想20:論自然選擇(英漢雙語)
- >
煙與鏡
- >
月亮與六便士
- >
回憶愛瑪儂
- >
隨園食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