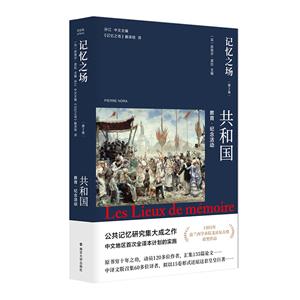-
>
清通鑒(全四冊)(精裝)
-
>
明通鑒(全三冊)(精裝)
-
>
跨太平洋的華人改良與革命 1898-1918
-
>
天有二日(簽名鈐印特裝本)
-
>
歐洲至暗時刻(1878-1923):一戰為何爆發及戰后如何重建
-
>
(精裝)奧托·馮· 俾斯麥與德意志帝國建立
-
>
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記憶之場 第2卷 共和國 教育·紀念活動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5281181
- 條形碼:9787305281181 ; 978-7-305-28118-1
- 裝幀:精裝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記憶之場 第2卷 共和國 教育·紀念活動 本書特色
☆ 拿破侖發動的兵變為什么叫作“霧月革命”,《馬賽曲》的作者是誰,三色旗如何成為法國國旗……快來這本書里尋找答案吧!
☆ 人們都以為共和國的“小紅書”《雙童環法記》背后的作者是一個儒雅的學者,但它居然出自一個離婚婦女之手。當真相的面紗被揭開,這背后又隱藏了怎樣的故事?
☆ 記憶在沉睡,那些沉淀著、凝固著、表現著的,已從我們集體記憶中枯竭的資源的場所有待我們走入。
☆ 深入歷史的符號與記憶之中,探索過去如何影響今天的文化與社會面貌。
☆ 這本書為你呈現法國歷史背后的深刻文化脈絡,是理解記憶與歷史關系的重要作品。
記憶之場 第2卷 共和國 教育·紀念活動 內容簡介
本書譯自法國著名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主編的《記憶之場》三卷本的《共和國》卷。原著《記憶之場》是當代法國史學界深具影響的歷史著作之一,匯總了法國集體史的研究成果,是一部經典的有關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本書作為《記憶之場》中文版的第二卷,包含了《共和國》卷中的“教育”“紀念活動”2個部分,考察了《雙童環法記》、第三區教育之友圖書館、法國國慶日、1931年的殖民地博覽會等法國代表性政治符號的生成及其流變歷程,呈現出法蘭西共和國政治文化的多重面相。
記憶之場 第2卷 共和國 教育·紀念活動記憶之場 第2卷 共和國 教育·紀念活動 前言
中文版序
諾拉
宋逸煒 譯
《記憶之場》已經被譯為世界上主要語言,但都是對部分篇目的翻譯。
因此,我對《記憶之場》中文全譯本的出版深感榮幸。無論從哪方面看,翻譯所有文章都是一項巨大的工程。我首先要向三位負責人表示感謝,他們是:南京大學教授、主編孫江先生,兩位主編助理于京東先生、宋逸煒先生。
通過他們,我要感謝《記憶之場》中譯本編輯委員會的全體成員。此外,我還要感謝參與這一項目的所有譯者、校對者和編輯。
記憶之場 第2卷 共和國 教育·紀念活動 相關資料
中譯本序
孫江
“歷史在加速”。
皮埃爾·諾拉在《記憶之場》導言劈頭如是說。基于這種緊迫感,諾拉動員一百多位作者,窮十余年之功,編纂出版了由135篇論文構成的3部7卷、超過5600頁的皇皇巨制。與研究過往之事的歷史學不同,也與“心態史”徑庭有別,這部巨著乃是要在文化社會語境中回溯歷史,探討形塑法國國民意識的“記憶之場”。
1931年11月17日,諾拉出生于巴黎一個外科醫生的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血雨腥風下,猶太裔的諾拉家族經歷了抵抗運動的驚險。戰后,諾拉進入路易勒格朗中學,最后在索邦大學取得學士學位。1958年,諾拉赴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亞拉莫里奇埃高中任教,1960年返回法國,翌年出版《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批判作為“殖民者”的法國人。
1965—1977年,諾拉先后在巴黎政治學院和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任職。1965年,諾拉加入著名的伽利瑪出版社,編輯“人文科學叢書”“證言叢書”“歷史學叢書”等。1980年,諾拉與哲學家戈謝創辦《論爭》,引領前沿話題。1974年,諾拉與勒高夫合作主編了三卷本的《制作歷史》。1978年,諾拉在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開設討論課。其時,法國歷史學界開始反省科學取向的歷史研究,呼喚歷史主體的回歸,“記憶之場”正是在這一脈絡中醞釀而成的。2002年,諾拉在給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重思法國:記憶之場》所寫的導言中回顧道,20世紀六七十年代“年鑒學派”布羅代爾的史學是對“事件史的十字軍”,而“心態史”不過是科學的數量統計方法的延伸,“量”的統計未必反映“質”的變化。
中譯本序
孫江
“歷史在加速”。
皮埃爾·諾拉在《記憶之場》導言劈頭如是說。基于這種緊迫感,諾拉動員一百多位作者,窮十余年之功,編纂出版了由135篇論文構成的3部7卷、超過5600頁的皇皇巨制。與研究過往之事的歷史學不同,也與“心態史”徑庭有別,這部巨著乃是要在文化社會語境中回溯歷史,探討形塑法國國民意識的“記憶之場”。
1931年11月17日,諾拉出生于巴黎一個外科醫生的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血雨腥風下,猶太裔的諾拉家族經歷了抵抗運動的驚險。戰后,諾拉進入路易勒格朗中學,最后在索邦大學取得學士學位。1958年,諾拉赴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亞拉莫里奇埃高中任教,1960年返回法國,翌年出版《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批判作為“殖民者”的法國人。
1965—1977年,諾拉先后在巴黎政治學院和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任職。1965年,諾拉加入著名的伽利瑪出版社,編輯“人文科學叢書”“證言叢書”“歷史學叢書”等。1980年,諾拉與哲學家戈謝創辦《論爭》,引領前沿話題。1974年,諾拉與勒高夫合作主編了三卷本的《制作歷史》。1978年,諾拉在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開設討論課。其時,法國歷史學界開始反省科學取向的歷史研究,呼喚歷史主體的回歸,“記憶之場”正是在這一脈絡中醞釀而成的。2002年,諾拉在給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重思法國:記憶之場》所寫的導言中回顧道,20世紀六七十年代“年鑒學派”布羅代爾的史學是對“事件史的十字軍”,而“心態史”不過是科學的數量統計方法的延伸,“量”的統計未必反映“質”的變化。
《記憶之場》第一部一卷出版于1984年,名為《共和國》,分“象征”“紀念儀式”“教育”“紀念活動”“反差記憶”等五個主題。1986年,第二部《民族》三卷出版。第一卷的“遺產”“歷史編纂學”“風景”偏于“非物質”;第二卷聚焦“物質”層面——“領土”“國家”“遺產”,既有國境、六邊形象征,也有凡爾賽宮,還有歷史遺產及其保護運動等;第三卷《思想》涉及“榮耀”“語詞”,有軍事上的榮耀和市民榮譽、語言和文學、與政治相關的事物等。1992年,第三部《復數的法蘭西》三卷出版。第一卷《沖突與分割》,圍繞政治分歧、宗教少數群體、時空的分割(海岸線、巴黎與外省、中心與邊緣等)而展開;第二卷《傳統》,涵蓋鐘樓、宮廷、官僚、職業和法語史等,旁及地方文化、法蘭西特性等;第三卷《從檔案到標志》,關乎記錄、名勝和認同等。
“記憶之場”是諾拉創造的術語,由場(lieu)和記憶(mémoire)構成。諾拉認為:“記憶之場”既簡單又含糊;既是自然的,又是人為的;既是最易感知的直接經驗中的對象,又是最為抽象的創作。“記憶之場”有三個特征:實在的、象征的和功能的。檔案館是實在的,被賦予了特定的象征意義;教科書、遺囑、老兵協會因成為儀式的對象而進入“記憶之場”;一分鐘的沉默堪稱象征的極端例證;世代觀念是抽象的“記憶之場”,其實在性存在于人口學中,功能性體現為形塑和傳承記憶的職能,象征性被視為某個事件或經驗,只有某些人才擁有。在這三個層面上,記憶和歷史交互影響,彼此決定。與歷史有所指不同,“記憶之場”在現實中只是指向自身的純粹符號。
在《記憶之場》第三部出版前發生了兩件事:一是冷戰結束后,兩極格局瓦解,民族國家遭遇新的挑戰;另一是法國史學出現了一系列名為“法國史”的敘事。對于后者,諾拉在《重思法國:記憶之場》導言中說:“記憶之場始于與這一研究不同的前提,反映了一種不同的激進觀點。”諾拉所追求的“記憶之場”既然是另一種歷史——與過去保持連續的并由現實的集體所傳承的當下的歷史,那么區分二者的關系便顯得十分必要。但是,在第一部和第二部出版后,諾拉發現“記憶之場”的曖昧性有礙這種區分。在第三部導言《如何書寫法蘭西史》中,諾拉再次談到“記憶之場”的內涵,認為“記憶之場”首先是一個狹隘的、限定的概念,體現為從紀念碑到博物館,從檔案到口號再到紀念儀式等,與現實有可觸可感的交叉關系。此外,“記憶之場”還有較為寬泛的含義,承載著象征化的歷史現實。與諾拉的主觀意圖相反,伴隨前兩部出版后的成功,“記憶之場”被人們廣泛使用,內涵縮小為僅僅指稱物質性的紀念場所。諾拉無奈地說:“記憶之場試圖無所不包,結果變得一無所指。”《記憶之場》本欲反省以往的法國歷史敘述,無意中卻構筑了基于當下情感的法蘭西整體史。在第三部最后一卷結尾《紀念的時代》一文中,諾拉稱之為“紀念變形”所致。
《記憶之場》在法國獲得巨大成功,諾拉一躍而為眾目所矚。1993年,《記憶之場》獲得法國最高國家學術獎,同年《羅貝爾法語大詞典》收入“記憶之場”詞條。2001年6月7日,諾拉當選為僅有40名定員的法蘭西學術院會員。在法國之外,《記憶之場》也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被譯為多種文字,有德文、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俄文、土耳其文、韓文、日文、中文(繁體和簡體)等。《記憶之場》的主題和研究方法,推動了各國關于自身記憶歷史的研究。
不同譯本在翻譯“Les lieux de mémoire”時,均碰到無從尋覓合適譯詞的難題。德譯本將《記憶之場》譯為《回憶場所》(Erinnerungsorte),西班牙文譯為《記憶與歷史》(Memoria e historia),俄譯本改名為《法國記憶》(Францияпамять)。“lieu”在英文中可譯為“背景”(background)、“地點”(site)、“場所”(place)等,但缺少抽象意涵,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英譯本《記憶的場域:重思法國的過去》(Realms of Memory: 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將lieu譯作“realm”(場域),似有補缺拾遺之效。在東亞地區,韓文譯本和日文譯本均有漢字背景,韓文作“??”(jangso),日文作“場”(ba),均為“場所”之意。但是,中譯本“記憶之場”的“場”,除“場所”外,還有“場域”之意,應該說最能體現諾拉的本意。
2015年,《記憶之場》節譯本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后,受到讀者的歡迎,先后于2017年和2020年再版。迄今為止,《記憶之場》所有文字的譯本都是節譯,中文簡體節譯本的成功令我燃起了翻譯全本的愿望。這是一項巨大的翻譯工程,譯者有60多人,對語言的理解因人而異,要把參差不齊的譯文統一起來絕非易事,校對工作超乎尋常的艱難。王楠博士、于京東博士、宋逸煒博士出力甚大,宋逸煒博士幫我處理了大量煩瑣的事務。2020年宋逸煒博士在巴黎留學期間曾向諾拉報告了翻譯情況,諾拉在為中國讀者特意錄制的五分鐘短視頻中表示,期待中國學者寫出屬于自己的“記憶之場”。悠悠我生,此言擊中我心。我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研習“年鑒學派”的著述,數十年從未間斷,念念不忘借鑒他山之石。對我來說,法國近代史與中國有很多可比之處,翻譯法國的《記憶之場》可為研究中國的“記憶之場”做準備。猶記2009年回南京大學開啟“南京:現代中國記憶之場”研究的初衷,屈指已十余年矣。
記憶之場 第2卷 共和國 教育·紀念活動 作者簡介
關于主編
主編: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1931年生,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和學術編輯,著有《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現在、國民、記憶》《追尋法蘭西》等,主編《記憶之場》。1993年,《記憶之場》榮獲法蘭西學術院戈貝爾大獎,同年“記憶之場”(Lieux de mémoire)一語被收入《羅貝爾法語大詞典》。2001年,諾拉當選為僅有四十名定員的法蘭西學術院院士。
中文主編:孫江,1963年生,澳門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名譽院長。著有《人種》(2023)、《重審近代中國的結社》(2021)、Revisiting China's Modernity (2020)、《重審中國的“近代”》(2018)等十余部著作;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學衡爾雅文庫”等集刊和叢書。
- >
巴金-再思錄
- >
月亮與六便士
- >
二體千字文
- >
隨園食單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歷史與人類學概述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苦雨齋序跋文-周作人自編集
- >
新文學天穹兩巨星--魯迅與胡適/紅燭學術叢書(紅燭學術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