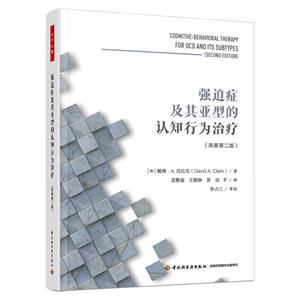-
>
妙相梵容
-
>
基立爾蒙文:蒙文
-
>
我的石頭記
-
>
心靈元氣社
-
>
女性生存戰爭
-
>
縣中的孩子 中國縣域教育生態
-
>
(精)人類的明天(八品)
萬千心理.強迫癥及其亞型的認知行為治療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8440092
- 條形碼:9787518440092 ; 978-7-5184-4009-2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萬千心理.強迫癥及其亞型的認知行為治療 本書特色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for OCD and Its Subtypes (Second Edition) 大量臨床實踐和實證研究都證實了認知行為療法對理解和治療強迫癥的作用,《強迫癥及其亞型的認知行為治療》**版在國外也受到了治療師的歡迎。修訂后的第二版不僅對強迫癥的癥狀、認知行為的理論和治療方案都有詳細闡述,并補充了新的發展和趨勢,非常適合治療師們學習使用。
萬千心理.強迫癥及其亞型的認知行為治療 內容簡介
《強迫癥及其亞型的認知行為治療》闡述了認知行為療法如何理解和治療強迫癥及其亞型,對強迫癥的理論、研究和治療進行了綜合的論述,還包含了近年來該領域發展的成果和趨勢。作者克拉克博士從事認知行為治療的臨床和研究工作多年,在強迫癥的治療方面也有非常豐富的經驗。通過本書,治療師們能了解強迫癥的臨床特征和治療方案,從而提升自己對強迫癥的認知行為治療技能。
萬千心理.強迫癥及其亞型的認知行為治療 目錄
**部分 強迫癥的本質
第1章 診斷、現象學及共病
第2章 強迫思維、侵入性思維及其相關
第3章 強迫行為、中和反應和控制
第二部分 理論、研究與實踐
第4章 暴露與反應預防:理論與實踐
第5章 認知行為模型:理論與研究
第三部分 強迫癥的認知行為治療基礎
第6章 治療關系
第7章 評估與個案概念化
第8章 治療目標、心理教育和認知干預
第9章 經驗性假設—檢驗實驗
第四部分 強迫癥亞型的治療方案
第10章 污染型強迫癥
第11章 懷疑、檢查和重復
第12章 與傷害、性和宗教有關的強迫思維
第13章 對稱、秩序和排列
萬千心理.強迫癥及其亞型的認知行為治療 節選
強迫癥對治療關系的威脅 對一些患者來說,建立積極的治療關系和工作聯盟可能更具挑戰性。本節討論了10個可能對治療關系產生負面影響的強迫癥特征。針對每種特征,我們都提出了建議,以消除其對工作聯盟的威脅。 矛盾心理 很多原因都會導致強迫癥患者無法全身心地投入治療過程。有些患者可能會覺得自己是被迫接受治療,因為家人和朋友比患者本人更相信這種疾病的破壞性影響。有些病程很長的患者可能在參與治療時感到挫敗、沒有信心,認為沒有什么能有效地消除根深蒂固的強迫癥狀。或者他們可能經歷過一系列的“治療失敗”,因此認為CBT也不會有效。另一些患者可能非常相信他們的癥狀具有生物學基礎,因此難以接受心理治療。強迫癥常常成為他們自我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以至于患者很難想象沒有強迫癥的時候自己會是什么樣子。*終的結果可能是對改變的矛盾心理,并減少對治療過程的投入。 當患者因渴望改變而尋求治療,同時又害怕和抗拒治療時,就會出現矛盾心理(ambivalence; Westra & Norouzian, 2017)。矛盾心理是治療阻力的一個重要方面,它會削弱治療聯盟、破壞治療效果,并導致治療過早地結束(Szkodny, Newman, & Goldfried, 2014; Westra & Norouzian, 2017)。 由于完美主義的存在,矛盾心理在強迫癥中尤其成問題。完美主義一直被認為是強迫癥的一個主要特征(Frost, Novara, & Rhéaume, 2002; OCCWG, 1997)。對完成儀式的高標準的嚴格遵從、對準確性和完整性的需求、對犯錯的恐懼、控制的重要性以及無法忍受不確定性,明顯都是強迫癥中完美主義的各個方面(見Egan, Wade, Shafran, & Antony, 2014)。在《完美主義的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Behavioral Treatment of Perfectionism)這一治療手冊中,Egan及同事(2014)指出,矛盾心理是一種常見的治療問題。患者可能會錯誤地將其優勢歸因于完美主義,并淡化它對自己日常生活的負面影響。這種反應會導致患者很難在投入并努力改變和保持功能失調的完美主義之間做出選擇(Egan et al., 2014)。 矛盾心理的第二個根源是強迫癥患者的自我認知。Bhar和Kyrios(2007)提出,強迫癥患者的自我觀念是脆弱或矛盾的,自我概念中包含著矛盾或對立的元素。其他人則認為強迫癥中的自我表征(self-representation)混淆了現實與可能性(Aardema & O’Connor, 2007)。通過這種方式,對傷害的責任、對錯誤和疏忽的懷疑、不道德以及失控,都可以成為個體自我表征的重要部分。如果強迫癥患者以整潔、道德感強、盡責、嚴謹等特點來看待自己,他們可能會猶豫是否要加入這種治療中,因為這種治療會徹底改變他們珍視的價值觀和自我屬性。 治療師可以采取兩種方法來回應患者的矛盾心理。首先,重要的是治療師不能將憤怒、批評和責備指向患者。同樣,對抗、直接和問題解決的治療取向可能會增加阻抗或矛盾患者的脫落(Westra & Norouzian, 2017)。相反,治療可能需要少一些指導、多一些支持,治療師要對諸如反對、忽視、打斷、退縮、批評等阻抗的跡象更加敏感(Westra & Norouzian, 2017)。 應對矛盾心理*好的方法之一是將動機性訪談(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MI)的要素整合到治療計劃中。動機性訪談強調發展一個安全、合作的治療環境,在這個環境中,治療師幫助患者理清他們關于改變的沖突觀點(Miller & Rollnick, 2013; Westra & Norouzian, 2017)。Egan及同事(2014)建議治療師返回到對共同的治療目標和一般性目標的討論中。同樣,某些錯誤的信念可能會維持這些需要改變的矛盾心理。通常,強迫癥患者認為CBT的治療目標是把他們變成與強迫性擔憂相反的人。因此,有病理性懷疑的患者會變得魯莽和不負責任,有污染恐懼的患者變得骯臟和具有傳染性。通過蘇格拉底式提問和引導式發現,治療師幫助患者識別出這些需要改變的認知障礙,并探索一個更加平衡的治療視角,即治療目的是正常化而非徹底消除患者的強迫性擔憂。 動機性訪談的另一個應對矛盾心理的方法是鼓勵患者寫下改變與不改變的成本和效益(Egan et al., 2014)。患者可以使用工作表6.1來列出主要生活領域中維持和減少強迫癥狀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只有當患者對改變表現出矛盾心理時,才考慮使用成本-效益分析。它應該在治療階段的早期引入,而且治療師可能需要在會談內幫助患者開始,因為有些患者可能會發現很難想到不改變的好處。然而,當合作已然完成時,工作表6.1可以作為一個有用的工具,用來充分探索患者對治療的矛盾心理。在引入ERP的時候,治療師可以返回到同樣的練習(也見工作表4.2)來解決患者不愿意做暴露作業的問題。 過度尋求保證 強迫癥個體經常從治療師那里尋求保證(見第3章關于過度尋求保證的進一步討論)。這可能從兩方面對治療關系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首先,那些無意中為強迫癥患者提供保證的治療師會破壞治療效果,因為這減少了學習耐受痛苦和不確定性的機會。其次,治療師對尋求保證的回應可能會傳達出一種對患者的痛苦漠不關心的態度。當治療師對過度尋求保證(ERS)處理不當時,治療關系可能會破裂。 認知行為治療師在治療會談中必須警惕ERS的出現。例如,在面對暴露作業的時候,患者可能會對治療師說,“你認為(我)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撞倒行人嗎?”治療師可能會無意中幫助患者找出相關的信息。雖然這是一種標準的認知干預,但治療師還是給患者提供了保證。更好的回答應該是,“我理解你為什么問我這個問題,但是你是否認為這是在尋求保證?在過去,來自朋友、家人或網絡的保證是否有幫助?你認為同樣的事情會不會發生在我的保證上?你是否愿意探索另一種方式來回應你對傷害他人的擔憂?” 當治療師落入ERS的陷阱時,會出現幾個問題。**,治療師*終會強化非適應性的中和策略,這是強迫癥一個重要的維持因素。第二,暴露練習旨在檢驗強迫相關的信念和對痛苦的無法容忍,提供保證會減弱其效果。第三,從治療師的保證中獲得的解脫*多只是暫時的,從而會破壞治療師及治療的可信度。第四,ERS通常要求特定的回應(如,“不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撞倒某人”),這削弱了CBT注重合作和調查的性質。第五,ERS的頻率和強度可能會上升,所以治療可能會被患者對治療師越來越多的保證尋求所主導。 當然,治療師需要冷靜、理解和共情地討論ERS的問題以維持治療關系。畢竟,拒絕為患者提供保證就等于無視患者的痛苦——許多脆弱的個體會對這種經歷非常排斥。以下是一些處理ERS問題的建議。 · 與患者一同回顧他們尋求保證的經驗及效果,強調治療師的保證*終也將變得無效。 · 將尋求保證正常化,要特別指出大多數人都會尋求保證,但*終會發現它沒有說服力。 · 以一種高度合作的方式,討論作為治療師如何以一種敏感、關懷的方式來回應ERS,同時保持治療的完整性。 · 布置一項家庭作業:治療師對一項特定活動提供保證,讓患者監測這個保證對痛苦的影響。可以與不提供保證的活動相比較。痛苦的強度和持續時間有什么不同?治療師的保證是否如患者預期的那樣有效和有用? 僵化和缺乏靈活性 偏離常規、面對不熟悉的事物,或做一些新奇或模棱兩可的事情,對強迫癥患者來說是非常危險的(如Kusunoki et al., 2000)。此外,認知和行為的僵化是強迫癥公認的缺陷(如Gruner & Pittenger, 2017; Meiran, Diamond, Toder, & Nemets, 2011)。因此,強迫癥患者經常在日常生活中尋求秩序、常規和可預測的事物。但是,認知行為治療強調找到新的學習機會,打破固有的思維和行為模式。對那些認為不確定性(或模棱兩可)、新奇性和靈活性意味著困難和痛苦的患者來說,治療代表著一種令人畏懼和高度威脅的情境。每一次需要用不同方式思考和反應的挑戰都會引發恐懼和抗拒,這再次給治療關系帶來巨大壓力。 當患者缺乏心理靈活性時,治療就像一種“推拉(push and pull)”練習。對于不情愿的患者,如果治療師專注于評估舊的方法并嘗試新的方法,可能會導致阻抗,甚至引發治療師和患者之間的直接沖突。為了避免這種對治療關系的不利影響,治療師應該承認并肯定患者與做出改變所做的斗爭。關于改變的功能失調信念可以被解決,患者和治療師可以一起將治療任務分解成威脅性較低的步驟。*重要的是,治療師要記住,對許多強迫癥患者來說,日常生活的改變可能是一個可怕的試探。 控制的需要 對控制的需要是強迫癥*突出的認知特征之一(進一步討論見第3章和第5章)。對失控的恐懼,尤其是失去對非意愿思維的控制,會在強迫癥中反復出現(Clark, 2004; Clark & Purdon, 1993, 2016)。在重度強迫癥狀態下,患者可能把一整天的時間都浪費在過度控制與強迫相關的瑣事上,家庭成員也常受制于患者的強迫癥狀。在約25%的共病強迫型人格障礙的患者中,完美主義以及對秩序和控制的需要尤為突出(討論見第1章;Egan et al., 2014)。毫無疑問,控制的問題會蔓延至治療關系中,導致患者和治療師之間的沖突。 CBT的合作性質對一個習慣按自己的方式做事的強迫癥患者來說是陌生的,至少在*開始時是這樣。與治療師分享強迫相關的責任感和控制時,患者可能會感到不安。當治療會談中出現分歧、敵意和批評時,治療師需要探索,對失控的恐懼是否會成為威脅治療關系的一個問題。治療會談可能需要將重點轉移到與害怕失控相關的非適應性信念上。治療師應與患者探討更多關于控制的適應性信念,并討論如何共享對治療設置的控制。至少,當控制的問題出現并威脅到治療關系時,直接解決它們對治療師來說很重要。 隱瞞 強迫癥患者,尤其是那些有著令人厭惡的強迫思維的患者,在嘗試談論自己的強迫癥狀時,會感到非常尷尬和害怕,以至于可能會拒絕把強迫內容透露給治療師(Newth & Rachman, 2001)。隱瞞(concealment)是回避的一種形式,如果想要取得進展,就必須克服隱瞞。良好的治療關系是治療環境的關鍵,這種環境讓患者感到足夠安全,可以坦然和誠實地談論他們*可怕的強迫癥狀。如果還沒有建立起治療聯盟,患者就更可能拒絕全面暴露自己的強迫癥狀。或者,他們可能會為強迫癥狀找借口,或淡化其不合理性和嚴重性,而這會再次威脅治療效果。針對令人厭惡的強迫癥狀,第12章提供了一個關于隱瞞以及CBT治療師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的擴展討論。當隱瞞很明顯時,治療師需要放慢治療的節奏,并專注于創造一個安全的治療環境,鼓勵患者全面暴露強迫恐懼和擔憂。 人際缺陷和情感疏離 對于許多重度強迫癥患者來說,強迫癥似乎無處不在,導致他們無法再與他人建立健康的關系。他們可能會退回到自己的“強迫癥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他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強迫思維和行為上。社會退縮與隔離變得極端,任何與他人的接觸都會因患者完全專注于強迫癥而扭曲。當有病理性懷疑和嚴重的重復性強迫行為的患者嘗試與他人交流時,他們的溝通可能非常奇怪、難以理解,導致自己被其他人疏遠。此外,40%的強迫癥患者共病明顯的社交焦慮障礙,約10%的強迫癥患者可能患有回避型人格障礙(見第1章的綜述)。患有強迫型人格障礙的患者可能缺乏情感表達的能力,在談論自己的強迫問題時顯得冷漠和疏離。 當嘗試建立治療聯盟時,人際關系困難和情感疏離會帶來特殊的挑戰。為了減輕社交技能不良對治療關系的負面影響,治療師首先必須確定是否存在社交焦慮障礙、強迫型人格障礙或回避型人格障礙。如果存在這些情況,治療就需要考慮到這些共病,進而做出調整。但是,那些不符合人格障礙或社交焦慮障礙診斷標準的患者,也可能存在人際功能不足和情感疏離的問題。當這些問題在治療過程中出現時,CBT治療師需要重新考慮治療的相關方面。早期的治療可能需要采取一種更正式的、情感疏離的、以問題為中心的方式,以減少對患者人際上的要求。而在治療會談中建立了安全和舒適的環境后,治療師就可以轉向更親密、更開放、更坦誠的人際關系,這更有利于建立治療聯盟。 懷疑和猶豫 懷疑和猶豫是強迫癥的一般特征,其嚴重程度因人而異,表現出檢查和重復的強迫行為的患者*為嚴重(見第11章)。這兩個問題都會給治療關系帶來很大壓力,尤其是在CBT中,因為蘇格拉底式提問是首選方法(modus operandi)。對一個表現出嚴重懷疑和猶豫的患者使用蘇格拉底式提問可能會令人挫敗。對于治療師提出的問題,患者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做出回答,因為他們會對回答進行修飾和改正。這會使治療過程變得緩慢,也會使治療師感到沮喪和不耐煩。 對于如何應對極度緩慢和猶豫的強迫癥患者,這里有一些建議。 · 在治療會談中,直接指出并確認患者的猶豫、懷疑及相關的痛苦。 · 抓住患者表現出猶豫的時機,找出猶豫背后的錯誤評價和信念,并努力幫助患者培養更健康的反應模式來應對懷疑以及對錯誤和正確的擔憂。 · 討論治療師如何改變溝通風格,以降低猶豫和懷疑惡化的可能。例如,至少在治療的早期階段,少使用一些蘇格拉底式提問可能是更可取的做法。 · 設計特定的行為任務,鼓勵患者更快更有效地做出決定。事實上,可以在會談內設計一些決策任務,以便患者能夠在治療師在場的情況下練習更有效的決策方式。 道德僵化和宗教虔誠 強迫癥的特征可以被描述為道德上的認知歪曲,表現為與特定的強迫癥狀有關的過分嚴格、刻板、僵化的道德規范。例如,與健康對照組相比,強迫癥患者在面對非個人道德困境時較少使用功利主義(靈活的)的道德判斷,但在非強迫的焦慮組沒有觀察到差異(Whitton, Henry, & Grisham, 2014)。強迫癥患者在TAF-道德分量表上的得分顯著更高(Abramowitz & Deacon, 2006; A. D. Williams, Lau, & Grisham, 2013),道德的自我領域受到的威脅也更高(Doron, Sar-El, & Mikulincer, 2012)。強迫癥中過強的道德感是高度選擇性的,只局限于患者主要的強迫癥狀,但它對治療關系的影響可能是毀滅性的。 合作以及考慮替代方案的意愿是CBT的必要條件(sine qua non),而這些恰恰是道德僵化的患者無法忍受的。如果再加上宗教虔誠(religiosity),患者可能會對治療師的觀點表現出強烈的抵抗。治療可能會淪為口頭爭論,患者會因為治療師缺乏道德操守或試圖破壞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不屑一顧。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治療聯盟破裂、治療過早終止都是可能的。 第12章(見表12.1)提出了針對與宗教相關的強迫思維的具體治療建議。確認和尊重患者的道德和宗教規范并關注患者的治療目標是很重要的。治療師應該始終強調合作,與患者一起制定對他的強迫思維和行為問題的替代反應,并且要與患者的道德觀和信仰相一致。患者可能會指責治療師無能,就像“你不是基督徒,你怎么能理解我的問題?”“你試圖使我背離信仰,所以我不能信任你”,或“即便你認為是愚妄的,我仍相信有些想法是有罪的,它們來自魔鬼”。 即使感受到了威脅和患者的拒絕,治療師也需要保持鎮靜,繼續關注患者陳述的治療目標,堅持用強迫癥的術語而不是道德或神學的語言來描述問題。治療師可以鼓勵有道德顧慮的患者考慮受人尊敬的朋友或家人的道德準則。有沒有可能改變患者的道德準則和價值觀的某些方面,使之與他*欽佩的人趨于一致?為了保持健康的治療關系,無論CBT治療師使用何種具體的策略,都要用尊重、溫和以及折中的方式來處理道德問題。要記住,道德嚴厲和刻板的患者仍然是脆弱的,而且承受著自己執著于對錯的折磨。 對記憶的低自信 與沒有強迫癥的個體相比,強迫癥患者對自己記憶的信任度較低(如Radomsky, Rachman, & Hammond, 2001; van den Hout & Kindt, 2003b; 進一步討論見第11章)。顯然,對記憶的不信任會對治療關系產生負面影響。獲取患者本人不能立即覺知到的相關信息是引導式發現的一個重要部分(Padesky & Greenberger, 1995)。然而,對記憶缺乏信心的患者可能很難回憶過去經歷的細節。問題不在于記憶的準確性,而在于對回憶過去經歷的自信。這意味著強迫癥患者可能會:(1)聲稱不了解過去的經歷;(2)無法回答那些探索更具體的想法和解釋的問題;(3)對所有的回答進行修飾。這可能會使治療會談變得緩慢而令人挫敗。治療過程可能會變得像一場詰問練習。一旦出現這種情況,治療關系就會中斷,患者可能會考慮終止治療,因為治療給人一種冰冷、迂腐的感覺。 要解決這一問題,治療師應該承認患者對記憶信心不足的問題,接受對問題暫時和部分的回答,然后尋求進一步的澄清。治療師應該鼓勵患者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回答問題,并指出這種做法其實也可以被視為“對抗強迫癥”的經歷。同樣,治療師也應該在之后的會談中再談論這些經歷,詢問患者是否還記得它們。這種方法是在向患者表明,任何回憶都能在以后再詳細闡述或糾正,這也能降低他們的恐懼——恐懼自己糟糕的記憶力可能對治療產生永久的負面影響。 自我失諧 通常強迫癥中常見的強迫思維與患者的核心價值觀、理想或道德信條會存在不一致,甚至沖突——這種自我評價過程被稱為自我失諧(ego dystonicity; Clark, 2004; Purdon, 2004a)。例如,一個道德感很強、有責任心的患者可能產生令人厭惡的強迫思維,如傷害他人或進行令人厭惡的、非法的性行為。此外,強迫癥可能代表了自我恐懼(feared self)的某些方面(Aardema et al., 2013)。這對治療關系的意義是,患者在治療過程中可能會變得焦慮、自我防御,并拒絕聚焦于這些問題。 第12章更廣泛地討論了強迫癥的自我失諧這一特征及干預策略。再次強調,治療師必須承認患者在這些不尋常的心理侵入中的掙扎,并討論如何在治療會談中談論這些令人不安的內容。這可能是某些功能失調信念,比如“我們越多談論這些惡心的想法,我就越有可能采取這種行為”(TAF-可能性),這些必須在治療會談中加以解決。同樣,有必要對患者的自我恐懼進行認知方面的工作(即患者堅信擁有這些令人厭惡的想法對自己的真實自我有某種意義)。*后,令人厭惡的侵入性思維引發了患者的強迫恐懼,如果治療師利用合作的經驗主義方法,采取可測量的、理論支持的和聚焦的方法來處理這些侵入性思維,自我失諧對治療關系的負面影響就會降低。
萬千心理.強迫癥及其亞型的認知行為治療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戴維·A.克拉克(David A. Clark) 博士,加拿大新不倫瑞克大學心理學系名譽教授,執業臨床心理學家;加拿大心理學會會員,認知治療學院創始會員和培訓顧問,貝克認知行為治療研究所特設顧問,阿倫·貝克認知治療重要和持久貢獻獎獲得者;強迫癥認知工作組的創始成員,曾擔任《認知治療與研究》的副主編。 主譯簡介 孟繁強 精神科主治醫師,中國心理學會注冊心理師,北京安定醫院心理測查科主任,北京市心理危機干預隊隊員,疫情防控國家心理專家隊成員;主要從事強迫障礙、焦慮及失眠的認知行為治療機制、實踐與推廣研究。 審校簡介 李占江 主任醫師,教授,博士生導師,首都醫科大學臨床心理學系主任;中國心理衛生協會、中國心理學會注冊督導師,中國心理衛生協會認知行為治療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醫師協會精神科醫師分會常務委員,中華醫學會精神醫學分會常務委員;主要研究領域為焦慮、強迫障礙、睡眠障礙及認知行為理論與治療。
- >
羅曼·羅蘭讀書隨筆-精裝
- >
回憶愛瑪儂
- >
有舍有得是人生
- >
姑媽的寶刀
- >
二體千字文
- >
山海經
- >
史學評論
- >
新文學天穹兩巨星--魯迅與胡適/紅燭學術叢書(紅燭學術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