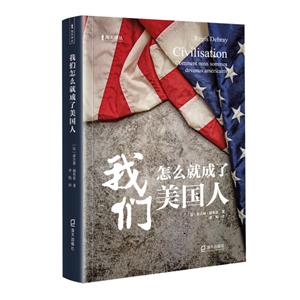-
>
清通鑒(全四冊)(精裝)
-
>
明通鑒(全三冊)(精裝)
-
>
跨太平洋的華人改良與革命 1898-1918
-
>
天有二日(簽名鈐印特裝本)
-
>
歐洲至暗時刻(1878-1923):一戰為何爆發及戰后如何重建
-
>
(精裝)奧托·馮· 俾斯麥與德意志帝國建立
-
>
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我們怎么就成了美國人》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0730533
- 條形碼:9787550730533 ; 978-7-5507-3053-3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我們怎么就成了美國人》 本書特色
作者雷吉斯·德布雷是法國著名作家、哲學家和媒介學家,龔古爾學院成員,著有《知識分子與權力》《新權力》《歐洲幽靈》《燃燒的雪》等近百部作品,因提出“媒介學”在法國思想界獨樹一幟,更新了媒介觀念,并開拓了全球人文研究領域的新方向。 雷吉斯·德布雷年輕時曾追隨切·格瓦拉,加入南美游擊戰,后在塞爾維亞被捕。關押審訊期間,薩特、拉康、薩岡、杜拉斯等人在巴黎為其發起聲援活動,席卷全球。 這位曾經的叢林戰士,以大膽的、全新的歷史視野,揭示了美利堅帝國和羅馬帝國類似的發展軌跡,悲哀地告訴大家“我們是怎么成為美國人的”:軍事制霸,語言壟斷,文化催眠…… 這是一份歐洲文明的死亡證明,佐以保羅·瓦萊里關于“所有的文明都將走向死亡”的洞察力。 年輕的美國懂得如何讓別人在戰后喜歡上自己,通過上下合圍的滲透,它讓空間戰勝了時間,影像打敗了文字,幸福取代了悲劇, “美式生活”也在不知不覺中成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
《我們怎么就成了美國人》 內容簡介
什么叫文明?文明是如何誕生,又是如何衰亡的?歐洲文明的式微有助于我們回答這些像世界一樣古老的問題。 從中情局到說唱音樂,從《紙牌屋》到《黑男爵》,法國著名學者雷吉斯·德布雷以詼諧幽默的方式,把我們的日常瑣事與人類漫長的歷史聯系起來,揭示了美國文明對歐洲文化的滲透,悲哀地告訴大家“我們是怎么成為美國人的”。但古希臘的歷史表明,如果一種文明足夠強大,哪怕丟失政權,文化也不會滅亡。
《我們怎么就成了美國人》 目錄
目錄
**章何為“文明”? / 1
第二章歐洲是何時停止創造文明的?/ 25
第三章法蘭西何時成了文化?/ 47
第四章何為新文明?/ 107
第五章為什么總是閉著眼?/ 65
第六章新羅馬帝國有何新意?/ 215
第七章為什么“沒落”討人喜歡且必不可少? / 269
致謝/ 284
《我們怎么就成了美國人》 節選
節選一 什么是傳播(communication)?通過空間輸送信息。什么是傳承(transmission)?透過時間輸送信息。傳播會嚙噬傳承,干擾傳承,*后吞噬傳承——美國精神和歐洲精神之間的關系就類似于這樣。傳播力*大的文明擁有*為杰出的傳播藝術和技術,這并不令人吃驚。令人吃驚的是,我們還未實現傳承,就提前滑向了傳播,教育領域、國家機關、博物館、教會、職業學校無不如此。熒屏嘲笑學校,記者嘲笑教授,旁門左道嘲笑正規訓練,智能手機嘲笑老祖父。近一個世紀以來,我們使用的傳播機器從何而來?來自一個將整個國度當作一個巨型實驗室的國家,它發明了這些傳播機器,并且年復一年地完善它們。在這些精密的傳播機器的幫助下,空間將時間打碎后填入其縫隙中,把富于幻想的文明置于匆忙而緊迫的計時系統的規制之下:“我們時間不多,請您說得盡量簡短,因為我們還得連線其他幾位記者與評論員。”人們會為時間討價還價,卻不再測量空間的大小。2000年的人們行色匆匆,打著電話,點擊鼠標,聯上網絡,開機,關機,從一架飛機跳上另一架飛機,以秒來設置時間碼,以一刻鐘為單位安排自己的日程,有效移動區域延展到數千公里之外。1900年的農民步行去做彌撒或去市政廳,從農莊騎馬到區域首府,情況恰與前者相反:他按照季節和農作物的生長周期來計劃自己的日子,但活動空間僅限于可用腳步和公里丈量的區域。眨眼間一個世紀過去了,世界從自行車鏈條時代進入柴油發動機時代,距離對我們而言變得無關緊要,可絲毫的延遲都會讓我們覺得無法忍受。全球化的速度與去歷史化的速度同樣迅速。隨著(地面、空中以及信息技術的)網絡和高速公路的擴展,我們的年代表在縮短。機器運轉的速度勝過我們的反射弧,家庭成員間的地位因此顛倒了過來:爺爺要請稚兒來教自己如何使用某些東西,而小家伙對長輩別無所求,除了要錢去買*新的電子游戲,或在自己的游戲機上來一場電子競技(全世界有2.05億玩家,游戲里所有詞匯都是英語)。良好的傳播技術將優秀的傳承藝術遠遠地拋在后面。在優兔視頻網站使用者和千禧一代的眼里,即便在歐洲本土,美國的這項看家本領也讓歐洲的原創性不復當年。 用了什么辦法?以設備替換制度。制度在昨天和今天之間架起橋梁,而設備則把這里和那邊連接在一起。對前者而言,它的職責(家庭、教會、國家、科學院、學校、語言)是保障傳承;對后者來講,要保證的是流通。伴隨著“流動性的激增”(人員、資金、觀點、才能、就業等)的是“連續性的斷裂”(以及由此產生的身份困擾)。借助數碼技術,空間構筑起的基礎結構不斷擠壓著時間。如今,有什么跟“空間”掛不上邊?汽車、劇院、等候室……街道被歸為“步行空間”,教堂被歸為“精神空間”,游樂場所被歸為“兒童空間”,會議室被歸為“交流和談判空間”,列車被歸為“聯合辦公空間”,布勞賽良德森林被歸為“綠色空間”。我們用俄羅斯套娃的方式,巧妙地將地方嵌入國家,繼而將國家嵌入世界。至于將生命的一個階段嵌入整個生命年輪,在這方面我們做得很差。人們忘記了父母的出生日期,忘記了祖輩葬在何處(如果他們不是火化的話)。但我們的汽車儀表盤上都裝著GPS導航(很快就會換裝伽利略導航)。我們在時間里的位置模糊不清,但在空間里,誤差不超過四米。我可以清晰地確定位置,但搞不清時間的節點。“你在哪兒?”這是我們打電話時的**個問題;“你從哪兒來?”則成了不合時宜的問題。日復一日,我們心照不宣地要求屏幕為我們展示一個翻新的、無中生有的世界,否則就不斷更換頻道,而換頻道則意味著切斷延續之物。這跟市場經濟是一個道理,早上還在暴漲,到了晚上突然暴跌,其中沒有明顯的原因。 節選二 美國喜歡直角,它的城市都是正交的,道路都是筆直的,其心靈也非黑即白。它要求自己必須勾勒出清晰的界線,因此不管是在物理上還是在道德上,都有一堵堵墻。適合美國的是二元對立,而不是細膩的濃淡差異、錯綜復雜的迷宮或富有層次感的明暗變化,后者是古希臘人和歐洲人固有的東西。生活在群島上的古希臘人尤其缺乏界限感,即沒有一個清晰的分界,正如現在的歐洲缺乏一層外質2。翁貝托·埃科正是出于一種對清晰、明確的定義的渴望,從邊界(包括空間邊界、時間邊界、語法邊界、政治邊界四個方面)的觀點出發,準確地定位了拉丁民族原型的組織核心。根據傳說,羅馬城是在一條不可侵犯的邊界線內建造起來的(羅慕路斯與雷穆斯)。而在建城千年以后,它的毀滅也源于其邊境的逐步消失。埃科寫道:“當那一天來臨,當清晰的邊界概念不再,當蠻族(一群游牧民族,拋棄自己原先的土地,可以在任何一塊土地上繁衍生息,仿佛那土地是自己的,同時又隨時準備遺棄這塊土地)成功地將其游牧民族視角強加于羅馬,羅馬也將就此走向末日。帝國一旦到了那個時候,其首都就可以定在任何一個地方,這也就意味著它不再擁有首都。一個沒有中心和外圍之分的帝國不再是一個帝國。羅馬是個中心,它的外圍區域由它確定,而一旦沒有了這個中心,外圍也就變得不再確定。”所謂的歐盟的子民還在尋找阿里阿德涅之線和輪廓,似乎也遭受著類似的不確定性的困擾。 羅馬與美國這一對帝國*讓人震驚的是,它們擁有一臺擁抱機器,即一座熔爐。這正是希臘人所極度欠缺的。塔西佗對此看得十分清楚:“斯巴達和雅典雖然善戰,*終卻萬劫不復。導致它們毀滅的,除了他們固執地排斥戰敗者和外邦人之外,還有別的原因嗎?”(《編年史》,第11卷,第23—25段)在這一點上,羅馬可以為其繼任者提供經驗教訓。美國的總統必須出生在美國,而羅馬皇帝的出生地可以是高盧、西班牙或敘利亞。公元1世紀,高盧的埃杜維人獲得了進入元老院的權利。允許與別國有淵源的“橋梁公民”的存在,這是民族文化不敢做的,只有帝國文明才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于是有了高盧裔羅馬人、華裔美國人、意大利裔美國人。這是一項雙贏的舉措,建立起的是一種雙向的依賴關系。
《我們怎么就成了美國人》 作者簡介
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1940一),法國著名作家、哲學家和媒介學家,法國巴黎高等師范學院畢業,國際哲學院教學計劃負責人,法國高等信息科學和圖書館科學學校主席,20世紀60年代曾追隨切·格瓦拉,2011年被選為龔古爾學院成員,著有《知識分子與權力》《新權力》《歐洲幽靈》《燃燒的雪》等各類作品近百部,1977年獲菲米娜獎,2019年獲法蘭西學院文學大獎。
- >
隨園食單
- >
龍榆生:詞曲概論/大家小書
- >
月亮與六便士
- >
推拿
- >
中國歷史的瞬間
- >
巴金-再思錄
- >
詩經-先民的歌唱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歷史與人類學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