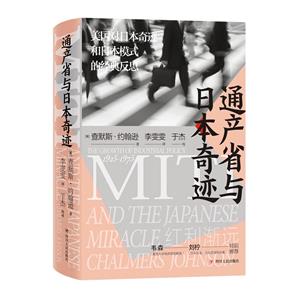-
>
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惡德,公眾的利益
-
>
世界貿易戰簡史
-
>
日本的凱恩斯:高橋是清傳:從足輕到藏相
-
>
近代天津工業與企業制度
-
>
貨幣之語
-
>
眉山金融論劍
-
>
圖解資本論
通產省與日本奇跡/日本奇跡系列 版權信息
- ISBN:9787220119736
- 條形碼:9787220119736 ; 978-7-220-11973-6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通產省與日本奇跡/日本奇跡系列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政治經濟學者和經濟政策制定者1、到20世紀70年代末,日本用占地表0.3%的國土面積、近3%的世界人口,創造出幾乎占整個世界10%的經濟活動。 復盤日本經濟發展路徑,思索中國經濟發展走向。 2、不了解通產省的功績,就難以理解日本的經濟奇跡: 需求的擴張、傲人的生產率、相對融洽的勞資關系、*高的儲蓄率……探索日本戰后經濟奇跡背后的原因,本書獨辟蹊徑,將經濟騰飛的奇跡歸功于制訂和執行獨*產業政策的通產省。 3、回顧二戰后美日關系歷史記錄的*佳著作之一: 從1925—1975年,作者循歷史脈絡,整理大量史實與數據,執著研究,還原戰后日本在國家發展問題上的爭論和選擇,并總結出日本模式的四大要素。 4、經典作品重譯: 本書是日本經濟類經典著作,是美國對日本奇跡和日本模式的經典反思。該書出版后即風**世界,激發并引領了美國國內和歐亞經濟體對日本模式的研究,此版為重新引進翻譯版本。 5、專家與媒體推薦: (1)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韋森、日本社會文化資深研究者劉檸特別推薦: “此書對于調整我們的認識坐標,平衡日本觀、世界觀,及拓寬以日本為他者反求諸己的視界,有莫大助益。” (2)《日本時報》推薦: “《通產省與日本奇跡》時下仍值得一讀,不僅因為作者的觀點,更因為他勤奮執著的研究。本書仍然是回顧戰后美日關系(包括軍事和經濟層面)歷史記錄的*佳著作之一。”
通產省與日本奇跡/日本奇跡系列 內容簡介
本書是作者查默斯·約翰遜從日本國內體制和其核心決策機構——通產省的沿革及作用的角度分析的關于日本戰后經濟騰飛的“奇跡”。本書循歷史進程,以實施產業政策的政府部門建立的1925年為起點,至1975年結束,通過通產省的沿革史及其間產業政策的討論和博弈過程,闡明了該部門戰前、戰后在人事、組織上的直接連續性,*終揭示出日本模式的四個要素:精干的公職隊伍、保障公職隊伍合法高效行政的政治制度、完善靠近市場經濟規律的國家干預手法、具備像通產省那樣的領航機構。
通產省與日本奇跡/日本奇跡系列 目錄
譯者序:紅利漸遠
前言
**章 日本的“奇跡”
第二章 經濟官僚
第三章 產業政策的興起
第四章 經濟參謀本部
第五章 從軍需省到通產省
第六章 高成長職能機構
第七章 行政指導
第八章 國際化
第九章 日本模式?
附錄
注釋
參考書目
通產省與日本奇跡/日本奇跡系列 節選
日本的“奇跡” 日本人普遍認為,“奇跡”一詞首次出現是在1962年。倫敦的《經濟學人》雜志在1962年9月1日和8日分兩期刊登了一篇題為《正視日本》(Consider Japan)的長文。后來,這篇長文迅速以《驚人的日本》(Odorokubeki Nihon)之名翻譯成日文并在東京出版成冊。即便到了這個時候,大多數日本人也并不相信他們當時造就的經濟增長率——日本史無前例的增長率,日本的權威人士和經濟學家甚至發文提醒這種繁榮會如何消逝、經濟衰退即將到來、政府政策存在不合理之處。不過,日本人關注的是不負責任的預算、“超額信貸”和巨大的國內需求;而《經濟學人》著眼的卻是需求的擴張、傲人的生產率、相對融洽的勞資關系,以及超高的儲蓄率。就這樣,日本國內外對戰后日本經濟的褒揚,對所謂“奇跡”背后原因的探索拉開了序幕。 首先是奇跡本身的一些具象。表1-1羅列了1926—1978年,也就是本書研究覆蓋的整個期間的各項工業生產指數,并將1975年的數值設定為基數100。該表顯示了幾個有趣的情況:奇跡實際上直到1962年才開始,且當時的產量僅為1975年的三分之一。所謂日本驚人的經濟力量有一半要等到1966年以后才能顯現出來。該表也清楚表明,1954年、1965年和1974年的經濟“衰退”倒逼日本政府轉向新的乃至更有創造性的經濟舉措。這體現了日本經濟從上述時期的逆境中恢復,甚至變得更強大的能力。該表也是經濟結構調整的記錄:礦業因煤炭為石油讓道而衰落;重心由紡織業轉向機械制造業和金屬制品業,日本人將這種部門遷移稱為“重化工業化”。 如果我們將基數稍作變動——比方說,將1951—1953年的數值設定為100,那么1934—1936年的國民生產總值指數就成了90,1961—1963年為248,1971-1973年為664;1934—1936年的制造業生產指數為87,1961—1963年為400,1971—1973年為1350。整個戰后期,即1946—1976年,日本經濟增長了54倍。當本書研究的期間行將結束時,日本的經濟活動幾乎占到了整個世界的10%,但其國土面積僅相當于地表的0.3%,并維持著近3%的世界人口。無論世人是否愿意將這一成就稱作“奇跡”,它都應當是值得探究的發展案例。 在我之前,已有許多學者在這些領域進行了探索,對他們的成果進行綜述是引入本書研究和我本人具體觀點的必要先導。“奇跡”一詞的頻繁使用表明,解釋日本經濟增長的原因并非易事——尤其這種增長還會在一個又一個短暫的有利條件耗盡或消失之后反復出現;“奇跡”一詞并不能單拿出來或僅用來指代始于1955年的高速增長。早在1937年,當時還很年輕的有澤廣巳教授(Arisawa Hiromi,1896年生)——任何羅列戰后二三十位產業政策主要制定人的名單必有其名,就曾用“日本奇跡”的提法來描述日本工業產值在1931—1934年間高達81.5%的增長率。今天,我們已經明白這一奇跡為什么會發生:那是時任大藏相高橋是清(Takahashi Korekiyo)實行通貨再膨脹的赤字財政政策的結果。因為高橋后來力圖中止這一由他開啟的赤字政策,一眾年輕軍官于1936年2月26日清晨刺殺了時年81歲的高橋。 然而,這一較早出現的奇跡仍令學者們心存疑惑,因為誠如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所說,日本如何做到“早在凱恩斯主義未成氣候的1932年便出臺凱恩斯政策”是個“謎團”。有些日本人并沒有過分糾結于這個謎團,他們索性把高橋是清稱作“日本的凱恩斯”。就像我希望在本書中明確的,這種類比并不恰當。日本20世紀30年代的國家干預比凱恩斯主義走得更遠,有澤廣巳及其政府同事在他們成長的關鍵期所積累的經驗教訓,與奠定今時今日西方公認的那些主流財政政策截然不同。 金德爾伯格所謂的“謎團”確實引起了現今研究日本經濟“奇跡”的主要流派——映射派的注意。這些學者將西方(主要是英美)經濟行為的概念、問題和標準映射到日本的案例上進行研究。無論該流派在各國從事的此類研究有何價值,它們都無須我們長久駐足。此類研究的宗旨與其說是解釋日本奇跡產生的原因(雖然也有可能提煉出一些日本政治經濟原理),不如說是參照日本的成就,找到本國的差距,或是就日本增長對世界其他地區可能產生的影響發出警告。甚至始見于1962年《經濟學人》雜志的那本精彩絕倫的小書,也要換成《瞧瞧日本在干什么,再想想英國》的題名才更合適。因為怎么看,那都是作者寫作的真正目的。此后陸續出現的類似著作包括:拉爾夫·休因斯(Ralph Hewins)的《日本奇跡風云人物》(The Japanese Miracle,1967年)、P.B.斯通(P.B.Stone)的《日本騰飛:經濟奇跡紀實》(Japan Surges Ahead:The Story of an Economic Miracle,1969年)、羅貝爾·吉蘭(Robert Guillain)的《日本的挑戰》(The Japanese Challenge,1970年)、赫爾曼·卡恩(Herman Kahn)的《崛起的超級大國日本》(The Emerging Japanese Superstate,1970年)和霍坎·赫德貝里(Hakan Hedberg)的《日本的復仇》(Japanese Revenge,1972年)。同類題材著作中*出色的一本,可能要屬傅高義(Ezra Vogel)的《日本**:帶給美國人的教訓》(Japan as Number One:Lessons for Americans,1979年),因為它明確提點了美國可以從日本學到什么,而不是在分析日本經濟驚人增長的原因。本書研究無意效仿上述早期著作——主張在日本以外的國家采取日本式制度,但確實有志于極盡翔實地展示日本經濟領域中一些主要制度的復雜性,好讓有心照搬這些制度的人意識到,他們將因此得到日本體制的哪些回饋——計劃中的、計劃外的,甚至不愿接受的。 還有一種對日本奇跡大相徑庭的解釋,來自社會經濟學派,我有時稱之為“奇跡”研究中的“非政治”派。這個門庭廣大的學派包括四種分析類型,它們彼此交叉,但倘使研究目的既定,仍可明確加以區分,盡管它們鮮少以單一形式出現。它們是:一般由人文學者,特別是人類學家推崇的“國民性—基本價值觀—共識”型分析;主要由經濟學家進行的“否定奇跡”型分析;由研究勞資關系、儲蓄率、公司管理、銀行制度、福利制度、綜合商社、現代日本其他制度和機構的學者所倡導的“獨特結構特征”型分析;各種形式的“搭便車”型分析。換言之,這種分析強調那些促進日本經濟在戰后高速增長經濟高速增長在日文中對應的表述為“高度經濟成長”,簡稱“高度成長”或“高成長”,為行文簡潔故,本書亦有使用“高成長”一詞來表達“經濟高速增長”之意。——譯者注的實際卻短暫的有利條件。在概括這些分析類型的優劣之前,我想說,在一定程度上,我贊同所有這些類型的分析。我的興趣既非爭論它們所揭示的事實,也非質疑它們與日本奇跡之間的關聯。不過,我相信,有一點可以得到證實:這些分析中有許多應當還原為更加基本的分析類型,特別是對國家政策影響的分析;衡量它們的標準也應當與以往不同,從而增加政府及其產業政策的衡量比重。 國民性分析認為,經濟奇跡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日本人獨有的、植根于文化的相互協作能力。這種能力體現在很多方面:相對其他多民族國家較低的犯罪率、個人服從集體、強烈的忠于集體意識和愛國熱情,*后卻同樣重要的是經濟表現。日本文化對經濟生活*重要的貢獻,據說是日本人著名的“共識”,即政府、執政黨、產業領袖和民眾之間,對整個社會的首要經濟目標,以及達到這些目標須采用的手段,做到了真正的觀點一致。用以指涉日本人這種文化能力的詞語應運而生:“動態共識”、“自發集體主義”、“天生集體主義”、“沒有蜘蛛的蜘蛛網”以及“日本公司”。 至于上述分析的價值,我的基本態度是,它過于籠統,存在阻斷而非推進審慎研究的傾向。共識和集體主義對日本的經濟增長固然重要,但與其說它們源自日本人的基本價值觀,不如說它們取決于魯思·貝內迪克特(Ruth Benedict)曾經所謂日本的處境因素:發展起步晚、資源匱乏、亟待發展貿易、國際收支制約等。將某種“特有的協作能力”臆斷為日本人的文化特性會導致探究的過程偏離當日本人協作時(在本書研究涉及的近一半時間里,他們并未協作)他們為什么會協作的問題,同時還會忽略這種協作系日本政府和其他組織精心設計和驅策的可能性——情況有時確實如此。戴維·泰特斯(David Titus)關于日本戰前利用天皇制將社會矛盾“私人化”而非“社會化”的研究,可以算是看待“共識”問題的新穎視角。 本書接下來討論的許多實例將闡明,政府如何有意識地引導了其委托人間的協作,而且效果比太平洋戰爭期間它試圖控制后者要好得多。總之,日本人的基本價值觀可能確實不同于西方世界,但這需要研究而不是假設,而且根據基本價值觀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應當另外分析,即專門研究那些用側重經濟分析的方式無法解釋的行為。實際上,從文化角度解釋日本經濟奇跡在幾年前更為流行,因為那時只有日本出現了奇跡。如今韓國、中國臺灣和香港,以及新加坡,甚至東亞以外的一些國家或地區也有了重演這種奇跡或與之一較高下之勢,文化層面解釋受到的關注大不如前。 典型的“否定奇跡”型分析其實并非主張日本經濟沒有成就可言,但它們暗示,這些成就還到不了奇跡的程度,不過是市場力量作用的正常產物。這些理論源于對日本經濟增長的專業經濟分析,它們因此自認無懈可擊。但是,這類分析往往也會得出整合了其提出者不曾研究卻無論如何想要從其模型中剔除的相關問題的延伸結論。休·帕特里克(Hugh Patrick)直言,“我派觀點認為,日本的經濟成就應主要歸功于個人和私營企業為把握完全自由的商品和勞務市場所提供的機會而采取的行動和努力。雖然政府助力經濟增長并確實為之創造了環境,但其作用往往被夸大”。不過,他也承認這種觀點有解釋不通的地方:“令人困惑的是,在對日本戰后經濟成就進行宏觀分析時,從勞動力和資本總體投入的增長及二者更有效的配置來看,產出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量中各有40%多和50%無法解釋。”如果能夠顯示,是政府的產業政策改變了某些經濟戰略性行業的投資率(比如石化或汽車工業的產量提升和成功營銷),那么,也許我們可以說,政府的作用并沒有被夸大。我相信這一點可以得到證明,本書后面自有分解。 休·帕特里克所謂日本政府僅僅是為經濟增長提供了環境的觀點自然也會遭到眾多日本人質疑。通產省前次官佐橋滋(Sahashi Shigeru)聲稱政府對經濟負有全面責任,他斷言:“認為政府只用給各個行業提供有利環境而無須為后者指明方向,是徹頭徹尾的自我中心(商人)論調。”是有發生過行業或企業抵制政府指示的情形——戰后政治中*敏感的事件,但這些過去不曾、現在也沒有頻繁發生,并不能成為常態。 從純經濟角度討論日本經濟,問題似乎出在其假設而非分析。例如,假設作為發展型國家的日本和作為監管型國家的美國是一碼事。菲利普·特雷齊斯(Philip Trezise)就認為:“日本政治本質上與西方民主國家沒什么不同。”17不過,二者在國家財政預算過程方面存在差異。在日本,預算的撥款先于批準,“國會自1955年以來從未修改過政府提出的預算,唯一的例外是1972年,政府行為失當加上在野黨聯合抵制導致國防開支小幅削減”。在那之前,國會批準政府預算的程序顯然只是走過場。 美日之間另一處不同應該是在銀行制度方面。戰前,日本所有公司的自有資本率都在66%左右,與美國目前的52%尚有可比性。但到了1972年,日本的自有資本率卻低至16%左右,且整個戰后時期都保持著這種狀態。大企業通過向城市銀行申請貸款取得資金,后者因此過度放貸,于是完全依賴中央銀行——日本銀行(簡稱“日銀”)的信用擔保,而日銀自身在經歷其“失去的”20世紀50年代的慘烈一搏后,實際已淪為大藏省的附庸。于是,政府便與“戰略性產業”(常規表述,使用得很普遍,但并非軍事意義上的)的命運有了直接、緊密的關系,且其影響無論在形式上還是法律上,似乎都要遠遠超過其他市場經濟國家內的同類關系。1974年,通產省公開引入“計劃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的概念,力圖對自己過去20年(在此之前為完善這種體制而歷經嘗試和失敗的20年)的所作所為進行命名和總結,但這樣做不光光是為了給自己樹碑立傳。19計劃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無疑包含一些與“其他民主制度”的不同之處,其中之一就是對經濟奇跡本身的重視和扶植。 研究日本經濟的“否定奇跡”派學者亦認同日本經濟確有增長,但堅稱這是資本、勞動力、資源和市場諸要素能夠在彼此間自由發生作用且不受任何真正意義上限制的結果。他們否定日本人在探討和管理日本經濟過程中不斷創造和應用的一切概念,比如“產業結構”“過度競爭”“投資協調”和“公私合作”,理由是違背經濟邏輯,因而無法成立。*要命的是,他們的解釋通過預設政府干預不會引起任何不同并以此作為原則,巧妙地避開了對這種干預實際影響的分析。結果就如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所言,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奇跡般’崛起為一流經濟大國被日本和外國作家極盡渲染,卻鮮有著作對個中曲折或何人主導做出可圈可點的解釋”20。本書的目的便是為這些問題尋找答案。 流行的第三種日本奇跡分析類型,重點強調日本獨特制度發揮的作用。它是我目前為止歸納出來的四種類型中*重要的一種,也是日本國內外研究*為深入的一種。用*簡單的話來說,這種類型的分析主張,日本通過被戰后日本雇主們習慣喚作自身“三大神器”的“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nenkō)工資制和企業工會制,獲得了特殊經濟優勢21。比如,通產省的天谷直弘(Amaya Naohiro)就稱這三種制度是他所謂日本團扇(uchiwa)喻所有人及其活動均系日本這個大家庭的組成部分,經濟上相應采取家庭式管理。——譯者注經濟制度的精髓。無獨有偶,1970年,通產省前次官大滋彌嘉久(jimi Yoshihisa)也作“大慈彌嘉久”。——譯者注在向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簡稱“經合組織”)下屬產業委員會報告時,曾提到幫助日本實現高成長的各種典型日本現象,他口中的現象也是指上面的“三大神器”。22由此推論:正是因為這些制度,日本獲得了更多勞動投入,降低了罷工風險,不僅能夠較為輕松地開展技術革新,在質量管理上也勝人一籌,總體而言,該國推出適銷商品種類之多、速度之快均非國際上的其他競爭者所能及。 這一論斷無疑是正確的,但卻從未得到清楚明白的闡述,至多是一種簡單的提法。另外尚有幾點需要指出:首先,“三大神器”并非“獨特制度”的全部,當然也不是*關鍵的。其他種種包括個人儲蓄制度、分配制度、政府高層官員退休后轉入私營企業擔任領導職務的“下凡”(amakudari)制度、產業集團化(經聯會,抑或各行業通過企業聯合形成的寡頭壟斷組織)、“二元經濟結構”(被克拉克[Clark]很務實地稱為“產業等級”制度23)及其催生的復雜分包結構、稅收制度、股東對公司微乎其微的影響力、一百多個“公共政策公司”(幾種不同形式的公營公司),以及許是所有制度中*重要的——由政府控制的金融機構,尤其是日本開發銀行,還有“第二預算”,或者說投資預算(財政投融資制度)24。 本書沒必要對上述制度一一闡述,因為即使是日本問題的新手研究者也十分熟悉其中大多數制度,剩下的那些將在本書后面的章節詳細分析,因為它們屬于政府影響和指導國民經濟基本工具的組成部分。需要強調的是,這些制度構成了一個體系——一個任何個人或機構都不曾設想過的體系,一個作為日本發展起步晚的即時反應或計劃外結果及政府促進增長的政策而與時俱進的體系。從一個完整體系的角度看,它們構成了推動經濟增長的一整套制度(天谷直弘喻之為“國民生產總值發動機”),但如果按照常見的做法,將它們單個拿出來看,它們卻毫無道理可言。25人們對獨特制度理論所持的主要保留態度自然也是其深度不夠,該理論于是淪為一種片面解釋。
通產省與日本奇跡/日本奇跡系列 作者簡介
查默斯·約翰遜(1931.8–2010.11),美國政治學家,生前為美國著名的中國和日本問題專家。一生著作頗豐,《通產省與日本奇跡》是其影響力*大的一本,該書出版后即風*全世界,激發并引領了美國國內和歐亞經濟體對日本模式的研究,同時也開創了一個新的學術研究方向。 李雯雯,職業律師,譯有《抗戰外援》《日本經濟奇跡的終結》。 于杰,多年從事銀行和投資業務,策劃并譯校“時運變遷”和“日本奇跡”系列叢書。目前還兼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微信公眾號:時運變遷。
- >
龍榆生:詞曲概論/大家小書
- >
唐代進士錄
- >
姑媽的寶刀
- >
月亮虎
- >
中國歷史的瞬間
- >
山海經
- >
羅曼·羅蘭讀書隨筆-精裝
- >
經典常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