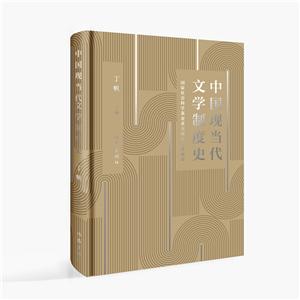-
>
百年孤獨(dú)(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制度史 版權(quán)信息
- ISBN:9787521209143
- 條形碼:9787521209143 ; 978-7-5212-0914-3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制度史 本書特色
文學(xué)與制度的糾纏,以及制度對文學(xué)的干預(yù)與滲透比我們想象的要深刻而復(fù)雜得多。從制度的角度研究文學(xué)是一個相對新穎的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尚未得到學(xué)術(shù)界的充分重視,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研究都為數(shù)不多。 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在其發(fā)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身的文學(xué)制度,作家的創(chuàng)作、文學(xué)文本、讀者的閱讀與文學(xué)的生產(chǎn)、流通、消費(fèi)發(fā)生著緊密聯(lián)系,作家的職業(yè)性和社團(tuán)歸屬,作品傳播對報刊和出版以及文學(xué)批評、文學(xué)論爭、文學(xué)審查和文學(xué)獎勵的參與等,共同形成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強(qiáng)大的制度力量。文學(xué)制度是文學(xué)與社會關(guān)系的表征形式,厘清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百年發(fā)展過程中這些紛繁復(fù)雜、犬牙交錯的文學(xué)制度,是一個繁雜而龐大的系統(tǒng)工程。 本書把制度引入文學(xué)研究,將其作為一個重要視域,著重從文學(xué)制度與文學(xué)、文學(xué)制度與文學(xué)史寫作、文學(xué)制度與文學(xué)理論的建構(gòu)、文學(xué)制度與具體的文學(xué)現(xiàn)象等方面對我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進(jìn)行系統(tǒng)的研究,拓展了該領(lǐng)域的研究空間,形成了新的文學(xué)研究格局,客觀上也把文學(xué)社會學(xué)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層次。 ——孟繁華 文學(xué)制度研究可以稱之為文學(xué)的過程研究和文學(xué)的生態(tài)研究。將文學(xué)制度和文學(xué)理論建構(gòu)、文學(xué)史研究與寫作聯(lián)系起來,文學(xué)的體制問題無論是對中國文論建設(shè),還是中國文學(xué)史研究都該成為一個有待深入探討的學(xué)術(shù)話題。目前對文學(xué)的社會背景、文學(xué)的出版與傳播、文學(xué)的社團(tuán)與流派、文學(xué)教育與文學(xué)創(chuàng)作之間復(fù)雜關(guān)系的研究,已經(jīng)涉及了文學(xué)的制度問題,卻鮮有專門論著上升到文學(xué)制度的理論高度,且缺乏制度研究的“自覺意識”。 《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制度史》一書,研究對象的時間上限劃定在清末鴉片戰(zhàn)爭以后現(xiàn)代文學(xué)制度的萌芽期,下至21世紀(jì),以文學(xué)制度研究為方法和切入角度,全方位梳理、分析和考察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系統(tǒng)論述了百年中國新文學(xué)的建制化歷史,不僅有利于闡明百年新文學(xué)歷程中的若干疑難問題,更可以為今后文學(xué)發(fā)展提供可資借鑒的經(jīng)驗(yàn),有助于相關(guān)學(xué)術(shù)研究的推進(jìn)和我國當(dāng)代文學(xué)的繁榮發(fā)展,具有深遠(yuǎn)的作用和影響。 ——陳曉明
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制度史 內(nèi)容簡介
《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制度史》以清末鴉片戰(zhàn)爭以后現(xiàn)代文學(xué)制度的萌芽期為研究起始點(diǎn),下限到21世紀(jì),在依托大量相關(guān)史料的基礎(chǔ)上,建構(gòu)了一個縱向的史的體系和橫向的空間比較體系,重點(diǎn)關(guān)注“有形文學(xué)制度”和“無形文學(xué)制度”如何建構(gòu)、如何支撐和支配著文學(xué)史的發(fā)展走向等問題,對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制度進(jìn)行理論的審察和歷史的分析,在宏觀的理論和微觀的歷史細(xì)節(jié)之間把握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制度的變遷,具有突破性和創(chuàng)新性。文學(xué)現(xiàn)象中的制度因素如何產(chǎn)生作用及影響于文學(xué)的實(shí)質(zhì)性演變?這是本書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也是文學(xué)研究包括文學(xué)制度研究的側(cè)重點(diǎn)。作者們并非直接進(jìn)行廣義的社會學(xué)、政治學(xué)范疇中的制度研究,而是尤其注重對制度實(shí)踐的考察,即文學(xué)遭遇和面對的制度性操作問題,而非一般理論或宏觀意義上的制度問題。這一研究思路及觀點(diǎn)對于當(dāng)代文學(xué)制度建設(shè)及文化強(qiáng)國的戰(zhàn)略都具有較大的借鑒價值,使本書具有較為重大的現(xiàn)實(shí)意義。
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制度史 目錄
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制度史 節(jié)選
**編晚清及“五四”:現(xiàn)代文學(xué)制度之創(chuàng)立 **章清末:現(xiàn)代文學(xué)制度萌芽期 清末拉開了中國社會轉(zhuǎn)型的序幕,文學(xué)在其中扮演了至關(guān)重要的角色,當(dāng)然,就現(xiàn)代文學(xué)制度而言,這一時期還只是新的文學(xué)制度的萌芽期。現(xiàn)代文學(xué)制度之所以于此時浮出水面,一方面得益于文學(xué)觀念的轉(zhuǎn)型,另一方面,更在于相關(guān)結(jié)構(gòu)性要素漸趨成熟并建構(gòu)起了一個相對完善的文學(xué)、文化運(yùn)作系統(tǒng)。就前者而言,王國維借鑒西方學(xué)術(shù)、哲學(xué)思想而產(chǎn)生的對文學(xué)的新的認(rèn)知頗為關(guān)鍵,特別是他慧眼獨(dú)具地提出了“古雅”說,為現(xiàn)代文學(xué)制度的建構(gòu)奠定了理論基礎(chǔ);就后者而言,清末相關(guān)出版法規(guī)的陸續(xù)出臺、“印刷資本主義”的漸趨發(fā)達(dá),以及因?yàn)樾率缴鐣止ぴ斐傻奈娜松罘绞健⑽膶W(xué)團(tuán)體組織方式的變化,則以合力緩緩造就了現(xiàn)代文學(xué)制度的雛形。 **節(jié)文學(xué)獨(dú)立性地位的確認(rèn) 現(xiàn)代文學(xué)制度是在晚清文學(xué)觀念變革的基礎(chǔ)上逐漸發(fā)展成形的。盤點(diǎn)清末的文學(xué)主張,確已出現(xiàn)許多區(qū)別于傳統(tǒng)的新觀念,不過大都只言片語,如魯迅曾很早指出文學(xué)的根本特征在于“增人感”,吉光片羽雖然讓人耳目一新,但應(yīng)該說,并沒有撼動古典美學(xué)的根基,更無從談到重建。從這個意義上講,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以系統(tǒng)的眼光、嚴(yán)密的邏輯剖析文學(xué)的性質(zhì)、功能,摧陷廓清,具有突破性的歷史價值。本節(jié)即以王國維與其《紅樓夢評論》為中心,系統(tǒng)陳述文學(xué)的性質(zhì)、功能、對象等相關(guān)內(nèi)容,適當(dāng)延及后來的白話文學(xué)實(shí)踐,討論王國維的文學(xué)觀對后來逐步成形的現(xiàn)代文學(xué)制度提出的要求與預(yù)設(shè)的限制、提供的理論資源等問題。 一、 文學(xué)的性質(zhì)對現(xiàn)代文學(xué)制度的限制 從系統(tǒng)的文學(xué)批評的角度看,文學(xué)在中國文化史上就一直缺乏應(yīng)有的獨(dú)立地位。從《典論·論文》所謂“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的名利論,到《文心雕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shè)教”的道統(tǒng)論,再到韓愈的“文以明道”和周敦頤的“文以載道”的赤裸裸的工具論,占主流的一直是這種功利的、附庸的、實(shí)用的文學(xué)觀,雖偶有屈原、陶淵明、杜甫、蘇軾這樣的“大詩人”出現(xiàn),但“純粹美術(shù)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無人為之昭雪”,難怪王國維有這樣的感慨,“美術(shù)之無獨(dú)立之價值也久矣”。王國維采用叔本華哲學(xué)、美學(xué)思想觀照,以系統(tǒng)的眼光、嚴(yán)密的邏輯研究《紅樓夢》,直接肯定了其文學(xué)的審美本質(zhì)。王氏認(rèn)為,“紅樓夢之精神”“在描寫人生之苦痛與其解脫之道,而使吾儕馮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離此生活之欲之爭斗,而得其暫時之平和”。人生于世,感到自身的不足、缺憾而有各種欲望,又為保存自己與種姓計,欲望無止境而甚難一一滿足,故生活的性質(zhì)是痛苦的。為求解脫,人類知識逐漸發(fā)達(dá),然而知識亦不過滿足部分愿望而已,人的欲望則水漲船高,永難饜足。因此,能夠使人暫時忘卻痛苦、心態(tài)得以平復(fù)的“美術(shù)”,必然是與人沒有利害關(guān)系的,“可愛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所謂“美術(shù)之為物,欲者不觀,觀者不欲”是也,當(dāng)此之際,人實(shí)際上就處于一種精神上的解放、自由、自在的境況。 文學(xué)之美有兩種表現(xiàn)形態(tài):一曰優(yōu)美,一曰壯美。王國維認(rèn)為:“今有一物,令人忘利害之關(guān)系,而玩之而不厭者,謂之曰優(yōu)美之感情。若其物直接不利于吾人之意志,而意志為之破裂,唯由知識冥想其理念者,謂之曰壯美之感情。然此二者之感吾人也,因人而不同;其知力彌高,其感之也彌深。”優(yōu)美、壯美作為相對的兩個美學(xué)范疇,其實(shí)有相對應(yīng)的兩種人生狀態(tài),這就是尼采所謂日神精神與酒神精神,或洪堡所謂散文人生與詩性人生。這兩種人生狀態(tài)以及相應(yīng)的兩種美學(xué)形態(tài),本無高下之別,但在晚清積弱積貧因而窮則思變的氛圍中,后者得到了較多肯定,其中的代表就是魯迅的《摩羅詩力說》。《摩羅詩力說》晚《紅樓夢評論》兩年出,魯迅雖與王國維在文學(xué)本質(zhì)觀念方面一致,但特重“偉美之聲”,“震吾人之耳鼓者”。當(dāng)然,兩者更重大的差別,在于王國維較為偏于形而上,魯迅則比較傾向于在形而下的意義上與王國維做出同樣的判斷。這也可以窺見魯迅后來的創(chuàng)作何以在總體上親近“為人生”的文學(xué)(當(dāng)然還有其他因素)。五四時期的“人的文學(xué)”,在胡適將“人的文學(xué)”闡釋為“主張‘人情以內(nèi),人力以內(nèi)’的‘人的道德’的文學(xué)”時,有的創(chuàng)作“情感水平滑到了偽參照系之下;在這個意義上,這種文學(xué)更類似于意識形態(tài)語言的和更日常形式的運(yùn)行”,其實(shí)偏離了《紅樓夢評論》確立的文學(xué)審美立場,而他們和王國維之間其實(shí)也形成了一種斷裂。這或如王國維所論,“個人之汲汲于爭存者,決無文學(xué)家之資格”,而這種在理論與創(chuàng)作兩方面都重“人”輕“文”的狀況白話文學(xué)興起以后,啟蒙已經(jīng)是一個強(qiáng)勢“傳統(tǒng)”。時人乃至局中人對此也有清醒的認(rèn)識。例如周作人在《小河·詩序》中對他個人所作詩歌的自我評判:“或者算不得詩,也未可知;但這是沒有什么關(guān)系。”,要到二十世紀(jì)三十年代及以后的一批獨(dú)立作家(如沈從文、老舍、張愛玲等)那里,才有較大改觀。他們的生活和寫作方式,使自由寫作成為可能,當(dāng)然也就更能體現(xiàn)、表達(dá)審美世界中的自由況味。 客觀地說,“五四”及以后的眾多作品在美學(xué)境界上大概接近王國維所謂“古雅”。古雅“存于藝術(shù)而不存于自然”,指的是那些“決非真正之美術(shù)品,而又非利用品者。又其制作之人,決非必為天才,而吾人之視之也,若與天才所制作之美術(shù)無異者”。相比于優(yōu)美、壯美的先天性、普遍性和必然性,古雅是后天的、經(jīng)驗(yàn)的、偶然的,所以對它的判斷取決于時代、環(huán)境、人種等因素。現(xiàn)代文學(xué)中絕大多數(shù)的作家作品都屬于這一層次,雖然,也自有其作用,因?yàn)楣叛烹m然從美學(xué)上看不及優(yōu)美、壯美,“然自其教育眾庶之效言之,則雖謂其范圍較大成效較著可也”。應(yīng)該強(qiáng)調(diào),這里的“教育眾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啟蒙,而是普及美育。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現(xiàn)代文學(xué)中真正的“美術(shù)者”也須有古雅之修為。這從現(xiàn)象上看,“書有陪襯之篇,篇有陪襯之章,章有陪襯之句”是無法避免的,而“此等神興枯涸之處,非以古雅彌縫之不可”,所以自然要借修養(yǎng)之功力。在這一方面,魯迅表現(xiàn)得甚是顯著——顯然,這么說不會貶低他作為“大詩人”的天才。所謂“文學(xué)者,不外知識與情感交代之結(jié)果而已。茍無敏銳之知識與深邃之感情者,不足與于文學(xué)之事”,對純粹知識的敏銳洞察和對微妙感情的深邃體察,正是魯迅表現(xiàn)于外的*重要的兩個特點(diǎn)。 由上面的論述可知,真正的文學(xué)是天才的事業(yè),其實(shí)與具體的文學(xué)制度無關(guān),而談文學(xué)制度,所關(guān)涉的美學(xué)層次應(yīng)該主要限于所謂古雅,即中智之人通過內(nèi)在的修為并倚賴外在的條件所能達(dá)到的境界。文學(xué)制度研究所能做到的,不過是對文學(xué)常態(tài)的一種系統(tǒng)化外在分析,這是文學(xué)的本質(zhì)對此一研究的限制,但反過去立論,其實(shí)也不難推想出它對文學(xué)制度的類似于“消極自由”的要求:既然真正偉大的文學(xué)如羚羊掛角不可尋蹤,那么進(jìn)行制度設(shè)計——這主要是指“看得見的腳”對文學(xué)的規(guī)訓(xùn)、管制與借由“看不見的手”所自然形成的對制度系統(tǒng)之缺陷的調(diào)整等主觀因素——時,就應(yīng)該盡量寬松,使之具有相當(dāng)?shù)膹椥浴_@樣,起碼可以促成較多的能夠提升民族審美能力、培養(yǎng)國人愛美習(xí)性的古雅之作出現(xiàn),也許就可以間接催生文學(xué)大家。 二、 文學(xué)的功能為現(xiàn)代文學(xué)制度提供的理論資源 《紅樓夢評論》本諸叔本華美學(xué)理論,認(rèn)為悲劇實(shí)有三種:“**種之悲劇,由極惡之人,極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構(gòu)之者。第二種,由于盲目的運(yùn)命者。第三種之悲劇,由于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guān)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質(zhì)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種悲劇,其感人賢于前二者遠(yuǎn)甚。”《紅樓夢》中寶黛之愛情悲劇,乃“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所致,所以稱得上“悲劇中之悲劇”。人生悲劇要么己身經(jīng)歷,要么旁觀而來,這二者恰恰就是王國維所認(rèn)為的從生活的痛苦中解脫出來的兩種途徑:其一為“觀他人之苦痛”,其二為“覺自己之苦痛”。雖然二者殊途同歸,境界卻有高下之別:后者的解脫“由于苦痛之閱歷”,屬痛定思痛后的“疲于生活之欲”所致,是被動的、“他律的”;前者的解脫則“由于苦痛之知識”,為洞察人生本質(zhì)以后的徹底決絕,是主動的、“自律的”。在《紅樓夢》中,惜春、紫鵑的解脫出于“覺自己之苦痛”,是神秘的超自然力量造成的宗教性質(zhì)的解脫;寶玉則出自“觀他人之苦痛”,是自然的人性導(dǎo)致的人生悲劇。
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制度史 作者簡介
丁帆,南京大學(xué)中國新文學(xué)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學(xué)資深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兼任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會會長、江蘇省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會副會長等。國務(wù)院特殊津貼專家,國家社科評委。發(fā)表文章400多篇,共500萬字,出版主編各類著作40余種。培養(yǎng)博士、碩士生共160多人。
- >
二體千字文
- >
【精裝繪本】畫給孩子的中國神話
- >
推拿
- >
新文學(xué)天穹兩巨星--魯迅與胡適/紅燭學(xué)術(shù)叢書(紅燭學(xué)術(shù)叢書)
- >
羅曼·羅蘭讀書隨筆-精裝
- >
中國歷史的瞬間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qū):歷史與人類學(xué)概述
- >
煙與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