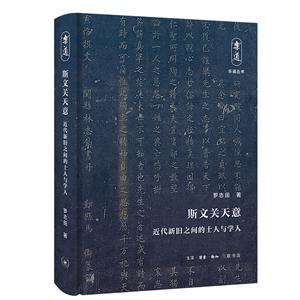-
>
清通鑒(全四冊)(精裝)
-
>
明通鑒(全三冊)(精裝)
-
>
跨太平洋的華人改良與革命 1898-1918
-
>
天有二日(簽名鈐印特裝本)
-
>
歐洲至暗時刻(1878-1923):一戰為何爆發及戰后如何重建
-
>
(精裝)奧托·馮· 俾斯麥與德意志帝國建立
-
>
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斯文關天意:近代新舊之間的士人與學人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8068897
- 條形碼:9787108068897 ; 978-7-108-06889-7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斯文關天意:近代新舊之間的士人與學人 本書特色
子貢所說的“君子”在近代逐步淡出,與斯文掃地的進程是相輔相成而共進的,的確有些“文化神州喪一身”的意味。書中的一些人不僅注意到這樣的思想和社會進程,為此而憂慮,且致力于挽狂瀾于既倒,卻又無力回天。他們那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努力,很像曾國藩所說的“苦撐”。回訪他們歷程,想想我們的社會心態怎樣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樣子,或也可以為如何成就一個更好的明天提供一些參考。
斯文關天意:近代新舊之間的士人與學人 內容簡介
本書是著名近代史學者羅志田的學術論文集。書名化用陳寅恪詩“吾儕所學關天意”,收錄的十篇論文,均以近代新舊之間的士人和學人為主題,包括張謇、梁濟、陳獨秀、林紓、胡適、陳寅恪等。 本書或可視作“借人以明史”的嘗試,即以人物為中心來貫串周圍的關系事實,以窺探時代風貌與世變潮流。所論之人,在其所處的時代及后人眼里,各自有或新或舊的標簽,實則他們身上都有新舊混雜的近代特性,也多少展現了以天下為己任的士人風貌,并揭示出過渡時代士人向學人的轉化。
斯文關天意:近代新舊之間的士人與學人 目錄
自序
近代湖南區域文化與戊戌新舊之爭
一、從邊緣走向中央的湘學
二、后湘軍時代湖南的守舊與趨新
三、近代湖南排外的實際與迷思
四、余論:官紳的互動與競爭
思想觀念與社會角色的錯位:戊戌前后湖南新舊之爭再思
一、舊中有新:王先謙與葉德輝對國情的認知
二、由新轉舊:舊派人物反戈一擊的關注所在
過渡時代的天下士:張謇與辛亥革命
一、革命乃朝廷促成
二、預作“亡后之想”
三、贊助共和與事后反省
對共和體制的失望:梁濟之死
一、有計劃的死:梁濟的憂慮和民初世風
二、社會反響:菁英忽視而民眾緬懷
他永遠是他自己——陳獨秀的人生和心路
一、發出時代的聲音
二、從國家到個人的覺悟
三、從文學到倫理的文化革命
四、從康、梁到胡、陳的時代轉折
五、走向行動的政治革命
六、一生定位
林紓的認同危機與民初的新舊之爭
一、新文人要做舊代表
二、文選派和桐城派爭奪北大
三、不許小說家代表道統
四、舊派不夠舊,新派不全新
五四到北伐期間胡適與中共的關系
一、“好政府主義”
二、胡適與中共的觀念歧異(對內)
三、胡適與中共的觀念歧異(對外)
四、中共的“聯合戰線”與胡適
五、胡適與中共“舌戰”莫斯科
六、胡適贊頌蘇俄的余波
斯文關天意:陳寅恪與1932年清華大學入學考試的對對子風波
一、語境:國難與國性
二、本事:對對子引發的詰難
三、陳寅恪的答辯及其旨趣
無名之輩改寫歷史:1932年清華大學入學考試的作文題爭議
一、大學考試成為社會性表述
二、作文題風波揭示的時代思想
斯文關天意:近代新舊之間的士人與學人 節選
一生定位 陳獨秀在南京獄中時,曾為鄉后輩汪原放寫過一張條屏,上面說:“天才貢獻于社會者甚大,而社會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緩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類進步之所以為蟻行而非龍飛。”不論這是抄自他人還是自作,都是自抒胸臆。陳氏對中國社會,一向責任心重而暢所欲言,貢獻不可謂不大;但社會對他的回報,則聲譽雖隆而“成功”實少。他在獄中書此,恐怕對所謂“社會迫害”,深有隱痛。 陳氏本人的自定位,其實也是充滿猶疑的。1922年他為科學圖書社題詞,回憶從二十多歲的少年時代起,就“為革新感情所趨使”而辦《安徽俗話報》;奮斗了二十年,除“做了幾本《新青年》,此外都無所成就”。那時他已投身實際政治,而自己可視為“成就”的,仍是文字的貢獻。但后來在獄中寫自傳時,卻說自己“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并自認其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失敗”的。這“失敗”的感覺,應與牢獄生涯無關。出獄后他仍說:“我奔走社會運動、奔走革命運動三十余年,竟未能給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擊,說起來實在慚愧而又忿怒。” 或許是“英雄不夸當年勇”,晚年的陳獨秀已幾乎不提《新青年》時代的光輝。當記者向他求證,是否如傳聞所說“今后要專做文化運動,不做政治運動了”時,他連忙否認。他承認自己的“個性不大適宜于做官,但是政治運動則每個人都應該參加”;尤其“現在的抗日運動,就是政治運動”,那是不能不參加的。這大致仍如他1918年恢復談政治時所說,關系到“國家民族根本存亡”之時,人人都不能“裝聾推啞”。但這樣一種非實際的政治,也隱約揭示出參與者自定位的尷尬。 在抗戰的艱苦時期,陳獨秀以自己不夠成功的經歷鼓舞國人說:“我半生所做的事業,似乎大半失敗了。然而我并不承認失敗,只有自己承認失敗而屈服,這才是真正的*后失敗。”永不向失敗屈服,的確是典型的陳獨秀精神。他那時特別強調,“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們幾個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夠自信有撥云霧而見青天的力量”。重要的是“不把光明當作黑暗,不把黑暗對付黑暗”;在那“黑暗營壘中,遲早都會放出一線曙光,終于照耀大地”。 所謂不把光明當作黑暗,不以黑暗對付黑暗,針對的不僅是侵略者,而是整個人類的前途。這已部分回歸到自由主義的立場,是他晚年的深刻解悟,更表現出對人性的信心。他注意到,由于“強弱”成為“判榮辱”的標準,于是“古人言性惡,今人言競爭”;這不僅是表述的轉換,更是善惡的混淆。在“舉世附和”作“人頭畜鳴”的現狀下,必須有哲人出來辨別黑暗與光明。他知道這樣做的代價,然而“忤眾非所忌”,哪怕“坷坎終其生”。陳獨秀仍寄望于少年的個人自覺,希望他們“毋輕涓涓水,積之江河盈;亦有星星火,燎原勢竟成”。 那句“忤眾非所忌,坷坎終其生”,既是言志,也是實述。魯迅曾說,真的知識階級,“對于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并“預備著將來的犧牲”。陳獨秀一生的不夠“成功”,很大程度上正因為他堅持扮演戰斗不息的哲人角色,時時都在“忤眾”。所以胡適說他是“終身的反對派”,他也樂于接受,僅指出這是“事實迫我不得不如此”。的確,為了堅持“探討真理之總態度”,他“見得孔教道理有不對處,便反對孔教;見得第三國際道理不對處,便反對它”。一切“迷信與成見”,均不放過。他的目的,是“要為中國大多數人說話,不愿意為任何黨派所拘束”。 晚年的陳獨秀,已被共產黨開除,又不可能認同逮捕他的國民黨,還不得不配合政府和兩黨抗日,處境的確艱難。但他堅持表態說:“我決計不顧忌偏左偏右,絕對力求偏頗,絕對厭棄中庸之道,絕對不說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我愿意說極正確的話,也愿意說極錯誤的話,絕對不愿說不錯又不對的話。”一言以蔽之,“我只注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他更頑強地說:“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我絕對不怕孤立。”按陳獨秀的厭棄“中庸之道”是一貫的,他在1915年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即曾勸告青年,要“利刃斷鐵,快刀理麻,決不作遷就依違之想”。 實際上,很少有人真能“不怕孤立”。英雄也有落寞寂寥之感。在他棄世的前一年,聽說一些后輩友人在屈原祭日飲酒大醉,陳獨秀賦詩贈友,起首便言“除卻文章無嗜好,世無朋友更凄涼”。那是中國很不如意的時候,大家心情都未必輕松。而別人還能相聚飲酒,他卻僻處鄉間陋室,孤身面對老病。已過耳順之年的陳獨秀,或漸趨于從心所欲,終于撇下了“超我”的面具,不再像魯迅看到的那樣虛張聲勢,而是回向“本我”,在后輩面前實話實說。 他仍然不曾“屈服”,卻也不復倔傲,坦承無友的凄涼。然而,能說凄涼者,就未必多凄涼。面具既除,輕松旋至。寂寞之中,透出幾分淡定,減去多少掛懷。更關鍵的是,陳獨秀不再以奔走政治自期,而是回歸了文章士的行列。這一回歸的重要在于,他一生事業的所謂失敗,也都隨“政治”而去。在“文章”這一領域里,他永遠是成功者,也始終不乏追隨者。 這是否即陳獨秀*后的自定位,我不敢說。與他有過接觸的人中,大都不甚承認他事功方面的作為,卻推崇他在思想方面的貢獻。*典型的,是昔日政敵吳稚暉在挽聯中說他“思想極高明”而“政治大失敗”。傅斯年或許是陳氏真正的解人,他不僅確認陳獨秀為“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更看到了其不遷就任何人而“只注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的特質——陳獨秀未必如胡適所說是“終身的反對派”,其實“他永遠是他自己”! (《他永遠是他自己——陳獨秀的人生和心路》節選)
斯文關天意:近代新舊之間的士人與學人 作者簡介
羅志田,四川大學歷史系七七級畢業,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現任四川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研究方向主要為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著有《權勢轉移》《經典淡出之后》《再造文明的嘗試:胡適傳》《國家與學術》《東風與西風》等,是目前中國近現代史領域Z具影響力的歷史學家之一。
- >
苦雨齋序跋文-周作人自編集
- >
巴金-再思錄
- >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實旅程
- >
羅曼·羅蘭讀書隨筆-精裝
- >
龍榆生:詞曲概論/大家小書
- >
山海經
- >
羅庸西南聯大授課錄
- >
唐代進士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