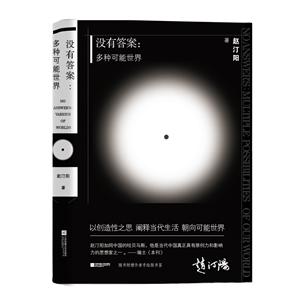-
>
道德經說什么
-
>
電商勇氣三部曲:被討厭的勇氣+幸福的勇氣+不完美的勇氣2
-
>
新時期宗教工作與管理
-
>
帛書道德經
-
>
傳習錄
-
>
齊奧朗作品·苦論
-
>
無障礙閱讀典藏版:莊子全書
沒有答案:多種可能世界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9445384
- 條形碼:9787559445384 ; 978-7-5594-4538-4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沒有答案:多種可能世界 本書特色
1.趙汀陽如同中國的哈貝馬斯,他是當代中國真正具原創力和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瑞士《本刊雜志》 對歷史的追問,對當代生活的思考,對可能世界的設想,對中國事物的關注,對人類成長的關懷。——你能在這本書中找到答案。
沒有答案:多種可能世界 內容簡介
本書精選了著名思想家、哲學家趙汀陽近年來的隨筆文章, 這些文章分為三個部分: 新知、思辨、評論。這本書以跨文化論辯的方式討論了中西文化從分化到融合的可能性、中國的思想傳統在全球語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人工智能日益發達的當代社會其界限在哪。這些文章是作者關于世界、生活和歷史的*具深度與詩意的解讀。
沒有答案:多種可能世界 目錄
沒有答案:多種可能世界 節選
歷史觀:一種文化還是一種知識? 歷史與共同記憶 或有人對遠方不感興趣,但少有人對歷史不感興趣,也少有人對未來不感興趣。這似乎意味著,在人類意識里,時間概念的影響力強于空間概念。對此可以有一個存在論的解釋:時間與存在有著*高的相關度,以至于唯有時間性能夠顯示存在之所以確實存在,因此,時間性幾乎等于存在性。不過,對存在自有不同理解,按照“巴門尼德—柏拉圖”傳統,時間性的存在被認為是俗世的存在,或者是非本真的存在,而純粹的或絕對的本真存在是無變化的因而也是超時間的。可是有個問題:即使絕對存在不是虛構,也是無從了解的;即使能夠在純粹概念上去理解它,既然它與事實的時間性無關,也就與生死和命運問題無關,而人們之所以關心存在,實際上關心的是存在的時間性。如果存在與時間性無關,也就與人無關了。關于純粹存在(being)的概念僅僅是概念,而關于變在(becoming)的事跡才是關于時間性的故事。 宗教和歷史都講述了存在之變在(being in becoming)的時間事跡,但關于存在之變在的兩種時間故事之間卻有著一種緊張關系。宗教往往指向一個歷史的終結,而歷史卻不愿意終結而傾向于無限性,或者是永遠變化的運動(比如中國歷史觀的想象),或者是一種無限循環(比如希臘歷史觀的想象)。宗教所建立的歷史觀預設了歷史的終結,這意味著一種終極解釋,也是宗教的吸引力之所在。人怕勞動,但更怕思想,因此樂聞*后答案,以便可以停止苦苦的思索。可是,終極答案只是一個信念,卻無從得見,永遠尚未來臨,也就難以有效地解釋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歷史。因此,對于沒有耐心等待永不來臨的戈多的人們,歷史終究只能歷史地解釋,就是說,歷史必須在歷史中解釋自身。 如果歷史不可能為自身提供任何終極答案,那么,歷史就總是能夠不同地理解和解釋,于是陷人于無解的不確定性之中,因此歷史不可能成為一種真正的知識。那么,我們為什么對歷史感興趣?歷史為什么會使人樂于思想或勇于思想?我們在歷史中到底在尋找什么?這些問題似乎也可以不同地理解。從人們*直接的興趣來看,歷史敘述的是一個共同體值得追憶的事情。在這個意義上,歷史敘事建構了共同體經驗和共同體記憶,是一個特定共同體的生命事跡,既包括輝煌成就也包括教訓和苦難,更準確地說,是在苦難和輝煌中的生長方式。既然歷史不是一種嚴格的知識,那么歷史就是包含創造性的敘事,正是歷史敘事創造了共同體記憶和共同體經驗,使歷史成為文化傳統自概念僅僅是概念,而關于變在(becoming)的事跡才是關于時間性的故事。 宗教和歷史都講述了存在之變在(being in becoming)的時間事跡,但關于存在之變在的兩種時間故事之間卻有著一種緊張關系。宗教往往指向一個歷史的終結,而歷史卻不愿意終結而傾向于無限性,或者是永遠變化的運動(比如中國歷史觀的想象),或者是一種無限循環(比如希臘歷史觀的想象)。宗教所建立的歷史觀預設了歷史的終結,這意味著一種終極解釋,也是宗教的吸引力之所在。人怕勞動,但更怕思想,因此樂聞*后答案,以便可以停止苦苦的思索。可是,終極答案只是一個信念,卻無從得見,永遠尚未來臨,也就難以有效地解釋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歷史。因此,對于沒有耐心等待永不來臨的戈多的人們,歷史終究只能歷史地解釋,就是說,歷史必須在歷史中解釋自身。 如果歷史不可能為自身提供任何終極答案,那么,歷史就總是能夠不同地理解和解釋,于是陷人于無解的不確定性之中,因此歷史不可能成為一種真正的知識。那么,我們為什么對歷史感興趣?歷史為什么會使人樂于思想或勇于思想?我們在歷史中到底在尋找什么?這些問題似乎也可以不同地理解。從人們*直接的興趣來看,歷史敘述的是一個共同體值得追憶的事情。在這個意義上,歷史敘事建構了共同體經驗和共同體記憶,是一個特定共同體的生命事跡,既包括輝煌成就也包括教訓和苦難,更準確地說,是在苦難和輝煌中的生長方式。既然歷史不是一種嚴格的知識,那么歷史就是包含創造性的敘事,正是歷史敘事創造了共同體記憶和共同體經驗,使歷史成為文化傳統自身復制的一種形式,它給每一代人解釋了“我們”從哪里來、是什么樣的、做過什么偉大事跡或做過哪些愚蠢的事情,它塑造了可以共同分享的經驗、一致默會的忠告、不言而喻的共同情感和作為共同話題的記憶,總之,歷史是承載著可以共同分享的精神故事,而這些故事又成為解釋現實生活具有何種意義的精神傳統。正是通過歷史,一個共同體才得以確認其文化身份,而歷史所構造的文化身份是一個共同體(國家或民族)的精神支柱,龔自珍深刻意識到這一點:“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歷史對文化身份或共享精神的建構不是一個知識論問題,而是一個存在論的問題,就是說,不是通過主體的純粹思想(cogito,我思),而是通過主體的行為(facio,我行)去定義一種存在的身份和意義。“我思”只能證明“我在”,卻不能證明“我是什么”或“我如何在”。純粹思想沒有故事,沒有事跡,純粹思想是無歷史的或者是超歷史的,只能證明概念性的、無變化的存在本身(being qua being),因此,要理解變化中的實際存在(existence),就只能通過其所為去理解,我是什么只能在我做什么之中被定義、描述和解釋。因此,我們有理由說,如果一種存在具有歷史性和未來性,那么,關于這種存在的敘事就必須基于“行”而不是“思”,其背后的奠基性哲學原則只能是“我行故我在”(facio ergo sum),而不是“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雖然歷史敘事超越了知識論問題,但并不是說,歷史無關真相,而是說,真相、假象以及想象都一起服從某種精神追求而一起建構了歷史,建構了某個國家和民族需要自我肯定的形象、經驗、忠告、情感和記憶。在這個意義上,歷史不是一種知識,而是一種含有知識的文化。歷史敘事試圖揭示的“真理”既不是邏輯的也不是科學的,因為它表達的不是客觀必然性,而是關于人與人、人與事之間互動的可能性,它涉及人類命運的秘密,一種與不確定變化有關的秘密,一種連接著過去與未來的秘密,就像司馬遷所說的,是關于“天人之際”和“古今之變”的秘密①。在嚴格意義上說,不確定性或未來性是不可知的,歷史學家不可能從已知的事實推論未來的未定之事,甚至,已知事實對于未來具有何種意義,也無法預知。因此,歷史試圖發現的“存在之道”并非必然之路,而是在天時、地利、人和的語境中的一種動態函數關系,其中當然有一些千古皆同的“常數”,比如說,幾乎從無變化的人性和欲望,以及一些理性的行為模式,但由于諸多變量無法預料,因此,歷史總是具有創造性的故事,而不是一個注定的過程。 在古希臘的知識體系里,歷史也被認為不是一種真正的知識。在希臘人看來,萬物之理(logos)以及思想之理(logic)屬于哲人,而歷史屬于歌者,這與希臘人對永恒、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偏愛有關:永恒不變意味著不會時過境遷而失效,所以才是真理,而偶然的歷史故事在永恒面前總是渺小的,至多能夠說明特定的事情和情形而不能普遍解釋所有事情,因此只有特定的意義。希臘人對永恒和普遍必然性的知識興趣可以解釋,為什么全才的亞里士多德寫作了當時幾乎所有門類的知識,唯獨沒有重視歷史的知識,就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已經發生的事情用不著考慮,需要考慮的是將要發生和可能發生的事情”①。看來亞里士多德不大相信“前車之鑒”之類的想法。后來,休謨關于從以往之事推論不出未來之事的強大論證進一步否定了以往知來的必然性。 既然歷史學家不可能知道必然規律,不可能知道未來,為什么我們堅信歷史的重要性?問題的關鍵在于,重要的未必都是知識。盡管歷史供給人們的不是一種必然知識,卻是一種有意義的“消息”。什么樣的消息如此重要?消息并不是告知必然性,而是提示了可能性。必然性是唯一答案,超越了歷史性,但是在缺乏必然性的地方,可能性就是*重要的消息,它留出希望的余地,有希望的地方才能夠創造歷史,才能創造意義。有一點不能忘記:必然性正是意義的終結,而可能性才是意義的基礎,沒有可能性就不再有任何意義,因此,可能性所留出的“余地”就是一種生命或文明的*重要問題。如果說,以概念作為對象的“我思”尋找并發現必然性,那么,“我行”的問題卻通向可能性所構成的未來。所謂“我行”,就是將某種可能性化為事實的行動。做過的事情對于將做什么有什么教益、忠告或者指引?過去與未來有什么相關意義?存在的過去時對于存在的將來時有什么聯系?這些都意味著行動的當代性,而當代性蘊含著未來性,我行的每一步都是變化的臨界點,都是對過去的告別,但是,我行的每一步雖然是告別卻不是遺忘,否則,任何行動就都無法建立意義和價值。因此,我行的未來性既是告別過去,同時也必須是在捍衛歷史,否則就只是無意義的運動而不是行動。這也許就是歷史消息的謎底:可能性意味未來性,而未來必須延續歷史的意義才能具有意義。就是說,未來性必須同時是延續性才能夠創造意義。這不是知識,而是文化,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信仰。 大事與大義 如前所述,歷史敘述的是需要銘記的大事,而大事蘊含大義(也就是重要消息)。可是,什么是大事?又是一個問題。顧名思義,大事就是那些創造了歷史的事情,先秦古人稱之為值得“述”之“作”,而希羅多德的樸實而中肯的說法是,歷史記述“值得贊嘆的豐功偉績”。但這樣說似乎是同義反復。司馬遷則采取了另一個可能更清楚的角度,他從歷史“不寫什么”去理解歷史:“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后世的顧棟高也采取類似角度:“凡褒貶無關于天下之大,故不書。”方苞的概括*為簡練:“《春秋》之義,常事不書。”這些都是在邏輯上等價的真知灼見。關乎天下興衰之事就是大事,這一點在概念上似乎是清楚了,但仍然不足以具體確定哪些事情在真正決定興衰。社會突變當然是*為顯眼的大事,比如建國立法、制度革命或者生死之戰,但并不能因此僅僅專注于顯眼事件而以為那些相對緩慢的變化不是決定興衰的大事,其實,一些悄悄的漸變有可能是更為深刻而深遠的變化。馬克思或者布羅代爾都會認為經濟、技術和社會生活的漸變是更深刻的大事,尤其以“長時段”尺度去觀察歷史變遷,就可以看出漸變之意味深長,其重大意義可能經過數十年或數百年才得以一目了然。以《春秋》和《史記》為范本的中國史學傳統甚至更早地意識到了長時段的歷史尺度,司馬遷所謂“通古今之變”已明示此意:古今在“通”之中方顯出其連貫的意義。顧棟高通過讀《春秋》的經驗也發現,歷史大事往往需要經歷很長時間之后才“結案”,因此說:“看《春秋》眼光須極遠,近者十年數十年,遠者通二百四十二年。” 時至今日,人類生活環環相扣,越來越難以斷定何種變化才是*為深遠的大事。政治、經濟、宗教、金融、戰爭、技術、能源、糧食、氣候甚至話語,都同樣有可能在某些關鍵時刻,所謂天時,成為決定命運的大事。何種事情能夠成為歷史中的大事,取決于何時何地之何事*具活力和后勁,*有可能成為牽動萬事的啟動點,或者反過來,取決于何時何地之何事*為脆弱而難以維持事態之均衡,因此*有可能成為連鎖反應的爆發點。但是,人們難有先見之明而不乏事后諸葛亮,許多*具深遠影響的大事的“歷史意義”往往是在事后很久才被重新發現的。事實上人們總在事后不斷重新發現歷史,不斷修改歷史解釋,甚至在數百年后還在給出顛覆性的全新解釋,以至于幾乎永無定論,古史常新。比如說,現代已歷數百年,而今正在被全球化帶入一個新時代,關于現代性的起源、本質和意義卻還在反思和討論中。比如,數十年來人們對現代性的起源解釋就一直不斷翻新,越追越遠。沃格林發現了現代性的神學根源,特別是遙遠的靈知主義根源;麥克法蘭則以古代生活的細節材料試圖證明,英國早在11世紀就已經是個人主義社會了,因此英國的現代性遠遠早于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啟蒙運動、市場資本主義、殖民主義、新教倫理以及民族國家①;吉萊斯皮則試圖說明現代性的深度思想根源來自中世紀“唯名論革命”這樣一個宗教內部的反思運動②。如此等等。不斷照此加以歷史反思和追認,或許,將來耶穌會被追認為現代的**人。“追認”的方式不僅能夠將歷史的線索伸延至遙遠的過去,從而建立歷史的超長連續性,而且,對歷史線索的追認在某種程度上是在重新建構歷史。這絕不是說歷史事實是虛構的,而是說,歷史事實的意義并非一種直接給予的一時經驗,而是在長時間中不斷生長而不斷展開的連續經驗,就是說,前事的意義是在后事中不斷展現的一個生長過程,是一個經驗的不斷再經驗過程,因此,歷史在后人的意向性中成為一種“現象學的”事實。
沒有答案:多種可能世界 作者簡介
趙汀陽,中國哲學家。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哲學研究所研究員、長城學者,主要研究元哲學、倫理學、政治哲學、美學等。曾出版哲學著作十余部。主要著作:《論可能生活:一種關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論》《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第一哲學的支點》《天下的當代性》。
- >
二體千字文
- >
人文閱讀與收藏·良友文學叢書:一天的工作
- >
苦雨齋序跋文-周作人自編集
- >
經典常談
- >
新文學天穹兩巨星--魯迅與胡適/紅燭學術叢書(紅燭學術叢書)
- >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實旅程
- >
羅庸西南聯大授課錄
- >
史學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