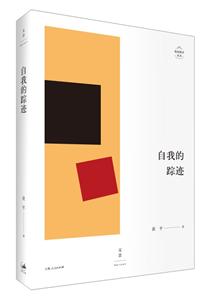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新書--述而批評叢書:自我的蹤跡 版權(quán)信息
- ISBN:9787208153127
- 條形碼:9787208153127 ; 978-7-208-15312-7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新書--述而批評叢書:自我的蹤跡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廣大讀者 ★上海極具潛力的文學(xué)批評家,書寫批評新浪潮。 ★上海青年評論家的di一次集體亮相。 ★作者探討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具有代表性的文學(xué)作品中“自我”與歷史之間的關(guān)系,延展到對于文學(xué)與文藝的社會責(zé)任的討論,作者選擇的文本和作家極具代表性,對相關(guān)學(xué)科理論理解透徹,引用得當,全書邏輯清晰連貫。
新書--述而批評叢書:自我的蹤跡 內(nèi)容簡介
“在上一本書《反諷者說》里,我透過‘反諷’這種美學(xué)形式,*終還是聚焦于‘自我’的虛無感。而這本書,延續(xù)《反諷者說》,匯聚了*近一兩年對于‘自我’歷史性的研究,試圖通過對于當代文學(xué)的形式/精神分析,捕捉大河奔流的‘改革’四十年來‘自我’的蹤跡。” 在本書中,前兩章集中于探討“自我”如何誕生、如何管控;后兩章討論“自我”如何被征用,是否還有突破的可能。
新書--述而批評叢書:自我的蹤跡 目錄
**節(jié) “自我”的誕生?
第二節(jié) 參與性危機?
第三節(jié) 虛無與反諷?
第二章 對于“自我”的管理
**節(jié) 格瓦拉來到了新時期?
第二節(jié) 對于“自我”的管理?
第三節(jié) 從“勞動”到“奮斗” ?
第三章 幻城中的小時代
**節(jié) 沒有差別的新美學(xué)?
第二節(jié) 作為技術(shù)的文學(xué)
第三節(jié) 幻城中的小時代?
第四章 “新的美學(xué)原則在崛起”
**節(jié) 拯救文學(xué)的先鋒性?
第二節(jié) “新的美學(xué)原則在崛起”
新書--述而批評叢書:自我的蹤跡 節(jié)選
**節(jié)“自我”的誕生 一、“內(nèi)在自我”的出現(xiàn) 1978年春,老作家駱賓基在北京突發(fā)腦溢血住院,探望的親友絡(luò)繹不絕。其中有一位駱賓基的忘年交:在**機械工業(yè)部機械設(shè)備成套總局工作的張潔女士,她也是契訶夫小說與古典音樂的愛好者。駱賓基在住院前和張潔聊起年初中央音樂學(xué)院高考招生的一則新聞,并鼓勵張潔試著以此寫篇小說。張潔將這篇小說投給了《人民文學(xué)》,和絕大多數(shù)作家的**次投稿一樣,這篇小說被退稿。然而駱賓基比張潔更堅持,他出院后去小湯山療養(yǎng),再一次問起這篇作品,并把題目改定為《從森林里來的孩子》,讓張潔轉(zhuǎn)投《北京文藝》試一試。果然,這篇小說*終發(fā)表于《北京文藝》1978年第7期并大獲成功,獲得了1978年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在獲獎的二十五部作品中名列第十一位,居于盧新華的《傷痕》之后,張承志的《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之前。 從此張潔登上了新時期的文壇。張潔本名董大雁,1937年4月27日生于北京。父親董秋水出生于東北,參加過東北軍。張學(xué)良組建東北大學(xué)后,東北大學(xué)代校長周鯨文請董秋水出任學(xué)校教官,董秋水由此和周鯨文相熟,聶紺弩曾說董秋水“依周為生多年”。后來董秋水于1937年夏去了延安,又由延安去了香港,協(xié)助1938年去香港的周鯨文編輯《時代批評》。1941年6月,周鯨文、端木蕻良開始主編一份新雜志《時代文學(xué)》,具體主編工作由端木負責(zé),蕭紅也參與編輯。該刊一共出版六期,因香港淪陷而停刊。這個時期在香港的文化人很多,周鯨文的刊物漸漸成為一個重要的據(jù)點。駱賓基于1941年9月到香港后也寄居于此,住在董秋水的宿舍,由此成為朋友。也是在這一年,張潔隨母親來到香港尋找父親,影影綽綽地留下對于這些作家的記憶。香港淪陷后董秋水帶著妻子和孩子去了桂林,駱賓基也來到桂林,長期住在董的家里。張潔漸漸和這位叔叔熟悉起來了,那時的張潔只是在經(jīng)過糖果店時糾纏著駱賓基買糖,還不會預(yù)想到這位叔叔將在多年后給她的命運帶來的變化。 和駱賓基對于張潔的溫情相比,董秋水則是一個不合格的父親。1941年周鯨文參與創(chuàng)建民盟,董秋水出任民盟中央組織委員會委員。在張潔的回憶中:“他一直搞‘民盟’,在‘民盟’地位比較高。……他是希望走‘民盟’這條路線的。”熱心于現(xiàn)世功名、在政界和文壇間徘徊的董秋水,漸漸將妻兒視為累贅。張潔回憶道:“我母親帶我到香港找父親,父親對我們已經(jīng)很壞,經(jīng)常打我,用腳踢我。‘珍港事變’,我們逃難到內(nèi)地,經(jīng)過廣西、四川,*后到陜西,父親就把我和母親丟在那里,自己跑了。”*終董秋水和張潔的母親在1940年代離婚,一個人去了北京,任三聯(lián)出版社的編輯。沈昌文在自傳中對于這位同事有過回憶:“這位董先生經(jīng)常是衣服穿得筆挺,頭發(fā)梳得光亮。用我們當年革命青年的說法,是舊官僚那樣的。每逢黨的代表大會開幕,他一定要寫一首‘五言’或是‘七律’,貼在墻上表示祝賀的心情。”1957年“反右”期間,董秋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秦皇島的青龍縣,從此以后一直生活在秦皇島,娶了第二任夫人,2009年去世。 由于父親近乎遺棄了母女倆,張潔“小時候過著一種近乎流浪的生活”,她和母親一路顛沛流離,從北京到香港尋找父親,又逃難一般從香港到內(nèi)地,*后在1950年代來到遼寧撫順。離亂之世,孤兒寡母,其間的貧苦與窘迫可以想見。在后來的長篇小說《無字》中,張潔塑造了一個叫顧秋水的人物,出身于東北軍,一心想當“上等人”,以各種卑劣的手段驅(qū)趕妻兒以逃避責(zé)任。這明顯是以董秋水為原型,父親帶給張潔的精神創(chuàng)傷可見一斑。 1954年張潔在撫順讀中學(xué)時,試著給駱賓基寫信,開始兩人常年的通信與交往。1956年張潔考入中國人民大學(xué)計劃統(tǒng)計系,這一年也是“人大”**次招收高中畢業(yè)生(以往只招調(diào)干生),讀完大學(xué)后去了**機械工業(yè)部工作。1969年張潔下放“五七干校”,1972年回城,在這期間張潔認識了第二任丈夫、后來擔(dān)任一機部副部長的孫友余,兩個人逐漸發(fā)展出戀情。由于孫友余當時是有婦之夫,這段戀情鬧得沸沸揚揚,孫友余*終離婚,與張潔在1983年結(jié)婚。 之所以勾勒張潔父親董秋水與張潔本人的人生歷程,原因在于張潔和新時期起源階段的其他作家有所區(qū)別——她的寫作帶有高度的自敘傳色彩,尤其是《愛,是不能忘記的》可以被視為精神創(chuàng)傷的表征。《愛,是不能忘記的》是新時期文學(xué)**篇真正的“**人稱”作品。由于新時期文學(xué)依然承擔(dān)著鮮明的政治性,第三人稱全知敘述更為常見,《哥德巴赫猜想》《班主任》《喬廠長上任記》無一例外都是第三人稱敘述,無所不知的上帝視角背后,是新時期政治對于敘述的把控。當然,在《愛,是不能忘記的》發(fā)表的1979年11月之前,在短篇小說領(lǐng)域也出現(xiàn)過不多的**人稱敘述,按發(fā)表時間為序,大致有以下作品:莫伸《窗口》、劉富道《眼鏡》、孔捷生《因緣》、劉心武《愛情的位置》、陳國凱《我應(yīng)該怎么辦》、周嘉俊《獨特的旋律》、葉蔚林《藍藍的木蘭溪》、孔捷生《因為有了她》。這類小說大都是愛情婚姻題材,之所以運用**人稱敘述,在于這類題材敘述上的便利——**人稱可以方便地表示出人物在愛情婚姻中的內(nèi)心波動,比較典型的是劉心武《愛情的位置》中以女主角孟小羽為敘述視角的敘述。在以上這些小說中,承擔(dān)敘述視點的“我”只是小說中的一個角色,受到隱含作者的高度控制,“我”說的不一定是自己的話,而是在表達著隱含作者的意圖。 只有回到新時期文學(xué)的歷史語境中,與其他的作品相參照,才能真正理解《愛,是不能忘記的》的“**人稱”意味著什么。《愛,是不能忘記的》以下面這一句開篇:“我和我們這個共和國同年。三十歲,對于一個共和國來說,那是太年輕了。而對一個姑娘來說,卻有嫁不出去的危險。”表面上,這似乎和以往的新時期愛情婚姻小說相似,以**人稱講一個大齡女青年的故事,這個女性的愛情婚姻故事將*終落座在新時期的政治與道德秩序之中,這是被確定了的“愛情的位置”。然而,《愛,是不能忘記的》敘述剛剛展開,作者就以一系列“內(nèi)/外”的區(qū)分,悄然驅(qū)逐外在于“自我”的一切敘述。 首先是“身體/靈魂”的對立,作者安排了一位身體條件近乎完美的求婚者喬林:“眼下我倒有一個正兒八經(jīng)的求婚者。看見過希臘偉大的雕塑家米倫所創(chuàng)造的‘擲鐵餅者’那座雕塑么?喬林的身軀幾乎就是那尊雕塑的翻版。即使在冬天,臃腫的棉衣也不能掩蓋住他身上那些線條優(yōu)美的輪廓。”以往的研究幾乎不關(guān)注喬林這個人物,大都泛泛地一帶而過,然而這個人物非常重要,他作為“身體”的象征,開啟了小說敘述的反向運動。“我”對于“愛”的追尋,開始于對雕塑般的身體的厭棄。“我”在乎的是喬林能否回答“你為什么愛我”,而喬林對此訥訥無語。在此小說特地寫了一個細節(jié),喬林“抬起那對兒童般的、清澈的眸子”。過于發(fā)達的“身體”,過于稚嫩的“靈魂”,對于尋求“愛”的“我”來說,“我的心被一種深刻的寂寞填滿了”。 這種“內(nèi)/外”的辯證將“人”區(qū)別為“靈魂/身體”,為的是從“身體”所代表的外部回到“靈魂”代表的內(nèi)部。查爾斯·泰勒在其巨著《自我的根源》第七章中,借助解讀奧古斯丁的思想,深刻地分析過“內(nèi)在的人”是如何出現(xiàn)的:“外在的是身體,這是我們與野獸相同之處,也包括我們的感覺,乃至于我們對于外部世界各種形象的記憶。內(nèi)在的則是靈魂。奧古斯丁并不是僅僅以此描述一種內(nèi)外的區(qū)別。對我們的精神來說,這種區(qū)別具有*重要的一種意義:從低到高的路,通過我們的內(nèi)在自我,這在方向上發(fā)生了關(guān)鍵的轉(zhuǎn)向。” ……
新書--述而批評叢書:自我的蹤跡 作者簡介
黃平,1981年生,中國人民大學(xué)文學(xué)博士,華東師范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館客座研究員。 著有《反諷者說:當代文學(xué)的邊緣作家與反諷傳統(tǒng)》《大時代與小時代》《賈平凹小說論稿》《“80后”寫作與中國夢》《以文學(xué)為志業(yè)——“80后學(xué)人”三人談》等。曾獲第四屆唐弢文學(xué)獎,《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叢刊》年度優(yōu)秀論文獎。
- >
隨園食單
- >
朝聞道
- >
史學(xué)評論
- >
二體千字文
- >
企鵝口袋書系列·偉大的思想20:論自然選擇(英漢雙語)
- >
巴金-再思錄
- >
伊索寓言-世界文學(xué)名著典藏-全譯本
- >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實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