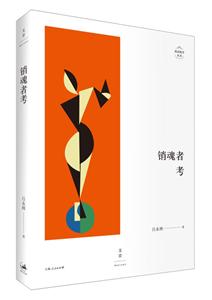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新書--述而批評叢書:銷魂者考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8153073
- 條形碼:9787208153073 ; 978-7-208-15307-3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新書--述而批評叢書:銷魂者考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廣大讀者 透過文學,看見一個個曾經被現實磨損得面目模糊的人。他們的動作、表情、一言一行,事關生命的質地、世界的尺度。呂永林通過寫作,審視文學作品中一個個人物的生與死、沉淪與復活。他們也是我們——作者將我們每個人視而不見的心性,從文本世界中重新打撈起來。看似痛苦的過程,實為提純與凈化:每一種叩問靈魂的書寫,都旨在召喚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未來。
新書--述而批評叢書:銷魂者考 內容簡介
《銷魂者考》共收錄15篇文章,主要聚焦于當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問題和作品,話題涉及“潘曉”討論、劉震云小說中小人物對歷史的承擔、衛慧小說的歷史隱喻功能等等。同時,也有對于相關學術著作的評論,如對于蔡翔《革命/敘述》和張新穎《沈從文的后半生》的評論。這些文章顯示了很強的哲學氣質,作者往往從文學出發,抵達更為抽象的文學觀乃至世界觀,試圖以文學的思考來回答有關審美、他者、正義等更為根本的哲學問題。
新書--述而批評叢書:銷魂者考 目錄
野部
玩笑的深度及其限度 3
——論劉震云之《故鄉面和花朵》
我們離苦難很近,離善良很遠 61
——溫故《溫故一九四二》及其他
山部
事關未來正義的正義 73
——從蔡翔教授之《革命/ 敘述》而來
澤部
審美的暴政 109
豬尾焦慮與屠蘇之死 129
——周曉楓《離歌》“閱讀筆記”
村部
常人世界及其活口 147
——《一地雞毛》《一腔廢話》《一句頂一萬句》對照記
文本世界的青年往何處去 175
——石一楓小說里的斗爭與無望
湖部
羅陀斯的天光與少年 193
——從吳亮的長篇小說《朝霞》而來
“我們”向何處去 213
—— 由話劇《WM(我們)》和《我們走在大路上》而來的一份時代精神考察
溪部
新生證實,有情有功 251
——讀張新穎《沈從文的后半生》
文本、理論、世界和自我的重逢 269
——關于項靜的文學研究與評論
致謝 287
新書--述而批評叢書:銷魂者考 節選
常人世界及其活口 —— 《一地雞毛》《一腔廢話》《一句頂一萬句》對照記 對于一些時時處于某種政治焦慮、文化焦慮的作者和讀者來說,*具逼迫性的問題只有兩個——未來世界的形式如何?主體為誰?所謂“世界的形式”,其根本在于人與物、人與人乃至人與神之間的關系形態;所謂“主體”,則終究要落實為一個個有著活生生的情感流淌和精神飄移的個人。前者,生成“世道”;后者,搭構“人心”。 多年以來, 劉震云的小說創作一直在做的事情, 便是對“世道人心”的反復勘探與呈現,而其小說世界的核心操持者——或者說其小說中的主人公們,則被作家長期鎖定為非神 非圣的常人。 或有論者稱,劉震云筆下多是小人物,其實不盡然。《塔鋪》里的農村大齡復讀青年,《新兵連》里的入伍新兵,《單位》、《一地雞毛》里的小公務員,《我叫劉躍進》里的劉躍進,《一句頂一萬句》里的楊百順和牛愛國,等等,這些固然都是中國社會中的小人物,但除此之外,劉震云小說中還有許多主人公是社會上的大人物,比如《故鄉相處流傳》里的曹成和袁哨,在歷史上一個當過丞相,一個當過主公,《故鄉面和花朵》里的孬舅則是“世界恢復禮義與廉恥委員會的秘書長”,屬于國際政要,還有小麻子是大資本家,瞎鹿是影帝,馮·大美眼、呵絲·溫布林、巴爾·巴巴、卡爾·莫勒麗等則都是世界級的明星,《一腔廢話》里的老杜、老蔣等,也都是實權派。《手機》里的嚴守一和費墨雖非大富大貴之人,卻也屬于當代中國的中產者和精英人士,而非社會下層的小人物。另外,當有記者問到:“你筆下有很多的小人物,沒有打算寫一些大人物嗎?”劉震云嘗作如是答:“人物大小要辯證來看,因為社會標準和生活標準不同。比如《一地雞毛》中的小林,他們家的豆腐餿了比八國首腦會議更重要,所以小林們的生活邏輯和價值標準與所謂的大人物是不同的。”[1] 綜上種種,盡管劉震云筆下聞名者多是小人物,但小人物卻非劉震云小說世界唯一的主人公和落腳點,更何況,作家本人并不認為這些小人物是“小人物”——在其各自的生活世界和生活邏輯中, 他們同樣也是“ 大人物”。這就意味著,人物大小之辯并不能解決我們*初提出的問題——“誰才是劉震云小說世界恒久的主人公?” 好在,人物大小之辯雖不能直接解決問題,卻可為我們牽連出一條很不錯的思考路徑。通過閱讀劉震云的全部小說,我們發現這些作品里的主人公們無論小大,實際上都被作家施以一種常人化的處理,因而都屬于非神非圣之輩。《塔鋪》、《新兵連》里的“我”和《單位》、《一地雞毛》的小林,以及《溫故一九四二》里逃荒的河南災民自不必說,《官場》、《官人》里的各級官員和《新聞》里的各路記者,包括《溫故一九四二》里的蔣委員長在內,也都各有各的毛病和小樣,都跟“給世人以指引”的神或“止于至善”的圣實在相去甚遠,也跟那些始終將他人的幸福作為自己幸福前提的圣徒相去甚遠。在劉震云的小說世界,神或圣以及圣徒的形象本來就十分罕見,且一旦出現,也往往會被作家“發配”到小說的“附錄”或“插頁”里面,從而成為一個在場的缺席者,比如《故鄉面和花朵》里的“姥娘”。[1] 又比如在《一句頂一萬句》里面,主人公楊百順數來數去,發現在他交往過的人當中,也就老詹“算個忠厚人”,“雖然不會傳教,但也從來不害人”,[2] 而且老詹幾十年如一日地在延津傳教,雖歷經挫折與失敗卻至死不渝,還真有點超凡入圣的意思,可問題是,“從來不害人”的老詹卻是個意大利人,是個天主教神父,他雖然在河南延津生活了五十來年,但其精神根底恰恰在中國的文化系統之外。對于從不跟神對話且不知信仰為何物的延津人來說,老詹的存在簡直無足輕重,眾人從來不把老詹的信仰與傳教當回事,同時也就不把老詹這個人當回事。 在劉震云筆下,非神非圣的常人構成了歷史與現實*持久的擔當者、承受者和挾持者。換句話說,常人構成了劉震云小說世界*為普遍的主體和*大的勢力。也正因為如此,小說家劉震云對世界的悲觀與樂觀、絕望與希望,皆自常人出。此可謂常人死,則世界死;常人活,則世界活;常人得救,則世界得救。 無名小林被現實“砍了頭” 《一地雞毛》中的小林是劉震云筆下著名人物,不過著名的小林也只是個有姓無名的人,小林之“小”跟阿Q 之“阿”頗為神似,其所呈現的,乃一種極其廣大、日常、弱勢的常人化存在,小林與阿Q *大的不同是阿Q *終稀里糊涂地被莫名砍了頭,小林則選擇了對現實生活死心塌地的歸順。但對于自我而言,這兩種不同的人生走向所呈現的又都是同一種生命的折斷,都是生命自主性的破碎或缺失。特別是在小林身上,日常生活的難度與陰險可謂暴露無遺,大學時代,小林也曾“發奮過,挑燈夜讀過,有過一番宏偉的理想,單位的處長局長,社會上的大大小小機關,都不在眼里”,然而工作幾年,經過種種日常操練與磨難,小林“很快淹沒到黑鴉鴉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這個“淹沒”不僅僅是小林與眾人在日常生活方式層面的趨同,更是人的少年情志的拗斷與喪失,比如生活熱情和詩意的消散,比如對自由意志和自我主張的刪除,比如對他人的愛與溫情的閹割,等等。小林有個曾教過他五年的小學老師,姓杜,杜老師當時既教數學,又教語文,“一年冬天小林搗蛋,上自習跑出去玩冰,冰炸了,小林掉到了冰窟窿里。被救上來,老師也沒吵他,還忙將濕衣裳給他脫下來,將自己的大棉襖給他披上”。因此對于杜老師,小林一直心存感念。十幾年后,杜老師來北京看病,找到小林,小林卻是有心無力,飯后送老師上了公交車,小林一個人往家走,感到身上沉重極了,“像有座山在身上背著,走不了幾步,隨時都有被壓垮的危險”。在此,我們一定要提出一個問題:這份像座山一樣的沉重對小林而言究竟意味著什么?首先,小林之所以感到沉重,是因為他對老師樸素的溫情依然強烈,而愧疚感和無能感正在折磨著這個“小人物”的心,也就是說,在這一刻的小林身上,人與人之間樸素的溫情還在發揮著一種正向的生產功能,生產著人對現實的不滿,不滿就意味著人對現實的改變和超越可能。但與此同時,這份沉重也構成了一種嚴酷的心理逼壓,許多人正是因為受不了這個溫情與不滿之“重”,才選擇了忘卻與自裁之“輕”,尤其是當合情合理的解決之道根本無望之時。三個月后,小林在辦公室收到一份信,是上次來北京看病的杜老師他兒子寫的:“說自上次父親在北京看了病,回來停了三個月,現已去世了;臨去世前,曾囑咐他給小林寫封信,說上次到北京受到小林的招待,讓代他表示感謝。”小林讀完信,想起當時老師來看病,自己也沒給找個醫院,在家里也沒讓老師洗個臉,心里難受一天。不過這個“短暫”的傷心*終還是被更加現實的大白菜問題給取締了,小林下班后“一坐上班車,想著家里的大白菜堆到一起有些發熱,等他回去拆堆散熱,就把老師的事給放到一邊了。死的已經死了,再想也沒有用,活著的還是先考慮大白菜為好”。其實*令人揪心的,還不是小林這一傷心的被取締,而是傷心背后人對現實不滿的被取締,唯有人對現實的不滿被取締了,人才能完成其忘卻和自裁的歷史行動,小林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恰恰就是這個:“小林又想,如果收拾完大白菜,老婆能用微波爐再給他烤點雞,讓他喝瓶啤酒,他就沒有什么不滿足的了。”[1] 在討論人之所以為人的問題時,黑格爾有云:“人既是高貴的東西,同時又是完全卑微的東西。它包含著無限的東西和完全有限的東西的統一,以及一定界限和完全無界限的統一。人的高貴之處,就在于能保持這種矛盾。而這種矛盾是任何自然東西在自身中所沒有的,也不是它所能忍受的。”說人是“有限”的,這從人的肉身性和社會性層面便可一目了然,但人和動物的不同之處在于,人同時又擁有一種能夠從一切生物、社會的現實規定性中抽象出來和超拔出來的可能,這便是人的“無限”性,人的“無限”性意味著:“我能擺脫一切東西,放棄一切目的,從一切東西中抽象出來。”黑格爾認為,盡管這是一種“否定的自由”,是片面的自由,但這種“片面性”始終包含著一個關于人的“本質的規定”,它是人獸之分的界碑所在,是我們身上彌足珍貴的東西,“所以不該把它拋棄”。[2] 然而《一地雞毛》中的小林*終所為,恰恰跟黑格爾的提醒迥然相反,在小林身上,人的“無限”性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切割,而人的“有限”性(或者說現實規定性)則上升為絕對的主子。對師恩與溫情的忘卻,對傷心和不滿的放棄,為查水表老頭解決蓋章問題,并*終坦然收受和享用作為賄賂的微波爐,給女兒所在幼兒園的老師送“炭火”,等等,這些都構成了小林匍匐在人的“有限”性之下的隱喻,同時也是小林成為各種宏觀或微觀權力之服從者、侍應者和再生產者的隱喻。關于這點,小說靠近收尾處的一句話可謂明證:“小林老婆高興地說,微波爐用處多,除了烤白薯,還可以烤蛋糕,烤饃片,烤雞烤鴨。小林吃著白薯也很高興,這時也得到一個啟示,看來改變生活也不是沒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1] 可問題是,一個不再具有強烈的無能感和屈辱感的小林,一個不用再在“漆黑的夜里”扇自己耳光的小林,或者說一個從此奉行“只要加入其中就行”的小林,也恰恰是一個被現實“砍了頭”的小林。 對于阿Q 和祥林嫂等人的悲劇,人們往往習慣用魯迅先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進行品判。可是除去死亡這一等價交換物,阿Q 和祥林嫂究竟拿什么去“爭”?這是一道實實在在的大難題。同阿Q 和祥林嫂一樣,小林也只是個常人,并且也屬于常人中的非強勢群體,對于小林,我們無法寄望太多,尤其是不能把他事先神圣化,然后再按神圣的標準去要求他如何如何。讓小林像史詩中的英雄一樣去“改變世界”甚或像神一樣去“創造世界”,顯然有些不切實際,小林既沒有那么多的可持續的力量,也沒有那么大的可持續的心志。更加要命的是,圍裹在小林四周的,恰恰又是一個由無數強勢或弱勢的常人編織而成的灰色世界,用韓寒的話說,“方圓幾百公里內,連個現實的勵志故事都沒有”[2],因此換了誰是小林,誰都難免對理想絕念。而一個人如果長時間找不到出口,就很容易會認同某種流行的大眾生存哲學——“如果你改變不了這個世界,就讓這個世界改變你”。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劉震云的《一地雞毛》是在有意無意間以一種十分陰郁的方式提出了一個事關當代政治和未來正義的命題——要改寫小林,先改變世界。
新書--述而批評叢書:銷魂者考 作者簡介
呂永林,內蒙古河套平原人,上海大學中文系教師,文學博士,碩士生導師。著有《個人化及其反動——穿刺“個人化寫作”與1990年代》(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譯有《創意寫作教學:實用方法50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在《文學評論》、《光明日報》(理論周刊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海文學》(“理論與批評”欄目)、《上海文化》、《南方文壇》等報刊發表學術論文若干。
- >
自卑與超越
- >
推拿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裝共3冊
- >
人文閱讀與收藏·良友文學叢書:一天的工作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實旅程
- >
史學評論
- >
二體千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