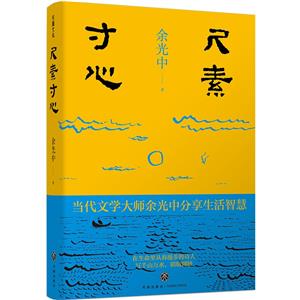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尺素寸心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5571011
- 條形碼:9787545571011 ; 978-7-5455-7101-1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尺素寸心 本書特色
1. 作者余光中因一首《鄉愁》為大陸讀者所熟知,其散文創作同樣具有很大影響力,被譽為“文壇璀璨的五彩筆”、“當代散文八大家”之一,在大陸、香港和臺灣都擁有較大讀者群。 2. 從大陸到港臺,從中國到歐美,余光中的一生都在漂泊,卻認定大陸永遠是自己的母親,他的文字時刻都能引起游子的共鳴。 3. 作者學貫中西,是永遠的華語文學大師,他的散文寫盡一代人的鄉愁、記憶與青春,傳遞跨越半個世紀的純粹與感動。
尺素寸心 內容簡介
本書是著名作家余光中的名篇合輯,精選了作者多篇經典散文作品,如《思臺北,念臺北》《憑一張地圖》等。本書以“故鄉”與“旅行”為主題,包括鄉愁記憶、游記見聞等內容。書中有壯闊鏗鏘的大手筆,有細膩柔綿的小寫意,還有深沉真摯的情感和思考,以及深厚的人文情懷。讀者閱讀此書可以進一步了解作者的內心,感受大師豐富的精神世界。
尺素寸心 目錄
**章 鄉愁綿綿,莫問歸期
萬里長城
思臺北,念臺北
從母親到外遇
思蜀
新大陸,舊大陸
第二章 故國千里,鄉關何處
山盟
沙田山居
關山無月
水鄉招魂——記汨羅江現場祭屈
片瓦渡海
清明七日行
故國神游
第三章 彼岸風景,詩意遠方
石城之行
南半球的冬天
從西岸到東岸——第四度旅美追記
憑一張地圖
海緣
山國雪鄉
紅與黑——巴塞隆納看斗牛
第四章 萬物可期,人間值得
地圖
聽聽那冷雨
尺素寸心
娓娓與喋喋
粉絲與知音
尺素寸心 節選
《新大陸,舊大陸》 1 自從一九四九年七月的一個夏日,我在廈門的碼頭隨母親登上去香港的輪船,此生就注定了半世紀之久不再見大陸。當時年少,更非先知,怎料得到這一走,早年的大陸歲月就劃然終止了。怎料得到,抗戰的長魘也不過八年 就還鄉了,而這次流離,竟然“掉頭一去是風吹黑發,回首再來已雪滿白頭”。怎料得到,當時回顧船尾,落到茫茫的水平線后的,不僅是一嶼鼓浪,而是厚載一切的神州。更未料到,從此載我蔭我,像諾亞方舟的,是一座靈山仙島。 但是不幸中隱藏著幸運,當日那黑發少年已經二十一歲了,漢魂已深,唐命已牢,任你如何“去中國化”都搖撼不了。所以日后記憶之庫藏,不,鄉思之礦產,可以一鑿再鑿,采之不盡。丹田自有一個小千世界(microcosm),齊備于我。如果當時我還是一個十三四歲甚或更小的孩童,則耿耿鄉心,積薄蘊淺,日后怎么禁得起彌天的歐風美雨? 在媽祖庇佑的蓬萊米島上一住八年,從臺大的插班生變成師大的講師,從文藝青年變成文壇新秀,從表兄變成男友、新郎然后是父親,那時并不很懷念大陸,反覺得那一片空闊愈來愈陌生,那陌生的社會正取代了我熟悉的童年。 舊大陸的種種像因緣未了的前世,不續不斷,藏在內臟的深處像內傷隱隱,隱隱未發。這么內耗兼偏安,到我三十歲那年,母親死了,舊大陸似乎更遠了。而幾乎是同時,珊珊生了,她響亮的啼聲似乎是一個新時代在叩門,銅環鏗鏗。也幾乎是同時,新大陸在西半球召我。 2 三去美國,**次讀書,只留一年,后兩次教書,各留兩年。那時有志青年的正途正是留學,所謂鍍金。我一年修得碩士,就迫不及待,匆匆回到島上,只能算是鍍銀。我匆匆回來,為了還沒有克服喪母之痛,為了丟不下還是新娘的妻子,而新生的女嬰還沒有抱夠,甚至看清。 **次旅美,我目眩于花旗帝國之新奇富麗,卻心懷故國與故島。 我的鄉愁真正轉深,在山河的阻隔之上,更與同胞、歷史、文化綢繆難解,套牢成一個情意糾結,一個不肯收口的傷口,是在第二次旅美之后。文化充軍、語言易境、晝夜顛倒、寒暑懸殊,使我在失去大陸之后更失去孤島,陷于雙重的流離。唯一能依靠甚至主宰的,只剩下中文了。只剩下中文永不繳械,可仗以自衛、驅魔、召魂。 美國的經驗似乎是陌生的,但是又不盡然。我出身于外文系,對西方后來居上的**強國當然不無了解,更不無向往。那時我們讀的英文其實是美語,對當代西方生活的印象也大半來自好萊塢。不過我在去美國之前早已讀過不少美國文學,甚至為臺北與香港的美國新聞處譯過五十多首美國詩,而我*早出版的兩本中譯小說:《老人和大海》《梵谷傳》 ,也都是美國作家所寫。 第二次去美國,教書的負擔不算很重,而待遇又不薄,更值壯年,體能正當巔峰,自信臻于飽滿。為了認識新大陸,做一個真正的現代人,我決定學駕駛,并且用三分之一的年薪買了一輛新車。從此美國之大,高速路之長,東岸與西岸之遠,都可以應召而來,繞著我的方向盤旋轉。我似乎馳入了惠特曼豪放的新史詩里,一目十行,縱覽美利堅魁偉的體魄,匯入了**世界的蕩蕩主流。 那當然只是方向盤后*初的幻覺。從大西洋滸到太平洋岸,四輪無阻,縱然踹遍了二十四州,也不過是被吸入了美利堅抖擻的節奏,隨俗流轉。高速的康莊大道無遠弗屆,但沒有一條能接到長安。時速七十英里 ,縱使將芝城旋成急轉的陀螺,也無法抖落歲月的寂寞。四輪之上的逍遙游,不過是一場睜眼的夢游。那幾年,尤其當家人尚未越洋去相會,這一縷郁郁的漢魂,深切體認了寂寞的意義:絕對的自由,徹底的寂寞。第三次再去火雞帝國,不但寂寞,而且孤高。命運把我的棋子下在西部的首都,城高一英里的丹佛,所謂Mile-High City 。不過這一次我不再逍遙夢游了,只孤懸在落磯峰群 的山影里,兩年悠悠的歲月像一程延長的重九登高,但用以辟邪的不是茱萸和菊酒,而是,你再也想不到吧,西部的民謠、鄉村歌曲、靈歌、藍調、搖滾樂。 其實也不是辟邪,而是抵抗寂寞。**次赴美,我修讀的是現代藝術,但認真聆聽的是古典音樂,從拉摩聽到拉羅,從格希文聽到拉赫曼尼諾夫, 其實大半都不算美國音樂,而現代藝術的大師也輪不到美國人。我只是站在美國的窗口,遙窺歐洲罷了。 第二次旅美那兩年,正當四披頭席卷西方,狄倫也崛起于美國, 我卻仍奉古典音樂的正統,渾不知美國青年側耳傾心的是另一種節奏,和眾而又曲高。第三次才輪到我,一個遲到的周郎,來側耳聽賞。于是從卻克·貝瑞到艾麗莎·富蘭克林,從瓊·拜絲到玖妮·米巧,從漢克·威廉姆斯到唐諾文到亞爾伯樂,我買了近百張的此類唱片。 至于四披頭的唱片,包括那張封套對折的《花椒軍曹寂寞芳心俱樂部樂隊》 ,我更是搜羅齊全。美國知識青年厭棄正統的美國生活格調,有意“去美國化”,而且拔去“黃蜂”(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的毒刺,所發展出來的嬉皮文化甚至反文化,要在這些江湖樂手的琴音歌韻里才能領會。 這種通俗而不庸俗的江湖風格,對我頗有啟發,令我認真思考,搖滾樂何以熱而現代詩何以冷,并且領悟,曲高未必和寡,深入不妨淺出。一九七一年我回到臺灣,一氣呵成的那幾首民謠風的短歌:《鄉愁》《鄉愁四韻》《民歌》《民歌手》,后來果然入樂成曲,匯成了民歌運動,助長了校園歌曲,都是由美國黃蜂社會的此一另類文化所觸發、轉化而來。 3 第三次旅美后回到臺灣,此生的“美國時代”就結束了。后來雖然又多次訪美,但內心的波動已遠不如前,自知新大陸的緣分已盡。一九七四年舉家遷去香港,本以為可以近窺大陸,多了解一點日漸陌生的母親,卻沒有想到,從此竟開啟了去歐洲之門,得以親近另一個舊大陸,西方的大陸。原本要用香港做北望的看臺,不期更進一步,竟找到了西游的跳板。 **次去英國,是從紐約起飛,倫敦入境的。這樣的行程正象征倒溯的懷古。其實當初我去新大陸,也是從西雅圖入境,然后是中西部,*后才是東岸。就懷古之旅而言,那漸入漸深的心情真可謂倒啖甘蔗。 美國東岸的地名,以“新”開頭的不少,大家習以為常,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原名是指何處了。紐約人里有多少說得出“約克”在哪里呢?換了是紐罕布什爾、紐澤西, 恐怕也一樣。我住慣了美國中西部,初去新英格蘭,就處處覺得古舊。在那一帶駕車,加油站的工人竟然對我說:Yes,governor !這“化石口語”據說在今日的英國仍然通用,當時我卻受寵若驚,幻覺是走進了舊小說里,聽人稱我一聲“官人”。 這種古腔英國人也會帶來東方。香港的“收銀處”,中文已經古色古香了,但其旁的shroff 就更加冷僻,連在大字典里都查不到,美國人當然更不認得。 到了倫敦,才會覺得美國有多新,多大,多囂張。英國的計程車是端莊的方軒,司機更像穩健的老紳士,談吐斯文。泰晤士河邊的國會大廈堂皇而不失莊重,那不倒翁的大笨鐘閱世太深,鐘面上卻看不出多少感慨。只有朱紅色的雙層巴士滿街游行,為遲暮而矜持的帝國古都帶來童話的稚氣。唐寧街十號該是全世界*不起眼的首相府了,跟白金漢宮的排場怎么相比?英國官署所在的White Hall 似乎迄無定譯,不知該叫白廳、白堂或白衙。沒有人不知道華府有個白宮,但敢說很少人知道倫敦有個白衙。 中文把美國的總統府譯成“白宮”,歪打正著,恰中洋雞的下懷。美國人盡管標榜民主,潛意識深處仍以帝國自命,但是總不好意思在波多馬克河岸建一座皇宮,也不便在落磯山上蓋一座古堡。其實,他們把甘乃迪與賈桂林是當做金童玉女的帝后來移情的。 不過英國畢竟不算正宗的歐洲。直到一九七八年,我五十歲時,走在香熱里榭 的街頭,甚至登臨凱旋門上,才真有實踐歐土的感覺。如果倫敦是美國人的閣樓,藏著祖父的日記,巴黎就是歐洲人的陽臺,可覽鄰居的花園。巴黎的成功在于包容拔萃,說它是歐洲首府也許還有爭議,但是當歐洲的藝都應該同然。梵谷、畢卡索、夏高、莫地里安尼、史特拉文斯基從各國蜂擁來朝圣,肖邦、王爾德、鄧肯、布朗庫西殊途同歸,都來此安息。 歐洲之子愛倫坡沒有死在巴黎,太可惜了,幸好他終于復活在法國。 凡坐船進紐約港的人,都會仰見矗立的自由女神,一手握著法典,一手高舉著火炬,歡迎前來投奔的移民。那景象太有名了,簡直成了美國的店招,卻是法國人送給美國人的,設計人也是法國雕塑家巴爾托地 。這是法國精神啟發美國的*顯赫地標,但其光芒卻遮蔽了同一造型的雕塑,許多游客竟然不知道還另有一座,具體而微,豎立在塞納河上,格禾納爾橋 畔的一個島上,正是美國人所回贈。 從初踐歐土迄今,我去過的歐洲國家已有十七,約為我周游列國之半;加起來旅歐的時間只有六個月,但啟發頗多。于此十七國中,所見當然有深有淺,淺的像盧森堡,只有一夕,他如丹麥與匈牙利,各僅兩晚;至于意大利,只到了科摩與米蘭,是從瑞士入境,當晚就回露加諾了。 比較深的是西歐的大國,依次是英、法、德、西。我在這四個國家都開過車,也搭過火車。在英國與德國且開過長途;尤其是在德國,從北到南,自波羅的海畔一直到波定湖 邊,縱貫了日耳曼的全長,不但路況完美,秩序井然,而且高速無限,真不愧飆車的“烏托邦”(Autobahn)。德國人在我所見的歐洲人中,是*愛整潔、*守秩序、*為勤奮的民族,一大清早日耳曼人就浩浩蕩蕩,在街上健步來去了。西班牙人正相反,不但早上人少,而且午休很長,晚餐要拖到九點以后,生活節奏一貫的悠悠緩緩,只有斗牛和跳佛拉曼戈 時才使出勁來。 南歐與北歐之分,全憑阿爾卑斯山系,再加上比利牛斯一脈吧。瑞士恰在分水脊上,南下的火車入隧道之前,輪踩的還是德語地區,一出隧道,咦,怎么竟闖進意大利語區了呢?德國跟西班牙的對照,也正是北歐與南歐,新教與舊教,矜持與朗爽,日耳曼子音切磋與拉丁文母音圓融的互異。至于法國,則介乎其間,難以歸屬南北,只能視為西歐。英國更其如此,還帶一點偏北。 相對于西歐,東歐從哪里開始呢?德國以東應該就算東歐了,不但由于地理方位,更因波蘭、捷克、匈牙利與巴爾干各國多用斯拉夫語,對西歐說來顯已非我族類了。我去歐洲二十多年間,前半期多游西歐,后半期也去了東歐,包括匈牙利與捷克,而波蘭與俄羅斯甚至各游了兩次,對這些國家認識更深。 九十年代初,匈牙利開而不放,觀光條件仍差,服務態度生硬而冷漠,但是多瑙河中分的布達佩斯卻難掩國色,臨流自鑒,明艷十分動人。一條斜行的大街以阿提拉(Atilla)命名,而匈牙利人姓在名前,也令我感到驚喜。至于布拉格,早已敞向西歐甚至全世界了,沒有旅客會不喜歡。年輕俊美的海關官員竟然會和旅客開玩笑,反比美國的海關可親。 在布拉格擁擠的地鐵車廂里,一位小學生竟然讓座給我。這種禮貌在“自由世界”也很罕見。華沙的街頭,汽車也非常有禮,常常慢下來,甚至停下來,讓行人過街。莫斯科的麥當勞速食店根本不播音樂,街邊確有乞丐,但那些老嫗的衣衫都樸素而整潔,只靜靜坐著,腳邊放著空盤,并不追纏游客。滿街都是纖修高挑的麗人,輕靈的步態似乎踏著天鵝湖而來,至于小孩子,幾乎找不到一個不好看的。 在圣彼得堡,一位俄國教授請我們去他家做客。狹窄的客廳里臨時搭起一張餐桌,主客六人必須在迫擠的沙發、書架與鋼琴之間繞道而過。那是二〇〇〇年初夏,俄國正苦于糧荒,許多人都被迫上山去采菇充饑了,主人卻罄其所有,做了美味的肥菇與魚湯饗客,我們嚼著、咽著,感動而又不安。想到普希金與托爾斯泰的子孫還有人正蹲在街角行乞,我幾度要掉下淚來。 二次大戰以后,英語與美國文化逐漸風行;所謂英語,其實是美語,這方面的全球化早已開始了。五十年來,臺灣接受西方的影響,主要以美國為門戶,其實美國文化只是西方文化的下游。我去歐洲,乃是溯其上源,正如愛倫坡所喟嘆的:“回到希臘不再的光彩,和羅馬已逝的盛況。”然而迄今我始終無緣去兩地:原本計劃好的亞波羅神廟 之旅,和威尼斯海上之行,先是阻于波斯灣的交兵,繼又挫于南斯拉夫的內戰。 4 另一個舊大陸,近十年來卻不斷召我回去,不是回希臘與羅馬,而是回去漢唐。我曾戲言:“歐洲是外遇”,然則回到自己的舊大陸,該是探親,不,省親了。 自從一九九二年接受北京社科院的邀請初回大陸以來,我已經回去過十五次了,近三年來尤其頻密。例如南京,我的出生地,也是我讀過小學、中學、大學的古城,三年內我就回去了四次,*近的一次是今年五月,去參加母校南京大學的百年校慶。像我這樣在兩岸三校(南大、廈大、臺大)都是校友的人,恐怕很少了。這樣的“圣三位一體”隱喻了我身逢戰亂的少年滄桑,滋味本來是苦澀的,不料老來古幣忽然變成現金,竟然平添出許多溫馨的緣分。在南大校慶的演講會上,我追述這一程夙緣,把“擠擠一堂”的熱切聽眾稱為“我隔代又隔代的學弟學妹”,贏得歷久不歇的掌聲。 十年來我去過的省份,如吉林、遼寧、黑龍江、湖南、山東、廣西,都是**次去;而訪問的名城,如北京、蘇州、武漢、廣州,小時候也無緣一游。聽眾和記者常問我回鄉有什么感觸,我答不出來,只覺得紛沓的記憶像快速的倒帶,不知道該在哪里停格,只知道有一樣東西咽不下去又吐不出來,像苦澀的喉核,那深刻而盤踞的情結,已根深蒂固,要動大手術才鏟除得掉,豈肯輕易被記者或聽眾挖出。若是母親能復活,而我又回到二十一歲,那我就會滔滔不絕,向她吐一個痛快。 我的祖籍福建永春,迄今尚未能回去,每次到廈門,都為行程所限,只能向北遙念那一片連綿的鐵甲山水,也是承堯叔父的畫境。中學時代整整住了七年的四川小鎮,江北縣悅來場,是我記憶的藏寶圖中一個不滅的坐標,也是我近作長文《思蜀》的焦點。我在心底珍藏著它的景象,因為它是我初識造化的樣品,見證巴山蜀水原來就如此,也見證一盞桐油燈映照的母子之情。真希望晚年還有緣回去一吊。 至于常州漕橋,我的母籍兼妻鄉,也是我江南記憶的依托,今年四月五日倒是回去了一趟。那天正好是清明節,我存 和我隨眾多表親與更繁的后輩,去鎮外的葬場掃墓。只見好多位舅舅的葬處,墓簡碑新,顯系“文革”期間從他處匆匆遷來,也就因簡就陋了。小運河仍然在流著,水色幸而不濁,流勢也還順暢,遠遠看得見下游那座斑剝的石橋,小時候那句童謠“搖搖搖,搖到外婆橋”似乎還繚繞在橋欄桿上。此外,一切都隨波逝去了,只留下河邊的一大片菜花田,盛開著那樣恣肆的黃艷,像是江南不朽的早春,對忙于加班的蜂群提醒:“有些東西永遠是不會忘記的。” 鄉愁真的能解嗎?恐怕未必。故鄉縱能回去,時光不可倒流。山河或許長在,但親人和友人不能點穴或冷凍,五十年不變地等你回去,何況回頭的你早已不是離鄉的你了。何況即便是山河本身,也難保不變形變色?洞庭不是消瘦了么,湘夫人將安托呢?再遲去一步,三峽就不再是古跡的回廊了。 所以鄉愁不全在地理,還有時間的因素,其間更綢繆著歷史與文化。同鄉會該是鄉愁*低的層次;高層次的鄉愁該是從小我的這頭升華到大我的彼端。七年前我在吉林作協的歡迎會上,追述自己小時候從未去過東北,但老來聽人唱“長城外面是故鄉”,仍然會震撼肝腸,因為那歌聲已深入肺腑;說著,竟忍不住流下淚來。未來如果有人被放逐去外星,回望地球該也會落淚,那便是宇宙的鄉愁了。 韋莊詞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難道老了再還鄉就不會斷腸嗎?李清照詞卻可以代我回答:“春歸秣陵樹,人老建康城。”就算春色不變,而歸人已老,回鄉的滄桑感比起去國的悲悵,又如何呢? 孩時的舊大陸早已消逝,只堪在吾心深處去尋找。我回到生我育我的南京,但父母和同學都已不在,也沒有馬車轆轆,蹄聲鏗鏗,駛在中山路旁。秣陵樹當然還蔭在兩側,都是劉紀文市長開路時栽植的法國梧桐,但是樹猶如此,還認得當時愛坐在馬車夫旁座的少年嗎? 不,舊大陸我已經回不去了,迎我的是一個新大陸,一個比美國古老得多同時比美洲更新的大陸。高速公路從上海直達南京與北京,鮮明的綠底白字,說,左轉是杭州,右轉是無錫。以前是我在美國,用一本中國地圖來療鄉愁,現在,是我在新建的滬寧高速公路上,把那張地圖攤成廿一世紀明媚的江南水鄉。想不到,六十年代在北美洲大平原上的逍遙游,一轉眼竟能跳接到姑蘇與江寧之間,通向吳越的戰場,六朝的古跡。 是啊,我回去的是這樣一個新大陸:一個新興的民族要在秦磚漢瓦、金縷玉衣、長城運河的背景上,建設一個嶄新的世紀。這民族能屈能伸,只要能伸,就能夠發揮其天才,抖擻其志氣,創出令世界刮目的氣象來。 二〇〇二年六月于高雄 《片瓦渡海》 1 從江北國際機場出來,天已經黑下來了。畢竟是大陸性氣候,正在寒露與霜降之間,夜涼侵肘,告訴遠客,北回歸線的余炎早拋在背后了。明蓉把我們接上工商大學的校車,平直寬坦的高速公路把我們迎去南岸。路燈高而且密,燈光織成繁華的氣氛。不過長途的終點若是一個陌生的城市,而抵達時又已天黑,就會有夢幻之感,感到有點恍惚不安。 說重慶是一個“陌生”城市,未免可笑。少年時代我在這一帶足足住過七年,怎么形容也絕非陌生;但畢竟是六十年前的事情,滄桑之余,無論如何也絕非“熟悉”了。車向南行,漸濃的夜色中,明蓉指著對江的一簇簇摩天樓說:“那邊正是重慶,你還認得出嗎?”我怎么認得出呢?成簇成叢的蜃樓水市,千門萬戶,幾乎都在五十層以上。六十年不見,重慶不但長大了,而且長高了那么多,而且燈火那么熱鬧,反而年輕起來。不但我不敢認他,他,只怕更不認我了吧? 第二天一早,王崇舉校長就來翠林賓館,陪我們夫妻在校園散步。校園很廣,散布在斜向江岸的山坡上,高樓叢樹,隨坡勢上下錯落,回旋掩映,所以散步就是爬山。秋雨霏霏,王校長和我共傘,一面指點著寒林深澗,有山泉泠泠流來,穿石橋更往下注。他又帶我們和徐學轉上一條很陡的山徑,青板石階盤旋南去,沒入蔽天林蔭。他說這條路叫做“渝黔古道”,工商大學的校園正是起點。我們仰望一徑通幽,懷古未已,王校長又帶我們曲折下山,來到一個井旁。那是一口開敞的古井,寬約四尺見方,水面一片虛明。王校長說這是傳說已久的仙泉,飲之可除百病,而且不論雨旱,總是水量飽滿。我立刻用瓢舀了仙水,淺嘗了一口,頓覺清甘入喉,又喂了我存一口。這才注意到附近的瓶瓶罐罐,散置了一地,村民或用手提,或用車推,幾乎不絕于途。黃老之治的校長在一旁顧而樂之,有福與民共享。 兩岸交流以來,這是我第三次訪蜀,卻是**次訪渝。承蒙蜀人厚愛,每一次待我都像游子還鄉,媒體報導都洋溢鄉情。這一次回重慶,前后七天,演講三次,前兩次在工商大學與教育學院,依次是“中文不朽——面對全球化的母語”“詩與音樂”。第三講在三峽博物館,題為“旅行與文化”。此外,工商大學更為我安排了緊湊的日程,先后帶我去了朝天門、瓷器口、悅來鎮、大足石刻博物館、江碧波畫室、重慶藝術學院。 2 凡是未登朝天門北望的人,都不能自稱到過重慶。因為這是水陸重慶的看臺,巴蜀向世界敞開的大門。有人不免會想到三峽,不過三峽長勝于寬,歷史與傳說回音不斷,就像河西走廊一樣,與其說是大門,不如說是長廊。 門謂朝天,據說是明初戴鼎建城,依九宮八卦之數置門十七之多:朝天門在重慶半島尖端,面向帝都金陵,百官迎接御史,就在此門。 細雨灑面,煙波浩渺,嘉陵江從西來,就在廣場的腳下匯入了長江的主流,共同滾滾北去,較清的一股是嘉陵之水,主流則呈現黃褐。江面頗寬,合流處更形空闊。俯臨在水域上空,重慶、江北、南岸,鼎立而三,矗起的立體建筑,遙遙相望,加上層樓背后的山影疊翠,神工之雄偉,人力之壯麗,那氣象,該是西南**。 倚立在螺旋形欄桿旁邊,我有“就位”之感。此刻我站的位置,正是少年時代回憶的焦點,因為兩條大河在此合流,把焦點對準了。人云回鄉可解鄉愁,其實未必。時代變得太快,滄桑密度加深。六十年前,在這碼頭隨母親登上招商局的輪船,一路順流回去“下江”的,是一個十八歲的男孩,勝利還鄉的喜悅,并不能抵償離蜀的依依。那許多好同學啊,一出三峽,此生恐怕就無緣重見了。那時的重慶,盡管是戰時的陪都,哪有今日的重慶這么高俊、挺拔?朝天門簡陋的陡坡上,熙熙攘攘,大呼小叫的,多是黝黑瘦小的挑夫、在滑竿重負下喘息的轎夫、背行李提包袱的鄉人,或是蹲在長凳上抽旱煙的老人。因為抗戰苦啊蜀道更難,我這羞怯的鄉下孩子進一趟城是天大的事,步行加上騎小川馬,至少一整個下午;而坐小火輪順嘉陵江南下,一路搖搖擺擺,馬達聲虐耳撲撲不停,也得耗兩個鐘頭。那時候,泡茶館是小市民主要的消遣;加一包花生、瓜子或蠶豆,就可以圍著四方小桌或躺在竹睡椅上,逍遙半個夏日,或打瞌睡,或看舊小說與帝俄小說的譯本,或看晚報,或與三兩好友“擺龍門陣”。這一切比起今日的咖啡館、火鍋店,似乎太土太老舊了,但今日的重慶,新而又帥,高而又炫,卻無門可通我的少年世界。 不過倚望著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我仍然有“歸位”的快感。人造的世界雖劇變而難留,神辟的天地仍鑿鑿可以指認。腳下這兩條洪流,長江遠從漠漠的青藏高原,嘉陵江遠從巍巍的秦嶺,一路澎湃,排開千山萬壁的阻礙,來這半島的尖端會師,然后北上東去,去撞開三峽的窄門,浩蕩向海。這千古不爽的約會,任何人力都休想阻擋。如果黃河是民族的父河,長江該是民族的母江,永不斷奶,永遠不可以斷奶。江河是山岳派去朝海的使者,支流與溪川,扈從無數。嘉陵江簇擁著長江,是何等壯闊的氣派,這氣派,到下游漢水率百川來追隨,我也曾在晴川閣上豪覽。 我這一生,不是依江,便是傍海,與水世界有緣。生在南京,童年多在江南的澤國,腳印無非沿著京滬鐵軌,廣義說來,長江下游是我的搖籃、木馬。抗戰時期,日本人把我從下游趕來上游,中學六年就在這腳下茫茫的江水,嘉陵投懷于母水的三角地帶,濤聲盈耳地度過。戰后回到石頭城,又歸位于浩蕩的下游。所以我的早年歲月,總離不開這一條母河。至于其余歲月,不是香港,就是臺灣,河短而海闊,一條水平線伴我,足足三十二年。 而今重上朝天門,白首回望,雖然水非前水,但是江仍故江,而望江的我,盡管飽經風霜,但世故的深處仍未泯,當年那“川娃兒”躍躍的童心。
尺素寸心 作者簡介
余光中(1928—2017) 文學家、詩人、學者、翻譯家。 生于江蘇南京,祖籍福建永春。曾任臺灣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 一生從事詩歌、散文、評論、翻譯的創作,在華語世界影響深遠,其作品被廣泛收錄于語文課本中。 代表作品有《白玉苦瓜》《鄉愁》《聽聽那冷雨》等。
- >
苦雨齋序跋文-周作人自編集
- >
史學評論
- >
巴金-再思錄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朝花夕拾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裝共3冊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中國歷史的瞬間
- >
有舍有得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