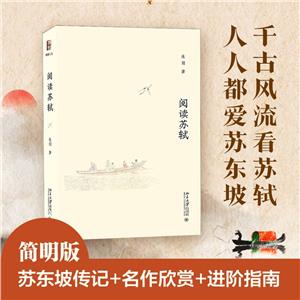-
>
魯迅全傳:苦魂三部曲-增訂版(全三冊)
-
>
大家精要- 克爾凱郭爾
-
>
尼 采
-
>
弗洛姆
-
>
大家精要- 羅素
-
>
大家精要- 錢穆
-
>
白居易:相逢何必曾相識
閱讀蘇軾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1333822
- 條形碼:9787301333822 ; 978-7-301-33382-2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閱讀蘇軾 本書特色
1. 作者是復旦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授,著名的蘇軾研究專家,文津圖書獎獲得者; 2. 簡明版蘇東坡傳記+名作欣賞+進階指南; 3. 全書選配了大量書法、繪畫、版刻名作,精裝印制,可讀可藏; 4. 內文采用微涂超感紙印刷,能更好地展現圖片效果。
閱讀蘇軾 內容簡介
蘇軾在詩、詞、文、書、畫各方面的成就如何?蘇軾在政治上有哪些才能?為什么說“烏臺詩案”是蘇軾人生的轉折點?如何評價蘇軾的一生?為什么人人都愛蘇東坡?除了蘇軾成就非凡以外,還因為他作品中的思索和關照,總能觸動人心,他的創作和人格,光輝璀璨,跨越時空,千百年后,依然令人敬仰。本書是復旦大學朱剛教授寫給大眾的蘇軾讀本,全書分為四部分,**部分是簡明版的蘇軾傳,敘寫了蘇軾特立獨行的人格,狂放不羈的個性,博大的心靈世界,以及無人企及的藝術成就;第二部分是“作品賞析”,全面深入地分析了蘇軾的代表作;第三部分“名家視角”,選取了黃庭堅和王水照的文章,第四部分“蘇軾年譜”,能幫助讀者全面而深入地理解蘇軾。
閱讀蘇軾 目錄
一 蘇軾傳 / 001
1. 科舉士大夫 / 003
2.“變法”風潮 / 013
3. 東南**州 / 021
4.“烏臺詩案” / 027
5. 東坡居士 / 036
6.“廬山真面目” / 058
7. 王、蘇和解 / 070
8. 元祐大臣 / 077
9.“還來一醉西湖雨” / 085
10. 萬里南遷 / 092
11. 海角天涯 / 106
12. 走向生命的完成 / 116
二 作品賞析 / 127
江城子·密州出獵 / 129
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 136
日喻 / 142
定風波 / 150
后赤壁賦 / 158
如夢令二首 / 172
試筆自書 / 177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 182
三 名家視角 / 187
黃庭堅《東坡先生真贊》 / 189
王水照《蘇軾的影響》 / 191
山本和義《詩人與造物》 / 195
四 蘇軾年譜 / 209
閱讀蘇軾 節選
就在這建中靖國元年(1101)的正月,蘇軾終于越過大庾嶺,進入今江西境內。然后,經虔州(今贛州)、廬陵(今吉安),從贛水過鄱陽湖而入長江。他在江西的時候,碰上了司馬光的忠實弟子,元祐黨爭中*強悍的政敵劉安世,此時也從嶺南獲釋北歸。蘇軾邀請他說:“附近的山里有一位玉版禪師,我們可去同參。”對禪宗也有興趣的劉安世欣然同往,但蘇軾卻把他引入一片竹林,挖出新生的竹筍煮了吃。劉安世問玉版禪師在哪里,蘇軾指著白皙的竹筍,說這就是玉版禪師,禪味極佳。二人放懷大笑,盡釋前嫌。劉安世后來很長壽,其晚年的言行,被弟子記錄為《元城語錄》,其中對東坡的評價甚高。 舟入長江的蘇軾,繼續東行,至當涂、江寧府、儀真、金山等地,直至他終焉之地的常州。據說,他“初復中原日,人爭拜馬蹄”(釋道潛《東坡先生挽詞》),引起人們極大的關注。當他舟行至常州時,“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運河岸,千萬人隨觀之。東坡顧坐客曰:‘莫看殺軾否?’其為人愛慕如此”(邵博《邵氏聞見后錄》卷二十)。仿佛頗有一點當年司馬光回京的聲勢,但他本人應該越來越清楚“建中”之政的內在含義,知道朝廷并不需要和歡迎他上京去“更化”。所以,越往北走,他的步伐就變得越滯重。他逐漸確定此行的終點在潁昌府,以便與蘇轍會聚。 但時局的變化說明定居潁昌府還是奢望。在“建中”路線下被重新起用的“舊黨”人物有著強烈的“邪正”觀念,在他們看來,“新黨”的人物都是“小人”,不可共事。他們一旦被起用,所表達的愿望就不僅僅是“建中”而已。這不但違背了曾布的意愿,也引起徽宗皇帝的反感,因為他雖然討厭章惇,但以庶子入嗣大統的他絕不能落下任何不尊敬神宗的口實。于是“新黨”臣僚再次醞釀起“紹述”之議,以迎合徽宗,使政局再度轉向不利于“舊黨”的方向。在此期間,據說蔡京對徽宗寵信的宦官童貫做了有效的工作,這可能也是局面轉向“紹述”的原因之一。當蘇軾獲取了這些信息后,便只好放棄定居潁昌府的打算,因為那里離京城太近,容易招惹麻煩。 同時,蘇軾的身體狀況也不允許他再投入嚴酷的政治斗爭了。六十六歲的年齡,在當時已算高壽;又從瘴癘之地的嶺南返回,已身染瘴毒;一年來行走道途,以舟楫為家,生活極不安定;時值盛暑,河道熏污,穢氣侵人——他終于病倒了。 自建中靖國元年六月一日在長江上喝了過多的冷水,半夜暴下(痢疾)起,他就處于與病魔搏斗的狀態。他懂得醫術,能自己開藥方,吃了黃蓍粥,覺得稍為平復。但幾天后到儀真,“瘴毒大作”,腹瀉不止。從此又胃部悶脹,不思飲食,也不能平臥,只能端坐喂蚊子,病情增重。以后病況時增時減,到六月十五日舟赴常州,賃居于孫氏館(即今常州市內延陵中路的“藤花舊館”遺址,現建為東坡公園),便向朝廷上表要求“致仕”(即退休),做了退出政界的*后打算。此時,曾經殘酷迫害“元祐黨人”的章惇,反過來被貶謫雷州,他的兒子章援是蘇軾元祐三年主持科舉時錄取的進士,據南宋筆記《云麓漫鈔》所載,章援致書于蘇軾,訴說了他們父子的困境,而蘇軾“得書大喜”,馬上復信,說自己與章惇交友四十年,雖因政見分歧而處境互異,但并不影響私交。他還抄寫了一個養生的藥方,贈送章氏。——這是蘇軾一生中,從嚴重傷害過自己的政敵身上爭取到的*后一份友誼。 轉眼至七月,天雖大旱,但蘇軾的病勢卻在立秋日(十二日)和十三日遞減,實非吉象,而是回光返照。果然,至十五日病勢轉重,一夜之間發起高燒,齒間出血無數,到天亮才停止。他認為這是熱毒,當以清涼藥醫治,于是用人參、茯苓、麥門冬三味煮濃汁飲下。但藥物勿靈,氣浸上逆,無法平臥。晉陵縣令陸元光送來“懶版”,類似于今日的躺椅。七月二十八日,一代文宗就在這“懶版”上溘然長逝。 據清代林昌彝《射鷹樓詩話》卷七的說法,蘇軾自病自診,用藥有誤。他認為蘇軾原本中有熱毒,卻因飲冷過度而受病,乃是“陽氣為陰所包”,應以服“大順散”為主,“而公乃服黃蓍粥,致邪氣內郁,豈不誤哉?……后乃牙齦出血,系前失調達之劑,暑邪內干胃腑,法宜甘露飲、犀角地黃湯主之,乃又服麥門冬飲子,及人參、茯苓、麥冬三味,藥不對病,以致傷生,竊為坡公惜之”。其說可備參考。也許,蘇軾用藥有誤是加速死亡之一因吧。 不過,蘇軾給自己開出藥方的同時,也是做好了走向生命完成之準備的,在此時與友人往來的許多書簡中,我們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他清醒地直面著生死大事。到彌留之際,除了因不能與蘇轍面辭而感到痛苦外,其他一無牽掛。后來蘇轍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里記述其臨終情狀云:“未終旬日,獨以 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后事,不答,湛然而逝。”面對死亡,他平靜地回顧自己的一生,光明磊落,無怨無悔,自信死亡也不會令他墜落黑暗之中,所以告誡家人不必哭泣,以免生命化去之際徒受驚擾。他只愿以*平淡安詳的方式無牽無掛地告別人世。當時黃庭堅也聽常州來人相告后說:“東坡病亟時,索沐浴,改朝衣,談笑而化,其胸中固無憾矣。”(《與王庠周彥書》)他對生命意義的透辟理解,他對人類自身終極關懷的深刻領悟,消融了瀕死的痛苦和對死亡的恐懼。“湛然而逝”“談笑而化”,他的確毫無遺憾地走向自己人生旅途的終點。 蘇軾面對死亡的這種心態,我們從他留下的*后作品,即其絕筆詩《答徑山琳長老》中也可看到。“琳長老”是云門宗禪僧徑山維琳,蘇軾在杭州的時候聘他做了徑山寺的住持,此時聽說蘇軾在常州病危,便于七月二十三日趕來相訪。夜涼時分,二人對榻傾談。維琳已經了解東坡的病情,他是專程為東坡居士的生死大事而來的(按當時的習慣,臨死的人身邊不能缺少一個宗教徒的)。二十五日,蘇軾手書一紙給維琳云:“某嶺海萬里不死,而歸宿田里,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細故爾,無足道者。”(《與徑山維琳二首》之二)已覺大限將至,而心態平和。二十六日,維琳以偈語問疾,東坡也次韻作答,就是《答徑山琳長老》: 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電往那容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平生笑羅什,神咒真浪出。 蘇軾清楚地記得維琳與他同齡,都是丙子年(宋仁宗景祐三年)所生。他先粗略地計算了一下他們生命的長度,三萬日不為不多,如果每天誦讀一千首偈語,則積累的佛學修養已經甚深,但此時回顧,則如閃電一般,迅疾而去了。對此無奈之事,東坡表現得甚為平靜。五、六兩句才是正式回答“問疾”的。疾病就是人身的機體出了問題,所以要追查這人身的來歷。人身本來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由自然的各種元素構成,其本質與自然無異,原不該與自然產生各種矛盾,當然也無所謂疾病。 但這些元素一旦匯合為一個人身,這個人身卻產生了意志、欲望,把自己從自然中分離出去,通過種種方式來破壞和占有自然物,并且幻想長久擁有這身體,從而,不但與自然產生矛盾,與同類也產生矛盾,患得患失,而不可避免地遭受疾病。故關鍵在于“有身”,即因此身存在的自我意識而引起的種種滿足自身的欲望。只有消去人身上這些與自然不符合的東西,才能根本地解脫疾病,而回歸生命與自然的本來和諧。就如《老子》所言:“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結尾“平生笑羅什”兩句,維琳看了后覺得難以理解,蘇軾索筆一揮而就:“昔鳩摩羅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誦以免難,不及事而終。”這鳩摩羅什是印度僧人,十六國時來到中國,傳播大乘佛教,臨終時令弟子們朗誦神咒,想以此延續生命,但沒有成功。蘇軾的意思是,那位高僧真不該作此無益之舉!這表示他認為用不自然的方法勉強延續生命是無益的。 據宋代傅藻的《東坡紀年錄》、周煇的《清波雜志》等書記載,東坡七月二十八日去世之際,是“聞根先離”,即聽覺先失去的。當時,維琳對著他的耳朵大聲喊:“端明宜勿忘西方!”大概維琳這位禪僧已經頗混同于凈土宗的觀念,故要在蘇軾臨死時提醒他及時想念西方極樂世界,以便他能夠往生。不過東坡似乎更理解禪宗“無念”的本旨,喃喃回應道:“西方不無,但個里著力不得。”在旁的錢氏朋友說:“固先生平時踐履至此,更須著力!”東坡又答道:“著力即差。”語畢而逝。既然像鳩摩羅什那樣以不自然的方法來延續生命是徒勞的,那么致力于往生的想念,不自然的“著力”也是徒勞的,東坡更愿意以了無掛礙的心態乘風化去。 蘇軾去世以后,所謂“建中”之政也在當年結束,次年改元“崇寧”,即尊崇熙寧之政,“新黨”大獲全勝,蔡京入朝,將“元祐黨人”的名單刻石頒布,曰“元祐奸黨碑”,蘇軾列名于顯要的位置,其文集、著作皆遭禁毀。而此時的蘇軾,已安眠于汝州郟城縣小峨眉山,這是蘇轍遵其兄長的遺囑主持安葬的。十余年夜雨蕭瑟之后,蘇轍亦安葬于此地,兄弟終于團聚。
閱讀蘇軾 作者簡介
朱剛,1969年生于浙江紹興,1987年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1997年獲博士學位。現為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宋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蘇軾學會副會長。著有《唐宋四大家的道論與文學》《蘇軾評傳》《宋代禪僧詩輯考》《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中國文學傳統》《蘇軾蘇轍研究》《蘇軾十講》《唐宋詩歌與佛教文藝論集》等。
- >
新文學天穹兩巨星--魯迅與胡適/紅燭學術叢書(紅燭學術叢書)
- >
姑媽的寶刀
- >
二體千字文
- >
隨園食單
- >
山海經
- >
經典常談
- >
龍榆生:詞曲概論/大家小書
- >
回憶愛瑪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