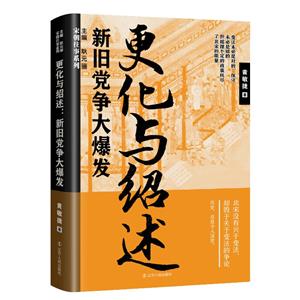-
>
清通鑒(全四冊)(精裝)
-
>
明通鑒(全三冊)(精裝)
-
>
跨太平洋的華人改良與革命 1898-1918
-
>
天有二日(簽名鈐印特裝本)
-
>
歐洲至暗時刻(1878-1923):一戰為何爆發及戰后如何重建
-
>
(精裝)奧托·馮· 俾斯麥與德意志帝國建立
-
>
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宋朝往事系列:更化與紹述--新舊黨爭大爆發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5105464
- 條形碼:9787205105464 ; 978-7-205-10546-4
- 裝幀:一般輕型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宋朝往事系列:更化與紹述--新舊黨爭大爆發 本書特色
變法未必是對的,保守未必是錯的 但搖擺不定的政策耗盡了北宋的能量
宋朝往事系列:更化與紹述--新舊黨爭大爆發 內容簡介
北宋后期的近半個世紀,是政治家們的理想與現實碰撞的時代。北宋元豐八年,哲宗以年幼即位,高太后垂簾聽政,朝廷開始全面否定熙豐新政,史稱“元祐更化”。高氏去世后,哲宗、徽宗兩兄弟,懷著繼承父志的理想,走上了兩條截然不同的“復興”之路。在哲宗短暫的親政歲月中,著眼于對熙豐條法的恢復,卻造成了嚴重的新舊黨爭。而徽宗在漫長而活躍的皇帝生涯中,為了超越父兄之治也是新政迭出,*終卻令大宋頂著虛假太平的帽子轟然倒塌……
宋朝往事系列:更化與紹述--新舊黨爭大爆發 目錄
引子 神宗的遺產 / 001
**章
女主初垂簾 / 018
一、高后可以依靠誰 / 018
二、更化之士聚洛陽 / 037
三、更化還是食古不化 / 047
第二章
“女中堯舜” / 056
一、“恬退”之人試掌舵 / 056
二、一再錯過的和解契機 / 063
三、簾前簾后眾生相 / 081
第三章
更化卻以“紹述”之名 / 096
一、“退三奸,進三賢” / 096
二、廟堂之側與江湖之遠 / 109
三、又一次轉瞬即逝的“和解” / 124
四、留政不留人 / 137
第四章
皇帝的“覺醒” / 150
一、更化的車輪 / 150
二、致君堯舜 / 169
三、望其臀背 / 190
四、“紹述”了什么? / 207
尾聲 不是不想“建中”與“靖國” / 225
后 記 / 237
宋朝往事系列:更化與紹述--新舊黨爭大爆發 節選
大宋元豐八年(1085)早春時節,這是后來被稱為神宗皇帝的趙頊統治宇內的第十九個年頭,汴梁古城似乎一切如常,但一切又似乎并不如常。 首先是大遼賀正旦使和副使在去年十二月抵達京師時,皇帝照常在紫宸殿接見他們,宣坐賜茶,但到今年正月初六,這些來賀新年的使節辭行時,皇帝卻既沒有在紫宸殿接見他們,也沒有由執政大臣在都亭驛賜宴餞行。上一次出現這種情況,還是在神宗的父親英宗皇帝病重的時候。 宋人稱大年初一為“正旦”,按常例,這天是舉國同歡的日子,皇帝將會在大慶殿舉辦大朝會,皇宮外將一早就車水馬龍,百官經“趨朝路”入宮賀正旦,然后到內東門拜表賀皇太后,遼國等各國的賀正旦使也會出席朝賀,諸路舉人、解首亦士服列班,而諸州長吏的賀表,也就是祝賀正旦的奏章也會在這天之前紛紛抵達京師。 但今年與往年不同,今年的正旦靜悄悄。 而且,初六那天,東京汴梁的宮觀、寺院突然大設消災祈福道場;初七,皇宮中還宣布大赦天下。大赦的由頭,據說是因為“屢獲豐年,中外安定美好,適逢和煦的春天到來,需要把皇帝的恩澤廣布海內”,但種種異象,讓敏感而且消息靈通的京城百姓議論紛紛。有的說,初三那天就聽說今上病重了,兩府大臣,也就是門下、中書、尚書三省加上樞密院的長官都已經進入內東門去問安了;有的說,何止呀,首相王相公在別的執政大臣解散后,還跟著大珰(宋人對大太監的稱呼)進了福寧殿東寢合去看望皇上,看來情況很不妙啊。現在,皇上已經下詔休息五日,都不能上朝了!可見那些道場、大赦,其實就是為皇上的病祈福的呀。 京城百姓的傳聞都沒錯,趙頊是真的病了。而且他起病并不突然。早在去年,也就是元豐七年(1084)秋宴的時候,他就“感疾”。此后他還表示,等過年后就立儲,還說到時就請司馬光和呂公著為太子的“師保”。他的這番話,著實嚇壞了當時的首相王珪和次相蔡確。 當時,趙頊虛歲才三十八,本是年富力強的時候,他的長子趙傭,也就是后來的宋哲宗,虛歲才八歲。按常理說,在位的皇帝都不想過早立太子,以免到自己老年時太子羽翼豐滿,反而成為自己的威脅。那么,是什么病使當時已有多名子女,年紀又尚輕的國君突然想到立儲呢?由于史料中秘而不宣,我們現在已經無法確切得知。但有一點很明顯:趙頊在元豐七年(1084)秋宴前后所犯的病,的確不是偶感風寒這么簡單,而是一種讓趙頊自己意識到需要對后事有所準備的大病。 盛年皇帝突然立儲雖然不太正常,卻并非沒有先例。讓蔡確等人高度警惕的,是趙頊提到的由司馬光與呂公著兩人任太子師保之事。師保實際上就是教輔太子的老師,在宋代,太子老師的職名有直講、翊善、贊讀、記室參軍等,往往由皇帝親自挑選士論公認的學行修明、出類拔萃的大臣來擔任。成為太子的師保之后,這些大臣就經常能與太子坐而論道,以道德文章陶冶太子的性情,讓他體悟治國之正道,如果師保們與太子關系好的話,他們的政治理念對太子的影響將十分深遠,而且只要太子順利登基成為新皇帝,師保也往往會成為新皇帝*信任與倚重的人。 然而,神宗提到的這兩名大臣,都是在神宗任用王安石進行變法的初期就已經旗幟鮮明反對變法的人。王安石甚至說,重用司馬光就相當于“為異論之人立赤幟”,即為反對變法的人們立一個標桿,是不利于變法的。后來,呂公著被莫名加上“污蔑韓琦”的罪名而被貶出朝廷,而司馬光則在被神宗提拔為樞密副使后,終因神宗不聽其廢除新法的建議而自請出守外郡。但是,神宗對司馬光的眷顧不減。 司馬光所任職的永興軍(治所在今陜西西安市)緊鄰西北前線,他到任之后,切身體會到當地百姓的困苦,而對西北用兵的準備更增加了當地百姓的負擔。他認為新法的很多措施并不利于當地的社會,所以他不停上章反映、勸諫。而神宗一方面對他禮貌而優待,另一方面卻對他的意見一再置若罔聞。*后,司馬光憤而辭任,領了一個“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的閑職,在洛陽閑居。這一去,就是近十年。 但這期間,神宗并沒有忘記司馬光。到元豐五年(1082),神宗親手制定新的官制時就曾說過,新的官制推行時,就要將支持新法的“新人”和反對新法的“舊人”摻雜著使用。還說御史臺的*高長官御史中丞這個職位,非司馬光莫屬。 其實,從神宗推行變法以來,無論是認同變法的,還是反對變法的大臣,在執行中央決定的這十幾年間,都對新法有了程度不同的新看法。但有幾個人,自始至終完全反對新法,這里面就包括司馬光、王巖叟等人。所以,聲稱要召回司馬光這位“異議”的旗幟,讓宰執們感到難以理解。次相蔡確連忙以“國是方定”為由,希望神宗能推遲一點做決定。司馬光所任的這個“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的任期是三十個月,眼見他已經準備第四次任此職。這一次,神宗雖然同意延后把司馬光召回京師,卻又留了一個口子。他讓司馬光這一個任期滿后,“不候替人,發來赴闕”,也就是說,在神宗心目中,這將是司馬光賦閑的*后三十個月,之后,皇帝就將起用他。 突然想到要重新重用反對變法的領軍人物,這表示什么?是暗示神宗對自己此前十多年的路線、對新法產生了動搖嗎?神宗提出這個計劃的元豐五年(1082),又是個什么時間節點呢? 這不得不說到神宗所屬的世系和“原生家庭”給他帶來的心結。 我們都知道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身故后,并未傳位給自己的兒子,而是傳位給弟弟晉王趙光義(后改名炅),是為宋太宗。太宗繼位之前發生過兩件撲朔迷離的事件。一件是太祖、太宗二人的生母杜太后指定太祖要傳位給弟弟的“金匱之盟”,有多人懷疑它的真實性;另一件是太祖身故當晚曾與太宗獨處,*后有人看到窗內燭影下兩人奇怪的舉動與聲音,然后太祖就去世,這是所謂的“燭影斧聲”事件。這兩件事使得太宗的繼位過程充滿疑云。雖然當時的人都對此深加隱諱,但不難想見的是,太宗在繼位后,后半生都一直處于繼位合法性遭質疑的陰影之中。而*有希望使太宗擺脫這一陰影的,莫過于在軍事上擊敗遼人,使大宋能收復幽云十六州這樣的歷史功績了。因此,在迫使吳越納土,吞并了南方數個政權后,太平興國四年(979),太宗就開始率軍親征北漢,滅北漢后又不顧群臣的反對,立即揮師伐遼。只是這次北伐的結果卻是三軍敗績,太宗負傷而逃,不但收復“漢唐舊地”、使自己一脈血緣發揚光大的夢想沒有實現,還使后世的坊間演義又多了一個想象性的疑問——假如當初北伐的是趙匡胤而不是趙光義呢? 后世的好事者對太宗北伐的失敗心有不甘,而作為太宗一脈的后人,虛歲二十就登基的宋神宗來說,就更是如鯁在喉。據滕甫(即滕元發)回憶,神宗剛繼位的時候,“慨然有取山后之志”。宋人以太行山為坐標,把幽云十六州中靠東南的檀、順、薊、幽、涿、莫、瀛這七州稱為“山前”,把靠西北的儒、媯、武、新、云、朔、寰、應、代九州稱為“山后”。滕甫早年在通判湖州時,已經被世人稱贊為“奇才也,后當為賢將”,可見有一定的軍事才能。神宗剛繼位,就重用滕元發,希望他能來輔助自己完成太宗未竟的事業。一天,神宗和滕甫聊起遼朝之事,動情地說:“太宗從燕京城下潰敗,遼兵一路追擊,宋軍臨時指揮中心的寶器、儀仗、侍從、宮嬪全部被劫奪,太宗自己還身中兩箭,僅能保命逃回來,而且箭傷年年復發,*后還因此而奄棄天下,可見遼人與我們大宋有不共戴天之仇。而現在我們卻反而要年年奉獻數十萬金帛給他們,把他們稱為叔父,我們做子孫的,能這樣嗎?”說完,痛哭失聲。要知道,那時他其實只不過是一位年僅十九歲的少年。 另一件讓這位少年無法釋懷,更讓他注定無法做一位安享太平的守成之君的事情,就是他父親英宗的遭遇與行為。 趙頊的父親宋英宗并非宋仁宗趙禎所生,而是仁宗的堂兄趙允讓之子。仁宗無子,因此按皇室慣例,曾把他接進宮中撫養了數年,賜名宗實。但當仁宗的親生兒子出生,趙宗實又被送回到生父趙允讓身邊。*后,仁宗的所有兒子都夭折,而且自己也得了重病,才不得不重新宣詔趙宗實入宮,并立其為皇子,改名趙曙。 從幼年被選入皇宮撫養開始,隨著仁宗親生兒子們的生生死死,趙曙的命運就不斷出現起伏與波折。他既不敢確定自己就是皇子,但又不能安穩地只做趙允讓的第十三子,據說他的兄弟也因其特殊的遭遇而妒忌、排斥他。而這種未定的身份既可能引人攀附,從而招來橫禍;也可能引人構陷,然后同樣是招來橫禍。因此英宗在正式繼位之前,不但其對家庭的身份認同出現嚴重的問題,而且由于長期的小心翼翼和對前途命運的擔憂,他變得非常神經質。*終,在趙曙正式成為皇帝后,沒幾天,他就開始得病,無法理政,也無法主持仁宗喪事中的很多環節,只能由英宗的養母,也就是仁宗的遺孀曹太后垂簾聽政,處理國事。 英宗的病情一直時好時壞,與曹太后的關系更是每況愈下。英宗的皇后高氏,本來是曹太后的外甥女,從小入宮,在曹氏身邊長大,與英宗曾是青梅竹馬的玩伴。但這時高皇后卻也與英宗一樣,與曹太后不和。在太后垂簾這段時間,宮中由此鬧出不少矛盾。好不容易英宗病好了,卻又執意要稱自己的生父濮安郡王趙允讓為“皇考”,由此又引發了持續近兩年的“濮議”風波。朝中大臣分為對立的兩派,相互攻訐,皇室禮議成為街頭巷尾的談資怪聞。*關鍵的是,這一次關于濮王身份的大討論,牽扯了大量的人力與行政資源,毒化了仁宗以來的政治氛圍,削弱了臺諫系統對皇權的約束,*終,等到濮議結束,英宗終于準備把精力放在治國理政上的時候,他的生命已經剩下*后幾個月了。 趙頊隨父親入宮時,虛歲十五,已經開始懂事了。這一切,作為長子的趙頊統統看在眼里。他心知朝廷中人對自己父親的觀感,也明白自己的父親實在算不上一位稱職的皇帝;而且,父親既然已經過繼給了仁宗與曹氏,在禮法上就是仁宗與皇后曹氏的兒子,但他既借病不為仁宗主持虞祭儀式,又與養母曹氏關系鬧僵,還執意要抬高自己的生父濮王的身份地位,因此也不能被稱為孝子。他為此而憂心。但他能做的,也只能是自己做得更好:代替父親,與曹氏、高氏搞好關系;與趕走臺諫、執意不聽建議的父親不同,趙頊苦學儒家經典,以嚴格的禮儀去善待自己的老師。據載,他剛跟隨父親入宮的時候,還未“出閣”,也就是搬出皇宮住到自己的王府里去,而是和兩位弟弟一起暫且在皇宮內居住與讀書。父親趙曙與曹太后關系的緊張,也影響了曹太后對趙頊的態度。趙頊的伴讀官韓維等人提醒他:“皇上已失太后的歡心,大王您更應該恭順孝敬太后,做些彌補,否則,你們兩父子都會受禍啊!”趙頊聽了大受震動,對曹氏就更孝敬了,曹氏有一天對宰輔大臣們說:“王子*近對我特別有禮,肯定是你們為他選的伴讀官員教得好。等哪天召他們到中書褒獎一下才行啊。”到嘉祐八年(1063)十二月,趙頊出閣辭別曹太后與母親的時候,“悲泣不自勝”,“太后亦泣”。再后來,趙頊自己成了皇帝多年后,養祖母太皇太后曹氏辭世,他還反復哀傷了很久,每次經過太皇太后曾經居住的宮殿,都還忍不住流淚。可見至少他自己與養祖母曹太后之間的感情還是比較深厚的。 治平四年(1067)正月,終于決心要做一個好皇帝的宋英宗,在尚未有真正的治跡證明自己的時候撒手人寰,被他留在身后的,是捉襟見肘的財政,是濮議后分裂的人心,是市井之間關于他孝與不孝的流言,以及把他這位繼承者與他人氣極高的養父仁宗作對比時的尷尬。 趙頊能怎么辦呢?做一個“大有為”之君,洗刷附著在父親與祖宗身上的恥辱,證明他們這一系的血統也是高貴的,也是能對大宋有卓越貢獻的,恐怕就是唯一的選擇。為此,他也已經準備了多年。史稱他從小“好學不倦”,還在皇宮中就讀的時候,常常拉著學官請教問題,天色已晚仍不肯停下來吃飯,直到英宗派內侍去催他;到他做皇帝后,每天都到邇英殿聽侍講大臣的講讀,風雨無阻;而且,就算是晚上回到宮禁之中,他也沒有休息,反而是讀書到半夜。他是勤勉的,好學的,也是志向高遠的。他雖然年紀輕輕,但已經達到“言必據經”的程度,而且每逢與大臣一起講論經史,總能有些出人意料的見解,但他的涉獵卻遠不止儒家經典。還在做皇子的時候,他甚至親手抄錄韓非子的著作。身為一個儒家的皇子,卻悄悄喜歡法家的理論,為了什么?不正是因為誕生于戰國的韓非,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圖治、變法圖強、以法制與君權駕馭群臣,*后達到國家的強大與統一的主張嗎?少年皇子對此心馳神往,青年皇帝也因此知遇王安石。 是的,一開始,他感覺只有王安石才能理解他,才能扶助他到達富國強兵、“收復漢唐故地”的彼岸。制定保甲法的時候,他倆曾有一個遠大的構想:先全國編排保甲,以解決治安問題,獲得穩定的基層社會;然后,沿邊各路開始對保甲人員進行軍事訓練,讓那些訓練成績好的保甲人員先跟隨本地的巡檢、縣尉“上番”,也就是值勤,這又代替了部分土兵、弓手,節約了本來要支付給土兵、弓手的錢糧;*后,就是逐漸使保甲成為民兵,成為禁軍的輔助隊、預備隊,一來逐漸代替老弱的禁軍,節省軍費,二來又可以與禁軍競爭,消解五代以來募兵的軍紀松弛、不受約束的“驕志”。同時,再輔以精簡禁軍的“揀兵并營”之法和使將帥更熟悉部隊的將兵之法。這可是涉及從農村社會到邊防、財政的宏大改革,如果成功,那經制西夏、削弱遼國就指日可待了。
宋朝往事系列:更化與紹述--新舊黨爭大爆發 作者簡介
黃敏捷,歷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后,中山大學南方學院講師。學術興趣點主要在近古財政、賦稅與基層社會研究,對政治、經濟變革也頗懷好奇,在《文史哲》《史學月刊》《史林》《中國經濟史研究》《安徽史學》等刊物發表論文多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一項、省部級基金一項。
- >
羅庸西南聯大授課錄
- >
伊索寓言-世界文學名著典藏-全譯本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大紅狗在馬戲團-大紅狗克里弗-助人
- >
史學評論
- >
龍榆生:詞曲概論/大家小書
- >
詩經-先民的歌唱
- >
中國歷史的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