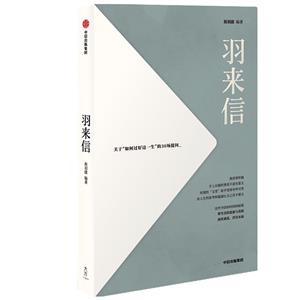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羽來信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1734850
- 條形碼:9787521734850 ; 978-7-5217-3485-0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羽來信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A. 核心讀者:作者粉絲 B. 20-28歲年輕文藝女性、大眾文學愛好者、生活方式愛好者 C. 對3◆祝羽捷shou部書信集,我們該如何過好這一生。30場提問,深度關聯當下困惑,嘗試在焦慮與搖擺中找到某種確定性,為人生尋找合適的坐標系。 ◆陳嘉映/閻連科/陳曉卿/吳曉波/翟永明/韓松落/苗煒/石康/路內/葛亮/鄭執/黎戈……等30位學者、作家、藝術家共同拆解:關于文藝青年之痛,關于怎樣面對低谷,關于焦慮與被定義、抑郁與社恐、理想主義與金錢觀、逃離北上廣還是選擇小鎮……你正在苦惱的問題,也許就在其中。 ◆我們也許不能改變世界,但至少可以理解自己。這些書信如時間的暗渠,將對生活的思索與真相,抽絲剝繭,浮出水面。 ◆把困惑變成自己的方法,將提問化為篤定的回答。抵住平凡和重復的磨損,專注于眼前對抗龐大、蕪雜、紛繁的外界,在大同小異的生活里找到激情和智慧。 關于低谷,她說: 遠方的人們和你有著別無二致的困惑,彼岸未必比此岸更美,你所躲避的很有可能改頭換面再次襲來。 關于自己,她說: 或許我們永遠都做不了那個“*好”的決定,但是沒關系,你不必事事完美。 關于焦慮,她說: 沒有所謂正當的生活,也沒有*好的時代,我們沒有必要為此焦灼,但如果無法避免焦灼,那就享受焦灼,一半尋覓,一半抵御。 ◆復古式信封書衣設計,重現人與人交流的誠懇與溫度。紙張溫潤,版式文藝美好,適合隨手翻讀。
羽來信 內容簡介
本書是祝羽捷與朋友們的日常通信合集。祝羽捷從自己的困惑出發,以書信方式向朋友們發問,提問及回答皆與當下生活息息相關,包括愛與孤獨、個體價值、藝術與寫作、匠人精神、身份焦慮、理想主義等。祝羽捷坦誠書寫了自己的困惑,把書信變成自己的方法,將提問化為篤定的回答。通過這本書,我們可以更好地讀懂人生,尋找屬于自己的答案。
羽來信 目錄
序/陳嘉映:如何建構富有想象力的理想生活
**章 與她們同行
閻連科:讓“她們”成為“人”
黎 戈:嬰兒看著水仙花
遼 京:女性的故事還要講多久
Ca tie :女人首先要穿得自由
赫恩曼尼:30歲就是那道幫人頓悟的光
第二章 任何微小的美好都不容小覷
陳曉卿:踏踏實實地做一個吃貨也蠻好
石 康:屬于任何生命的時間都太少了
葛 亮:以手藝度己度人而不自知
韓松落:走吧走吧,去敦煌
賦格:“反旅行”也可以成為一種方法
第三章 愛與藝術是見自己的過程
翟永明:記住我們都是弗里達
趙 松:時間與寂寞自會淘洗掉生活里的雜質
鄭 執:寫作是逆流而上的行為
張定浩:作家其實是寫作困難的人
黃昱寧:明知不可為而為,大概是譯者的宿命
第四章 向人生發問
路 內:文青們后來發生了什么
維 舟:30歲之后,我更加憤怒了
吳曉波:選擇了就去努力,放棄了就不必糾結
馬 良:愿每個人都能發現自己并完全生活
崔 樹:生命的篤定與模糊,都在咖啡館里
第五章 當年輕人問年輕人
李西閩:當一個抑郁癥朋友沒有赴你的約
于 是:再也不用為不甘寂寞痛苦了
沈大成:相信要認識的人一定會認識
張之琪:死神來臨之前不顧一切狠狠愛
阿棗:總有一個地方聊以慰藉
第六章 何為理想生活
苗 煒:但愿我們還能再次愛上花花世界
尤 勇:日積跬步,不舍晝夜
思 遠:我是個年輕人,我只想開書店
顧 湘:做愉快的“田野”女孩
后記/祝羽捷:往“有信”的方向行走
羽來信 節選
陳嘉映老師: 你好!很高興以書信的形式和您交流,這也是我一整年都在努力嘗試和恢復的—能不能回到一種更加古典的方式和諸位老師們溝通。回到魚雁往返是不現實了,但至少不只是在手機上給大家點贊,轉發和評論微博,或者在直播上看到大家,給大家送上虛擬的花束。我喜歡的藝術家馬列維奇說過“人類生發出來的知覺比人類本身更加強烈”,他認為人類造飛機的初衷不是為了把商業信函從柏林運到莫斯科,而是為了滿足對于速度、飛翔的知覺。我想這也能解釋我為什么開始這個通信計劃,并非真得鋪開信紙、貼上郵票,大費周折地投送,而是需要共同找回典雅交流的知覺。 疫情*嚴重的時期,每個人不能出門,我像只癡情的蜘蛛趴在互聯網上,疾速地緝捕新聞,立竿見影做出反應。為不相干的事情,網友們時不時地廝打成一團,片言難盡,魚死網破,很少人愿意飽含耐心地聽你把話說完,交流變得即時且粗暴,還有一部分人進入“假死”的狀態—他們不再表明自己的態度,曾經不少網上的大V“金盆洗手”,不問網絡,沉默是另一種態度,更是失望的表現。大概有三個月的時間,我沒有見過家人以外的任何一個朋友,有人在網上建了一個直播房間,邀請我進去和大家“云喝酒”,仿佛網絡為我們提供了穿越時空的可能性,可那并不是真正的“在場”,終歸不能感受到彼此身體的溫度,也不能聽見酒杯真正碰撞在一起的聲音。如果空間的改變還只是浮光掠影,我感受到人們相處時的心態、共鳴出現了衰退的跡象。我堅信,與人分享感情和記憶是每個人的本能,比任何時候,我都渴望與人交流。 有個朋友開舊書店,偶然間在收回來的舊物里發現了幾封1982年的手寫信,東西是以接近廢品的價格買回來的,朋友打電話過去問需不需要送還。賣舊物的人回答說,信是父親和朋友寫的,父親在醫院,情況并不樂觀,東西都不要了。朋友把信用堅固的透明文件夾保存起來,恰好被我看到,我如獲至寶地讀,仿佛走進了一個人的內心深處。寫信人是重慶機械廠的一位工人,寫給上海鋼鐵廠的另一位工人,先是關心了彼此身體的狀況,然后講起喜歡的古典樂,談到柴可夫斯基、約翰·施特勞斯,并拜托對方用錄音機轉錄這些音樂家的磁帶。一紙寫竟,有些字寫錯了,寫信人就劃掉改正。這樣一封信在世上存留了四十年,紙張發黃,薄如蟬翼,再次讀的時候仍覺得鮮活,這樣感染人,喚起了我對于書信的記憶。 我從小過著平靜規律的生活,覺得有人來遞信、大人拆信、讀信、裁下五花八門的郵票都是頂有意思的事情。對書信的興趣被激起,我才驚覺自己書柜里就有不少書信集。奈保爾、傅雷、梁啟超、曾國藩的家書,都頗具智慧;在民國文人的情書里,徐志摩肉麻直白,讀得我雞皮疙瘩起了一身;*喜歡的是朱生豪寫給宋清如的,活潑生動,怪不得大家都說他一生就干過兩件事: 翻譯《莎士比亞全集》,給宋清如寫情書;谷林與揚之水持續了二十年的百余封通信,內容圍繞約稿、校對展開,談到讀書考證和生活,*讓人心折的是信中流露出的親切古意。 懷著好奇心,我開始閱讀一些針對書信的書籍,得益于英國歷史學家西蒙·蒙蒂菲奧里、學者肖恩·亞瑟等對書信的癡迷,他們收集了女王、皇帝、明星、總統、首相、詩人、作家、藝術家、科學家、集中營里的受難者、探險家、人權斗士等各色人物的書信,有道歉信、求職信、情書、公開信、公告、家書、決斗書、外事交涉、戰爭宣言等題材,讓我重溫了書信的發展。這些珍貴的書信像琥珀一樣,封存著歷史關鍵時刻背后人的情感和內幕,為世界史提供了另一個維度,更加私密,更加感性。 很可惜,書信的黃金時代已經隨著手機、互聯網普及而結束。我們對科技抱有期待,以為會迎來更加緊密的連接,可惜事與愿違,即便對話框可以隨時跳出,我時常覺得比十年前更加孤獨——交流的工具越簡單,我們越不會交流。西蒙·蒙蒂菲奧里說:“書信是對癥生命無常的文學解藥,當然也是人們面對互聯網的脆弱和不穩定時所需的良藥。”有時候,我想刻意避免一些這個時代給的便捷,能與朋友見面的事就盡量不打電話,能寫一封信就盡量不用微信溝通,用不便利來改變自己處理事情的方式,從中延緩急切以及減少浮躁。 我也是在看嘉映老師書的時候得到一些啟迪,看似交流在高度流通,一切變得急切和脆弱,哲學大師們認為人活著就是對話,荷爾德林說:“人已體驗許多。自我們是一種對話,而且能彼此傾聽,眾多天神得以命名。”“聆聽”在當下尤為困難。現代化讓生活變得簡單容易,簡化后的生活每個人好似在干巴巴地活著,心是孤獨的獵手。我開始寫信,也是因為面對瞬息萬變的世界以及不斷出現的新事物,常常覺得無力還手,也來不及思考。如果人們越來越干巴巴地活著,缺乏精神活動和深度交流。我常常一段時間不看微博就發現自己落伍了,一些新興的詞匯和熱門事件不知道來龍去脈,更不可能和朋友以此打趣,大家使用著同質的話語,你很容易掉隊,也很容易變成不重要的邊緣人。更可怕的是,被煽動起來的集體意識像癌細胞一樣快速繁殖,只有情緒沒有理性。網上硝煙如云,布滿看不見的狙擊手,稍有不慎你就會被打成篩子,我已經以身試法過了,滋味很不好受——抨擊者并不真正想要說服你,只想迅速壓倒你。 這是我一點粗鄙的思考,我們對這個時代的不適感并不只是因為社會財產的重新分配,更多時候是這個時代的價值標準、評判標準徹底改變了。我常常懷疑手上在做的事是不是有意義,所謂的“文青”變得有些可笑,對人生的思考和疑惑常常讓自己苦不堪言。跟大家在紙上娓娓談心,用寫信互訴衷腸的時候,我發現自己逐漸克服了羞恥心,越來越勇敢地暴露自己的缺點,實際上,這也是我無法回避的必然結果—你寫得/說得越多,就越暴露底牌。如今跟大家交流,我不想抖機靈,也不想為了冒充聰明說一些故作高深的話,我不再擔心被看到幼稚和不夠高明。因為我知道,想要得到真誠的回應,就不能遮遮掩掩,笨嘴拙舌也是因為真實和強烈,就像一個真正墜入愛河的人那樣喪失技巧。比起謀求共識,更重要的是相互的理解和寬容。華麗的表象總會褪去,希望我們都能接受真實的自己,用*樸素的方式袒露心聲。我承認自己還是有很多困惑: 愛、孤獨、隔離、身份焦慮、性別偏見、事業、分別、死亡、信仰、旅行、藝術、倦怠與喪、隔離與宅……這些困惑化作書信流轉,我忍不住感嘆: 原來有趣的靈魂跟自己挨得這樣近。 我喜歡陳嘉映老師說過的一段話:“未來之思不是哪個偉大思想家之思,而只能在思想者的交談之際生成。每一個思想者都是謙抑的思想者,思的目標不是偉大,而是真誠。”我們都期望自己可以獲得理想中的生活,心揣著對這個時代的怕與愛,我們能不能再次找回一種對話方式,建立深度溝通的可能性,一起抵達更廣闊的世界。比起獨自在黑暗中踉蹌,我更向往建立你我之間的對話,猶如在黑夜中點燃火把,映照彼此的臉。 附近消失,友鄰形同陌路,近在咫尺的人充滿誤解和敵對,與遠方的人共享恰如一封信的距離,也許就是我們這代人的必經之路。日子一天天在手機上劃過,內存里是漂亮的照片和碎片化的感受,我想能不能用對話重現個體,用對話接近真實,用對話獲得見識,*終建構富有想象力的理想生活? 佇候明教。 祝羽捷上 祝羽捷好! 謝謝你的來信,信中所言差不多我都有同感,我自己也常常想到這些,這里那里談過一點兒。 記得在哪里讀到,考古學家找到古埃及一位富豪的幾封家書,他出差在外,向家人講述他的差旅,指示怎樣處理各種家務,印象不大準確,記得這些家書距今應有三千年了吧。我還模糊記得,發掘出來的漢簡里也有不少是戍卒的家書,如今都是珍貴的歷史學資料。唐詩宋詞里,怎能沒有“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一春猶有數行書,秋來書更疏”?科學革命開始之后的很長時間,哲學—科學的演變和發展有一半要從思想家的廣泛通信中尋覓蹤跡,萊布尼茨的通訊錄幾乎包括歐洲當時所有重要的思想者。在我們年輕時候,遠程交流全靠寫信,箱底至今還積壓著大批信件,也積壓著好多古老的故事。1968年冬天,我從插隊所在的內蒙突泉回北京,有朋友從內蒙烏旗來信,附有給秦生的信,要我轉交——這既可省去8分錢的郵票,也有意邀我旁聽兩位親密友人之間的交談。我們那時唱蘇聯歌曲,一句“Kakim dei beil,takim ostaltsia”(“從前是這樣,如今還是這樣”)流傳在青春的憂傷里,這封致秦生的信就沿著這句歌詞作結:“從前是這樣,如今還是這樣—將來不會是這樣了。”青春無論多少混亂和迷惘,似乎青春總有未來。我揣上信,暮色中走向鄰樓,樓門口圍著一圈年輕人—秦生在我們這一帶是出名頑主,樓前常有年輕人扎堆。我遠遠地喊秦生,他們轉過頭來,我卻沒有聽到期待中的歡快回音;片刻沉默之后,有幾個朝我跑來,直迎到我跟前,壓著聲音: 秦生走了。到哪兒去了?兩個小時之前,一場時不時會爆發的街頭斗毆,一把三棱刀捅進他的后腰。 不多說這些私人回憶,說點兒宏大的。我常說,這幾千年的歷史,就是文字主導的歷史。讀寫是高標特立的精神活動,沒有任何其他精神活動可以替代。書信又不同于一般著述,它寫給特定的人,即使寫信人想著將來會公開于世,特定讀信人的影子仍在他的筆端。隨手抄一段舊時來信—— 嘉映: 自7月中旬以來,一直忙著給你寫東西,不料又出了一大堆廢紙。“說者容易做者難”,真要讓我辦個專欄,恐怕要誤事。不過,人是逼出來的,也許有了責任也就有了動力亦未可知。眼下我是江郎才盡,差不多已活生生地感覺到頭腦的枯竭。寫了論非暴力原則,論及革命運動中的道義、策略與領袖三者間的關系問題,論及病態的理論興趣問題等等(不止這些,實在不好意思再多說了) 。多篇未完成稿,都覺得太臭,提不起興趣來修改。我覺得我也許已誤入歧途: 本不是革命者,卻煞有介事地反思革命。與胡君相比較,我現在*大的弱點是下筆不自信,總覺得寫出來的東西都十分可疑。常想起《圣經》上的話(我近來又在反反復復地讀它):“你不可論斷人,以免別人也同樣地論斷你。”胡君的反思論道精辟,雖然也有有失武斷之處。我的反思就未免像個指手畫腳說三道四的“批評家”。我眼下害怕一本正經的腔調,雖然我又已經寫了好幾萬字一本正經的文字。且不談它,我想我總會給你寄點兒東西的(我現在覺得除了寫點東西,真不知還可以干什么)。 這些話在你讀來也許平平常常,在我,卻寫著時代的轉折,寫著這一轉折給一代人帶來的困境。這封信來自20世紀90年代初,是我*后收到的長信之一。沒多久,普通人開始用上了fax,私信也沾上了公文的身份。轉眼又被email取代。再后,你們年輕人就更熟悉了,微信,facebook。是的,將來不再像從前那樣了。那是怎樣的將來呢?神經科學*近證實,“數字原生代”的大腦運作方式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他們在智商測驗中的表現、反應時間以及工作記憶提高了,同時,共情能力、人際交往能力、進取心降低了很多。 我知道無論哪個時期都有人認為他生活在一個巨大轉折的時代,但我還是固執自己的看法: 兩千多年的文字時代正在我們眼前落幕,書信的消失應是一個明顯的標記。常聽人感嘆,現在的年輕人不讀書了,而“書”這個字從前更經常用來指書信。太史公《報任安書》,曾國藩家書,確實像典籍那樣值得反復詠誦。微信的文字則是一個不同的族類,它們只為傳達信息;情感也已轉換為信息,編碼在表情符號里—這些符號不似紙上的筆跡,體現著獨有的經歷和心情。無數的比特在基站之間以光速生滅,與之相比,魚游雁翔的確太慢,受到自然條件的種種限制。書,倒還有幾個人在讀,卻沒誰還在寫信了。 非非叟原本借讀寫討生活,看著文字時代逝去,難能無動于衷;你嘗試重拾這種交流方式,聞知而喜。讀來信,好像是你偶然讀到舊書店淘來的書信而起的因緣,讓我想起陋室的角落里還存著一兩箱恐龍時代的舊書信,上引的那段就是從中翻檢出來的。一直有意整理這些信札,卻一直拖著。現在,我應該會及早去做這件愉快且有益的事情吧。倒不是妄想扭轉歷史大勢,但將來的世界,不管怎么發展,總要時時能聽到往昔的回聲,才算得上人類繼續生存。祝愿你繼續你的嘗試,并得到更多朋友的響應。也希望及早會面,如果不更早,3月份應能在上海相見。 陳嘉映 2021年1月22日
羽來信 作者簡介
祝羽捷 作家,策展人,青年文化學者。 著有《萬物皆有歡喜處》《世界從不寂靜》《人到了美術館會好看起來》等,翻譯作品《嘩眾取寵》《文藝復興人》《簡潔如相片》。 主持播客節目“藝術折疊”,并為《新周刊》《三聯生活周刊》等媒體撰寫專欄。
- >
企鵝口袋書系列·偉大的思想20:論自然選擇(英漢雙語)
- >
經典常談
- >
史學評論
- >
巴金-再思錄
- >
伊索寓言-世界文學名著典藏-全譯本
- >
煙與鏡
- >
隨園食單
- >
莉莉和章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