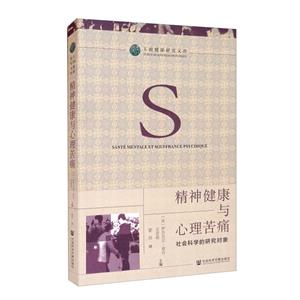-
>
妙相梵容
-
>
基立爾蒙文:蒙文
-
>
我的石頭記
-
>
心靈元氣社
-
>
女性生存戰爭
-
>
縣中的孩子 中國縣域教育生態
-
>
(精)人類的明天(八品)
精神健康與心理苦痛: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0186131
- 條形碼:9787520186131 ; 978-7-5201-8613-1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精神健康與心理苦痛: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 本書特色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全球有1-4的人受到精神障礙的困擾。在法國,精神疾病每年導致1萬人死于自殺、20萬人企圖自殺。在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抗抑郁藥物的銷售量增加了7倍。這些病癥不能純粹歸結為腦神經的問題,因為悲傷、痛苦、壓抑、失望、焦慮和恐懼也與社會和文化環境密切相關。 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待心理現象,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分析和管理心理健康。埃米爾·涂爾干(Emile Durkheim)關干自殺的論述以及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關于瘋癲的論述為我們開辟了道路。《精神健康與心理苦痛: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旨在沿著這一道路,探索醫療保健系統與公共政策之間的相互作用,重新思考精神病學的作用與功能,以更貼近實踐以及精神健康工作者的視角去進行調查,密切關注構成“心理”(psy)干預對象的個人及群體。 精神健康已成為社會博弈的全新語言。該書的構思、組織和出版正是為了回應上述當代世界的全新要求。
精神健康與心理苦痛: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 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了來自法國社會科學與心理健康領域的前沿論文19篇,介紹了法國精神健康研究的理論傳統脈絡及其精神衛生服務體系的建設歷程、狀況和特點。全書分為三個部分,部分從法國社會科學經典理論的角度,探討了個人的精神心理如何成為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第二部分從醫護工作者的視角出發,勾勒了法國當代精神健康領域的專業實踐歷程,闡述了其精神衛生服務體系在20世紀下半葉重組的情況;第三部分從病患及其家庭的視角展開,講述了他們作為“精神心理”干預的對象所承受的精神疾苦。
精神健康與心理苦痛: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 目錄
精神健康與心理苦痛: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 節選
事實上,隨著章節的展開,哈布瓦赫不動聲色卻系統地推翻了涂爾干所提出的三種自殺類型,這一分類構成了其論證的支柱之一:因整合度低的利己型自殺、因整合度高的利他型自殺以及規則弱化而導致的失范型自殺。他從不把功勞歸為已有。他甚至將所謂的利他型自殺排除在外,因為對他來說這是一種犧牲。而自殺與犧牲雖是“同屬的兩種同類”,但我們不能將兩者相混淆,因為社會在這兩種行為上所打下的印跡是截然不同的。社會將犧牲視為自身的作品,而自殺則非如此,它被視為非法的行為。至于利己型自殺,他卻只字不提。但他依據統計數字,證明新教徒的自殺率不一定比天主教徒的自殺率更高,并不是因為天主教對自殺持譴責態度,責令其反躬自省,單獨面對上帝,沒有整合儀式,而是因為都市生活方式比農村天主教徒的生活方式更容易使人走上自殺之路,從而解釋新教徒為何自殺率較高。他尤其直言不諱地抨擊了“失范”的概念,這種“欲望的放縱,不受任何規訓的指導和限制”。這種失范現象并不是一種現代疾病,更不是新鮮事物,也并不僅僅關系到渴望變得更加富有的個人。在過往的社會中,貧窮也會導致自殺:“為生存而掙扎的痛苦并不亞于今天想發財致富的人的失望所帶來的痛苦。”現代社會生活并非處于無序和無政府狀態,而是相比于過往更具規范性。在市場規律的支配下,每個人都要評估“其服務、工作和努力”,社會生活擁有自身的節奏和我們必須遵從的傳統形式。現代社會生活所不能容忍的特立獨行者必定會被無情消滅。根據哈布瓦赫的觀點,更為糟糕的是,今天人們的舉止、思維和感受的方式受到比過去更為“專制”的管治,激情被塑造成單一模式。因此,今天的現代社會生活并非比昨天混亂,只是變得“更為復雜”而已。職業生活領域與家庭生活領域的分離迫使每個人至少同時要過兩種生活,每種生活都有不同的規范、習俗和價值觀。資本主義不再是一種功能失調,而是搖身成為組建社會關系的新方式。這就徹底推翻了“失范”概念的解釋性優點,涂爾干曾運用此概念來解釋鄉村、手工業和宗教社會向城市、工業和世俗社會過渡所導致的自殺急劇增多的現象。 然而,哈布瓦赫卻是在該書的*后幾頁中,在論述個人動機的解釋性作用時,才與涂爾干的學說明顯地拉開距離。這當然是為了解釋自殺,但更多的是為了設想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其分析中,涂爾干從一開始就駁斥了受害者為自己的行為賦予意義所援引的主觀動機。在涂爾干看來,受害者援引的動機是導致他們行為的原因,所表達的要么是一些自然傾向(肉體痛苦、精神疾病、醉酒和酗酒),在這種情況下,無關乎社會生活;要么是一些個體特性,可以相互抵消、相互消除,淹沒在其他特性中。哈布瓦赫則反其道而行之,認為個人動機和個人情況“取決于社會團體的結構”,從而恢復其正當地位,并認為有必要將之視為自殺的正當原因,與集體信仰和習俗同理。 哈布瓦赫指出,在涂爾干看來,個人與社會相對立,一如“偶然和不可預測性與必然和法律及秩序相對立”。但這種分離,是兩種現實之間的近乎物質性的分離,對哈布瓦赫來說似乎是虛幻的。個人動機與一般原因是密切相關的:它們與一般原因組成系統,將集體生活的大潮與這些特定事故任意分開是錯誤的。“改善神經系統”并使其“過于微妙”的器質傾向自有其社會原因,因為這種情況“相比于其他群體,在自由職業、工業和商業領域以及城市群體中較為常見,這并非偶然”。另外,個人與社會的區別并不是絕對的,因為社會存在于個人內部。換言之,若排除構成社會的個人,社會則不可存在:“家庭情感、宗教實踐、經濟活動并非實體。它們體現在將個人存在彼此聯結和聯系的信仰與習俗中。”得益于愛德華·薩皮爾(Edward Sapir)、諾伯特·埃利亞斯、皮埃爾·布爾迪厄和諸多人類學家的著作,個人與社會現實融為一體(“一體化”)的概念在20世紀后半期占據主流地位①。但早在20世紀30年代,哈布瓦赫就在評論涂爾干的自殺論述中為此奠定了基礎,從而在精神病學和社會學之間構建起一種更為互補平和的關系。不再有涇渭分明的兩種自殺類型——一是屬于精神病學對象的器質決定論,二是屬于社會學對象的社會決定論——每種自殺都兼合了這兩個角度。“無論從哪一個角度出發,我們將會看到身體原因引起的神經紊亂或社會原因導致的集體平衡破裂的后果。”不同的角度產生不同的對象。實際上,隨著科學流行病學的發展,精神科醫生、心理咨詢和救援中心紛紛介入其中,通過對具體案例的研究,認定了自殺通常與抑郁狀態有關。如今,個人因素的重要性已不可否認。 社會學家考慮受害者援引的輕生理由,是對個人與社會關系的思想傳統的一種原始表達,這是涂爾干學派的特征。涂爾干用一種現實而粗暴的認識論來規范他的思考,將認識對象按不同領域分類:心理學的對象是個人現實,社會學的對象是社會現實。但對現實的劃分卻無從掩蓋其等級差異:心理學中的自我融合了本能和情感的內涵,而社會則負責在每個個體中納入智力類別、道德價值、審美和宗教評判原則。雖然涂爾干的弟子想效仿其先師去思考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但他們卻以更大的自由去擺脫了“老板”的教條式認識論。馬塞爾·莫斯研究人格形成的社會基礎,但不對各學科進行等級劃分與區別。在其社會需求理論中,哈布瓦赫巧妙地結合了涂爾干和哲學家柏格森彼此互為矛盾的靈感,借以重新思考個體的問題。 ……
精神健康與心理苦痛: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 作者簡介
[法]伊莎貝爾·顧丹(Isabelle Coutant),社會學家,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主任研究員,法國社會問題、社會科學、政治與健康跨學科研究所(IRIS)成員。主要從事城市民族志研究,注重從社會學的角度探索心理痛苦的問題。 王思萌,社會學家,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員,法國醫學、科學、健康、心理健康與社會研究中心(CERMES3)成員,法國東亞和東南亞移民多學科研究網絡(MAF)協調員。專注于國際移民、健康、精神健康,以及當代中國(中國大陸及其僑民)的研究。 蒙田,畢業于巴黎高等翻譯學校(ESIT)筆譯系。
- >
月亮與六便士
- >
隨園食單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歷史與人類學概述
- >
史學評論
- >
巴金-再思錄
- >
大紅狗在馬戲團-大紅狗克里弗-助人
- >
【精裝繪本】畫給孩子的中國神話
- >
苦雨齋序跋文-周作人自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