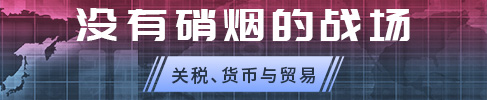-
>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茨威格短篇小說集
-
>
女人的勝利
-
>
崇禎皇帝【全三冊】
-
>
地下室手記
-
>
雪國
-
>
云邊有個小賣部(聲畫光影套裝)
-
>
播火記
派對恐懼癥(精裝)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8170063
- 條形碼:9787208170063 ; 978-7-208-17006-3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派對恐懼癥(精裝) 本書特色
❈ 陳楸帆、淡豹推薦。曾獲美國國家圖書獎提名、星云獎提名。入選《紐約時報》《巴黎評論》《洛杉磯時報》《ELLE》年度好書。
❈ 作者是師承安吉拉·卡特、奧康納、麥卡勒斯的美國新生代小說家。她以細膩敏感又古靈精怪的聲音,打破科幻、奇幻、現實主義、成長小說文類界限,直面□接地氣的女性話題。
❈ 八篇故事,帶來八種驚奇與洞察,有關女性生活和內心的混亂與狂喜,思考性、權力、快樂、痛苦和自我掙扎,書寫生活中那些未曾言明但無處不在的真相。無論你是男性還是女性,它們都會促使你重新審視當下的生活選擇和情感關系。
派對恐懼癥(精裝) 內容簡介
八個故事,關于女性與她們的身體。游走于奇幻、童話與寫實間,守護那些被限制的、被暴力對待的、乃至被忽視的女人,等待著重生的可能。
派對恐懼癥(精裝)派對恐懼癥(精裝) 前言
吃八口
他們給我上麻藥讓我睡著時,我感覺口中都是月亮上致命的微細沙塵。我以為自己會被嗆著,但那些沙塵在我口中進進出出,而我竟不可思議地仍在呼吸。
我曾夢見自己在水下呼吸,而現在就是那種感覺:驚慌,然后接受現實,然后興高采烈。我要死了,但不是垂死,而是在干一件我從沒想過自己可以完成的事。
回到地球上的現實:U醫生正在我體內。她的雙手在我體內,正用手指搜尋著。她正把血肉從外殼解下,同時在喜愛她的人中走來走去,還跟一名護士聊起在智利度過的假期。“我們本來打算搭飛機去南極,”她說,“但票價太貴了。”
“可是能看企鵝啊。”護士說。
“下次吧。”U醫生回答。
在此之前,是一月的事吧,新的一年剛開始。我在一條靜默的街上艱難地穿過兩英尺高的積雪,來到一家店鋪,店鋪的窗玻璃里有靜靜懸吊的風鈴、美人魚形狀的小飾品、一塊塊浮木,還有用釣魚線吊起的過于閃亮的貝殼,但沒有一絲風,所以也沒發出任何聲響。
整座小鎮死寂一片,若是到了季末,為了服務一日游旅客和那些忍到現在才花錢的人,會有少數幾家店開門營業;但距離季末還有好一段時間。大部分店鋪老板已逃到波士頓或紐約,更幸運的話已經逃到更南的地方。這個季節沒生意可做,他們留在櫥窗里的商品看來像個笑話。而在這些表象之下,令人同樣熟悉又陌生的第二座小鎮蘇醒過來了。每年都一樣。酒吧和餐廳會為當地人制訂秘密的營業時間,這些如同巖石般堅忍的科德角居民早已這么度過數十個冬季。隨便挑一個晚上,你在吃飯時抬頭,都能見到這些渾圓健壯的家伙走進大門;而唯有當他們把身上衣物層層剝掉,你才能看出衣服里是誰。就算是你在夏天認得出來的人,在這種敷衍馬虎的光線中多少都有點像陌生人;他們全是獨行俠,即便跟別人在一起時也都是獨行俠。
不過走在這樣的街上,簡直就跟走在外星球上一樣。那些沙灘美女和藝術品經紀人一定沒見過小鎮的這一面,我想。所有街道都無比陰暗,還有種液態的冷冽在所有縫隙和巷弄中翻騰。寧靜和喧響彼此碰撞,但永遠無法交融;溫暖夏夜的歡騰熱鬧遙遠得難以想象。在這個季節,就連從一扇門走到另一扇門都無比艱辛,但如果你這么做了,你能感到生命力刺穿一片死水般的寂靜:從當地酒館飄出的低沉話語,為建筑賦予生命的風聲,有時在巷弄中撞見的窸窣蠢動的動物——令人喜悅或恐懼的,都是同一種喧鬧。
狐貍在夜間街道穿行。有只白色母狐動作輕巧迅速,看起來就像其他狐貍的鬼魂。
我不是家族中的□□個。我的三個姐妹這些年來陸續接受了手術,不過她們來拜訪我時完全沒提。以前那些年,她們始終跟我一樣以有機狀態生長,因此看到她們突然變得纖細,我就像鼻子受到重擊,感覺比想象中還痛苦許多。□□個接受手術的姐姐呢,好吧,我本來以為她快死了。我一直以為我們這幾個姐妹都快死了,因為共同基因的緣故。當我以飆高八度的聲音焦慮質問:“在整棵家族樹中,到底是什么病在殘害我們這一支啊?”此時那個姐姐坦承:是某種手術。
接著她們每個人都成了信眾。成了手術的信眾。某種手術的信眾。這手術非常簡單,就跟你小時候摔斷手臂時需要打釘子進去一樣,而且可能還更簡單:其實就是通過某種束帶、某種袖狀物切除,來完成腸胃繞道。繞道?但他們的說法很簡單——反正胃的一部分就是消解了,消失了——手術效果就像春天早晨的暖意,太陽升起時,你會和她們一樣幸福,不再在陰影中打戰。
以前,只要我們一起出門,她們就會點□大份的餐點,然后說:“我不可能吃得完。”她們一定會這樣說,一定,她們一定會優雅地堅持說自己不可能吃得完,但這一次,她們確實沒說謊─通過醫學手術,這個丟臉的謊言總算成真。她們用各種角度落叉,把食物切成難以置信的小塊,比如小娃娃尺寸的西瓜、極細的豆苗,或者像是要把食物分給一群人吃那樣把三明治切出一個小角,配上一人份雞肉沙拉——她們將那一小口吞下,一副好像無比墮落的表情。
“我覺得狀態很好。”她們都這么說。每次跟她們說話,她們嘴里冒出的就是那句話。其實那幾張嘴只能算是一張嘴,這張嘴曾經用來進食,但現在只用來說:“我感覺狀態真的、真的很好。”
天知道我們怎么會有這種毛病——這種需要動手術的身體。不是我們母親的錯,她身材始終正常,不健壯、不豐滿、不帶有魯本斯的□□風格、不算是“中西部身材”,也不豐腴,總之就是正常。她總說人只需要吃八口就能有進食的感覺。雖然她從沒計算出聲,但我總能聽到那八口的咀嚼聲,清楚得就像競賽節目中的觀眾在倒數,音量震天價響,口氣又得意揚揚,等倒數到一之后,她會放下叉子,就算盤子里還有食物也一樣。我的母親從不亂來,她絕不會翻弄盤子里的食物,也不會假裝自己還在吃。人要有鋼鐵意志,才有纖瘦腰線。吃八口就足以讓她贊美招待她的主人。吃八口成為她腸胃的守護防線,就像包裹在屋墻上的絕緣層。我真希望她還活著,活著目睹她的女兒們變成什么模樣。
后來有一天,第三個做了手術的姐妹輕巧走出我家,我從未見過她的腳步如此輕盈,然后過了沒多久,我吃了八口后就不吃了。我把叉子放在盤子旁,動作比我預想的還要粗魯,還不小心把瓷盤邊緣敲掉一個小角。我用手指把碎片拈起,扔進垃圾桶,回頭望向盤子,里頭的食物原本就放得很滿,現在還是很滿,那一整團意大利面和蔬菜完全看不出缺口。
我再次坐下,拿起叉子,又吃了八口。不能再吃了。那團食物還是沒有減少的跡象,我對它的渴求卻變成原來的兩倍。沙拉里的蔬菜葉子上還滴了油醋,面條上還灑了檸檬汁、撒了現磨胡椒,一切看起來是這么美,而我還是這么餓,所以我又吃了八口。吃完之后,我把鍋里的食物也一并解決,然后氣得哭出來。
我不記得自己變□的過程。我無論幼時還是青春期都不□。照片中年輕的我不□□,就算真的□□,也是因為大家在那個階段本來就有些丟臉之處。瞧我多年輕呀!瞧我當時穿衣風格多怪!牛津鞋!誰發明這種鬼東西?踩腳褲!開什么玩笑?松鼠發夾?瞧那副眼鏡,瞧我當時正在對相機扮鬼臉呢。那表情簡直是在對未來拿到照片的人扮鬼臉,真令人懷念。我以前以為自己很□,但其實不□;照片中少女時代的我很美,那是一種終將逝去而令人傷感的美。
但后來我生了個寶寶。我生了卡爾——難搞又目光銳利的卡爾,她始終都不了解我,但我更不了解她——然后突然之間,我們的關系徹底毀了,她就像在離開旅館房間前摔爛一切的重金屬搖滾歌手。而我的肚子就是被她摔出窗外的電視機。她現在已是成年女性,各方面都與我迥然不同,但她曾經存在的證據仍堅守在我身上。我的模樣再也不可能和以前一樣了。
我站在空蕩蕩的鍋旁,感覺十分厭倦。我厭倦上教堂時,看到那些瘦巴巴的女人贊嘆地撫摸彼此手臂,然后再來稱贊我的“皮膚好好”;我厭倦每當穿越任何一個空間,得不停把屁股扭來扭去,仿佛看電影時得爬過某人才能抵達座位;我厭倦試衣間那種平板、毫不留情的燈光;我厭倦在望向鏡子時,捏住身上我痛恨的那些肉,拎起,指甲深陷其中,然后任由它們垂下,同時感覺身體到處都痛。我的姐妹已經丟下我去了其他地方,而就跟之前一樣,我一心只想追上她們。
對我的身體而言,吃八口這件事行不通,而我打算讓它行得通。
我每周去找U醫生咨詢兩次,她的辦公室位于科德角往南開上半小時車程的地方。我開得很慢,而且總是繞路。這幾天斷斷續續下著雪,懶洋洋的雪覆蓋在樹干和欄桿上,仿佛被風吹落的衣物。我知道路怎么走,因為之前就曾開車經過她的辦公室——通常都在某位姐妹離開我家之后——所以這次開車前往時,我還幻想在當地一家衣飾店購物;我買了件從假人身上脫下來的背心裙,完全超出我原本的預算。我在午后陽光下穿上那條裙子,比兀立在原處的假人幸運多了。
然后我置身于她的辦公室,就站在她的素色地毯上,有名接待員為我開門。醫生跟我預期的樣子不同。我想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落差,是因為我以為她既然選了這個職業,必定對此抱持深刻信念,所以應該會長得瘦一些:就算不是個自制力極強的女人,也會是個極具同理心的人,而且經過調整,她的腸胃一定早已跟自己理想的狀態沒有太大落差。但她其實甜美、微□——為什么我自己跳過了這個階段呢,這個圓滾滾、毫無威脅性,像熊貓一樣可愛的階段呢?她露齒大笑。她到底在干嗎?她為何要把我送上這趟她自己從未踏上的旅程?
她指指椅子,我坐下。
兩只博美狗在辦公室里到處奔跑。當它們各自行動時——其中一只蜷曲在U醫生的腳邊,另一只優雅地在走廊拉屎——樣子看起來完全一樣,溫順無害,不過當其中一只接近另外一只時,情況卻變得有點詭異,它們的頭會同步抽動,仿佛是同一個整體的兩個分身。醫生注意到門口那堆屎,立刻叫了接待員過來。門被關上了。
“我知道你來這里的目的。”她說,我甚至還沒來得及張開嘴巴。
“你之前研究過減肥手術了嗎?”
“研究過,”我說,“我想要那種不能逆轉的。”
“我很欣賞像你這種有決心的女人。”她說。她開始從某個抽屜中抽出活頁夾,“你得先走一些程序。拜訪心理醫生,再看一位醫生,參加互助團體——就是一些沒什么意義的行政手續,花上很多時間。但一切都會為你帶來改變。”她保證,同時在我面前搖動一根手指,臉上帶著既有責難意味又可愛的微笑,“手術會痛。不會很輕松。但結束之后,你會成為□□□□快樂的女人。”
我的姐妹們在手術前幾天來到我家。她們把自己安頓在屋內眾多空房里,還在床頭柜上擺滿乳液和拼字游戲。我可以聽到她們在樓上制造出的噪音,聽起來像一群鳥,雖然各有各的聲音,但又清晰地合唱著。
我跟她們說,我要出門吃□后一餐。
“我們跟你一起去。”□□個姐妹說。
“去陪你呀。”第二個姐妹說。
“去支持你。”第三個姐妹說。
“不用,”我說,“我自己去。我需要獨處。”
我去了□喜歡的餐廳“鹽屋”。這家餐廳無論名字還是氣質都不始終如一,之前曾有陣子叫“琳達餐廳”,接著是“家庭餐館”,然后是“餐桌”。建筑都是同一棟,但外表不斷呈現新樣貌,而且總是比之前更好看。
我坐在角落的座位上,想到那些準備接受死刑的人,想到他們吃的□后一餐,然后那個星期第三次開始擔心自己的道德觀出了問題,還是我根本沒有道德感可言?我的這一餐和死刑犯的□后一餐完全不同,我在大腿上攤開餐巾時提醒自己。二者根本無法比較。他們的□后一餐是死前的□后一餐,我的□后一餐迎接的不只是生命,還是新生命。你這人真是糟透了,我想,我把菜單舉得比臉還高,那種高度完全沒有必要。
我點了一整個騎兵隊的牡蠣。其中大多已做過必要修剪,所以我能像喝水一樣咕嚕吞下,仿佛吞下海洋,仿佛吞下一片空無,但其中有一顆卻頑強對抗:它就是死死粘在殼上,完全是塊負隅頑抗的肉。它不從。它簡直就是抵抗這個概念的化身。這些牡蠣還活著,我突然意識到。它們其實就是一塊塊肌肉,沒有腦或任何內在器官可言,嚴格來說是這樣,但仍活著。如果世界上有任何正義可言,這些牡蠣會纏住我的舌頭,讓我活活噎死。
我幾乎要把牡蠣嘔出來,但還是吞下去了。
我的第三個姐妹出現在桌子對面,坐下。她的深色頭發讓我聯想到母親:她的頭發也是這樣又亮又柔順,簡直不像真的,但確實是真的。她對我親切微笑,仿佛正要告訴我一個壞消息。
“你干嗎跑來?”我問她。
“你看起來糟透了。”她說。她刻意用某種方式擺放雙手,借此展示她的艷紅指甲,由于指甲表面涂得無比滑亮,幾乎像是出現立體景深,仿佛有朵玫瑰深陷于玻璃。她用指甲輕敲自己的顴骨,用非常靈巧的撫觸往下刮擦。我打了個冷戰。然后她拿起我的水杯,大口喝下,水流過冰塊再流入她口中,而剩下的冰塊不過是一整片即將塌毀的網格構造,□后,她把杯子仰舉得更高,整個構造就這么滑到她臉上,然后她開始咀嚼那些落入她口中的碎冰。
“不要浪費你胃里的空間去裝水,”她說,咔啦咔啦咔啦,“好啦,那么,你在吃什么?”
“牡蠣。”我說,明明她能看見我面前有一大堆快坍塌的牡蠣殼。
她點點頭。“好吃嗎?”她問。
“好吃。”
“跟我描述一下吧。”
“它們就是所有健康事物的集合:海水、肌肉和骨頭,”我說,“沒有心智的一團蛋白質。沒有痛覺。也沒有可驗證的思想。卡路里非常低。不算什么放縱的放縱。要來一顆嗎?”
我不希望她在這里——我希望她離開——但她的眼神閃爍,仿佛正在發燒。她用指尖留戀地滑過一只牡蠣殼。牡蠣殼晃動后紛紛往下滾落,整堆殼坍塌下來。
“不用,”她說,然后又開口,“你跟卡爾說了嗎,說
你要動手術?”
我咬了咬嘴唇。“沒,”我說,“你跟你女兒說過嗎,動手術前?”
“說過呀。她很為我興奮。還送了花來。”
“卡爾不會興奮的,”我說,“卡爾沒打算盡的女兒義務很多,這正是其中之一。”
“你覺得她也需要動手術嗎?這是原因嗎?”
“不知道,”我說,“我總是不懂卡爾需要什么。”
“你覺得她會因此看不起你嗎?”
“我總是搞不懂她的想法。”我說。
她點點頭。
“她不會送花來的。”我總結道,雖然她也沒什么必要這么做。
我點了一堆熱乎乎的松露炸薯條,結果燙傷了上顎。直到被燙傷之后,我才開始思考自己有多么思念這些食物。我開始哭,姐妹把手輕輕放在我的手上。我嫉妒牡蠣。它們永遠不用思考跟自己有關的事。
回家之后,我打電話把事情告訴了卡爾。因為焦慮,我的下巴繃得死緊,電話接通時,我的下顎關節還發出了咔啦一聲。我可以聽見電話另一端傳來另一個女人的聲音,但隨即某人用我看不見的手指壓住她的嘴唇令她停止作聲;接著有只狗嗚嗚叫。
“手術?”她又說了一次。
“對。”我說。
“我的□□□□呀。”她說。
“別用他的名字罵人。”我說,但其實我也沒多虔誠。
“什么?那根本□□□算不上罵人好嗎?”她大叫,“剛剛那才□□□是罵人。至于□□□□根本稱不上罵人,純粹是個正常的稱呼。要是真有個適合罵人的時刻,就是當你媽告訴你,毫無理由地,她要把自己□重要的器官切掉一半——”
她還在講個不停,但逐漸變得像是咆哮。我只能像是趕蜜蜂一樣不停發出“噓!噓!”的驅趕聲。
“——難道你沒想到你再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樣進食——”
“你到底有什么毛病?”我終于還是問她了。
“媽,我只是不懂,你為什么就不能喜歡自己。你以前從來都不會——”
她講個不停。我盯著話筒看。我的孩子是何時壞掉的呢?我完全不記得是怎么發生的,不記得這種每下愈況,一開始是甜美的,□后整個人只剩下令人血液凝固的惱怒。她總是在發火,總是在指控些什么。她強行占據相對于我的道德高位,一次又一次。她不停讓我知道自己犯下大量罪行:為什么我沒教她什么是女性主義?為什么總是堅持什么都不去理解?還有這次,這次的指控拔得頭籌,值得以蛋糕獎勵,不,別跳過這個俏皮話;語言就像其他事物一樣和食物交織在一起,至少可以說本來就該和食物交織在一起。她很生氣,我真高興自己無法讀出她的想法。我知道她的想法會讓我心碎。
電話沒聲音了。她掛了我電話。我把話筒擺回去,意識到我的姐妹正在門口望著我,其中兩人一臉同情,另一人看來揚揚得意。
我轉頭不看她們。為什么卡爾不能理解呢?她的身體不完美,但仍新鮮、充滿適應環境的能力。她還能避開我犯過的錯誤。她還能享受擁有全新開端的輕松。我是沒有自制力的人,但到了明天,我會直接把控制權交出去,一切就能再次回到正軌。
電話響了。卡爾?是她又打回來了嗎?結果是我的外甥女。她為了回學校讀書正靠著賣刀具存錢,而她回學校是為了——唉,我好像沒聽到這部分,但反正,她只要跟我談論刀子,就能拿到薪水,所以我乖乖聽她介紹一切,聽她一步步介紹,□后買了一把中間有特殊切孔的干酪刀——“這樣干酪就不會粘在刀片上了,懂嗎?”她說。
派對恐懼癥(精裝) 目錄
為丈夫縫的那一針 —15
母親們 —55
十惡不赦 —83
真女人就該有身體 —16□
吃八口 —194
駐村者 —□□1
派對恐懼癥 —□86
致 謝 —317
派對恐懼癥(精裝) 相關資料
這部書是充滿野性的,覆滿亮片和鱗甲,安吉拉·卡特、凱莉·林克、海倫·奧耶耶美這些寓言作者的影響在馬查多的作品中閃耀,也混合了科幻、恐怖故事的元素。
——《紐約時報》
這本書有一些科幻,有一些幻想,通篇都幽默風趣。馬查多的小說討論的是一些不可思議的身為女人的方式:完全做她自己。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這是一部令人意外、獨具一格、野心勃勃的小說集,充滿了獵奇的故事,但它們揭示的是有關身為女性的那些無處不在又未曾言明的真相,而這是那些更“現實主義”的寫作所難以企及的。
——美國國家公共電臺
《派對恐懼癥》是無與倫比的:作者用荒誕奇詭的敘事才能講述的是那些切中要害,但此前卻被我們忽略的事……馬查多展現了發自肺腑深處的寫作可以多么獨特、具有顛覆性、充滿驕傲和樂趣,即使這肺腑已經受到創傷。
——《洛杉磯時報》
《派對恐懼癥》的語言如此富有質感,你簡直想把這些句子拿起來放在手指間摩挲……一種強健的女性主義精神流溢在整部書中,作者對女性身體的思考集中于性、權力、快樂、痛苦和自我掙扎。很少有作者像馬查多這樣善于在寫作中激發身體感覺:在血肉中棲息的無數種感受及其混亂與狂喜。馬查多將迥然不同的、互相沖撞的元素融為一體。
——《波士頓環球報》
《派對恐懼癥》是一部令人贊嘆的處女作,黑暗而熠熠閃光,如黑夜,如刀鋒。
——書籍論壇
在馬查多筆下,似乎一切事物都經歷了摧毀和重生。
——《明星論壇報》
派對恐懼癥(精裝) 作者簡介
卡門•瑪麗亞•馬查多(Carmen Maria Machado),1986年生,美國作家、批評家。她的作品以充滿荒誕的想象力著稱,曾入選美國年度□佳怪異小說選集等。《為丈夫縫的那一針》入圍□014年星云獎決選名單。她的小說集《派對恐懼癥》入圍□017年美國國家圖書獎決選名單。
- >
自卑與超越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
- >
苦雨齋序跋文-周作人自編集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歷史與人類學概述
- >
企鵝口袋書系列·偉大的思想20:論自然選擇(英漢雙語)
- >
中國歷史的瞬間
- >
伊索寓言-世界文學名著典藏-全譯本
- >
史學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