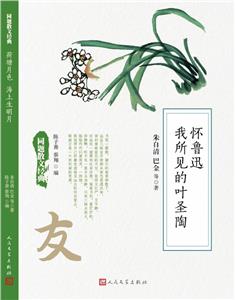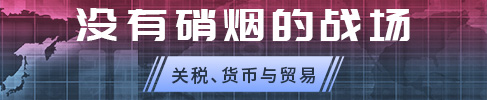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人民文學社《我所見的葉圣陶懷魯迅》 版權信息
- ISBN:9787020125982
- 條形碼:9787020125982 ; 978-7-02-012598-2
- 裝幀:一般輕型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人民文學社《我所見的葉圣陶懷魯迅》 內容簡介
中國素來是一散文大國,古之文章,已傳唱千世。而至現代,散文再度勃興,名篇佳作,不勝枚舉。閱讀經典散文,親近母語的魅力,具有著重要的意義。“同題散文經典”叢書對中國現當代的散文名篇進行重新分類,按照不同的主題編選成冊,比如山、河、湖、海、春、夏、秋、冬、風、花、雪、月、醉、生、夢、死、衣、食、住、行等。這樣的分類編選,將不同名家創作的相同主題的經典散文編選成書,每冊的內容相對集中,既方便讀者閱讀,也可作為學習寫作的范本。 本書精選現當代著名作家以“友”為題的經典散文,有魯迅的《范愛農》和《憶劉半農君》,有徐志摩的《吊劉叔和》,也有冰心的《憶淑敏》、林徽因的《悼志摩》,郁達夫的《懷魯迅》、朱自清的《我所見的葉圣陶》等,共收編散文37篇。
人民文學社《我所見的葉圣陶懷魯迅》 目錄
人民文學社《我所見的葉圣陶懷魯迅》 節選
范愛農 ◎魯迅 在東京的客店里,我們大抵一起來就看報。學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專愛打聽社會上瑣事的就看《二六新聞》。一天早晨,辟頭就看見一條從中國來的電報,大概是: “安徽巡撫恩銘被Jo Shiki Rin刺殺,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煥發地互相告語,并且研究這刺客是誰,漢字是怎樣三個字。但只要是紹興人,又不專看教科書的,卻早已明白了。這是徐錫麟,他留學回國之后,在做安徽候補道,辦著巡警事務,正合于刺殺巡撫的地位。 大家接著就預測他將被極刑,家族將被連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紹興被殺的消息也傳來了,徐錫麟是被挖了心,給恩銘的親兵炒食凈盡。人心很憤怒。有幾個人便秘密地開一個會,籌集川資;這時用得著日本浪人了,撕烏賊魚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蓀的家屬去。 照例還有一個同鄉會,吊烈士,罵滿洲;此后便有人主張打電報到北京,痛斥滿政府的無人道。會眾即刻分成兩派:一派要發電,一派不要發。我是主張發電的,但當我說出之后,即有一種鈍滯的聲音跟著起來: “殺的殺掉了,死的死掉了,還發什么屁電報呢。” 這是一個高大身材,長頭發,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總像在渺視。他蹲在席子上,我發言大抵就反對;我早覺得奇怪,注意著他的了,到這時才打聽別人:說這話的是誰呢,有那么冷?認識的人告訴我說:他叫范愛農,是徐伯蓀的學生。 我非常憤怒了,覺得他簡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殺了,連打一個電報還害怕,于是便堅執地主張要發電,同他爭起來。結果是主張發電的居多數,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來擬電稿。 “何必推舉呢?自然是主張發電的人啰~~”他說。 我覺得他的話又在針對我,無理倒也并非無理的。但我便主張這一篇悲壯的文章必須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為他比別人關系更密切,心里更悲憤,做出來就一定更動人。于是又爭起來。結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誰承認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只留下一個擬稿的和一兩個干事,等候做好之后去拍發。 從此我總覺得這范愛農離奇,而且很可惡。天下可惡的人,當初以為是滿人,這時才知道還在其次;**倒是范愛農。中國不革命則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須將范愛農除去。 然而這意見后來似乎逐漸淡薄,到底忘卻了,我們從此也沒有再見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鄉做教員,大概是春末時候罷,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見了一個人,互相熟視了不過兩三秒鐘,我們便同時說: “哦哦,你是范愛農!” “哦哦,你是魯迅!” 不知怎地我們便都笑了起來,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還是那樣,然而奇怪,只這幾年,頭上卻有了白發了,但也許本來就有,我先前沒有留心到。他穿著很舊的布馬褂,破布鞋,顯得很寒素。談起自己的經歷來,他說他后來沒有了學費,不能再留學,便回來了。回到故鄉之后,又受著輕蔑,排斥,迫害,幾乎無地可容。現在是躲在鄉下,教著幾個小學生糊口。但因為有時覺得很氣悶,所以也乘了航船進城來。 他又告訴我現在愛喝酒,于是我們便喝酒。從此他每一進城,必定來訪我,非常相熟了。我們醉后常談些愚不可及的瘋話,連母親偶然聽到了也發笑。一天我忽而記起在東京開同鄉會時的舊事,便問他: “那一天你專門反對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么緣故呢?” “你還不知道?我一向就討厭你的,——不但我,我們。” “你那時之前,早知道我是誰么?” “怎么不知道。我們到橫濱,來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么?你看不起我們,搖搖頭,你自己還記得么?” 我略略一想,記得的,雖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時是子英來約我的,說到橫濱去接新來留學的同鄉。汽船一到,看見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將行李放到稅關上去候查檢,關吏在衣箱中翻來翻去,忽然翻出一雙繡花的弓鞋來,便放下公事,拿著仔細地看。我很不滿,心里想,這些鳥男人,怎么帶這東西來呢。自己不注意,那時也許就搖了搖頭。檢驗完畢,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須上火車。不料這一群讀書人又在客車上讓起坐位來了,甲要乙坐在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讓未終,火車已開,車身一搖,即刻跌倒了三四個。我那時也很不滿,暗地里想:連火車上的坐位,他們也要分出尊卑來……。自己不注意,也許又搖了搖頭。然而那群雍容揖讓的人物中就有范愛農,卻直到這一天才想到。豈但他呢,說起來也慚愧,這一群里,還有后來在安徽戰死的陳伯平烈士,被害的馬宗漢烈士;被囚在黑獄里,到革命后才見天日而身上永帶著匪刑的傷痕的也還有一兩人。而我都茫無所知,搖著頭將他們一并運上東京了。徐伯蓀雖然和他們同船來,卻不在這車上,因為他在神戶就和他的夫人坐車走了陸路了。 我想我那時搖頭大約有兩回,他們看見的不知道是那一回。讓坐時喧鬧,檢查時幽靜,一定是在稅關上的那一回了,試問愛農,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們帶這東西做什么?是誰的?” “還不是我們師母的?”他瞪著他多白的眼。 “到東京就要假裝大腳,又何必帶這東西呢?” “誰知道呢?你問她去。” 到冬初,我們的景況更拮據了,然而還喝酒,講笑話。忽然是武昌起義,接著是紹興光復。第二天愛農就上城來,戴著農夫常用的氈帽,那笑容是從來沒有見過的。 “老迅,我們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復的紹興。我們同去。” 我們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滿眼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什么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柜是軍械司長……。這軍政府也到底不長久,幾個少年一嚷,王金發帶兵從杭州進來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會來。他進來以后,也就被許多閑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大做王都督。在衙門里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天氣還并不冷。 我被擺在師范學校校長的飯碗旁邊,王都督給了我校款二百元。愛農做監學,還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談閑天。他辦事,兼教書,實在勤快得可以。 “情形還是不行,王金發他們。”一個去年聽過我的講義的少年來訪問我,慷慨地說,“我們要辦一種報來監督他們。不過發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還有一個是子英先生,一個是德清先生。為社會,我們知道你決不推卻的。” 我答應他了。兩天后便看見出報的傳單,發起人誠然是三個。五天后便見報,開首便罵軍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員;此后是罵都督,都督的親戚,同鄉,姨太太……。 這樣地罵了十多天,就有一種消息傳到我的家里來,說都督因為你們詐取了他的錢,還罵他,要派人用手槍來打死你們了。 別人倒還不打緊,**個著急的是我的母親,叮囑我不要再出去。但我還是照常走,并且說明,王金發是不來打死我們的,他雖然綠林大學出身,而殺人卻不很輕易。況且我拿的是校款,這一點他還能明白的,不過說說罷了。 果然沒有來殺。寫信去要經費,又取了二百元。但仿佛有些怒意,同時傳令道:再來要,沒有了! 不過愛農得到了一種新消息,卻使我很為難。原來所謂“詐取”者,并非指學校經費而言,是指另有送給報館的一筆款。報紙上罵了幾天之后,王金發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于是乎我們的少年們便開起會議來,**個問題是:收不收?決議曰:收。第二個問題是:收了之后罵不罵?決議曰:罵。理由是:收錢之后,他是股東;股東不好,自然要罵。 我即刻到報館去問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說了幾句不該收他錢的話,一個名為會計的便不高興了,質問我道: “報館為什么不收股本?” “這不是股本……。” ...... 第二天打撈體,是在菱蕩里找到的,直立著。 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還是自殺。 他死后一無所有,遺下一個幼女和他的夫人。有幾個人想集一點錢作他女孩將來的學費的基金,因為一經提議,即有族人來爭這筆款的保管權,——其實還沒有這筆款,——大家覺得無聊,便無形消散了。 現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兒景況如何?倘在上學,中學已該畢業了罷。 十一月十八日。 (1926年) 吊劉叔和 ◎徐志摩 一向我的書桌上是不放相片的。這一月來有了兩張,正對我的坐位,每晚更深時就只他們倆看著我寫,伴著我想。院子里偶爾聽著一聲清脆,有時是蟲,有時是風卷敗葉,有時我想象是我們親愛的故世人從墳墓的那一邊吹過來的消息。伴著我的一個是小,一個是“老”:小的就是我那三月間死在柏林的彼得,老的是我們鐘愛的劉叔和,“老老”。彼得坐在他的小皮椅上,抿緊著他的小口,圓睜著一雙秀眼,仿佛性急要媽拿糖給他吃,多活靈的神情!但在他右肩空白上分明題著這幾行小字:“我的小彼得,你在時我沒福見你,但你這可愛的遺影應該可以伴我終身了。”老老是新長上幾根看得見的上唇須在他那件常穿的緞褂里欠身坐著,嚴正在他的眼內,和藹在他的口頷間。 ...... 但是隨你怎樣看法,這生死間的隔絕,終究是個無可奈何的事實,死去的不能復活,活著的不能到墳墓的那一邊去探望。到絕海里去探險我們得合伙,在大漠里游行我們得結伴;我們到世上來做人,歸根說,還不只是惴惴的來尋訪幾個可以共患難的朋友,這人生有時比絕海更兇險,比大漠更荒涼,要不是這點子友誼的同情我**個就不敢向前邁步了。叔和真是我們的一個。他的性情是不可信的溫和,“頂好說話的老老”;但他每當論事,卻又絕對的不茍同,他的議論,在他起勁時,就比如山壑間雨后的亂泉,石塊壓不住它,蔓草掩不住它。誰不記得他那永遠帶傷風的嗓音,他那永遠不平衡的肩背,他那怪樣的激昂的神情?通伯在他那篇《劉叔和》里說起當初在海外老老與傅孟真的豪辯,有時竟連“吶吶不多言”的他,也“免不了加入他們的戰隊”。這三位衣常敝,履無不穿的“大賢”在倫敦東南隅的陋巷,點煤氣油燈的斗室里,真不知有多少次借光柏拉圖與盧騷與斯賓塞的迷力,欺騙他們告空虛的腸胃——至少在這一點他們三位是一致同意的!但通伯卻忘了告訴我們他自己每回加入戰團時的特別情態,我想我應得替他補白。我方才用亂泉比老老,但我應得說他是一竄野火,焰頭是斜著去的;傅孟真,不用說,更是一竄野火,更猖獗,焰頭是斜著來的;這一去一來就發生了不得開交的沖突。在他們*不得開交時劈頭下去了一瓢冷水,雨竄野火都吃了驚,暫時翳了回去。那一瓢冷水就是通伯;他是出名澆冷水的圣手。
人民文學社《我所見的葉圣陶懷魯迅》 作者簡介
陳子善,有名學者、書人、張愛玲研究專家。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文學數據與研究中心主任。長期致力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蔡翔,有名文學評論家、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上海作家協會理事,曾任《上海文學》雜志社執行副主編,現為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生導師。
- >
詩經-先民的歌唱
- >
中國歷史的瞬間
- >
隨園食單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裝共3冊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歷史與人類學概述
- >
史學評論
- >
煙與鏡
- >
企鵝口袋書系列·偉大的思想20:論自然選擇(英漢雙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