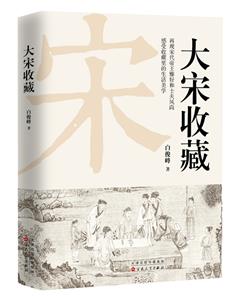-
>
兩種文化之爭 戰后英國的科學、文學與文化政治
-
>
東方守藝人:在時間之外(簽名本)
-
>
易經
-
>
辛亥革命史叢刊:第12輯
-
>
(精)唐風拂檻:織物與時尚的審美游戲(花口本)
-
>
日本禪
-
>
日本墨繪
大宋收藏 版權信息
- ISBN:9787530679944
- 條形碼:9787530679944 ; 978-7-5306-7994-4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大宋收藏 本書特色
☆ 引證豐富,資料翔實,經典插圖,講述了宋代收藏的故事 作者治學嚴謹,本書引證資料非常豐富,既包括《宋史》《續資治通鑒續長編》《宣和博古圖》《宣和書譜》《宣和畫譜》等歷史和藝術資料,也包括《夢溪筆談》《東京夢華錄》《夢梁錄》等宋人筆記,此外作者還參考了當前新的研究成果,如伊沛霞的《宋徽宗》和若干文獻資料,真正做到了下筆有出處,言之有據。 ☆ 再現宋代帝王雅好與士夫風尚 本書從宋人的收藏行為入手,以兩宋皇家和士夫的收藏活動為主,分別考察皇家與士夫的藏品搜集、保存、整理以及由此生發的政治功用、文化活動、社會現象乃至歷史事件等。同時,又圍繞宋人的收藏活動,在收藏的行為邏輯上串聯成線,試圖勾勒出宋代收藏的圖景,再現宋代的帝王雅好和士夫風尚。 ☆ 感受收藏里的生活美學 宋人借助收藏、唱和等文化活動“雅化生活”,把收藏深度融入了生活,不僅使收藏行為多了一份詩意的美學趣味,而且將收藏納入“生活美學”,提出了重要的收藏觀。千年后,我們依然能感受到宋代那份獨特的生活美學。 ☆ 天津博物館館長陳卓 推薦 《大宋收藏》由天津博物館館長陳卓作序并推薦。
大宋收藏 內容簡介
本書從宋代收藏活動切入, 系統闡釋了宋代文物藝術品收藏的歷史脈絡和主要特征。本書視角獨特, 摒棄了收藏史研究中注重文物藝術品遞藏信息、真偽辨別的套路, 而是借鑒了行為學的研究方法, 從文物藝術品的獲取、整理、儲放、研究、流傳等方面入手, 分別從皇家收藏、士夫收藏這兩個領域, 對宋人的收藏活動進行了系統、全面、深刻的解讀, 這些收藏囊括了宋代收藏的主要時代特征, 具有很強代表性, 體現了作者獨特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思路。
大宋收藏 目錄
導言001
帝王雅好
集藏與賞賜009
保存與整理026
分享與展示046
皇帝與高參058
嗜古與復古071
律令與盜掘086
圖諫與權謀095
戰爭與命運111
士夫風尚
市集與淘寶126
交換與唱和139
書樓與畫船159
疑古與正史179
考古與圖譜190
寓意與留意198
存真與作偽216
民風與時俗230
后記242
主要參考文獻246
大宋收藏 節選
圖諫與權謀 北宋神宗時期,“監門小吏”鄭俠畫過一幅《流民圖》獻給皇帝。嚴格說,這幅畫并不算真正的藝術品,也稱不上皇家收藏,但有繞不開、躲不過的理由。作為鄭俠的“圖諫”,《流民圖》就像一個橫沖直撞的小子,突然間走進歷史舞臺的中央,裹挾于宋代重大的政治事件,被賦予“一幅畫扳倒王安石”的政治想象,影響實在是太大了。既然曾被皇帝過眼,哪怕只是短暫地擁有,我們姑且作為特例和個案,將其納入皇家收藏的范疇。 鄭俠與《流民圖》的故事,太過曲折離奇,簡直是一出波詭云譎的宋代宮廷生活連續劇,如今再好的編劇恐怕也寫不出如此精彩的劇本。《宋史》為鄭俠專門立傳,我們就依據史料記載,抽去枝蔓,簡述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一幅畫扳倒了王安石 鄭俠(1041—1119),字介夫,福州福清(今屬福建)人,家住福清海口鎮覆釜山下(今為牛宅村),后遷至縣城西塘,世稱“西塘先生”,作品有《西塘集》《西塘先生文集》等。嘉祐四年(1059),鄭俠的父親鄭翚任江寧(今江蘇省南京市)酒稅監。治平二年(1065),鄭俠到父親任所,讀書于清涼寺。當時王安石任江寧知府,對鄭俠關愛有加。治平四年(1067),鄭俠中進士,授將仕郎,秘書省校書郎。 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受神宗重用,擔任參知政事(宰相),正式實行變法。此時,王安石依然沒有忘記鄭俠,提升其為光州(今河南省潢川縣)司法參軍。這是鄭俠與王安石人生中的“蜜月期”。作為后生晚輩,能夠得到當朝宰相的提攜與厚愛,鄭俠充滿感激。 熙寧五年(1072),兩人開始產生嫌隙。鄭俠任期期滿后入京三次拜見王安石,直陳變法弊端,并拒絕了王安石讓其通過考試做京官的建議。 “耿直男孩”離京后,還寄信王安石,陳述新法的危害。此后,鄭俠被重新任命,當了個京城安上門的監門小吏,即守門官。王安石對鄭俠的作為雖然不太開心,還是讓其子王雱轉告鄭俠,希望他去擔任修經局檢討的職位,后又讓門客黎東美再次勸說,未果。期間,鄭俠向黎東美陳述了變法帶來的弊端,黎東美轉呈王安石,王安石對變法做了局部修正。 熙寧六年(1073)至翌年三月,久旱不雨,史稱“人無生意”“身無完衣”。熙寧七年(1074)三月,鄭俠在京城再也憋不住了,畫《流民圖》,寫《論新法進流民圖疏》,請求朝廷罷除新法。奏疏送到閣門,遞不進去,鄭俠只好“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終于呈到神宗手里。鄭俠在奏疏中說:“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這算是拿性命相搏的“毒誓”,鄭俠將自己逼到了墻角。 接下來,神宗登場,歷史的一場大戲才算進入高潮。《宋史》記載:“疏奏,神宗反復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翌日,神宗下令更改王安石的政策,“民間歡叫相賀”。神宗又下《責躬詔》,廣求言路。三日后,果然天降甘霖,“遠近沾洽”,真是令人匪夷所思。這段記載頗有小說家的風格,不排除是后人“小說入史”的演繹。輔政大臣們此時也粉墨登場,入內祝賀,神宗把《流民圖》及奏疏甩給他們看,一通斥責,言外之意很明確:你們早干什么去了? 拍馬屁的時候比誰都積極! 王安石見此情形,不辭職也說不過去了。這一辭職,朝廷內外才知道神宗罷除新法竟然是《流民圖》和《論新法進流民圖疏》導致的,于是“群奸切齒”,把鄭俠交給御史臺,定了個“擅發馬遞罪”,也就是說,鄭俠當初上疏獻圖時,謊報了軍情,這也算是“實事求是”。而此時的神宗竟然也沒攔著。呂惠卿、鄧綰等人更是勸皇上不能聽“狂夫之言”,把新法“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神宗又任命呂惠卿為相,恢復了新法。 鄭俠還是那么耿直,再次上疏,這次他畫了《正直君子社稷之臣圖》《邪曲小人容悅之臣圖》,痛斥新任宰相呂惠卿。呂惠卿知道后大怒,奏為“謗訕”之罪,后來又覺得不過癮,想治鄭俠死罪。這次,神宗又登場了,他認為鄭俠的言行都是為了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既忠誠又可嘉,哪能深究? 于是,鄭俠保住一條命,被流放到英州。 元祐元年(1086),哲宗登基,大赦天下,鄭俠遇赦回到福清,后經蘇軾等人推薦,被起用為泉州教授。紹圣元年(1094)四月,“元祐黨人”受到打擊,包括蘇軾、鄭俠在內的人被貶斥放逐,鄭俠“二進宮”又被貶到英州,直到元符三年(1100)復職。大觀元年(1107),蔡京立“元祐黨人碑”,鄭俠又名列其中,再次被罷職還鄉,在家鄉待了12年后,鄭俠于宣和元年(1119)八月離開紛擾的人世,享年79歲。 《流民圖》的故事,眾說紛紜,有“站”王安石的,也有“站”鄭俠的。有人認為王安石當了“冤大頭”,被反對派設計陷害。而鄭俠無非是反對派手中的一顆棋子罷了,反對派祭出的“殺器”,就是《流民圖》。有人認為王安石驕傲偏執、打擊異見,變法確實不接地氣,弄得民不聊生,而鄭俠的“義舉”可彰千古。后人對這段公案的探幽實在是太多,在此不贅述,倒是王安石的“老對頭”司馬光對其有過公允評價:“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其實,這段評價用在鄭俠身上,也頗為貼切。 “流民圖”的圖畫范式 《流民圖》這幅畫是不是鄭俠所畫? 史料里沒有詳細記載。筆者認同高居翰的觀點——肯定是找人代筆。理由當然能找出很多,*直接的就是鄭俠不會畫畫,而且這幅畫要獻給皇帝,肯定不能敷衍了事,但又不能找當世高手代筆,否則易生破綻。這是依據歷史情景做出的判斷,在沒有確切史料證偽之前,筆者對此深信不疑。這就牽扯出另一個問題,如果是找人代筆,就意味著鄭俠絕不是心血來潮,而是蓄謀已久,背后肯定還有隱匿而不為人知的故事。 從收藏的角度而言,這次進獻,完全不同于宋代通常意義上的文物藝術品進獻,鄭俠壓根就沒有把《流民圖》作為藝術品對待,神宗也絕對不會將其歸類為藝術品———《流民圖》就是一張承載了政治訴求的“圖諫”———藝術屬性只是政治生活的附屬而已, 并非為了滿足皇帝對藝術的需求。所以這幅作品一旦完成政治使命,就沒有多少人關注了。它看上去像是王安石辭相的“關鍵因素”,實際上只是個工具。 這幅畫今已失傳,我們看不到了。神宗是否收藏過《流民圖》?如果收藏過的話,為什么不見于官方的書畫著錄?這兩個疑問好回答。神宗肯定是擁有過此畫,不管是長期擁有還是轉手送人。它不納入書畫著錄的原因,也無非是算不上正統意義上的書畫藝術品。如果沒有歸為內府而是流落民間,又是如何傳承、何時消失的? 今天,我們可以從南宋時期的《南游紀舊》《佩韋齋輯聞》等筆記中找到相關記載。據說此畫紙本設色,長六尺、高尺半,白描勾勒后敷色,畫技并不那么老成。畫上一支逃荒的隊伍逶迤于田間驛道,人物近百,有求乞老者、背幼農婦等等,還有惡吏騎馬持鞭,抽打衣不蔽體的少女。南宋后,元代版本的《三柳軒雜識》及明刻本《六硯齋筆記》也有記載,稱其真跡保存于鎮江民間的藏家手中。但明代之后,就不見于史料了。
大宋收藏 作者簡介
白俊峰,生于1976年,祖籍冀南,現居天津。畢業于南開大學中文系,曾作記者,現從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主要研究方向為藝術史與收藏史。
- >
推拿
- >
我從未如此眷戀人間
- >
朝聞道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朝花夕拾
- >
月亮虎
- >
唐代進士錄
- >
巴金-再思錄
- >
龍榆生:詞曲概論/大家小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