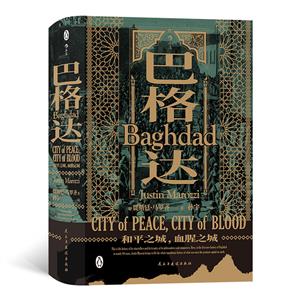-
>
清通鑒(全四冊)(精裝)
-
>
明通鑒(全三冊)(精裝)
-
>
跨太平洋的華人改良與革命 1898-1918
-
>
天有二日(簽名鈐印特裝本)
-
>
歐洲至暗時刻(1878-1923):一戰為何爆發及戰后如何重建
-
>
(精裝)奧托·馮· 俾斯麥與德意志帝國建立
-
>
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巴格達:和平之城,血腥之城:city of peace, city of blood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3930420
- 條形碼:9787513930420 ; 978-7-5139-3042-0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巴格達:和平之城,血腥之城:city of peace, city of blood 本書特色
◎近年來歷經諸多戰亂的屠宰場、人間煉獄巴格達為何曾經擁有和平之城的美譽?本書開創性地系統論述了巴格達的千年歷史,打破了人們對于這座城市動蕩混亂的固有印象,還原了它作為世界文明金頂明珠的璀璨一面,在這方面填補了中文世界的空白。 ◎為何巴格達被認為是伊斯蘭世界遜尼、什葉兩派分裂的中間點?為何千年以來巴格達大規模沖突不斷?薩達姆帶領遜尼派屠殺什葉派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本書詳細解釋了團城巴格達的建立以及由盛轉衰的復雜過程,深刻挖掘了隱藏在無數流血事件表象下的生動真相。 ◎新銳歷史學家賈斯廷·馬羅齊關于征服者帖木兒的暢銷傳記,被《星期日電訊報》評為該年度圖書。本書則是關于世界歷史名城巴格達前世今生的歷史著述,更是榮獲了頗具分量的2015年度英國皇家文學學會翁達杰獎。 ◎中東史專家休·肯尼迪稱贊本書是我們在英語世界所能獲得的有關巴格達歷史的*佳論述。
巴格達:和平之城,血腥之城:city of peace, city of blood 內容簡介
自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哈里發曼蘇爾于762年營建巴格達以來,這座城市就有“和平之城”的美譽,但從它不同尋常的歷史來看,它也經歷過十分血腥的統治年月。當美軍于2003年進入巴格達城時,他們成了這座城市動蕩歷史的新參與者。回溯其歷史,在阿拔斯王朝統治時期,巴格達一直是阿拉伯帝國的中心,金碧輝煌的宮殿群、宏偉的清真寺、伊斯蘭學院和熱鬧的集市鱗次櫛比。它是“代數之父”花拉子米生活過的城市;也是哈里發哈倫·拉希德的都城,古代阿拉伯民間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描寫了諸多有關這位哈里發及其都城的故事。作為一個繁榮的交易中心,巴格達吸引了大量來自中亞和大西洋地區的商人,其經濟的繁盛程度曾招致西方和東方的同等羨慕。 然而,巴格達的歷史也有其血腥殘酷的一面。這座城市經常遭受瘟疫、饑荒和洪水的侵襲;經歷過大量恐怖的外敵入侵和軍事占領;也時常需要忍受獨裁者的殘暴統治。因此,巴格達的歷史也是其統治者和征服者的歷史,例如奧斯曼帝國的蘇丹、波斯沙阿、成吉思汗之孫旭烈兀、“上帝之鞭”帖木兒。當然,本書還生動地講述了從奴隸到士兵等普通民眾所經受的漫長而艱辛的生活。作者賈斯廷·馬羅齊通過流暢的文筆和富有新意的視角敘述了巴格達1300多年的輝煌和苦難,勾勒出了巴格達這座城市迷人的歷史輪廓。
巴格達:和平之城,血腥之城:city of peace, city of blood 目錄
第1章 哈里發與他的首都 1
曼蘇爾與巴格達的建立,750—775年
第2章 哈倫·拉希德與巴格達的“一千零一夜” 35
775—809年
第3章 “學者的源泉”,世界的中心 81
809—892年
第4章 阿拔斯王朝晚期 121
別了,黃金草原,892—1258年
第5章 “毀滅朝圣” 177
蒙古與韃靼的浩劫,1258—1401年
第6章 黑羊,白羊 211
1401—1534年
第7章 土耳其人與旅人 235
1534—1639年
第8章 瘟疫、帕夏與馬穆魯克 269
1639—1831年
第9章 帝國碰撞 309
1831—1917年
第10章 英式君主 365
巴格達三王,1917—1958年
第11章 政變與復興黨 425
屠戮之母,1958年至今
注 釋 488
參考文獻 515
出版后記 534
巴格達:和平之城,血腥之城:city of peace, city of blood 節選
英式君主 巴格達三王,1917—1958年 英國人征服了這個國家,他們傾散財富,在這片土地上遍灑他們的熱血。英國人、澳大利亞人、印度穆斯林和拜偶像者的鮮血浸入了伊拉克的土地。他們難道不該享受贏得的戰利品嗎?先前的征服者給這個國家施加了太多苦難。正如它曾被他們征服一樣,它如今被英國人征服了。他們將要建立起自己的統治。女士,您的國家偉大,富有且強盛。而我們的權力算得上什么呢?假如我說我希望能受英國人統治,而英國人并不樂意管理我們,我能怎樣強迫他們呢?假如我說我希望別人來統治我們,但英國人執意要擔此重任,我又怎么能驅逐他們呢?我認可你們的勝利。你們是統治者,而我們是臣民。如果問我對英國繼續統治有何看法,我會回答我服從于勝利者。 ——巴格達的納吉布 (致格特魯德·貝爾,1919年2月1) 我們這里的天氣和我們一樣,都是熱一天,冷一天。我們也會勃然而起,直至讓你以為全宇宙都要分崩離析,然后又平靜下來,以至于讓你以為我們已不剩一點激情。 ——賈布拉·易卜拉欣·賈布拉 (《狹街獵人》,1960年) 被戰爭摧殘,被火焰吞噬,爆炸聲回響不已,凄慘的人民忍饑挨餓,許多建筑被徹底夷為平地,莫德于1917年3月11日進入的巴格達城與傳說中的阿拔斯王朝都城毫無相似之處。面對滿目臟亂、凄慘和被以各種方式毀滅的殘跡,英國人在**次見到令人驚嘆的藍金穹頂,修長的宣禮塔,以及在朝霞與暮色中倒映在底格里斯河平靜如鏡的河面上的椰棗林和桔園時心中所懷的一切浪漫憧憬,很快便消解盡凈了。 據英國官方的**次世界大戰史記載,巴格達城外圍散落著“死去動物的尸骨”。英印軍隊開進城市后,看到了“悲慘荒廢、搖搖欲墜的棕色泥磚房屋和……狹窄骯臟的街道”,“這里既沒有人維持衛生,也沒有人打掃環境,惡臭的味道彌漫不散,數百條餓得半死的病犬四處游蕩”。2 從沙漠和瘧疾蔓延的沼澤中艱苦跋涉而出,經歷了令人萎靡的暑熱和刺人骨髓的嚴寒后,英軍將士們原本渴望在那個理想化的巴格達城內休養生息,甚至對一年多沒有見到過的女子大飽眼福一番,毫不令人驚訝的是,他們都感到“大失所望”和“幻想破滅”。**批進入巴格達的軍人之一、戰地記者艾德蒙·坎德勒干巴巴地寫道:“幻滅之后,浪漫全無。”事實上,“這里沒有什么遺跡了,巴格達所有的精尼也舉不起一杯啤酒”。3然后,英軍繼續向北方和西方進攻土軍。 更讓英軍官兵心碎不已的是,土軍在撤退時在全城布下了隱藏的爆炸物。高墻宏偉的城堡被籠罩在汽油燃起的熊熊大火與滾滾黑煙之中,“因為被滿載著(炸藥)的火車引爆了軍火庫”。4莫德的部隊花了一天一夜才撲滅大火。 城內的英國產業曾興隆了幾十年。但如今“沒有一點點英國財產幸存下來,除了英國領事館,這座氣派的建筑矗立在河岸上,令人禁不住回想起大英帝國與土耳其帝國曾經維持著一段特殊而莊嚴的關系”。英國領事館被改建成了一座戰地醫院,據震驚的同時也是熱情支持英軍的美國記者埃莉諾·伊根記錄,即使是這座醫院也“骯臟混亂以至于任何人都無法描述”。5英國官方歷史也為這出悲慘的景象作了證明,據其記載,土軍征用作為醫療場所的大型建筑都“骯臟雜亂,害蟲橫行,難以言喻”。在城市適宜駐軍之前,“英軍馬不停蹄地開始了衛生工作”,其中包括為7000名傷病員供應醫院床鋪。6狹窄的街道上充斥著軍隊巡邏的叮當聲,士兵們逐家逐戶搜查武器,在集市維持治安,盡管大部分房屋和商戶都早已遭到洗劫,如今門戶大敞,徐徐悶燒。巴格達的暴徒利用從土軍撤離到莫德到來之間混亂無序的短短幾小時迅速動手,城中的猶太商人在3月11日凌晨2點至上午9點間共損失了200萬法郎。 大群巴格達人—阿拉伯人、猶太人、伊朗人、亞美尼亞人、迦勒底人和許多基督教支派信徒—紛紛出來迎接新的征服者。“他們在街道、陽臺和屋頂上列隊,一邊歡呼一邊拍手慶賀,”坎德勒寫道,“一群群學童在我們面前起舞,一邊喊叫一邊喝彩,城里的女子也穿起節慶裝束出來了。”7不到一個世紀后,巴格達也將以同樣稍縱即逝的熱情歡迎美軍士兵。 盡管滿目瘡痍,受莫德及其指揮部庇護的伊根還是發現這座被征服的城市極為迷人,頗具異域風情。在斗折蛇行的街道上,無數頭飾組成了一個源源不絕的隊列:裹頭巾,塔布什帽、軟草帽、軟木帽、草帽、無邊便帽,傳統的阿拉伯頭箍,盧爾人和庫爾德人頭戴的長氈管帽和巴赫蒂亞里人的無邊高帽,偶爾也有北方人的羊羔皮帽。這里有身穿英國長大衣、打著赤腳的布希爾苦力,裹著腰布的孟加拉人,戴耳環的馬德拉斯仆役,還有戴著草帽和眼鏡、一臉學究氣的中國人。頭戴綠色裹頭巾的賽義德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他們與穿黑袍的伊朗人比肩接踵,還有帕西人和外貌狂野的桑給巴爾人,斯瓦希里人和阿比西尼亞人,希臘人和猶太人,以及各門各派的基督徒—從加色丁禮教徒、亞美尼亞教徒到賽伯伊基督徒、聶斯托利教徒和雅各派教徒。她傾心于“ 波斯人、阿拉伯人和東方猶太人一同懶洋洋地喝咖啡,吸水煙”,數百位身穿多彩繽紛的長袍、不戴面紗的女子,“背著難以置信的重負艱難前行的庫爾德人”,以及“引人注目的一群群女苦力工,背著大捆木桿和沙漠草根”。之后還有身穿寬大黑袍、“頭戴高大裹頭巾的穆斯林長老”,“穿著不合身歐洲服飾、頭戴紅色菲茲帽的猶太人”,以及令她想起圣約瑟的“身穿多彩絲綢長袍、頭戴羔羊毛小帽的英俊波斯人”。她尤其為“古老的迦勒底基督徒”感到驚奇無比,他們身穿阿拉伯服飾,卻生著藍眼睛,而且“膚色白得像德國人一樣”。唯一負面的評論是關于東非奴隸的,這些男男女女“黑得好似黑檀木,眼睛瞟來瞟去,充滿了質疑與敵意”。8 當戰友還在家信中寫滿欣喜的思鄉之情、無趣的行伍玩笑以及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和辛巴達航海的奇特故事時,第38旅的擲彈兵喬治·科爾斯直接跑去了*近的酒家。他找到了一家酒館,“大約100個阿拉伯人正懶洋洋地倚在長沙發上,打著哈欠,喝著小杯薄荷茶,與此同時,一個亞美尼亞女孩站在略高的平臺上,在鋼琴和兩種奇異的弦樂器伴奏下跳著莎樂美舞”。在這場表演的高潮階段,那女孩“ 瘋狂起來—赤裸得仿佛剛從娘胎出來一樣!……真個是原形畢露的東方”!9 在倫敦,攻陷巴格達的消息受到戰爭叫囂者的大肆慶賀。“英國國旗飄揚在巴格達上空”,《戰爭畫報》如是宣稱道,“德國對東方帝國的黃粱美夢就此終結。”莫德攻陷這座城市,給了德國“整場戰爭中*為沉重的一擊,也給了奧斯曼帝國250年來*具毀滅性的一擊”。10 3月19日,莫德發表了著名的《巴格達宣言》,該宣言由英國政治家馬克·賽克斯起草,他是阿拉伯辦事處的創始人,也是1916年的《賽克斯-皮科秘密協定》起草者之一——這一協定在阿拉伯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奧斯曼帝國的中東領土割裂成分別由法國和英國影響與控制的地區。這份宣言明確提及阿拔斯王朝的往日榮耀、蒙古人的兇殘破壞和奧斯曼帝國在巴格達犯下的罪惡。 演說開始時,莫德向伊拉克人保證: 我們的軍隊并非作為征服者或敵人,而是作為解放者進入你們的國家和城市的。自從哈拉庫(旭烈兀)的時代以來,你們的城市和國家屈服于異族的暴政之下,你們的宮殿化為丘墟,你們的花園淪為荒蕪,你們的祖輩和如今你們自己只得在鐐銬中悲嘆。你們的男兒被強征去打你們不想打的戰爭,你們的財富被不義的人剝奪,揮霍在了偏遠的土地上。 然后,莫德重重抨擊了土耳其人,他們承諾的改革*終化作了可悲的畸形產物。而與之相反,大英帝國的決心已定,“你們將繁榮起來,一如既往,你們的土地曾經肥沃,你們的祖先一度為世界貢獻了文學、科學和藝術,巴格達往昔是世界一大奇跡”。 莫德強調了英國與巴格達之間“緊密的利益紐帶”,雙方的商人兩百年來共同經營,“互利共贏,友誼深厚”。德國人與土耳其人將巴格達作為自己的權力中心,用于進攻英國和它在波斯及阿拉伯地區的盟友;“因此英國政府不能對你們國家在當前或未來發生的事情袖手旁觀”。 他還為巴格達的政治命運做出了另一項——含糊而不祥的——保證。英國并不想“給你們強加外國的政府機構”,但希望在遵從“神圣律法”與“民族理想”的政府機構治理下,巴格達能夠繁榮起來,“你們的哲人和作家的期望能夠實現”。莫德將巴格達人的注意力吸引至阿拉伯沙漠,在那里,阿拉伯人已經“趕走了壓迫他們的德國人和土耳其人,擁立謝里夫·侯賽因為王,他的統治獨立而自由”。* 宣言*后以煽動性的強調作結,“許多高貴的阿拉伯人都已經為爭取阿拉伯的自由而死去了,死在了異族統治者的手上,死在了壓迫他們的土耳其人手上”。大英帝國決心保證“這些高貴的阿拉伯人不會白白死去。英國人民以及與其同盟的民族衷心希望阿拉伯民族能夠再度偉大起來,在世界各民族中間重現聲名”。 哦,巴格達的人民,還記得你們已在異族暴君統治下忍受了26代人的時間,他們一向挑撥阿拉伯各家族互相為敵,只為了從你們的分裂局面中牟利。這種政策深為大英帝國及其盟友所厭惡,因為在敵意與惡政之下,和平與繁榮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我受命邀請你們,通過你們的貴族、長老和代表,與大英帝國的政治代表以及英國軍隊合作,共同參與管理你們的民政事務,這樣你們便能與北方、東方、南方和西方的同胞團結起來,實現你們民族的理想。
巴格達:和平之城,血腥之城:city of peace, city of blood 作者簡介
賈斯廷·馬羅齊(Justin Marozzi),英國記者、歷史學家和旅行作家,畢業于劍橋大學,是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成員和白金漢大學高級研究員。曾在《金融時報》和《經濟學人》擔任駐外通訊記者,在伊拉克、阿富汗、達爾富爾、利比亞和索馬里等國和地區工作和生活過很長一段時間。已出版的著作有South from Barbary: along the Slave Routes of the Libyan Sahara和Tamerlane: Sword of Islam, Conqueror of the World等。 孫宇,畢業于河北民族師范學院英語翻譯專業,對于中世紀史、晚期古典史和伊斯蘭世界古代史有較深興趣和研究,譯作有《大征服:阿拉伯帝國的崛起》等。
- >
伊索寓言-世界文學名著典藏-全譯本
- >
唐代進士錄
- >
羅庸西南聯大授課錄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朝聞道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
- >
姑媽的寶刀
- >
推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