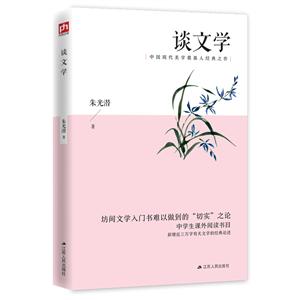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中國現代美學奠基人經典之作:談文學 版權信息
- ISBN:9787214236296
- 條形碼:9787214236296 ; 978-7-214-23629-6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現代美學奠基人經典之作:談文學 本書特色
本書是著名文藝理論家、現代美學奠基人朱光潛先生的經典作品,詳細論述了文學作品的形式體裁、表現風格、涵蓋內容等,皆是作者自己“學習文藝的甘苦之言”。他從文學的趣味講到文章的運思與節奏,再談文學與語文之關系以及翻譯技巧,由簡入繁層層推進,逐漸引領讀者體味文學之美,探索文學奧妙。 誠如作者所言:“在寫這些短文時,我一不敢憑空亂構,二不敢道聽途說,我想努力做到“切實”二字。我愿與肯用心的愛好文學的讀者們印證經驗。”那么翻開本書,與先生開啟一場跨越時空的文學會談吧!
中國現代美學奠基人經典之作:談文學 內容簡介
本書出自著名美學家朱光潛之筆,是青年朋友入門文學的優質讀本,是中學生課外閱讀書目。書中皆是朱光潛先生平生研究文藝的甘苦之言,既談文學,也談人生,把讀者輕松引入到學習文學的氛圍之中,內容深入淺出,語言平實自然。 另外,書中新增近三萬字朱光潛先生有關文學的經典論述作為附錄,使全書覆蓋的知識更加深廣,更有利于讀者進行研習。
中國現代美學奠基人經典之作:談文學 目錄
談文學
文學與人生 / 2
資稟與修養 / 9
文學的趣味 / 16
文學上的低級趣味(上):關于作品內容 / 23
文學上的低級趣味(下):關于作者態度 / 31
寫作練習 / 39
作文與運思 / 46
選擇與安排 / 53
咬文嚼字 / 60
散文的聲音節奏 / 66
文學與語文(上):內容、形式與表現 / 74
文學與語文(中):體裁與風格 / 82
文學與語文(下):文言、白話與歐化 / 89
作者與讀者 / 100
具體與抽象 / 110
情與辭 / 117
想象與寫實 / 124
精進的程序 / 130
談翻譯 / 136
附錄
我與文學 / 152
談學文藝的甘苦 / 155
談文學選本 / 160
談趣味 / 164
談讀詩與趣味的培養 / 168
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 / 174
人文方面幾類應讀的書 / 186
中國現代美學奠基人經典之作:談文學 節選
文學與人生 文學是以語言文字為媒介的藝術。就其為藝術而言,它與音樂圖畫雕刻及一切號稱藝術的制作有共同性:作者對于人生世相都必有一種獨到的新鮮的觀感,而這種觀感都必有一種獨到的新鮮的表現;這觀感與表現即內容與形式,必須打成一片,融合無間,成為一種有生命的和諧的整體,能使觀者由玩索而生欣喜。達到這種境界,作品才算是“美”。美是文學與其他藝術所必具的特質。就其以語言文字為媒介而言,文學所用的工具就是我們日常運思說話所用的工具,無待外求,不像形色之于圖畫雕刻,樂聲之于音樂。每個人不都能運用形色或音調,可是每個人只要能說話就能運用語言,只要能識字就能運用文字。語言文字是每個人表現情感思想的一套隨身法寶,它與情感思想有*直接的關系。因為這個緣故,文學是一般人接近藝術的一條*直截簡便的路;也因為這個緣故,文學是一種與人生*密切相關的藝術。 我們把語言文字聯在一起說,是就文化現階段的實況而言,其實在演化程序上,先有口說的語言而后有手寫的文字,寫的文字與說的語言在時間上的距離可以有數千年乃至數萬年之久,到現在世間還有許多民族只有語言而無文字。遠在文字未產生以前,人類就有語言,有了語言就有文學。文學是*原始的也是*普遍的一種藝術。在原始民族中,人人都歡喜唱歌,都歡喜講故事,都歡喜戲擬人物的動作和姿態。這就是詩歌、小說和戲劇的起源。于今仍在世間流傳的許多古代名著,像中國的《詩經》,希臘的荷馬史詩,歐洲中世紀的民歌和英雄傳說,原先都由口頭傳誦,后來才被人用文字寫下來。在口頭傳誦的時期,文學大半是全民眾的集體創作。一首歌或是一篇故事先由一部分人倡始,一部分人隨和,后來一傳十,十傳百,輾轉相傳,每個傳播的人都貢獻一點心裁把原文加以潤色或增損。我們可以說,文學作品在原始社會中沒有固定的著作權,它是流動的,生生不息的,集腋成裘的。它的傳播期就是它的生長期,它的欣賞者也就是它的創作者。這種文學作品*能表現一個全社會的人生觀感,所以從前關心政教的人要在民俗歌謠中窺探民風國運,采風觀樂在春秋時還是一個重要的政典。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說,原始社會的文字就幾乎等于它的文化;它的歷史、政治、宗教、哲學等等都反映在它的詩歌、神話和傳說里面。希臘的神話史詩,中世紀的民歌傳說以及近代中國邊疆民族的歌謠、神話和民間的故事都可以為證。 口傳的文學變成文字寫定的文學,從一方面看,這是一個大進步,因為作品可以不純由記憶保存,也不純由口誦流傳,它的影響可以擴充到更久更遠。但從另一方面看,這種變遷也是文學的一個厄運,因為識字另需一番教育,文學既由文字保存和流傳,文字便成為一種障礙,不識字的人便無從創造或欣賞文學,文學便變成一個特殊階級的專利品。文人成了一個特殊階級,而這階級化又隨社會演進而日趨尖銳,文學就逐漸和全民眾疏遠。這種變遷的壞影響很多,**,文學既與全民眾疏遠,就不能表現全民眾的精神和意識,也就不能從全民眾的生活中吸收力量與滋養,它就不免由窄狹化而傳統化,形式化,僵硬化。其次。它既成為一個特殊階級的興趣,它的影響也就限于那個特殊階級,不能普及于一般人,與一般人的生活不發生密切關系,于是一般人就把它認為無足輕重。文學在文化現階段中幾已成為一種奢侈,而不是生活的必需。在*初,凡是能運用語言的人都愛好文學;后來文字產生,只有識字的人才能愛好文學;現在連識字的人也大半不能愛好文學,甚至有一部分鄙視或仇視文學,說它的影響不健康或根本無用。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人要鄭重其事地來談文學,難免有幾分心虛膽怯,他至少須說出一點理由來辯護他的不合時宜的舉動。這篇開場白就是替以后陸續發表的十幾篇談文學的文章作一個辯護。 先談文學有用無用問題。一般人嫌文學無用,近代有一批主張“為文藝而文藝”的人卻以為文學的妙處正在它無用。它和其它藝術一樣,是人類超脫自然需要的束縛而發出的自由活動。比如說,茶壺有用,因能盛茶,是壺就可以盛茶,不管它是泥的瓦的扁的圓的,自然需要止于此。但是人不以此為滿足,制壺不但要能盛茶,還要能娛目賞心,于是在質料、式樣、顏色上費盡機巧以求美觀。就淺狹的功利主義看,這種功夫是多余的,無用的;但是超出功利觀點來看,它是人自作主宰的活動。人不憚煩要作這種無用的自由活動,才顯得人是自家的主宰,有他的尊嚴,不只是受自然驅遣的奴隸;也才顯得他有一片高尚的向上心。要勝過自然,要彌補自然的缺陷,使不完美的成為完美。文學也是如此。它起于實用,要把自己所感的說給旁人知道;但是它超過實用,要找好話說,要把話說的好,使旁人在話的內容和形式上同時得到愉快。文學所以高貴,值得我們費力探討,也就在此。 這種“為文藝而文藝”的看法確有一番正當道理,我們不應該以淺狹的功利主義去估定文學的身價。但是我以為我們縱然退一步想,文學也不能說是完全無用。人之所以為人,不只因為他有情感思想,尤在他能以語言文字表現情感思想。試假想人類根本沒有語言文字,像牛羊犬馬一樣,人類能否有那樣燦爛的文化?文化可以說大半是語言文字的產品。有了語言文字,許多崇高的思想,許多微妙的情境,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跡才能那樣流傳廣播,由一個心靈出發,去感動無數的心靈,去啟發無數心靈的創作。這感動和啟發的力量大小與久暫,就看語言文字運用的好壞。在數千載之下,《左傳》《史記》所寫的人物事跡還能活現在我們眼前,若沒有左丘明、司馬遷的那種生動的文筆,這事如何能做到?在數千載之下,柏拉圖的《對話集》所表現的思想對于我們還是那么親切有趣,若沒有柏拉圖的那種深入而淺出的文筆,這事又如何能做到?從前也許有許多值得流傳的思想與行跡,因為沒有遇到文人的點染,就湮沒無聞了。我們自己不時常感覺到心里有話要說而不出的苦楚么?孔子說得好:“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單是“行遠”這一個功用就深廣不可思議。 柏拉圖、盧梭、托爾斯泰和程伊川都曾懷疑到文學的影響,以為它是不道德的或是不健康的。世間有一部分文學作品確有這種毛病,本無可諱言,但是因噎不能廢食,我們只能歸咎于作品不完美,不能斷定文學本身必有罪過。從純文藝觀點看,在創作與欣賞的聚精會神的狀態中,心無旁涉,道德的問題自無從闖入意識閾。縱然離開美感態度來估定文學在實際人生中的價值,文藝的影響也決不會是不道德的,而且一個人如果有純正的文藝修養,他在文藝方面所受的道德影響可以比任何其他體驗與教訓的影響更較深廣。“道德的”與“健全的”原無二義。健全的人生理想是人性的多方面的諧和的發展,沒有殘廢也沒有臃腫。譬如草木,在風調雨順的環境之下,它的一般生機總是欣欣向榮,長得枝條茂暢,花葉扶疏。情感思想便是人的生機,生來就需要宣泄生長,發芽開花。有情感思想而不能表現,生機便遭窒塞殘損,好比一株發育不完全而呈病態的花草。文藝是情感思想的表現,也就是生機的發展,所以要完全實現人生,離開文藝決不成。世間有許多對文藝不感興趣的人干枯濁俗,生趣索然,其實都是一些精神方面的殘廢人,或是本來生機就不暢旺,或是有暢旺的生機因為窒塞而受摧殘。如果一種道德觀要養成精神上的殘廢人,它的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表現在人生中不是奢侈而是需要,有表現才能有生展,文藝表現情感思想,同時也就滋養情感思想使它生展。人都知道文藝是“怡情養性”的。請仔細玩索“怡養”兩字的意味!性情在怡養的狀態中,它必是健旺的,生發的,快樂的。這“怡養”兩字卻不容易做到,在這紛紜擾攘的世界中,我們大部分時間與精力都費在解決實際生活問題,奔波勞碌,很機械地隨著疾行車流轉,一日之中能有幾許時刻回想到自己有性情?還論怡養!凡是文藝都是根據現實世界而鑄成另一超現實的意象世界,所以它一方面是現實人生的反照,一方面也是現實人生的超脫。在讓性情怡養在文藝的甘泉時,我們霎時間脫去塵勞,得到精神的解放,心靈如魚得水地徜徉自樂;或是用另一個比喻來說,在干燥悶熱的沙漠里走得很疲勞之后,在清泉里洗一個澡,綠樹陰下歇一會兒涼。世間許多人在勞苦里打翻轉,在罪孽里打翻轉,俗不可耐,苦不可耐,原因只在洗澡歇涼的機會太少。 從前中國文人有“文以載道”的說法,后來有人嫌這看法的道學氣太重,把“詩言志”一句老話抬出來,以為文學的功用只在言志;釋志為“心之所之”,因此言志包含表現一切心靈活動在內。文學理論家于是分文學為“載道”“言志”兩派,仿佛以為這兩派是兩極端,絕不相容—“載道”是“為道德教訓而文藝”,“言志”是“為文藝而文藝”。其實這個問題的關鍵全在“道”字如何解釋。如果釋“道”為狹義的道德教訓,載道顯然就小看了文學。文學沒有義務要變成勸世文或是修身科的高頭講章。如果釋“道”為人生世相的道理,文學就決不能離開“道”,“道”就是文學的真實性。志為心之所之,也就要合乎“道”,情感思想的真實本身就是“道”,所以“言志”即“載道”,根本不是兩回事,哲學科學所談的是“道”,文藝所談的仍是“道”,所不同者哲學科學的道理是抽象的,是從人生世相中抽繹出來的,好比從鹽水中提出來的鹽;文藝的道是具體的,是含蘊在人生世相中的,好比鹽溶于水,飲者知咸,卻不辨何者為鹽,何者為水。用另一個比喻來說,哲學科學的道是客觀的、冷的、有精氣而無血肉的;文藝的道是主觀的、熱的,通過作者的情感與人格的滲瀝,精氣和血肉凝成完整生命的。換句話說,文藝的“道”與作者的“志”融為一體。 我常感覺到,與其說“文以載道”,不如說“因文證道”。《楞嚴經》記載佛有一次問他的門徒從何種方便之門,發菩提心,證圓通道。幾十個菩薩羅漢輪次起答,有人說從聲音,有人說從顏色,有人說從香味,大家共說出二十五個法門(六根、六塵、六識、七大,每一項都可成為證道之門)。讀到這段文章,我心里起了一個幻想,假如我當時在座,輪到我起立作答時,我一定說我的方便之門是文藝。我不敢說我證了道,可是從文藝的玩索,我窺見了道的一斑。文藝到了*高的境界,從理智方面說,對于人生世相必有深廣的觀照與徹底的了解,如阿波羅憑高遠眺,華嚴世界盡成明鏡里的光影,大有佛家所謂萬法皆空,空而不空的景象;從情感方面說,對于人世悲歡好丑必有平等的真摯的同情,沖突化除后的諧和,不沾小我利害的超脫,高等的幽默與高等的嚴肅,成為相反者之同一。柏格森說世界時時刻刻在創化中,這好比一個無始無終的河流,孔子所看到的“逝者如是夫,不舍晝夜”,希臘哲人所看到的“濯足清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所以時時刻刻有它的無窮的興趣。抓住某一時刻的新鮮景象與興趣而給以永恒的表現,這是文藝。一個對于文藝有修養的人決不感覺到世界的干枯或人生的苦悶。他自己有表現的能力固然很好,縱然不能,他也有一雙慧眼看世界,整個世界的動態便成為他的詩,他的圖畫,他的戲劇,讓他的性情在其中“怡養”。到了這種境界,人生便經過了藝術化,而身歷其境的人,在我想,可以算是一個有“道”之士。從事于文藝的人不一定都能達到這個境界,但是它究竟不失為一個崇高的理想,值得追求,而且在努力修養之后,可以追求得到。
中國現代美學奠基人經典之作:談文學 作者簡介
朱光潛(1897-1986) 筆名孟實、盟石,安徽桐城人,中國著名美學家、文藝理論家、教育家、翻譯家。生前長期擔任北京大學教授。主要著作有《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談修養》《談美》《談美書簡》《西方美學史》《悲劇心理學》《文藝心理學》《詩論》《談文學》等。
- >
我從未如此眷戀人間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裝共3冊
- >
月亮虎
- >
龍榆生:詞曲概論/大家小書
- >
伯納黛特,你要去哪(2021新版)
- >
有舍有得是人生
- >
朝聞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