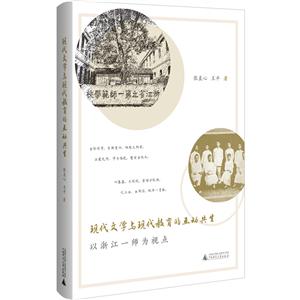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現代文學與現代教育的互動共生:以浙江一師為視點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9829412
- 條形碼:9787559829412 ; 978-7-5598-2941-2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現代文學與現代教育的互動共生:以浙江一師為視點 本書特色
本書提到了中國文學、藝術史上數十位赫赫有名的大師,如魯迅、李叔同、豐子愷、朱自清、俞平伯、葉圣陶等,他們都曾在浙江一師任教或求學。通過對他們在一師期間生活、工作與學習的描寫,本書闡述了現代文學與現代教育之間有著怎樣密不可分的關聯。
現代文學與現代教育的互動共生:以浙江一師為視點 內容簡介
二十世紀初葉,在新文化運動的感召下,南方一隅的浙江一師破空啼出了自己的初聲。新文學作家紛紛會聚于一師。一師不僅成了魯迅、李叔同、許壽裳、夏丏尊、劉大白、朱自清、俞平伯、葉圣陶、劉延陵、汪靜之、馮雪峰、潘漠華、曹聚仁、豐子愷、柔石、魏金枝等作家在彼一動蕩時代的托身所在;更衍為他們實踐社會理想、培植生命信念的場域。在一師,他們談學問道,交友結社,讀書濟世,于電光石火般的思想交流碰撞間,助成了教育改革與文學革命。
現代文學與現代教育的互動共生:以浙江一師為視點 目錄
導言
**章 守成與革新:清末民初現代型師范學校的崛起
一、清末學堂新制與現代教育的萌生
二、一師的“日化”建筑格局表象與留日教師
習得于日本的西方民主主義思想內蘊
三、“木瓜之役”:新學與舊學矛盾沖突的激變
四、首在立人:魯迅在浙江兩級師范個案探析
五、風口浪尖的掌校者:許壽裳在浙江兩級師范個案探析
第二章 文學教育的知識譜系與建制考辨
一、從切割“辭章”到走出邊緣:文學學科地位的確立
二、舊與新:一師三代國文教師的知識譜系與蘊藉
三、辯與不辯:以文學革命引入作為分期標志的課堂教學改革
四、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師范教育模式與新文學培養目標抵牾的調適
第三章 潤物有聲:發出“現代的聲音”
一、破空之聲:“浙潮**聲”
二、回到一師聲音的現場
三、塑形之潛移默化:“經式”訓育
四、講出國語:白話與方言的參差
第四章 審美主義:一師標舉的文藝乃至生存層面的價值取向
一、人格教育與職業教育:經亨頤教育思想與江蘇教育會教育思想之歧異
二、感精神之粹美:作為美育的音樂教育
三、改變世道人心:以“美”育人的薪傳
四、理想主義的文本:抒情審美與現實實踐
五、大美之境界:舍監夏丏尊的人格教育個案探析
第五章 讀書與濟世:“一師風潮”論衡
一、一師“挽經運動”與北大“挽蔡運動”:慢半拍生出的微妙意味
二、蔡元培、蔣夢麟遙控一師船舵使之重歸學術港灣
三、社會革命與文學革命的交相辯駁與補正
四、北京女高師“驅許迎楊”風潮參讀
第六章 課堂上下與校園內外的現代文學時空與場域
一、春風終化雨:晨光社的成立與《詩》的孕育萌生
二、“湖畔”學生社團:《浙江新潮》之后“無所為而為的做詩”
三、風靜人定:劉延陵的謙卑躬耕
四、晨光里的“罪之花”:潘漠華詩歌創作個案探析
五、赤子之魂:馮雪峰一師時期詩歌創作個案探析
第七章 棄文從政復又棄政從文:建黨宏業中的風生水起
一、由文人結社而漸次演變成的君子群而黨之
二、“合群”理念的*高旨歸:從浙江匯聚上海
三、求同存異抑或黨同伐異
四、退而結網:“用馬克思主義的鋤鍬”掘通文學與社會科學領域
第八章 一師作家群選題與創作風格烙有的現代教育職業標記
一、“教育小說”:現代教育與現代文學結合的產兒
二、詩史互闡:一個教員的心靈史
三、畢竟是書生:校園敘事與學堂想象中的一師情結
四、偏執與激憤:魏金枝一師心結個案探析
五、后青春期的羸弱與憂郁:柔石心理個案探析
第九章 從詩化青春到散文人生:一師文人精神氣質的衍變
一、“火氣”與“清氣”的消長
二、詩化青春:少年意氣的詩性表征
三、散文人生:中年沉潛的審美積淀
四:人生的撇與執——俞平伯詩文創作個案探析
余論
參考書目
后記
現代文學與現代教育的互動共生:以浙江一師為視點 節選
1909年8月、9月至次年7月,魯迅由許壽裳向監督沈鈞儒推薦,至浙江兩級師范學堂任初級師范部的化學課程與優級師范部的生理學課程教員,同時兼任博物課(含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日籍教員鈴木珪壽的翻譯。 曾經構想棄醫從文的遼遠抱負,一時竟不得不為謀生與職業所框限,仍被時潮視為“虛文”的文學亦成了魯迅塵封的記憶。然而精神救國、啟蒙“立人”的志向,卻依然百折不撓,每每情不自禁地滲透于他教書育人的每一瞬間。即便翻譯科學講義,他亦兼以美文“美育”;而在擔任化學課、生理課時,更是毋忘學生首先應成其為人,孜孜于啟蒙“立人”“灌輸誠愛”而不倦。 魯迅“作事常從遠處著眼,可是也以認真的態度從小處下手”。如在兩級師范學堂任教時,“他提倡種樹,別人都笑他傻;因為樹要十年才長成,那些人卻主張‘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魯迅先生提起這件事時,卻說,只要給我當一天和尚,鐘我總要撞,而且用力的撞,認真的撞”。 魯迅與許壽裳、夏丏尊等朝夕相共,相互幫助,如期間魯迅曾替許壽裳譯講義,繪插圖;又如曾贈送夏丏尊一部《域外小說集》。夏彼時初讀小說,而以日本作者的作品居多,雖亦曾讀過一些西洋小說如小仲馬、狄更斯等作,卻大都是林琴南翻譯的。周氏兄弟所譯《域外小說集》使其眼界大開,內中所收的都是更現代的作品,且都是短篇,無論是翻譯的態度,還是文章的風格,都與他以前讀過的不同,頗有新鮮味。自此以后,夏丏尊除日本作者的著述外,還搜羅了不少日譯歐美作品來讀,知道的事物多了起來。三十年后,夏在回憶中,仍念念不忘當年在閱讀小說方面所受魯迅的“啟蒙”。 魯迅極少游玩,在杭州教書一年,西湖距住處不過咫尺,游湖卻只有一次,那還是因許壽裳新婚邀其作陪才去的。“他對于西湖的風景,并沒有多大興趣。‘保俶塔如美人,雷峰塔如醉漢’,雖為人們所艷稱的,他卻只說平平而已;煙波千頃的‘平湖秋月’和‘三潭印月’,為人們所留連忘返的,他也只說平平而已。” 他喜歡與同事或學生出去采集植物標本,行走于吳山浙水之間,不是為游賞而是為科學研究。滿載歸來后,便忙著做整理、壓平、張貼、標名,樂此不疲。斗室中因是堆積如丘,琳瑯滿目。現仍留存著他三月間在杭州采集標本的記錄本;此外,他還準備寫一本《西湖植物志》,惜未能完成。在一師期間,魯迅編定《化學講義》《人生象斅》《生理講義》等教材。《人生象斅》長達十一萬字,附錄《生理實驗術要略》后經作者修訂,發表于1914年10月4日杭州《教育周報》第55期。該刊由浙江省教育會主辦,于1913年4月創刊,1919年3月停刊,計235期。兩級師范學堂的同仁李叔同所著《唱歌法大略》、夏丏尊所譯盧梭的《愛彌爾》即發表于該刊第125期。《生理實驗術要略》系至今能見到的魯迅在兩級師范學堂任教期間撰寫、后正式發表的唯一一篇文章,彌足珍貴。 魯迅初到校時,仍著學生制服;或穿西裝。彼時他攝有照片: 西裝內著一件雪白的立領襯衣,系領帶,短發短髭,眼神炯炯,英氣勃發。而學生中卻仍有留長辮,穿長衫者。部分學生較魯迅年長,他們在背后戲言: 這么小的教員,我的兒子比他還大呢! 魯迅在講授生理學課程時,因學生要求,增加了生殖系統一節。在課堂上向學生講解生殖器官的組織結構與生理機能,這一內容即使在今日的中學里仍不無曖昧,何況在百年前的清代。彼時其堅裹于千年教化的厚甲里,諱莫如深,并因此每每引發出不無狹邪的“中國人的想象”。然而,魯迅卻坦然對待。他只對學生們提出一個要求: 聽講時不許笑。他說:“在這些時候,不許笑是個重要條件。因為講的人的態度是嚴肅的,如果有人笑,嚴肅的空氣就破壞了。”就這樣,魯迅以在科學面前百無禁忌的態度,不僅傳授了生理知識,更教會了學生如何尊重科學,精神成人。 魯迅有一次在化學課上講硫酸,告訴學生硫酸的腐蝕性很強,只要皮肉上碰到一點,就會感覺像被胡蜂螫了那樣痛。后來做實驗時,突然有一個學生手按后頸痛得叫了起來。原來是另一學生用竹簽蘸了一點硫酸,偷偷地在他的頸上點了一下。魯迅趕緊過去給這個學生搽藥止痛。 另一次化學課講氫氣,魯迅在教室里演示氫氣燃燒實驗。他把燒瓶中的純氫等實驗用品帶到教室時,發現忘了拿火柴,就回辦公室去取。離開教室時,他特意關照學生,不要搖動燒瓶,否則混入空氣,燃燒時是會爆炸的。但等他拿著火柴回到教室,一邊講氫氣不能自燃,卻可以點燃;一邊動手做實驗。剛將劃著的火柴,往氫氣瓶里點火,那燒瓶卻“膨”地一聲突然爆炸了,手上的血濺滿了講臺、點名冊與襯衫。而他卻顧不上自己的傷痛,急著先去照看坐在前面幾排的學生,唯恐傷著他們;令其驚異的是,學生在他回來之前,竟然早已躲到后排去了。 事隔十多年后,魯迅還對房東女兒俞芳述及此事。上述事件在俞芳的回憶中,更多地凸現了魯迅“對學生愛護備至的精神”這一面。那么陰影中的另一面呢? 手流著血,心更受了傷,深深地刺激著魯迅,但他卻無言以對。 直到多年后,寫作《狂人日記》時,那創傷才混融著所有的心靈郁結,終于迸成了那么一句感天動地的吶喊:“救救孩子!” “孩子總是好的。他們全是天真……”亦是小說,《孤獨者》中魏連殳如是說。 “那也不盡然。”而“我”偏那么回答。 “不。大人的壞脾氣,在孩子們是沒有的。后來的壞,如你平日所攻擊的壞,那是環境教壞的。原來卻并不壞,天真……我以為中國的可以希望,只在這一點。” “不。如果孩子中沒有壞根苗,大起來怎么會有壞花果?”“我”一味任意地說…… 在《孤獨者》中,魯迅化身為二,以復調的筆觸苦苦展開著關于孩子性本善還是性本惡、“后來的壞”源于環境抑或源于天性的論辯質詰。 對于學生、對于青年,他唯有信,唯有寄予希望,唯有愛。那是絕望中的一線希望。 如果說,三年前在日本仙臺醫學專門學校的課間,目睹幻燈片里中國人被砍頭時的麻木神情的那次刺激,曾促使魯迅從一名醫科生轉而棄醫從文;那么,此時在兩級師范學堂化學課上的創傷經歷,則使歸國后為謀生不得不重拾自然科學舊業的魯迅,備增臨時思想,直至*終成為致力于精神啟蒙的作家。 1910年5月13日,魯迅因祖母蔣氏病故,離校回家料理喪事,“大殮之前,魯迅自己給死者穿衣服”,“所有喪葬的事都由他經理”,其情其景十五年后一并寫入了小說《孤獨者》中。是的,魯迅便是“孤獨者”:“木瓜之役”一平息,年輕開明的孫智敏便完成了其過渡人物的使命,不久便由翰林徐定超接任,徐到校后大凡出文告均寫有“京畿道監察御史兼浙江兩級師范學堂監督徐定超署”字樣,一副官僚作派。摯友許壽裳風潮后即辭職以示清白,遠渡日本;曾與魯迅在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礦務鐵路學堂及東京弘文學院同學多年的同事張邦和亦不知所在,一時間“木瓜之役”戰友分散盡矣!乍一靜下來,魯迅備感寂寞;加之祖母故去,母親年邁,魯迅頓生歸鄉之意。1910年7月,魯迅辭去兩級師范學堂職務,回鄉就任紹興府中學堂教職。 魯迅在浙江兩級師范學堂的任教時間,自1909年9月新學期始至1910年7月下學期末,共計兩學期。
現代文學與現代教育的互動共生:以浙江一師為視點 作者簡介
張直心,杭州師范大學教授,浙江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浙江省魯迅研究會副會長。著有《邊地夢尋── 一種邊緣文學經驗與文化記憶的探勘》《思想·文本·史實:魯迅研究三維》《批評:生命的呈示》《比較視野中的魯迅文藝思想》《晚鐘集》等多部專著及論文集。 王平,文學博士,浙江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 >
自卑與超越
- >
隨園食單
- >
企鵝口袋書系列·偉大的思想20:論自然選擇(英漢雙語)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
- >
人文閱讀與收藏·良友文學叢書:一天的工作
- >
經典常談
- >
回憶愛瑪儂
- >
山海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