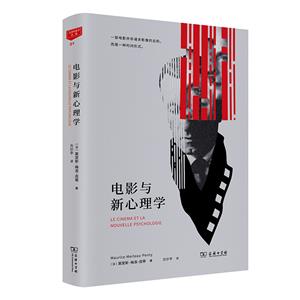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電影與新心理學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0166676
- 條形碼:9787100166676 ; 978-7-100-16667-6
- 裝幀:100g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電影與新心理學 本書特色
勘稱經典的電影心理學經典著作,原文精譯+文本解析+圖像解讀! ——完整收錄梅洛-龐蒂《電影與新心理學》;在新心理學目光之下,我們才能真正懂得為什么說電影是“旋律性的整體”,是一種“時間性的形式”。 ——補充“從攝影到文本”“文本解析”等相關資料,在對梅洛-旁蒂的回應與解讀中,我們才能真正懂得梅洛-龐蒂與《電影與新心理學》的思想精髓。
電影與新心理學 內容簡介
1945年莫里斯·梅洛-龐蒂在法國高等電影學院的演講《電影與新心理學》,代表了他有關電影美學的基本思想,即一種在新心理學目光審視下的電影美學。本書完整收錄《電影與新心理學》,并補充了 “從攝影到文本”與“文本解析”等相關資料,盡可能地展現出這本經典之作的魅力。
電影與新心理學 目錄
**部分
003
電影與新心理學
第二部分
031
從攝影到文本
——評貝爾納·普洛緒的《阿爾梅里亞,安達盧西亞》
049
文本解析
049 一、文中術語:知覺、他者、電影
068 二、作品在思想史中的地位:反思客觀世界,
存在于客觀世界
083 三、哲學家的形象:奇特的現象性
099 四、向文本提三個問題
119 五、文集:意義的工廠
141 六、延伸閱讀
附 錄
149 專有譯名對照表
電影與新心理學 節選
電影與新心理學 傳統心理學認為,我們的視覺是多個感覺(sensation)的總和或拼湊,其中每一種感覺都嚴格地取決于相應的視網膜刺激。然而,新心理學一上來就告訴我們,即便*簡單、*直接的感覺,我們也不能斷定,它與支配它的神經現象之間存在著這種一一對應關系。我們的視網膜絕不是同質的,它的某些部分感覺不到藍色或紅色等顏色。可是,在注視某個藍色或紅色的表面之時,我卻不會從中看到任何無色區域。這是因為,從*簡單的對顏色的視覺這一層面開始,我的知覺(perception)就不只限于記錄視網膜刺激的結果,而是對其進行重組,重新構建同質的視野。一般說來,我們應當把知覺視為一種配置(configuration)系統,而不是一種拼湊。*先進入我們知覺的,不是一些并列的元素,而是一些整體(ensemble)。我們像古人那樣把星星組合為星座,但毫無疑問的是,星空中很多其他組合同樣也是可能的。如果有人擺出這樣一個字母序列:a b c d e f g h i j我們總是會把它按照“a-b”“c-d”“e-f”等形式兩兩組合,但“b-c”“d-e”“f-g”等組合原則上也完全可能。一個病人凝視著臥室里的掛毯,如果掛毯上的圖案和形體變成背景,而一般被視為背景的部分變成形體,那么他就會發現,掛毯一下子就變樣了。如果我們能夠把事物之間的空隙(例如街邊樹木之間的空間)視為事物,同時把事物本身(街邊的樹木)視為背景,那么世界的面貌在我們眼中就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圖謎便屬于這種情況:兔子和獵人不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二者形狀的元素已經解體,并融入了其他形狀之中。例如,兔子的一只耳朵原來是樹林里兩棵樹之間的空白。通過視野的重新分割,通過整體的重新組織,兔子和獵人才會現身。偽裝就是把某一形體隱藏起來的技術,是把確定該形體的主線條融入其他更顯眼的形體之中。 我們可以將同樣的分析用于聽覺,只是此時所涉及的不再是空間的形態,而是時間的形態。舉個例子,一首樂曲是一個聲音形象,它不會與背景處可能同時發出的噪音——比如某一場音樂會期間我們聽到遠處傳來的一聲汽車喇叭聲——混在一起。樂曲不是諸多音符的總和,每個音符只有憑借它在整首樂曲中的功能才有意義。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如果我們對樂曲進行移調,也即改變構成樂曲的所有音符,同時遵守樂曲整體的關系和結構,樂曲并不會發生顯著變化。相反,音符之間的關系哪怕只發生一點變化,樂曲的面貌也會隨之改觀。比起對獨立元素的知覺,這種對整體的知覺更為自然、更為原始:在條件反射實驗中,人們多次將某一光線或聲音與一塊肉的出現相結合,來對狗進行訓練,使狗對這一光線或聲音做出唾液分泌反應。人們發現,某一音符序列獲得的訓練效果與一首結構相同的樂曲獲得的訓練效果是一樣的。可見,分析式知覺——它使我們能夠理解單個元素的絕對價值——是后天習得的一種特殊姿態,是進行觀察的學者或進行思考的哲學家的姿態,而對結構、整體、配置系統等各種形式的知覺才應當被視為我們知覺的自發模式。 在另一點上,當代心理學也顛覆了傳統生理學和心理學的偏見。以前有這么一個共識:我們有五種感官,其中每一種乍一看都是獨立的,與其他感官之間沒有交流。光線或顏色作用于眼睛,卻不會作用于耳朵或肌膚。然而,我們早就知道,有的盲人能夠用他們聽得到的聲音來描繪他們看不到的顏色。比如,有個盲人說過,紅色應該是某種類似于一聲喇叭聲的東西。很久以來,我們一直認為這是一種特殊現象,但事實上這種現象是普遍的。在麥司卡林中毒的癥狀中,聲音往往伴有彩色斑點,其色調、形狀、高度因聲音的音色、音高和音強而異。即便是正常人,也經常會說暖色、冷色、噪色或硬色,或是清晰的、尖銳的、燦爛的、粗糙的或圓潤的聲音,或是輕柔的噪音、刺鼻的香味。塞尚就曾說過,我們能夠看到物體是否柔滑,是硬還是軟,甚至能看到它的氣味。因此,我的知覺不是若干視覺、觸覺、聽覺信息的總和,我是以一種與我整個人密不可分的方式進行感知,我抓住的是事物唯一的一種結構,是其同時作用于我的所有感官的唯一的一種存在方式。 當然,傳統心理學很清楚,視覺的不同部分之間存在著某些關系,不同感官獲得的信息之間也存在著某些關系,但它認為,這種統一性(unité)是后來構建的,靠的是智力和記憶。笛卡爾的《沉思集》 中有一段話廣為人知,“我說我看到街上有人走過”,但事實上我到底看到了什么呢?我只看到了一些帽子和大衣,它們也可能罩著一些靠發條驅動的玩具人,而我之所以說我看到了人,是因為我“通過思維的省察而理解了我認為我親眼所見之物”。我深信,事物是持續存在的,即便我看不見它們,比如當它們在我身后之時。不過很顯然,對于傳統思想而言,我之所以認為那些看不見的事物持續存在,只是因為我的判斷力斷定它們一直存在。即便是我面前的事物,它們也不是真的被看到,而是被想象到。因此,我不可能看見一個立方體,也即一個由 6 個平面和 12 條等長的棱所構成的物體,而永遠只能看到一個透視的形象,其側面發生了變形,背面則完全被隱藏了起來。我之所以說它是立方體,是因為我的思維矯正了那些外觀,同時復原了隱藏的那個平面。我無法看到幾何定義中的立方體,只能想象到它。對運動的知覺更好地體現了智力如何介入所謂的視覺。我的火車停在車站里,在它啟動的那一刻,我常常會覺得啟動的是停在旁邊的一列火車。可見,感官獲得的信息本身是中性的,能夠根據我的思維所預設的假定而得到不同的詮釋。總的來看,傳統心理學是把知覺當成了智力對感覺的解碼,認為這是科學的起點之一。我得到了一些符號,我得從中剝離出含義;我得到了一篇文章,我得閱讀并闡釋它。即便在考慮知覺的統一性之時,傳統心理學仍然執著于“感覺”這一概念,把它作為分析的起點。正因為傳統心理學首先把視覺看作多個感覺的拼湊,它才需要把知覺的統一性建立在智力活動的基礎之上。在這一點上,完形心理學理論給我們帶來了什么呢?它毅然地拋開了“感覺”這一概念,同時教我們不再區分符號與其含義、被感覺到的東西與被判斷出來的東西。我們怎樣才能準確地定義某一物體的顏色,同時又不提及構成該物體的物質,比如不把地毯的藍色說成“毛絨絨的藍色”?塞尚曾提出一個問題,如何把物體的顏色和圖案與該物體區分開來?知覺不能被理解成將某個含義施加于某些可被感覺到的符號,因為在描述這些符號的*直觀的、可被感覺到的構造之時,我們不可能不提到它們的含義。我們之所以在不斷變換的照明下認出了某一物體的固有屬性,并不是因為我們憑借智力考慮到了變換的光線的本質,進而推斷出物體的真實顏色,而是因為空間內的主導光線發揮出照明的作用,確定了物體的真實顏色。當我們注視著兩個照明程度不同的盤子之時,只要來自窗戶的光束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之內,這兩個盤子就都呈白色而照明程度不同。相反,當我們透過一塊打了一個孔的屏幕去觀察這兩個盤子,其中一個立刻就呈灰色,另一個則呈白色,而即便我們知道這不過是照明的效果,針對盤子外觀的任何智力分析也不會告訴我們兩個盤子的真實顏色。可見,各種顏色和各種物體的恒定特性并非由智力所構建,而是被視線結合或根據視野的結構所捕獲。黃昏時分,打開電燈,燈光一開始呈黃色,但不一會兒便失去了這一顏色。與此相應的是,燈光下的物體一開始顏色大有不同,不久也恢復了與白晝時相仿的面貌。各種物體與照明構成了一個趨向于某種恒定性和某種穩定層級的系統,這種趨向并不是由于智力行為,而是由于知覺范疇的配置。在獲得知覺之時,我并不是在思考外在世界,而是外在世界在我面前自行組織。在感知一個立方體之時,并非我的理性矯正了呈透視形象的外觀并據此想到立方體的幾何定義。我遠未矯正它們,甚至沒有注意到透視形象的變形,我之所見即為立方體本身的真面目。同樣的,我背后的物體并非借助某種記憶或判斷行為而重現在我腦海里,它們對于我是存在的,它們作用于我;某一背景的一部分被事物遮住了,我看不見它,但它仍然繼續存在于該事物的下方。即便是對運動的知覺,雖然乍一看好像直接取決于智力所選取的參照點,其實也只是視野的整體結構中的一個元素。當我的火車和一旁的火車其中一列啟動之時,我的確是有時覺得是我的火車在運動,有時又覺得是一旁的火車在運動,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一幻覺不是隨意的,也不是我全憑智力隨便選擇一個參照點而主動引發的。如果我正在我的車廂里打牌,那么啟動的仿佛是旁邊的那列火車。相反,如果我正盯著旁邊那列火車,四處搜尋某個人,那么啟動的仿佛就是我的火車。每一次,總是我們臨時選為“居所”(domicile)或關注的那列火車顯得靜止不動。對我們來說,我們周圍的運動和靜止并非取決于我們的智力主動建立的假定,而是取決于我們在客觀世界中的觀察方式,以及我們的軀體在客觀世界中所處的情境。有時,我發現鐘樓在天幕中是靜止的,云朵在其上方飛翔;有時,云朵似乎是靜止的,鐘樓反而在下墜,從空中劃過。在這里,靜止點的選定同樣不是智力所為:我所注視和錨定的對象總是顯得靜止不動,只有當我注視別處之時,它的形態才會發生變化。同樣的,我也不是用我的思維給予它這一含義。知覺不是一門剛起步的科學,也不是智力*初的演練,客觀世界比智力古老得多,我們要找到一種與客觀世界相處、存在于客觀世界之中的方式。 *后,關于對他者(autrui)的知覺,新心理學也帶來了一個全新的概念。傳統心理學未經深究,便承認內部觀察或內省(introspection)不同于外部觀察,認為只有經歷過發怒、恐懼等“心理事實”(fait psychique),才能直接在內心認識它們。人們覺得,我顯然只能從外部獲得憤怒或恐懼體現在軀體上的符號,而要解釋這些符號,就必須借助我通過內省而得到的關于我自己的憤怒和恐懼的認知。當代心理學家卻告訴我們,內省其實幾乎給不了我什么。如果僅僅通過內部觀察去研究愛或恨,那么我只能得到很少可描述的東西,比如一些焦慮、一些心跳,總之是一些平常的心理紛擾,它們不能為我揭示愛或恨的實質。每次獲得一些有價值的發現,都是因為我不滿足于迎合我的感覺,是因為我成功地將它作為一種行為、作為我與他者以及客觀世界的關系發生的一種變化來研究,是因為我能夠像思考我親眼所見的另一個人的行為那樣去思考它。事實上,兒童早就能理解身體動作和面部表情,后來才去模仿它們,這些舉止的含義可以說是“附著”在他們身上的。把愛、恨、憤怒等視為“心理事實”,認為只有見證者也即經歷過它們的人才能理解它們,這是一種偏見,我們得拋開這一偏見。憤怒、羞恥、愛、恨并不是藏在他者的意識*深處的“心理事實”,而是處于外部的、可見的各種行為類型或舉止風格。它們就在臉上、在舉止中,而非隱藏其后。直到不再區分軀體與意識的那一天,直到放棄內部觀察與生理心理學這兩種相關聯的模式的那一天,心理學才開始得以發展。人們若只限于測量憤怒時的呼吸速度和心跳頻率,便根本無法教我們何為情感(émotion),若總是試圖去描述曾體驗過的憤怒在性質上無法言表的細微差異,也便根本無法教我們何為憤怒。對憤怒進行心理學研究,就是去確定憤怒的含義,就是質問它在人的生活中有何功能或者說有何用途。這樣的話,我們就會發現,正如雅奈所言,情感是當我們身陷死胡同時的一種“混亂中的反應”——更進一步,我們就會發現,正如薩特曾指出的那樣,憤怒是一種“魔術般的舉止”,通過它,人們放棄了客觀世界中的有效行為,同時在想象中給自己一種純粹是象征性的滿足感。比如,有的人在聊天的過程中,當他無力說服對方的時候,會轉而求助于辱罵,而辱罵什么也說明不了;有的人在不敢攻擊敵人的時候,會遠遠地沖他揮一揮拳頭。情感并非“心理事實”,而是我們與他者以及客觀世界之間的關系發生的一種變化,這種變化可以在我們軀體的表征中解讀出來,因此不能說呈現給旁觀者的只有憤怒或愛的符號,也不能說只有通過闡釋這些符號才能間接地知覺到他者,而應該說他者是作為行為而清清楚楚地呈現在我面前。關于行為的科學比我們認為的走得更遠。把多張肖像照或全身照、多種筆跡的副本、多種嗓音的錄音交給一些事先不知情的人,要求他們從中選出一張肖像、一幅全身像、一種筆跡和一種嗓音組合在一起,我們發現,他們的組合一般是正確的,至少正確的組合遠遠多于錯誤的組合。米開朗琪羅的筆跡共有 221 次被準確無誤地辨認出來,共有36次被錯認為拉斐爾的筆跡。這是因為,我們會從每個人的嗓音、面貌、舉止和姿態中辨認出某一種共同的結構,對我們而言,這“每個人”不是別的,正是這種結構或這種在客觀世界中存在的方式。不難發現,上述觀點應同樣適用于語言心理學:一個人的軀體和“靈魂”只不過是他在客觀世界中存在的方式的兩個方面,同樣的,語言及其指稱的思想不應被視為兩個外在項;語言承載著它的含義,軀體則是一種行為的化身。 總而言之,新心理學讓我們看到,人并不是以其智力構建客觀世界,而是被置于客觀世界之中,像是通過一種自然的關系與其緊密相連。接著,新心理學重新教我們如何去看待這個我們通過我們自己的整個外表而與之相接觸的客觀世界,但傳統心理學卻為了智力所構建的客觀世界而忽視了我們所體驗的客觀世界。 ……
電影與新心理學 作者簡介
莫里斯·梅洛-龐蒂(1908—1961),法國20世紀Z重要的哲學家、思想家之一。他在存在主義盛行的年代與薩特齊名,是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的杰出代表。他的代表性哲學著作《知覺現象學》被視作法國現象學運動的奠基之作。 譯者簡介:方爾平,畢業于北京大學,法語系碩士,已翻譯出版《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電影的時間與存在之痛的問題》《電影符號學質疑》《欲望的眩暈——通過電影理解欲望》等譯著。
- >
二體千字文
- >
自卑與超越
- >
龍榆生:詞曲概論/大家小書
- >
我從未如此眷戀人間
- >
回憶愛瑪儂
- >
隨園食單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歷史與人類學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