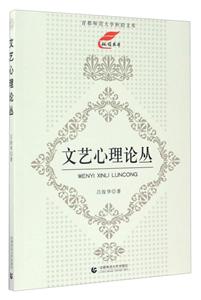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文藝心理論叢 版權信息
- ISBN:9787565634642
- 條形碼:9787565634642 ; 978-7-5656-3464-2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文藝心理論叢 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了作者歷年發表的多篇文章, 研究范圍涵蓋現代文學創作心理、變態心理、教育研究等多個方面, 有的研究突破的固定模式, 開辟了新的途徑, 具有一定的創新性, 可為現代文學的學習者、文藝心理的研究者提供參考依據。內容包括: 論阿Q精神勝利法的哲理和心理內涵 ; 文藝創作與變態心理等。
文藝心理論叢 目錄
文藝創作與變態心理
變態心理與文藝
魯迅論創作心理
阿Q的精神勝利法小議
論非對象性思維
非對象性思維談
也談應該用什么“準則”來要求作家
論自發性
為自發性正名
體認論
情理新論
談愛情的生滅與消長——從魯迅小說《傷逝》得到的教訓
談觀察與體察
談審美知覺
談“體會”
從《獨立蒼茫自詠詩》看獨立的心理內涵
“神入”與“身入”
西方文學:心靈的歷史·序
寫意——中國美學之靈魂·序
談談反向努力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新解
從“他人就是地獄”說開去
《魯迅雜文選》序言
論魯迅的民族自尊心
尊重人、尊重教育對象——讀蘇霍姆林斯基的著作有感
教育的本質是什么?
文藝心理論叢 節選
《首都師范大學·秋韻文庫:文藝心理論叢》: 精神病學家證明,所謂變態心理,其*顯著的特征就是混淆現實與想象或幻想的界限,失去與外界情境的真實聯系而生活在想象的或幻想的世界中,如同做夢一樣。其實做夢也就是一種變態心理,人們在夢境中也生活在虛幻世界中。精神病學家C.費希爾指出:“夢是正常的精神病,做夢是允許我們每個人在我們生活的每個夜晚能安靜地和安全地發瘋。”由此可知,心理正常的人也有時發生變態。常態與變態,很難明確區分。世界上沒有絕對常態的人,也沒有絕對變態的人。任何常態的人都有幾分變態,而任何變態的人也都有幾分常態。所謂變態只不過是泯沒了幻想和現實的界限,并沒有什么特殊的不同于常態的心理內容。變態時的心理內容在常態的心理中也完全存在,而且,同樣的心理現象,可因不同的人,不同的時間、地點,不同的社會歷史環境而有不同的含義。例如,未開化的人就分不清虛幻世界與現實世界的界限。他們白天可有幻聽幻象或可以和鳥獸草木進行對話,實際他們生活在幻想和迷妄的世界中,這在今天看來顯然是變態表現,但在他們卻是司空見慣的常態。但今之視昔,猶后之視今,今天我們認為是事實的東西,明天可能會被證明是錯覺。現代科學證明:人們據以生活的許多真理,在一個新的參考系統中也許不得不承認是一種幻覺、一種變態心理的反映。可見變態與常態的區分只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像原始人那樣的幻聽和迷妄現象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也時有發生,特別是在感情激動或一往情深之際。據報載,作家楊沫愛花草,她把花草稱為自己“*真摯、*接近的朋友”,她對花草的感情“如醉如癡”。每逢她看到美麗的花,她總要久久地凝視,甚至忍不住向它們低低絮語:“生活——人的一生應當像這美麗的花,自己無所求,而卻給人間以美……”以花為友、視無知為有知,不是也有點幻想和迷妄嗎?但這樣的變態心理,有誰未曾體驗過呢?像這樣的例證是隨處可見的。在文藝創作中,出現心理變態更是常見現象。 現在,讓我們從“對牛彈琴”說起。不消說,在日常生活中,任何心理健全的人都不會去做對牛彈琴的蠢事。但在有情要抒,除了牛以外又一時找不到抒發對象的情況下,“對牛彈琴”這種反常或變態的行動卻是可能出現的。高爾基在《我的大學》里,寫到他在流浪的日子里,在一家面包作坊里當伙計,得到外祖母——他的“*知心的人”、“*了解、*珍貴的人”——逝世的消息的時候,他強烈地想要對人講述一下他的外祖母,藉以抒發他的痛苦和哀傷,但他一時找不到任何可以作抒發對象的人。 “過了許多年以后,當我讀到契訶夫的關于馬夫的異常真實的故事的時候,我想起了這些日子。在契訶夫的故事中,馬夫對馬訴說著自己兒子的死。遺憾的是,在那些辛酸的悲涼的日子里,我的周圍既沒有馬,也沒有狗,我沒有想到把悲哀分一些給老鼠,在面包作坊里,老鼠是很多的,我和它們的關系也很友好。”和對牛彈琴一樣,把馬甚至老鼠作為知音不是同樣反常或變態嗎?其實,不僅牛馬之類的動物可作知音,山川草木同樣可以成為抒情的對象。約翰·克利斯朵夫在孤獨中,曾把萊茵河作為唯一的知己,“他唯一的朋友,聽到他吐露思想的知己,只有在城里穿過的那條河,就是在北方灌溉他故鄉的萊茵河,在它旁邊,克利斯朵夫又想起了童年的夢境”。這種心理變態現象,無論在日常生活中,還是在文藝創作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人在悲哀、寂寞、孤獨中,在人世間找不到溫暖和同情之際,就必然寄情于自然,和小草對話,聽天籟奏樂,“正須閉口林間坐,莫道青山不解言”(王守仁);“鄉無君子,則與云山為友;里無君子,則與松竹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元結)。晉王徽之把竹作為不可須臾離開的親密伴侶,他對朋友指竹日:“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尤其是在忠貞賢士、怨悱君子眼中,則美人明月、芳草珍禽,無往而不可藉之抒發我之懷抱,亦無往而不可自其窺見我之性情。應該說,這是普遍的自然的現象,它出于生理一心理的要求,符合生理心理學的規律。正如饑思食、渴思飲一樣,人有情就要宣泄、抒發,否則便活不下去。而宣泄、抒發就要有點反常或變態;不反常、不變態,則無由宣泄、抒發。變態的深淺、久暫是與情感的強度成比例的。 ……
- >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實旅程
- >
有舍有得是人生
- >
羅曼·羅蘭讀書隨筆-精裝
- >
煙與鏡
- >
推拿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中國歷史的瞬間
- >
龍榆生:詞曲概論/大家小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