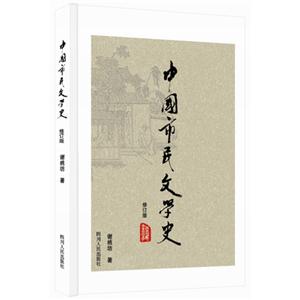-
>
百年孤獨(dú)(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cè))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中國市民文學(xué)史 版權(quán)信息
- ISBN:9787220093708
- 條形碼:9787220093708 ; 978-7-220-09370-8
- 裝幀:簡裝本
- 冊(cè)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市民文學(xué)史 本書特色
市民文學(xué)是封建社會(huì)后期于市民階層中興起后流行于都市的、通俗的、表現(xiàn)市民社會(huì)的文學(xué)。該書探討了中國市民社會(huì)與市民文學(xué)的諸多理論問題及其在近世的命運(yùn)。作為我國**部市民文學(xué)史,其在整體架構(gòu)與表述方式等方面皆有所創(chuàng)新,對(duì)某些有爭議的問題亦作了較深刻的評(píng)論。該書具有較高學(xué)術(shù)價(jià)值。
中國市民文學(xué)史 內(nèi)容簡介
該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初版3000冊(cè)、2003年重印3000冊(cè),早已售罄。
被收入中國文學(xué)專史書目提要、中國近代史論著目錄。
中國市民文學(xué)史 目錄
中國市民文學(xué)史 節(jié)選
**章 中國的市民社會(huì)與市民文學(xué)
市民社會(huì)是在封建社會(huì)后期城市商品經(jīng)濟(jì)發(fā)展到一定階段而出現(xiàn)的,相應(yīng)地隨即產(chǎn)生了為市民階層所喜愛的和表達(dá)市民思想意識(shí)的都市通俗文學(xué),即市民文學(xué)。中國市民社會(huì)是在北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隨之也產(chǎn)生了中國市民文學(xué)。由于中國市民文學(xué)長期以來為正統(tǒng)文學(xué)家所排斥,以致其思想意義與文學(xué)價(jià)值在近世才逐漸為學(xué)者們所認(rèn)識(shí)。
**節(jié)中國市民社會(huì)的形成及其特點(diǎn)
“市民社會(huì)”這個(gè)用語有三種含義:一是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的近義語,指一切時(shí)代的物質(zhì)生活的總和;二是指不同于自然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和未來社會(huì)的整個(gè)商品經(jīng)濟(jì)社會(huì);三是指近現(xiàn)代西方發(fā)展的商品經(jīng)濟(jì)社會(huì)。馬克思和恩格斯關(guān)于第二種含義的說明是:“市民社會(huì)包括各個(gè)個(gè)人在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zhì)交往。它包括該階段上整個(gè)商業(yè)生活和工業(yè)生活。”引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卷,第41~42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這種含義里所概括的物質(zhì)交往是指獨(dú)立商品所有者之間的社會(huì)關(guān)系而且將自給自足型的自然經(jīng)濟(jì)排除在外。參見沈越:《市民社會(huì)辨析》,《哲學(xué)研究》1990年第1期;《馬克思市民經(jīng)濟(jì)思想初探》,《經(jīng)濟(jì)研究》1988年第2期。這種并非泛指一切歷史階段上的、也非近代的商品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的市民社會(huì),它是在古代社會(huì)商品經(jīng)濟(jì)發(fā)展到較高階段上出現(xiàn)的與自然經(jīng)濟(jì)相區(qū)別的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它的形成宣告了在舊的封建社會(huì)中一個(gè)新的社會(huì)力量——市民階層的興起。中國歷史上,市民社會(huì)的形成與市民階層的興起,應(yīng)當(dāng)是在北宋的初期,即公元11世紀(jì)之初。這時(shí)歐洲也開始城市化運(yùn)動(dòng)并形成市民社會(huì)。我國的歷史發(fā)展較為特殊,但在這一點(diǎn)上與世界歷史的發(fā)展進(jìn)程是保持著基本的同步性的。
中國的封建社會(huì)自唐代中葉以后政治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變化,到了北宋時(shí)期漸漸趨于定型。它表明我國封建社會(huì)進(jìn)入了后期發(fā)展階段。北宋的政治經(jīng)濟(jì)和文化都呈現(xiàn)與前代相異的面貌,尤其是在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方面達(dá)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可以說,北宋時(shí)已初步具有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物質(zhì)條件,或者說具有了資本主義的若干因素。這促使勞動(dòng)分工的新變化:城市與農(nóng)村分離。因此,我國市民社會(huì)在北宋的形成是有其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必然性的。
宋以前我國古代的城市基本上是屬于以政治為中心的郡縣城市,在經(jīng)濟(jì)上不存在與鄉(xiāng)村分離的情況。當(dāng)城市商品經(jīng)濟(jì)發(fā)展到一定程度時(shí),便出現(xiàn)了新的變化:“一切發(fā)展了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與鄉(xiāng)村分裂為基礎(chǔ)”。引自馬克思:《資本論》**卷,第424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宋代的城市與以前比較已具有了若干新的特點(diǎn),主要特點(diǎn)是:市場制代替了坊市制,鎮(zhèn)市和草市上升為經(jīng)濟(jì)意義上的城市,與舊城連毗的城郊的經(jīng)濟(jì)意義非常突出。唐代兩京及州治被劃分為若干里坊,每個(gè)里坊以高墻圍著。里坊既是行政管理單位,也是一個(gè)獨(dú)立的商業(yè)區(qū)。里坊內(nèi)設(shè)有固定的東、西、南、北等市。市內(nèi)商店以商品種類分行營業(yè),而且有的是定期的市。市內(nèi)一切營業(yè)時(shí)間以早晚坊門的開閉為準(zhǔn),日沒時(shí)坊門關(guān)閉便停止?fàn)I業(yè)。經(jīng)過五代的戰(zhàn)亂,城市的里坊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與變遷,在宋初已難復(fù)舊觀。北宋太平興國五年(980),京都開封的商業(yè)活動(dòng)已出現(xiàn)侵街現(xiàn)象,突破了時(shí)間與區(qū)域的限制,標(biāo)志舊的坊制開始崩潰了。自此,商店可以獨(dú)立地隨處設(shè)置,同業(yè)商店的街區(qū)可見到跨行的現(xiàn)象,以致交通便利的埠頭、橋畔、寺觀等處亦成為商業(yè)活動(dòng)的場所,尤其是出現(xiàn)了各種各樣的夜市。“由此可知,當(dāng)時(shí)都市制度上的種種限制已經(jīng)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經(jīng)頗為自由、放縱,過著享樂的日子。不用說這種變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業(yè)的繁盛,它的財(cái)富的增大,居民的種種欲望強(qiáng)烈起來的緣故”引自[日]加藤繁:《中國經(jīng)濟(jì)史考證》**卷,第277頁,商務(wù)印書館1962年版。。北宋至道元年(995)和咸平年間(998~1003)雖然兩次曾經(jīng)試圖恢復(fù)舊的坊市制,但都以失敗告終;到了仁宗初年,坊市制度徹底崩潰而為市場制所代替了。這種不以統(tǒng)治階級(jí)意志為轉(zhuǎn)移的變化過程,正體現(xiàn)了一種城市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它以不可阻擋的力量沖擊著封閉的自然經(jīng)濟(jì)。由此使都市的性質(zhì)漸漸有所改變,并使都市活躍起來,面貌為之一新。北宋末年的都城東京已是“人煙浩穰,添十?dāng)?shù)萬眾不加多,減之不覺少。所謂花陣酒池,香山藥海。別有幽坊小巷,燕館歌樓,舉之萬數(shù)”(《東京夢華錄》卷五)。宋代鎮(zhèn)市和草市發(fā)展很快。鎮(zhèn)具有經(jīng)濟(jì)意義,凡較大的居民聚居地而不夠設(shè)置縣的則設(shè)鎮(zhèn)市并置監(jiān)鎮(zhèn)官以管理稅務(wù)。北宋熙寧年間全國鎮(zhèn)市已將近兩千個(gè),而南方諸路則有1300個(gè)。草市是鄉(xiāng)村的定期集市,為農(nóng)村貿(mào)易交換之所,有的發(fā)展為相當(dāng)規(guī)模的經(jīng)濟(jì)貿(mào)易點(diǎn)。北宋政府鼓勵(lì)發(fā)展鎮(zhèn)市和草市,因?yàn)樗鼈兊纳潭愵~已占全國商稅額的百分之十八(據(jù)熙寧十年商稅計(jì)算),在整個(gè)國民經(jīng)濟(jì)中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它們的發(fā)展表明社會(huì)商品經(jīng)濟(jì)的活躍,大大推動(dòng)了商品交換,有利于商品經(jīng)濟(jì)的繁榮。參見鄧廣銘、漆俠:《兩宋政治經(jīng)濟(jì)問題》第185~190頁,知識(shí)出版社1988年版。同時(shí),新商業(yè)市區(qū)的形成也逐漸改變著舊的郡縣城市的性質(zhì)。北宋城市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還突破了城郭限制,往往在舊城的附近開設(shè)店鋪、作坊、貿(mào)易場所,漸漸出現(xiàn)了新的商業(yè)區(qū)域。如鄂州城外的南市,“沿江數(shù)萬家,廛甚盛,列肆如櫛,酒壚樓欄尤壯麗,外郡未見其比。蓋川廣荊襄淮浙貿(mào)遷之會(huì),貨物之至者無不售。”(《吳船錄》卷下)北宋初年京都附近商業(yè)市區(qū)的發(fā)展非常迅速。太宗至道元年(995)京城設(shè)八廂行政區(qū)。“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二月置京新城外八廂。真宗以都門之外居民頗多,舊例惟赤縣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廂吏,命京府統(tǒng)之。”(《宋會(huì)要輯稿》兵三之二)城內(nèi)城外各設(shè)八個(gè)行政區(qū),正反映了新的商業(yè)區(qū)促進(jìn)了京都性質(zhì)的改變,它不再僅僅是政治的中心,而且在經(jīng)濟(jì)上也居于顯著的地位。熙寧十年(1077)東京的商稅比舊額已增加三分之一。由于市場制的確立、鎮(zhèn)市和草市的發(fā)展、舊城附近新商業(yè)區(qū)的形成,這使北宋城市面貌發(fā)生新變化,反映了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達(dá)到一個(gè)前所未有的階段。
城市的新變化又表現(xiàn)在出現(xiàn)了一個(gè)城市化的過程。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鎮(zhèn)或城市地帶集中的過程見《國外城市科學(xué)文選》第1~2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北宋時(shí)人口增長較快,太祖開寶九年(976)全國共三百多萬戶,到徽宗大觀四年(1110)增長了將近七倍,總?cè)丝诔^了一億。這百余年間,每年戶口數(shù)以千分之十一的增長率增加。人口的蕃衍表現(xiàn)了社會(huì)生產(chǎn)的發(fā)展和經(jīng)濟(jì)的繁榮。其中城市人口的增加是極快的。太宗太平興國年間(976~983)開封府主客戶合計(jì)十六萬八千余,至徽宗崇寧年間(1102~1106)合計(jì)二十六萬余戶,東京城市總?cè)丝诳蛇_(dá)一百四十萬左右,是當(dāng)時(shí)世界上人口*多的大都市見吳濤:《北宋都城東京》第35~37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城市人口的增長可從商稅的增加間接地反映出來。濰州、徐州、襄州、晉州、揚(yáng)州、楚州、杭州、越州、蘇州、潤州、湖州、婺州、明州、常州、溫州、衢州、秀州、虔州、吉州、潭州、衡州、江陵府、福州、廣州、韶州、英州等處,熙寧十年的商稅額比舊額增加一倍甚或五六倍。這些州治所在的城市人口大約也以相應(yīng)的速度增加著。農(nóng)村人口向城市大量移入,為城市提供了勞動(dòng)力,加速了城市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北宋政府鼓勵(lì)人們(包括農(nóng)村人口)出外經(jīng)商:“營求資財(cái)者,謂貿(mào)遷有無,遠(yuǎn)求利潤”,在刑法上是不作逃亡罪或浮浪罪論處的(《宋刑統(tǒng)》卷二八)。政府準(zhǔn)予商人及手工業(yè)者經(jīng)商與遷徙的自由。農(nóng)村里地主與農(nóng)民之間普遍實(shí)行租佃契約,這相對(duì)削弱了佃戶對(duì)地主的依附關(guān)系。佃戶在契約期滿后可以從事別的職業(yè)或離鄉(xiāng)背井。北宋在戶籍上將常住的有固定產(chǎn)業(yè)的編為主戶,而對(duì)無固定產(chǎn)業(yè)的外來戶編為客戶。客戶的增加,表明人口有較大的流動(dòng)。宋初太平興國年間開封府主戶九萬二百余,客戶八萬八千余,主客戶的比例相差無幾。以汀州為例,城市主戶二千八百余,客戶二千三百余;其鄉(xiāng)村主戶九萬九千余,客戶四萬五千余(據(jù)《臨汀志》,《永樂大典》卷七八九○引。)。汀州鄉(xiāng)村客戶比主戶少一倍,而城市主客戶數(shù)目則基本上相等。這可說明城市的客戶大大多于鄉(xiāng)村的客戶。城市客戶的比例很大,體現(xiàn)了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的趨勢。城市除了在籍的客戶而外,還有往來的客商、手工業(yè)工匠、個(gè)體手工業(yè)者、小商販、船工、流民、民間藝人等等浮浪流動(dòng)之輩。這些涌人城市的移民,由于職業(yè)、財(cái)產(chǎn)、社會(huì)地位等的區(qū)分,形成了社會(huì)的各種利益群體。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商人和手工業(yè)者的社會(huì)利益群體。
商業(yè)和手工業(yè)的各行都有同業(yè)行會(huì)組織,“行”也稱“團(tuán)”;各行業(yè)推舉經(jīng)濟(jì)勢力雄厚者為“行首”或“團(tuán)頭”。這雖然是前代之制,但在北宋時(shí)行業(yè)的分工更為細(xì)密,行會(huì)組織更加健全,尤其在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中顯示出重要的意義。孟元老《東京夢華錄》里關(guān)于北宋京都各行的情況及行會(huì)的作用均有一些記載,如說“西宮南皆御廊杈子,至州橋投西大街,乃果子行”;“北去楊樓,以北穿馬行街,東西兩巷,謂之大小貨行,皆工作伎巧所居”;“馬行(街)北去,乃小貨行”;“朱雀門外及州橋之西,謂之果子行。紙畫兒亦在彼處,行販不絕”;“凡雇覓人力、干當(dāng)人、酒食、作匠之類,各有行老供雇。”南宋時(shí)吳自牧說:“市肆謂之‘團(tuán)行’者,蓋因官府回買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為團(tuán)行,雖醫(yī)卜工役,亦有差使,則與當(dāng)行同也。然雖差使,如官司和雇支給錢米,反勝于民間雇倩工錢,而工役之輩,則歡樂而往也。”(《夢粱錄》卷十三)行會(huì)組織的作用在于:可以根據(jù)市場的變化統(tǒng)一商品價(jià)格,以便獲得更多的利潤;可以保護(hù)本地區(qū)商業(yè)利益,限制外地商人進(jìn)入市場貿(mào)易;可以調(diào)節(jié)與官府的關(guān)系,在保護(hù)商人利益的原則上應(yīng)付官府的科索和勞役。行會(huì)組織在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生活中的作用的發(fā)揮,充分體現(xiàn)了城市商人和手工業(yè)者由于職業(yè)和經(jīng)濟(jì)地位的共同利益而結(jié)成了社會(huì)利益群體。它的意義在于:“行會(huì)控制資本并管理勞動(dòng);它們支配生產(chǎn)分配;它們規(guī)定價(jià)格與工資。但在它們的組織里,也有著一種社會(huì)的影響。行會(huì)的目的部分是社會(huì)性的,部分是互相性的。商業(yè)行會(huì)和手工業(yè)行會(huì),即使非完全同樣,幾乎都是在早期出現(xiàn)的。它們組織的目的中的一個(gè)巨大因素,是互相保護(hù)與保證,無論在國內(nèi)或國外。行會(huì)尤其是手工業(yè)行會(huì),在初期是具有顯著的民主精神的;從學(xué)徒到匠師這一條路,開放給所有合乎資格的人們”引自[美]湯普遜:《中世紀(jì)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史》第438頁,商務(wù)印書館1963年版。。商人和手工業(yè)者利益群體的出現(xiàn),標(biāo)志著在封建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中產(chǎn)生了新的成分,預(yù)示著一個(gè)新的社會(huì)階層的興起。
從北宋城市出現(xiàn)的新變化,移民向城市提供大量的勞動(dòng)力,商人和手工業(yè)者社會(huì)利益群體的形成,這一都市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過程中基本上構(gòu)成商品經(jīng)濟(jì)與自然經(jīng)濟(jì)的分裂,城市與農(nóng)村的分離,從而隨之形成了一個(gè)熙熙攘攘、追逐財(cái)富、充滿物欲、自私自利的市民社會(huì)。
宋代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是由官戶階層、鄉(xiāng)村戶階層和坊郭戶階層構(gòu)成的。北宋政府首先將享有統(tǒng)治特權(quán)的品官之家與被統(tǒng)治者區(qū)分開來,在戶籍管理上區(qū)分官戶與民戶。市民社會(huì)的主體是市民階層。北宋初期在民戶中將坊郭戶和鄉(xiāng)村戶區(qū)分開來,以戶籍形式將全國普通居民分為城市居民和鄉(xiāng)村居民。坊郭戶的單獨(dú)列籍定等是中國歷史上市民階層興起的標(biāo)志。
五代戰(zhàn)亂之后戶籍散亂或佚失,而全國人口又出現(xiàn)了很大的變化和流動(dòng)。北宋政權(quán)建立以來的三十余年間,戶籍管理仍然紊亂,未能形成良好的制度。這給行政管理、賦稅收入、科配和買等都帶來了很多困難。太宗時(shí)隨著經(jīng)濟(jì)的逐漸恢復(fù)和人口的蕃衍,戶籍管理問題便非常突出。淳化四年(993)三月太宗下詔:
戶口、稅賦、賬籍皆不整舉。吏胥私隱稅賦,坐家破逃,冒佃侵耕,鬼名挾戶。賦稅則重輕不等,差役則勞逸不均。所申戶口,逃移皆不件析,田畝稅數(shù),無由檢括。斯蓋官吏因循,致其積弊。今特釋前罪,咸許上言。詔到,知州、通判、幕職、州縣官,各具規(guī)畫。(《宋會(huì)要輯稿》食貨一二之二)
太宗至道元年(995)六月正式下詔,令全國重造戶口版籍。這一工作進(jìn)行了數(shù)年之久,到真宗咸平五年(1002)完成,“詔三司取天下戶口數(shù)置籍較定以聞”。顯然重造戶籍過程中發(fā)現(xiàn)城市與鄉(xiāng)村戶籍混編一起在行政管理與經(jīng)濟(jì)管理方面出現(xiàn)種種不便和困難。這種舊的戶籍制度已不能適應(yīng)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新形勢,于是醞釀著試行新的戶籍制度,即將城市與鄉(xiāng)村戶口分別列籍定等。真宗“天禧三年(1019)十二月,命都官員外郎苗稹與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從戶部尚書馮拯之請(qǐng)也。”(《宋會(huì)要輯稿》食貨六九)于是先在洛陽試點(diǎn)坊郭戶定等,稍后按其房地課稅額和經(jīng)營工商業(yè)資本的數(shù)量,以財(cái)產(chǎn)為標(biāo)準(zhǔn)分為十等而成為定制。這在我國社會(huì)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史上是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的。
北宋時(shí)期全國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jiān)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均有數(shù)目不等的坊郭戶。天禧五年(1021)都城東京(河南開封)坊郭戶人口城內(nèi)外共約五十萬以上;元五年(1090)杭州城內(nèi)約計(jì)四五十萬;北宋末年建康府約十七萬。各地坊郭戶與鄉(xiāng)村戶的比例甚有差異,但就全國而言,鄉(xiāng)村戶是占絕大多數(shù)的,估計(jì)坊郭戶的數(shù)目,可能占全國民戶的百分之五左右參見王曾瑜;《宋朝的坊郭戶》,《宋遼金史論叢》**輯;周寶珠、陳振:《簡明宋史》第138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按此計(jì)算,哲宗元符二年(1099)全國民戶共計(jì)為一千九百七十余萬戶,其中則有坊郭戶九十八萬余戶;每戶以五口計(jì),則坊郭戶人口約有五百萬之眾,它自成為一個(gè)新的市民社會(huì)的主體。
坊郭戶的定等標(biāo)準(zhǔn)各地不一致,但都定為十等。歐陽修說:
往時(shí)因?yàn)槌煎计鹫?qǐng),將天下州縣城郭人戶,分為十等差科。當(dāng)定戶之時(shí),系其官吏能否。有只將堪任差配人戶定為十等者;有將城邑之民,不問貧窮孤老盡充十等者;有只將主戶為十等者;有并客戶亦定十等者。州縣大小貧富,既各不同,而等第差科之間,又由官吏臨時(shí)均配,就中僻小州縣,官吏多非其人,是小處貧民,常苦重?cái)俊#ā镀蛎飧】图跋碌热藨舨羁圃印罚逗訓(xùn)|奉使奏草》卷下)
雖然定等出現(xiàn)這些問題,十等之分并不一定很準(zhǔn)確,但大體是能反映城市居民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地位的。宋人又習(xí)慣將十等人戶分為三類,即上戶、中戶和下戶;大致上戶是豪強(qiáng)之家,中戶為中產(chǎn)之家,下戶為貧苦之家。
坊郭上戶為一、二、三等人戶。其中一等戶又稱高強(qiáng)戶,包括居住在城市中的大地主、大房產(chǎn)主、大商人、高利貸者、大手工業(yè)主、賦稅包攬者;他們構(gòu)成城市剝削階級(jí)。中戶為四、五、六等人戶,包括一般中產(chǎn)的商人、房主、租賃主、手工業(yè)主。下戶為七等以下的人戶,包括小商、小販、小手工業(yè)者、工匠、雇傭、自由職業(yè)者、貧民。歐陽修曾建議對(duì)一般州縣的第八、九、十等人戶免去差配,因?yàn)樗麄儍H能維持較低生活水平,無力負(fù)擔(dān)政府下達(dá)的差配任務(wù)。坊郭戶內(nèi)貧富懸殊很大:富者“不知稼穡之艱難,而粱肉常余,乘堅(jiān)策肥,履絲曳采,羞具、居室過于王侯”(《樂全集》卷十四),貧者“食常不足”,而且往往“役作中夜始息”。他們?cè)诙际猩钪幸蚵殬I(yè)與經(jīng)濟(jì)狀況的不同而形成種種社會(huì)利益群體,如商人群體、工匠群體和雇傭群體。這些社會(huì)利益群體都依賴于都市經(jīng)濟(jì),共同參與都市經(jīng)濟(jì)生活,因而在封建社會(huì)中構(gòu)成一個(gè)較大的新的社會(huì)階層。北宋政府將這一階層從編戶中分出專列定等是從統(tǒng)治階級(jí)利益和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客觀需要而決定的。封建統(tǒng)治階級(jí)很重視坊郭戶在經(jīng)濟(jì)上與政府的直接利益關(guān)系。如蘇轍說:“城郭人戶雖號(hào)兼并,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賴。饑謹(jǐn)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cái)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欒城集》卷三五)與鄉(xiāng)村戶比較起來,政府同坊郭戶的關(guān)系頗為密切。它可以幫助政府解決一些困難的經(jīng)濟(jì)問題,更是政府商稅的負(fù)擔(dān)者。因此,北宋政府在對(duì)待坊郭戶方面是給予了某些優(yōu)于鄉(xiāng)村戶的待遇的,使其在民戶中顯得較為特殊。
在民戶中坊郭戶與鄉(xiāng)村戶比較,其社會(huì)地位特殊之處主要表現(xiàn)為定等、科配和勞役方面與鄉(xiāng)村戶的差異。鄉(xiāng)村戶以財(cái)產(chǎn)狀況分為五等,而坊郭戶則分為十等。在宋代文獻(xiàn)里沒有關(guān)于其原因的說明。據(jù)歐陽修所說“往時(shí)因?yàn)槌煎计鹫?qǐng)將天下州縣城郭人戶分為十等差科”,這是指天禧三年戶部尚書馮拯的建議,分等之事即成為定制。這顯然反映了城市商品經(jīng)濟(jì)已發(fā)展到較高階段,坊郭戶之間的經(jīng)濟(jì)狀況復(fù)雜,而且貧富懸殊很大,為了賦稅征收與科配更為合理,于是比鄉(xiāng)村戶的分等細(xì)致。坊郭戶對(duì)政府負(fù)有完成科配——包括和買的義務(wù)。官府向坊郭戶征購和配賣物品稱為差配、科買、科率、科賣、配賣等。凡由政府置場招誘商人按市價(jià)或高于市價(jià)將物品入納者為和買,官府將多余的物資配賣與商人為科配參見魏天安:《宋代的科配和時(shí)估》,《河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1982年第2期。。中唐以來科配與宮市實(shí)質(zhì)上是對(duì)工商業(yè)者無償?shù)穆訆Z。北宋至和五年(1056),宮市完全廢除,按市場價(jià)格的科配制度普遍施行。孫升說:“城郭之民,祖宗以來無役而有科率,科率有名而無常數(shù)。”(《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八九四)這樣使政府對(duì)坊郭戶存在一種經(jīng)濟(jì)上的密切關(guān)系,而科配因按時(shí)估市價(jià)進(jìn)行,對(duì)于坊郭戶并無多大的經(jīng)濟(jì)損失,有時(shí)在價(jià)格方面還優(yōu)于市場價(jià)格。坊郭戶與政府之間的這種經(jīng)濟(jì)聯(lián)系,使政府較關(guān)注坊郭戶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利益,所以他們長期以來享受免役的待遇,而各級(jí)政府的義務(wù)勞役全部由鄉(xiāng)村戶負(fù)擔(dān)。自王安石熙寧變法,坊郭戶與鄉(xiāng)村戶都限交免役錢。蘇轍說:“徭役之事,議者甚多。或欲使鄉(xiāng)戶助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與鄉(xiāng)戶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與齊民并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他主張對(duì)坊郭戶仍實(shí)行免役,以為:“方今雖天下之事,而三路芻粟之費(fèi),多取京師銀絹之余配賣之。民皆在城郭,茍復(fù)充役,將何以濟(jì)?故不如稍加寬假,使得休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欒城集》卷三五)元時(shí)期,蘇轍再次上疏論差役之事。他說:“坊郭人戶,熙寧以前常有科配之勞。自新法以來,始與鄉(xiāng)戶并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所出役錢太重,未為經(jīng)久之法。今若全不令出,即比農(nóng)民反為僥幸;若依新法以前科配,則取之無藝,人未必安。今二月六日指揮,并不言及坊郭一項(xiàng)。欲乞指揮并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并據(jù)見今所出役錢裁減酌中數(shù)目。”(《論差役五事狀》,《欒城集》卷三七)這個(gè)建議基本上被采納了。坊郭戶即使停止科配而出免役錢時(shí),政府也予以適當(dāng)減少。以上都可說明坊郭戶的社會(huì)地位是較優(yōu)于鄉(xiāng)村戶的。政府在政策上對(duì)它采取了一些保護(hù)措施,以便促進(jìn)都市的發(fā)展。
北宋初期對(duì)坊郭戶單獨(dú)列籍定等,將它與鄉(xiāng)村戶區(qū)分開來,這表明我國封建社會(huì)發(fā)展到一定程度,商品經(jīng)濟(jì)沖擊著舊的統(tǒng)一的自然經(jīng)濟(jì),而以城市與鄉(xiāng)村的分離使之表面化了,于是出現(xiàn)了這種情形:“在這里居民**次劃分為兩大階級(jí),這種劃分直接以分工和生產(chǎn)工具為基礎(chǔ)。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產(chǎn)工具、資本、享樂和需求的集中;而在鄉(xiāng)村里所看到的卻是完全相反的情況:孤立和分散”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7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因此,完全可以說:坊郭戶的出現(xiàn)標(biāo)志著我國封建社會(huì)中一個(gè)新的社會(huì)階層——市民階層的興起。當(dāng)然這絕不是意味著坊郭戶完全等同于市民階層。顯而易見,坊郭戶所包含的社會(huì)利益群體是十分復(fù)雜的。市民階層的基本組成部分不是舊的封建生產(chǎn)關(guān)系中的農(nóng)民、地主、統(tǒng)治者及其附庸,而是代表新的商品生產(chǎn)關(guān)系與交換關(guān)系的手工業(yè)者、商人和工匠。坊郭戶中的地主、沒落官僚貴族、士人、低級(jí)軍官、吏員,以及城市的統(tǒng)治階級(jí)附庸,都不應(yīng)屬于市民階層的;只有手工業(yè)者、商販、租賃主、工匠、苦力、自由職業(yè)者、貧民等構(gòu)成坊郭戶中的大多數(shù),他們組成了一個(gè)龐雜的市民階層。市民階層在城市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與社會(huì)生活中發(fā)揮了巨大作用,處于城市勞動(dòng)的中心地位,成為城市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歐洲經(jīng)濟(jì)史家脫尼斯說:
無論城市的實(shí)在起源是怎樣,就它的生存講,它必須看作一個(gè)整體,而它所由成立的單個(gè)社員和家庭必然依賴這個(gè)整體。這樣,城市挾著它的語言、習(xí)慣及信仰,和挾著它的土地、建筑物和財(cái)寶一樣,它是一個(gè)硬性的東西,雖有許多世代的嬗變,這東西仍然長久存在,并且半由它自身,半由它的市民家庭的遺傳與教育,總是重新產(chǎn)生大致相同的特質(zhì)和思想方法。轉(zhuǎn)引自[德]偉·桑巴特:《現(xiàn)代資本主義》**卷,第112頁,商務(wù)印書館1962年版。
自從市民階層登上歷史舞臺(tái)后,城市社會(huì)具有前所未有的新特點(diǎn),而實(shí)質(zhì)上是市民社會(huì)。這個(gè)社會(huì)的世俗享樂方式、等價(jià)交換原則、充滿物欲的活力、利己主義的精神等等,都對(duì)舊的封建主義文化采取了消極抵制的態(tài)度,為封閉的社會(huì)打開了一個(gè)窗口,迎來了人本主義的一線曙光。
我國市民階層的興起是以公元1019年(北宋天禧三年)坊郭戶單獨(dú)列籍定等為標(biāo)志的,這在世界歷史進(jìn)程上恰恰與歐洲市民的出現(xiàn)基本上是同時(shí)的。歐洲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史家亨利·皮雷納說:
城墻不僅是城市的象征,而且也是當(dāng)時(shí)用來現(xiàn)在仍然用來稱呼城市居民的名稱的由來。正因城市是筑壘之地,所以城市成為城堡……商人聚居地稱為新堡,以別于原來的舊堡。從而新堡的居民*遲從11世紀(jì)初期得到市民(burgenses)這個(gè)名稱。據(jù)我所知,這個(gè)詞于1007年**次出現(xiàn)在法蘭西;1056年出現(xiàn)在佛蘭德爾的圣奧梅爾;以后經(jīng)莫澤爾河地區(qū)(1066年出現(xiàn)在于伊)傳入神圣羅馬帝國。因此,新堡即商人城堡的居民,得到了或者可能是他們?yōu)樽约簞?chuàng)造了市民這個(gè)名稱。[比利時(shí)]亨利·皮雷納:《中世紀(jì)的城市》第93~94頁,商務(wù)印書館1985年版。
中國的坊郭戶和歐洲的市民都同時(shí)出現(xiàn)在公元11世紀(jì)之初,這絕非歷史的巧合,而是體現(xiàn)了東方與西方有著大致相似的歷史文化進(jìn)程。這個(gè)進(jìn)程也表現(xiàn)為城市的發(fā)展與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北宋時(shí)京都的城市人口在百萬以上,杭州有五十萬,建康有十七萬,此外洛陽、江陵、潭州、隆興、平江、福州、泉州、廣州等的城市人口也約在十萬以上據(jù)王曾瑜:《宋朝的坊郭戶》,《宋遼金史論叢》**輯。。在歐洲中世紀(jì),“大的都市人口又一次出現(xiàn)了。巴勒摩在12世紀(jì)約有五十萬人;佛羅倫薩在13世紀(jì)有十萬人,在威尼斯和米蘭有十萬人以上,阿斯提有六萬到八萬人;巴黎在12世紀(jì)末有十萬人,在13世紀(jì)可能有二十四萬人;杜埃、里爾、伊普雷、根特、布魯日各有將近八萬人;倫敦有四萬到四萬五千人”。[法]P.布瓦松納:《中世紀(jì)歐洲生活與勞動(dòng)》第206頁,商務(wù)印書館1985年版。古代城市化的過程,中國與歐洲也基本上是同步的,然而中國在世界文明進(jìn)步中確是居于領(lǐng)先的地位,宋都東京是當(dāng)時(shí)世界上*大和人口*多的城市了。盡管中國與歐洲歷史進(jìn)程在這方面是同步的,然而由于歷史文化及地理環(huán)境的諸差異,中國市民社會(huì)的形成與市民階層的興起卻又有自己特殊的道路,并由此使中國市民階層具有某些特點(diǎn)。這些特點(diǎn)是只有將它與西方參照才可能見到的。
宋王朝結(jié)束五代十國的封建割據(jù)局面,再度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權(quán)的國家并使中央集權(quán)制穩(wěn)固發(fā)展。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gè)重大轉(zhuǎn)折,在世界歷史進(jìn)程中也是一個(gè)特殊的現(xiàn)象。公元10世紀(jì)之末中國封建中央集權(quán)的建立給市民階層的誕生制造了一個(gè)非常不適宜的環(huán)境,這決定了中國市民階層具有坎坷而軟弱的命運(yùn)。皮雷納說:
……
中國市民文學(xué)史 作者簡介
四川省社科院文學(xué)研究所研究員,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其致力于中國古代文學(xué)專業(yè)研究,并以詞學(xué)和宋代文學(xué)為主攻方向。著有《柳永》《蘇軾詩研究》《宋詞概論》《中國詞學(xué)史》《宋詞辯》《詞學(xué)辯》《唐宋詞譜校正》《中國市民文學(xué)史》《詩詞格律教程》《敦煌文化尋繹》《四川國學(xué)小史》《國學(xué)論集》等。
- 主題:相關(guān)研究不多,對(duì)這方面有興趣的讀者還是值得一讀的
但作者本人的文學(xué)立場,主要是在寫到近現(xiàn)代小說領(lǐng)域的時(shí)候,總給我一種士大夫紆尊降貴下來審視你們喜歡的這是個(gè)什么東西的感覺。雖然研究的是市民文學(xué),可立場依然是士大夫階級(jí)的雅正派目光。最諷刺和可笑的是作者揚(yáng)言必將消亡的武俠小說,雖然作為一種類型小說它早已風(fēng)光不再,可比武俠小說更加通俗和大眾化的網(wǎng)絡(luò)爽文已經(jīng)興起,甚或有些非自發(fā)性地向外傳播的態(tài)勢。 可以說,我國文學(xué)依然走在由貴族化(包括新型文化士大夫)走向平民化的大趨勢中,至少到現(xiàn)在為止還未曾改變。 我希望研究者們研究事物發(fā)展史,尤其是文化藝術(shù)類的時(shí)候可以少發(fā)表點(diǎn)自己的看法,更不要言之鑿鑿地預(yù)言,免得成為笑柄。 不是打工人就別比比打工人喜歡看啥了,沒了武俠小說也有網(wǎng)絡(luò)爽文,哪天網(wǎng)絡(luò)爽文沒了也會(huì)有更通俗普及的替代品的。
- 主題:中國的市民文學(xué)過去研究不多,本書有所開拓
中國的市民文學(xué)過去研究不多,本書有所開拓。但對(duì)市民文學(xué)的界定似乎太寬泛了些。
- >
羅曼·羅蘭讀書隨筆-精裝
- >
【精裝繪本】畫給孩子的中國神話
- >
名家?guī)阕x魯迅:朝花夕拾
- >
詩經(jīng)-先民的歌唱
- >
姑媽的寶刀
- >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實(shí)旅程
- >
有舍有得是人生
- >
月亮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