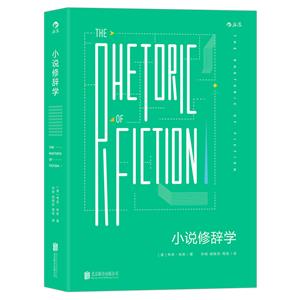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小說修辭學(八品-九品)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9601377
- 條形碼:9787559601377 ; 978-7-5596-0137-7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小說修辭學(八品-九品) 內容簡介
《小說修辭學》出版于1961年,以后再版多次,被列為西方現代小說理論的經典之作。《美國百科全書》將該書譽為“20世紀小說美學的里程碑”。本書主要討論了西方小說的歷史發展,梳理了小說技巧及其理論的演變,批判地考察了現代有關小說的流行觀點,建立了經典的現代小說理論,為現代小說創作、批評和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書中提出的一些觀念和術語,如“隱含的作者”“不可靠的敘述者”等,均為當今敘述學領域的經典術語。
小說修辭學(八品-九品)小說修辭學(八品-九品) 前言
修訂版序
“小說會殺人嗎?”
如果直接這么提問,會顯然有些幼稚可笑。小說所講的故事當然是虛構的,這是婦孺皆知的常識。但是,如果認真地對待這個問題,這個提問倒也觸及文學復雜的社會功能和倫理影響。法國新小說派作家羅布-格里耶的小說《窺視者》曾流行一時,該小說作品的封面有文字介紹云:閱讀此書必使讀者深入到書中殺人狂的內心深處,進而去強烈地體驗殺人狂的感覺,并使讀者*終成為殺人“同謀”。如此煽動性的語言雖不免有些夸大,卻也道出了小說與“殺人”的某種可能的關聯,只不過閱讀小說中的“殺人”未必一定變成讀者的外在社會行為,但在讀者內心造成某種深刻的影響卻是完全可能的。看來,文學的虛構性并不能與某種道德后果的脫離干系。
文學批評的“芝加哥學派”(又稱“新亞里士多德學派”)第二代人物布斯(WayneBooth,1921—2005),曾在其代表作《小說修辭學》中,非常嚴肅地討論了小說敘事技巧與倫理關系。這部著作的書名頗有些歧義,乍一看來是在討論文學敘事修辭方面的技術問題,實則揭橥了一個深層的文學問題:虛構性的文學修辭與小說家的道德責任之間的潛在關系。該書英文版于1961年面世,曾被批評界譽為20世紀小說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述。時隔26年后,中譯本由北京大學出版社發行,距今已有30年。后浪出版公司現在要出版該書的修訂版,作為該書的譯者之一,我欣然應允為新版寫個簡短的序言。然而,一提起筆竟不免唏噓,感慨良多。記得20世紀80年代早期,剛剛大學本科畢業不久的我,算是一個初出茅廬的文學批評后生,對任何新理論新觀念都十分好奇,偶爾在一本英文工具書中看到對布斯《小說修辭學》的高度評價。于是四處尋找這本書,眾里尋他千百度地得到復印本后,約好友華明和胡蘇曉一起翻譯。前前后后經歷好幾年,后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現在回想起來,80年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年代,那時是文學有某種異常獨特的影響力,它后來被文學史家稱為“新時期文學”,在當時勇敢地承擔了解放思想和更新觀念的角色。每當一部有思想鋒芒和道德力量的新作問世時,都會掀起大大小小的“轟動效應”,成為坊間爭相傳看的文本。文學的功能在那個時代被放大了,但確實助推了整個社會的思想解放,這與今天娛樂至死的文學迥然異趣。“新時期文學”頗有些類似晚清和新文化運動時期,小說承擔了開啟民智的功能。如“小說界革命”的倡導者梁啟超所言:“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然而,80年代的文化面臨著一些特殊問題,一方面要破除極“左”的文藝思潮的束縛,另一方面又迫切需要改變文學研究觀念和方法,所以80年代中期興起了文學研究方法論大討論。不過,當時可資借鑒的國外小說研究的資源并不多,記得一本內部發行的福斯特的《小說面面觀》,在文學批評界廣為傳看。在這樣的情況下,翻譯布斯的《小說修辭學》對推進國內小說研究就具有積極意義。雖然當時并未意識到這一點,但時隔30年后回頭看,這本書的中譯本的面世,的確對國內的小說研究起到了相當積極的推動作用,布斯在此書中提出的那些獨特概念,諸如“隱含的作者”“講述—顯示”“敘述距離的控制”和“非人格化敘述”等,很快成了當今小說研究文獻中習見的術語了。
布斯的《小說修辭學》中譯本在80年代刊行,也遭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現在回顧起來,大致有兩方面的問題。首先是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在文學藝術領域啟動了對“文化大革命”和“十七年”文學藝術的批判性反思,尤其是對那種曾經占據主導地位的政治說教式的文學藝術的深刻批判。文學藝術的創作擺脫了政治教條束縛,開始走向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新局面。正像一切社會文化現象所有的物極必反趨向一樣,厭惡了說教式的文學藝術,當然也會抵制一切與之相關的理論主張。布斯這本書有一個基本主題,那就是小說家如何通過敘事技巧的運用來踐履文學的道德責任。可以想見,這個主張在當時一定不為人們所重視,甚至被人們所鄙夷,因為在“十七年”乃至“文化大革命”有過太多的道德說教和意識形態規訓。在這樣的背景中,布斯的《小說修辭學》就難免被誤解和誤讀。很多批評家和研究者將其敘事技巧形式的理論與其敘事倫理內在關聯,生硬地割裂開來,把一系列布斯式的概念,諸如“講述—顯示”的二分、“隱含的作者”概念、敘述“視點”“類型”與“距離控制”等,當作小說敘述的技巧范疇加以理解,與其*為關切的敘事倫理全無關聯。其實,這是一個經常會看到的跨文化接受的規律性現象,本土對任何外來文化的接受,總是要受到接受者自己的現實語境的制約。接受者有所選擇地理解甚至誤讀外來文化并為我所用,常常在所難免。據說,魯迅當年曾一度非常鐘愛挪威畫家蒙克,并打算編撰譯介蒙克的畫集。遺憾的是此事一直沒有付諸實施,他很快移情別戀于德國畫家珂勒惠支,并大力宣介珂勒惠支的版畫,帶動了“新興木刻運動”。我猜想大概是當時中國的社會文化境況,并不適合引入蒙克式的高度自我張揚的表現主義,珂勒惠支的寫實主義以及對下層民眾疾苦的藝術表現,則是一個當時語境的合適選擇。布斯的小說修辭學理論的中國接受情況亦復如此,當時對文學的道德說教的反感和抵制,驅使這本書的讀者生生地在布斯小說修辭學中劈開一個裂隙,只取其小說敘事技術一半,而摒棄了敘事倫理的另一半。
另外一個可觀察到的有趣現象,是英美小說理論與法國結構主義敘事學在中國接受中所產生的某種張力。從整個西方學界的情況來說,80年代是法國結構主義敘事學一統天下的局面,英美小說理論顯得有點頹勢和過時。布斯的《小說修辭學》中譯本在80年代后期面世,正巧遭遇了這一局面。我們知道,英美小說理論與法國敘事學是兩個不同的理論學派,前者有英美經驗主義的色彩,后者則帶有歐陸理性主義的傳統,這就形成了對小說敘事研究完全不同的理路。80年代一些英美小說理論的著作陸續被譯介,初步形成了一個小小的理論場域。*初是80年代初內部發行的福斯特《小說面面觀》,爾后詹姆斯的《小說的藝術》、盧伯克的《小說技巧》、洛奇的《小說的藝術》等著述相繼問世,當然,布斯的這部著作作為英美小說理論的一部分,也在這一時期被介紹進來,并成為英美小說理論的中國接受的關鍵一環。在我看來,較之于法國敘事學更加技術性和符號學的學理性研究,英美小說理論帶有更明顯的實用性和實踐性,因而與小說創作和批評分析的關系更為密切。換言之,如果說法國結構主義敘事學更偏向于理論分析和符號學建構的話,那么,以布斯為代表的英美小說理論則更傾向于現實的文學問題和批評實踐,所以敘事倫理在小說修辭學中被提出是合乎邏輯的。只消把布斯的《小說修辭學》和托多洛夫的《散文詩學》稍加比較,可以清晰地看出兩者差異:前者更加偏重于小說敘事的倫理學,而后者則強調小說敘事的技術層面和語法層面。也許正是這個原因,布斯的《小說修辭學》對敘事倫理的討論,在如日中天的法國結構主義敘事學面前略顯保守。此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英美小說理論往往先于法國敘事學提出一些概念,但后者會將這些概念納入其結構主義敘事學的理論框架,往往重新界定,因而形成一個全新的概念。如英美小說理論的“視點”概念,到了法國結構主義敘事學,便發展成為所謂的“聚焦”概念。隨著法國結構主義敘事學的強勢登場,人們在大談法式“聚焦”概念時,卻忘記了它源于英美式的“視點”概念。這大概就是理論發展的邏輯,新概念取代了舊概念成為時尚后,后者的歷史貢獻很容易一筆勾銷。另一個頗為有趣的比較是,布斯在論證小說修辭學的倫理特性時,選擇了法國新小說作家羅布-格里耶的《窺視者》這樣的前衛作品,這也許是因為越是前衛的文學,在敘事技巧上就越是富于創新,同時也就越容易彰顯敘事倫理問題的迫切性。布斯所要證明的問題是,小說敘事方式及其敘述距離的控制,并不只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而是牽涉到敘事所產生的復雜的道德效果。反觀托多洛夫的敘事學研究,則較多地選取了《奧德賽》《一千零一夜》或《十日談》等古典作品,但他要談及的卻是一個很前沿和時髦的敘事語法和結構分析問題。
布斯的《小說修辭學》在中國被有所選擇地加以理解甚至誤讀,也許是這本書在中國“理論旅行”(薩義德)的必然命運。然而過了30年,當我們重讀這部經典著作時,卻會有不同的想法。在娛樂至死風氣很盛的今天,在敘事技巧無所不用其極和敘述內容無所不及的當下,媚俗的、情欲的、暴力的、過度娛樂化的和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文學敘事,已經成為當代文學的普遍景觀,于是,敘事倫理便成為任何嚴肅的理論研究不可忽視的問題。布斯這部著作的再版,可謂恰逢其時。從20世紀80年代對說教式文學的鄙夷,到21世紀對敘述倫理的重新關注,看起來只是一個“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風水輪轉,實際上卻更觸及當代中國社會和文化轉變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今天,中國的道德危機已經非常明顯,社會道德底線被一再突破,從食品安全問題,到環境風險,從大學生投毒案,到電話詐騙,整個社會的道德規范處于岌岌可危之中。文學對這種道德困境不能袖手旁觀,作家有責任在促使社會向善轉變方面有所作為。所以,重讀布斯的《小說修辭學》便有某種積極意義。布斯所提出的小說修辭學的道德意涵,在今天來看是一個不可小覷的問題。2005年10月10日,芝加哥大學新聞辦公室就布斯逝世發表了一篇特稿,把布斯視為一個踐履了學者、教師、人文主義者和批評家多重角色的思想家,贊譽他是20世紀*重要和*有影響的批評家之一,其理論貢獻是“把技巧和倫理分析相結合,從而改變了文學研究的形貌”,并宣稱布斯的著作業已成為文學研究中倫理批評的“試金石”。
那么,文學對道德重建能起作用嗎?換句話說,文學能阻止殺人嗎?我想起了布羅茨基的一個精彩說法:“與一個沒讀過狄更斯的人相比,一個讀過狄更斯的人更難因為任何一種思想學說面向自己的同類開槍。”為何狄更斯的作品或者更為廣闊的文學會具有如此功能呢?布羅茨基堅信:“文學是人的辨別力之*偉大的導師,它無疑比任何教義都更偉大,如果妨礙文學的自然存在,阻礙人們從文學中獲得教益的能力,那么,社會便會削弱其潛力,減緩其進化步伐,*終也許會使其結構面臨危險。”較之于布羅茨基道義上的論斷,布斯更強調文學必須回到修辭學的本原,那就是修辭學乃是“發掘正當信仰并在共同話語中改善這些信仰的藝術”。在《小說修辭學》之后,布斯進一步發展了這一學術理念,理直氣壯地舉起了“傾聽的修辭學”之大旗,他強調文學有必要“致力于推動當前爭論中的各方相互傾聽對方的觀點”,進一步彰顯出修辭學的倫理學作用,因為道理很簡單,“修辭學(涉及了)人類為了給彼此帶來各種效應而分享的一切資源:倫理效應(包括人物的點點滴滴)、實踐效應(包括政治)、情感效應(包括美學),以及智性效應(包括每個學術領域)”。
也許我們有理由說,布斯的理論所以不同于“文以載道”,就是在于他并沒有把文學修辭學當作達成特定倫理目標的工具,毋寧說,在布斯的文學理念中,文學修辭學本身就是倫理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在布斯看來,*好的倫理思考往往并不直接指向“你不應該如何”,而是鼓勵人們追求一系列“美德”,即:值得稱贊的行為舉止之典范習慣。因為他確信文學教育和文學閱讀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形態改變著讀者。以我之見,這一點在當下的中國文學中顯得尤為重要,而布斯《小說修辭學》的修訂再版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值得我們重視。布斯后來在其一系列論著中深化了他的修辭倫理學觀念,他深有體會地說過:“英語教師從倫理上教授故事,他們比起*好的拉丁語、微積分或歷史教師來說對社會更為重要。”因為“我們都應該努力用故事世界塑造有自我推動力的學習者”,“從倫理上去教故事比其他任何教學都更重要,實際上,它還比其他任何教學都更難”。細讀《小說修辭學》,我們可以清晰地感悟到布斯深刻倫理關懷的人道主義。
在信息爆炸和出版物汗牛充棟的今天下,很難想象一本書30年后會有修訂再版的機會。如果作者布斯先生活著,他大概也會欣喜萬分的。大約十年前,我在譯林出版社主編了一套“文學名家講壇”的書系,特意又選擇了一本《布斯精粹》,進一步譯介了布斯的文學思想。作為文學批評的“芝加哥學派”第二代領軍人物,布斯秉承了這一學派奠基人麥克基恩(RichardMcKeon)和克萊恩(R.S.Crane)的基本理念,一方面并不為時髦的多元論所迷惑,另一方面又在多元論的語境中亮出并恪守自己的道德底線。這樣就保持了某種必要的平衡,既認可多元論的積極意義,又警惕多元論后面的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他堅信自己的方法是既不皈依一元論也不屬于無限多樣論,他辯證地指出,“完全意義上的批評多元論是一種‘方法論的視角主義’,它不但確信準確性和有效性,而且確信至少對兩種批評模式來說具有某種程度的準確性”。這里,布斯在“方法論的視角主義”基礎上,提出了一個獨特“雙重視角”的方法。如果我們用這種方法來看小說修辭學,一方面是要關注敘事修辭學的技巧,另一方面則須謹記小說修辭技巧所具有的倫理功能。這樣的方法論在避免了形式主義的極端化和片面性的同時,又擺脫了道德主義者的文以載道的教條。我想,這大概就是布斯作為人文主義的文學批評家過人的睿智之處。
如果我們歷史地看待布斯的修辭倫理研究,還可以置于更加廣闊的20世紀文學理論格局中加以審視,放到形式主義和文化政治兩種取向的緊張關系中加以理解。照伊格爾頓的說法,1917年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什克洛夫斯基的《文學即技巧》一文的面世,拉開了形式主義文學思潮的大幕。此一觀念深刻地影響了當代文學理論的走向,有力地塑造了當代文學理論的地形圖。毫無疑問,形式主義文學理論顯然有其存在的深刻理由,它深化了我們對文學形式和審美層面的理解,奠定了文學研究作為一門學科的合法性與基本研究范式。但形式主義的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它排斥了文學與社會的復雜關聯,把文學研究當作某種純形式和文學技巧的分析,進而抽離了文學的政治意義和社會功能。也許正是由于形式主義的這一局限性,20世紀60年代后結構主義思潮崛起,導致了文學研究的激進轉向,高度政治化的文學研究大行其道,理論家和批評家們放棄了早先關注的風格、修辭、技巧、形式等問題,熱衷于討論諸如階級、性別、種族、身份認同等問題。形式主義和文化政治的緊張可以說始終未能真正緩解,一直到21世紀初,才出現了審美回歸的思潮,“新形式主義”登上歷史舞臺。然而,如果我們回溯20世紀60年代布斯的《小說修辭學》以及后來他的一系列著述,會驚異地發現,他的文學理論很好地解決了這個矛盾,化解了形式主義和文化政治的張力。布斯深信文學研究始終面臨著一個兩難困境:一方面,文學研究的流行觀念是強調“詩就是詩,不是別的什么”;另一方面,熱愛文學的人又不得不秉持一個信念,即“好的文學對我們的生活至關重要”。正是基于對這一兩難困境的深刻體認,他才努力扮演文學研究中的一個“雙重角色”,即:他不但是一個精于技巧或形式分析的大師,比如他對敘述視點、距離、隱含作者的創新性發現;同時,他又是一個有著深刻人道關懷的思想家,他重返修辭學的倫理根基,將形式分析與道德關懷有機地結合起來,這也許就是“芝加哥學派”值得我們關注的思想遺產,也是這本書再版的意義所在。
*后,我要感謝后浪出版公司頗有見地地再版此書,感謝華明教授撥冗修訂疑譯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翻譯此書時我們幾位譯者還在“而立之年”,修訂再版時我們已到了“耳順之年”了。作為本書的譯者和*早的讀者,30年時光使我們可以更加從容地評價布斯的《小說修辭學》,更加深入全面把握這本著作的精髓。此外,30年時光披沙揀金,在中國社會和文化經歷了巨大變遷之后,在汗牛充棟的西學著述中,《小說修辭學》仍為出版家和讀者們所鐘愛,這意味著什么毋庸贅言。
是為序。
周憲
2016年12月
小說修辭學(八品-九品) 目錄
譯 序
序 言
編 藝術的純潔性與小說修辭
章 “講述”與“顯示”
早期故事中專斷的“講述”
《十日談》中的兩個故事
作者的多種聲音
注 釋
第二章 普遍規律之一:“真正的小說一定是現實主義的”
從正當的反叛到殘缺的教條
從不同的種類到普遍的性質
早期的普遍標準
普遍標準的三個根源
現實主義幻覺的強度
作為直接現實的小說
論現實主義之間的區別
強度的安排
注 釋
第三章 普遍規律之二:“所有的作者都應該是客觀的”
中立性和作者的“第二自我”
公正性和“不公正的”強調
“冷漠性”
非人格化技巧所促進的主觀主義
注 釋
第四章 普遍規律之三:“真正的藝術無視讀者”
“真正的藝術家只為自己寫作”
純藝術的理論
偉大文學的“不純性”
純小說在理論上是合意的嗎?
注 釋
第五章 普遍規律之四:感情、信念和讀者的客觀性
“在審美上,眼淚和笑聲都是欺騙”
文學趣味(和距離)的類型
趣味的結合與沖突
信念的作用
舉例說明信念:《荒唐故事》
注 釋
第六章 敘述的類型
人 稱
戲劇化與非戲劇化的敘述者
旁觀者與敘述代言人
場面與概述
議 論
自覺的敘述者
距離的變化
贊同或修正的變化
不受限制的敘述
內心觀察
注 釋
第二編 小說中作者的聲音
第七章 可靠議論的運用
提供事實、“畫面”,或概述
塑造信念
把個別事物與既定規范相聯系
升華事件的意義
概括整部作品的意義
控制情緒
直接評論作品本身
注 釋
第八章 作為顯示的講述:戲劇化的敘述者,可靠的和不可靠的
作為潛在作者的戲劇化代言人的可靠敘述者
《湯姆?瓊斯》中的“菲爾丁”
菲爾丁的模仿者
《項狄傳》和形式整一性的問題
三種形式傳統:喜劇小說、文集和諷刺作品
《項狄傳》的整一性
項狄式評論,好的與壞的
注 釋
第九章 簡?奧斯丁的《愛瑪》中的距離控制
《愛瑪》中的同情與判斷
通過控制內心觀察得到同情
判斷的控制
可靠的敘述者和《愛瑪》的思想規范
對愛瑪?伍德豪斯的明確判斷
作為朋友和指導的隱含作者
注 釋
第三編 非人格化的敘述
第十章 作者沉默的作用
再一次的“作者隱退”
同情的控制
清晰與含混的掌握
作者與讀者之間的“秘密交流”
注 釋
第十一章 非人格化敘述的代價之一:距離的混淆
令人困惑的《螺絲在擰緊》
早期文學中反諷導致的困難
《青年藝術家的肖像》中的距離問題
注 釋
第十二章 非人格化敘述的代價之二:亨利?詹姆斯與不可信的敘述者
從有缺陷的反映者到主題的發展
《說謊者》中的兩個說謊者
“阿斯彭遺稿的竊取”與“威尼斯的召喚”
“ 深諳世故的讀者,要當心!”
注 釋
第十三章 非人格化敘述的道德與技巧
誘人的觀察角度:以塞利納為例
作者道德判斷的晦澀
精英的道德
注 釋
參考文獻
出版后記
小說修辭學(八品-九品) 節選
早期故事中專斷的“講述”故事講述者*明顯的人為技法之一,就是那種深入情節表面底下,去求得確實可信的人物思想感情畫面的手段。無論我們關于講述故事的自然技法的概念是怎樣的,每當作者把所謂真實生活中沒人能知道的東西講述給我們時,人為性就會清楚地出現。在生活中,通過完全確實可信的內心信號,我們除了知道自己之外不能知道其他任何人,而且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對自己的了解也是相當偏頗的。然而在文學中,從開頭起,就以奇特的方式直接地和專斷地告訴我們各種思想動機,而不是被迫依賴那些我們對自己生活中無法回避的人們所做的可疑的推論。
“在烏斯地方有個男人,他的名字叫約伯;此人純潔正直,是個敬畏上帝、不做壞事的人。”不知名的作者一下就給了我們一種在現實的人身上,即使是在我們*親密的朋友身上也不曾獲得過的信息。如果我們要把握隨后發生的故事,我們就必須毫無疑問地認可這個信息。在生活中,如果一位朋友說出他的朋友是“完美正直的”這么一種看法,那么我們就要帶著我們對說話人性格的了解,或我們對人類難免失誤的認識所產生的限制,來接受這一信息。我們永遠不會像我們相信作者關于約伯的公開陳述那樣,完全相信哪怕是*確定可信的證詞。
我們在《約伯記》中緊接著進入由并非根本不受限制的信息所表現的兩個場面:撒旦對上帝的誘惑和約伯*初的損失與悲哀。但是,我們用任何觀察者
都不能從真實事件中得到的判斷來結束了**部分:“在所有事物中約伯都無罪,也沒有愚蠢地指責上帝。”我們怎么知道約伯無罪呢?誰對這個問題表了態?只有上帝自己才能確定無疑地知道約伯是否愚蠢地指責過他。然而,作者還是做出了判斷,并且我們毫不懷疑地接受了他的判斷。
開始時,作者好像不要求我們相信他的未經證明的話,因為他還給我們以上帝自己與撒旦談話時所做的鑒定,以證實他有關約伯道德完善的觀點。在約伯被他的三個朋友糾纏,說出了對自己經歷的意見后,上帝又被帶上臺來證明約伯意見的真實可信。但是十分清楚,上帝陳述的可靠性*終還是取決于作者本人,正是他提到了上帝并要我們確信這些話真是他的。
直到近代,這種形式的人為的專斷還表現在大多數故事中。盡管亞里士多德贊揚荷馬,說他比其他詩人更少以自己的聲音講話,但即使荷馬也很少寫下一頁不對事件的主旨、預測和相對重要性做某種直接闡述的詩篇。雖然眾神本身時常是不可信的,但是荷馬——我們所知道的荷馬——卻并非不可信。他講述給我們的東西經常比我們從現實的人和事中可能得知的東西更深刻更精確。例如,《伊利亞特》開頭的幾行假托引文明確地告訴我們這個故事是關于什么的。“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憤怒和它的破壞。”故事直截了當地說,我們得關心希臘人勝過關心特洛伊人。并告訴我們,希臘人是具有“強大靈魂”的“英雄們”。還告訴我們,他們要變成“猛犬精美的筵席”正是宙斯的意愿。我們還得知,“萬軍之主”阿伽門農和“英武”的阿喀琉斯之間的具體矛盾是由阿波羅挑起的。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永遠不會相信任何這類事物,然而當我們一直和荷馬并肩穿過《伊利亞特》時,我們卻確信了這類事情,它嚴格地支配著我們的信念、興趣和同情。雖然他的議論一般是簡短的并時常裝扮成明喻,但我們卻從中了解到了每顆心的確切特性,我們知道誰無辜地死去,誰死有應得,誰愚笨,誰聰明。而且每當有某種理由要我們知道人物在想什么的時候,我們就知道了,“圖丟斯的兒子疑慮地沉思/……在他的心靈中,他三次陷入反復沉思……”(該書第八卷第二章第167—169行)。
在《奧德賽》中,荷馬以同樣明確和系統的方式,使我們保持著這類評價。雖然在不能從荷馬的作品中發現他本人的真實生活經歷這個意義上說,E.V.里歐稱荷馬為“非人格的”和“客觀性的”作者無疑是正確的,但是荷馬有意和明顯地“強要”我們對“英雄的”“足智多謀的”“令人欽佩的”“聰明的”奧德修斯做的評價。“然而眾神都為他難過,除去波塞冬,因為他懷著殘酷的惡念追擊著英雄奧德修斯,直到他返回自己國家的那一天。”
的確,在宙斯宮殿里開場的主要理由不僅僅是對奧德修斯受困的事實進行陳述,荷馬還要求我們對受困這一事實富有同情地介入,雅典娜對宙斯的公開回答提供了對隨后事件的權威性評價。“我的心正是為奧德修斯而絞痛——這聰明而不幸的奧德修斯,他已經和他所有的朋友分離了這么久,現在被困在大海中一個遙遠而孤寂的島嶼上。”對于她因為人們為遺忘奧德修斯而做的指責,宙斯回答:“我怎么會忘記可敬的奧德修斯呢?他不僅是活著的人中*聰明的,而且他的奉獻也是*慷慨的……波塞冬……竟對他如此不寬容……”
當我們碰到奧德修斯的敵人時,詩人再一次毫不猶豫地要么以他自己的身份說話,要么提供出神的昭示。珀涅羅珀的求婚者們在我們看來一定顯得很壞,忒勒馬科斯則一定是令人敬佩的。荷馬不僅詳細敘述了雅典娜對忒勒馬科斯的贊揚,還給自己的直接評價加上美好的色彩。“傲慢的”“狂妄的”和“兇惡的”求婚者們被拿來與“聰明的”(雖然幾乎還是個稚弱青年)忒勒馬科斯和“善良的”曼陀相對照。“忒勒馬科斯現在顯示了他良好的判斷力。”曼陀“現在挺身而出,向他的同胞們提出忠告,顯示了他善良的愿望”。我們很少碰到沒有受到詩人某種直接攻擊的求婚者,“這就是他們自負的情形,雖然他們這些人一點也沒猜到事情究竟如何”。每當對一個人物所處的地位可能存在疑問時,荷馬就會直接向我們指出,“‘我的女王’,彌東回答,他絕不是一個惡棍……過了幾百頁之后,當彌東幸免于奧德修斯的屠殺時,我們幾乎不感到驚奇。”
所有這些直接指示都和雅典娜的神圣證言結合了起來,她的證言是,眾神與忒勒馬科斯“沒有爭執”,并決定他“將平安回家”,其結果是,當我們開始在第五卷中進入奧德修斯的**次歷險時,我們完全清楚我們能期待什么事件和擔心什么事件;我們會明確地對英雄們表示同情,并對求婚者們表示輕蔑。不用說,要是另一位詩人從求婚者的角度來處理這一系列情節,他也許會輕易地引導我們帶著截然不同的期待與擔心進入這些歷險。
我們在《約伯記》和荷馬作品中看到的這種直接而專斷的修辭法,一直沒有從小說中完全消失。但是正如我們都知道的,如果我們打開一部典型的現代長篇小說或短篇小說的話,這些可能是看不到的。
吉姆有一種旅行時就要玩的嗜好。例如,他正乘坐著火車,到某個小鎮去,好,比如說吧,像本頓那樣的小鎮。吉姆會打車窗里往外張望,瀏覽商店的招牌。
例如,它們是這么個招牌,“亨利·史密斯谷物商店”。好,吉姆就要寫下這個名字和這個小鎮的名字,當他到達他要去的地方,他就寄一張明信片給本頓鎮的亨利·史密斯,并非不署姓名。但他要在明信片上寫下,好,比如說,“問問你妻子上周來消磨了一下午的訂貨商”,或者“問問你太太,上次你在卡特威爾時她是如何擺脫寂寞的”,然后他在明信片上簽名,“一位朋友”。
當然,他永遠不會知道這些玩笑中的任何一個真正引起了什么事,但他能夠想象可能會發生什么,這就夠了……吉姆是個怪人。
拉德納《理發》(1926)一書的大多數讀者都已經看出來,拉德納對吉姆的看法在此是與敘述者的看法截然不同的。但是故事里卻沒有人這么說過。拉德納沒有出來這么說,沒有,至少就荷馬在其史詩中出現這一意義上說是沒有。就像許多其他現代作家一樣,他自我隱退,放棄了直接介入的特權,退到舞臺側翼,讓他的人物在舞臺上去決定自己的命運。
在睡眠中她知道她在自己床上,但卻不是幾小時以來她一直睡的那張床,房間也不是原先的,而是她在哪兒見過的那個房間。
她的心臟是她身體外面壓在胸前的一塊石頭,她的脈搏遲緩并停頓,她知道某種奇異的事情就要發生,甚至在晨風涼爽穿過窗欞的時候……現在我必須起床,在他們都安靜的時候出去。我的東西在哪兒?在這兒東西都有它們自己的意志,藏在它們喜歡藏的地方……現在我該為這次我不想踏上的旅程借什么樣的馬呢?……來吧,格雷利,她說,抓住韁繩,我們必須脫離死神和魔鬼……
在這里,作者與敘述者的關系更復雜了。凱瑟琳·安妮·波特的米蘭達(《灰駿馬·灰騎手》[1936])無法像拉德納的理發師那樣被簡單地歸因于道德和智力的低下;在人物、作者和讀者之間起作用的反諷是更難描述的。然而對于讀者來說,問題基本上與《理發》中的相同。故事被不加評價地表現出來,使讀者處于沒有明確評價來指導的境地。
自從福樓拜以來,許多作家和批評家都確信,“客觀的”或“非人格化的”或“戲劇式的”敘述方法自然要高于任何允許作者或他的可靠敘述人直接出現的方法。有時,正如我們在后面三章中將看到的,涉及這一轉變的各種復雜問題,已被簡單地歸納為藝術的“顯示”和非藝術的“講述”的區別。“我將不告訴你任何事情,”一位優秀的青年小說家在為他的藝術辯解時說,“我將讓你去偷聽我的人物說話,有時他們要說真話,有時他們要撒謊,你必須在他們這么干時自己去判斷。你每天都是這么做的。屠夫說:‘這是*好的貨色。’你就回答:‘那是你說的。’我的人物難道應該比你的屠夫更多地暴露心思嗎?我可以多‘顯示’些,但僅僅是顯示……指望小說家確切地告訴你某些事情是‘怎樣’敘述的。就像指望他站在你椅子旁邊給你拿著書一樣的不可能”。
但是對作家在小說中的聲音發生了變化的看法,卻引起了遠比這種簡單化的關于角度的看法更深刻的問題。珀西·盧伯克在40年前教導我們相信,“直到小說家把他的故事看成一種‘顯示’,看成是展示的,以致故事講述了自己時,小說的藝術才開始”。在某種意義上,他可能是正確的——但是這么說引起的問題比它所回答的問題更多。
為什么菲爾丁所“講述”的一段情節,能夠比詹姆斯或海明威的模仿者一絲不茍地“顯示”的許多場景更充分地打動我們呢?為什么某些作家的議論毀滅了這種有議論的作品,而《項狄傳》中大段的議論仍然能吸引我們?*后,當一位作家“介入其中”,告訴我們有關他的故事的某些事情時,他所做的到底是些什么呢?這些問題迫使我們仔細去考慮,當一位作者使一個讀者充分介入一部小說作品時會出現什么;它們把我們引向一種關于小說技巧的觀點,這種觀點必然會超出我們有時根據“角度”概念所認可的理論上的簡單化。
小說修辭學(八品-九品) 相關資料
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芝加哥學派”第二代領軍人物韋恩·布斯的代表作The Rhetoric of Fiction初版于1961年,其后再版多次,被列為西方現代小說理論的經典之作。《美國百科全書》將該書譽為“20世紀小說美學的里程碑”。
1986年,《小說修辭學》的中文簡體版*次在國內出版,對國內的小說批評和理論研究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眾多大學中文系將此書列入文藝理論或者外國文學專業參考書目。
本書并非單純討論文學修辭的技術問題,而是提出了一個深層的文學問題:虛構性的文學修辭與小說家的道德責任之間的潛在關系。
此次重出簡體中文版,由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影視藝術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華明教授對譯稿進行了修訂。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周憲教授撰寫了修訂版序言。
本版訂正了正文及注釋中的錯譯、漏譯之處,梳理了部分語句,將部分人名、書名改為時下通行譯法,并更新了部分注釋中的作家生卒年等資料。
小說修辭學(八品-九品) 作者簡介
韋恩?布斯(Wayne Clayson Booth,1921—2005),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著名文學批評家,“芝加哥學派”(又稱“新亞里士多德學派”)第二代領軍人物。布斯是20世紀重要和有影響的批評家之一,其理論貢獻是“把技巧和倫理分析相結合,從而改變了文學研究的形貌”。
- >
二體千字文
- >
龍榆生:詞曲概論/大家小書
- >
煙與鏡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
- >
中國歷史的瞬間
- >
羅曼·羅蘭讀書隨筆-精裝
- >
巴金-再思錄
- >
唐代進士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