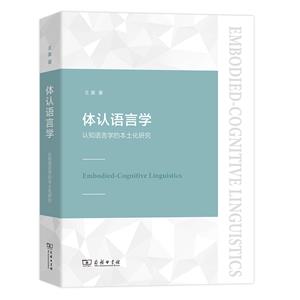-
>
妙相梵容
-
>
基立爾蒙文:蒙文
-
>
我的石頭記
-
>
心靈元氣社
-
>
女性生存戰爭
-
>
縣中的孩子 中國縣域教育生態
-
>
(精)人類的明天(八品)
體認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的本土化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0183970
- 條形碼:9787100183970 ; 978-7-100-18397-0
- 裝幀:平裝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體認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的本土化研究 本書特色
本書作者耗費20多年對“認知語言學”進行了深入研究與思考,為了凸顯該學科的體驗性和實踐性,主張將其本土化為“體認語言學”,且將其核心原則歸納為“現實—認知—語言”,從而實現了由國外“認知語言學”到國內“體認語言學”的飛躍。
體認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的本土化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作者耗費20多年對“認知語言學”進行了深入研究與思考,為了凸顯該學科的體驗性和實踐性,主張將其本土化為“體認語言學”,且將其核心原則歸納為“現實—認知—語言”,從而實現了由國外“認知語言學”到國內“體認語言學”的飛躍。本書共為15章,前9章主要從理論角度詳細地闡述了語言體認性得以成立的根據,分別從哲學史、神經科學、語言起源、語言學發展史等角度做出了較為系統的嘗試。書中還論述了作者提出的“語言世界觀多元論”“語言的體認起源”“認知語言學的核心原則”,且詳細剖析了“認知過程”(有助于理解物質如何決定精神)。認知語言學批判了索氏和喬氏的語言任意觀,強調語言的像似性,本書認為,語言的體認性正可為像似性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本書還關注了中國古代學者留給我們的寶貴文化遺產,專辟一章論述了伏羲、周文王和荀子等人的相關觀點。書中從第10章開始運用“體認原則”較為詳細地剖析了語言的語音、詞法、句法、話語、修辭等層面的具體情況。這一方面可為語言提出一個統一的解釋方案;另一方面也為語言教學提供了全新的教學方法,以能實現理論緊密結合實踐的科研方向。
體認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的本土化研究 目錄
**章 后現代哲學視野下的體認語言學
**節 概述
第二節 體認語言學之我見
1.術語的模糊性
2.“體認”的全面性
3.體認的基礎性
4.體認語言學的前衛性
5.語哲的延續性
6.體認一元性
7.語言與哲學的共生性
8.體認語言學的發展性
9.體認語言學的體系性
10.體認語言學的應用性
第三節 體認一元觀
1.一元與二元之爭
2.19至20世紀:對二元論的反思與批判
3.體認原則
……
體認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的本土化研究 相關資料
從“某種語言學”觀照體認語言學的理論性“某種語言學”意味著:①一種理論的標簽;②該理論與其他理論有別。繼而,我們可以推斷:這種理論應是以某種語言的事實為基礎的(即受限的),不可能有某種理論是建立在人類所有語言的事實的基礎上的;這種理論對語言研究具有一定價值(但也是受限的),不可能有某種理論對人類所有語言的事實都具有同樣的普遍價值。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推測:在該理論的背后,即在其提出者的語言觀的背后,可能存在某種哲學思想作為支撐。換言之,當我們說“某種語言學”時,指的是一種可能基于某種哲學思想、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普遍價值的語言學理論。1. 歐洲語言研究的傳統術語1777年以前,歐洲學者稱其語言研究主要來自古希臘的兩個術語。一個是grámmatiké(即讀寫知識,通常譯為“文法學/語法學”),該詞來自grámmatikós(即讀寫者),而其中的grámmat(即字母)來自gram(即書寫)。Dionysius Thrax(公元前170—公元前90)的Téchnē Grámmatiké(《讀寫技藝》,亦譯為《文法技藝》)被視為歐洲語法學原典。另一個術語是philologia(通常譯為“語文學”)。公元前3世紀,古希臘學者對亞歷山大里亞圖書館收藏的書稿進行研究,并將這種活動稱為“philologia”(philo 愛好 logia語言知識)。Eratosthenes of Cyrene(公元前274—公元前194)曾經擔任亞歷山大里亞圖書館的館長,他也是最早自稱“philologos”(語文學家)的學者。這兩個術語都與語言研究相關,但grámmatiké與“讀寫”的關系更密切,而philologia與“文獻”的關系更密切。盡管不同學者的研究各有側重,但19世紀以前的歐洲語法學或語文學就已經囊括了語言研究的方方面面(邱雪玫、李葆嘉,2020)。1574年,日內瓦大學教授B. C. Bertram(1531—1594)在《希伯來語和阿拉米語的比較語法》中已經使用了“比較語法”(comparatio grammaticæ)一詞。17世紀時,盡管荷蘭學派中語言親緣比較的理論和方法(Boxhorn,1654)已經成熟,但是“比較語法”并未得到正式定名。直到19世紀初,比較解剖學風靡一時,德國學者才為這門學科加冕。首先是J. S. Vater(1771—1826)在《試論普通語法學》(1801)中提出應建立“比較語法”(vergleichende Sprachlehre),兼指親緣比較和結構對比;之后,A. W. von Schlegel(1767—1845)在《本哈迪〈語法學〉評校》(1803)中提出專指語言親緣關系的“比較語法”(vergleichende Grammatik);再后來,F. von Schlegel(1772—1829)在《論印度人的語言和智慧》(1808)中沿用了其兄 A. W. von Schlegel 的術語。德裔俄國學者 F. von Adelung(1768—1843)在《凱瑟琳大帝對比較語言學的重要貢獻》(1815)中最早使用了“比較語言學”(vergleichende Sprachenkunde)這一術語,德裔英國學者 F. M. Müller(1823—1900)則在《論印歐語比較語文學與人類早期文明的關系》(1849)中最早使用了“比較語文學”(Comparative Philology)這一術語。2. Linguistik 的出現和傳播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一大批記錄異邦語言的字母表、詞表、語法書和會話手冊等紛紛面世。1777年,奧地利神父J. M. Denis(1729—1800)創造了“Linguistik”(語言學)這一術語:“德文的語言學(Sprachenkunde)或拉丁文的語言學(Linguistik)包括以下書籍:①關于語言術語的小冊子或論文;②關于文字和字母圖形的小冊子或論文;③語言教材或語法書;④詞典或字典”(Denis,1777:274)。1808 年,該術語出現在J. S. Vater 主編的《民族志和語言學總體檔案》中,Auroux(1987:450)指出,當時對“Linguistik”的定義是:“調研不同語言的特點,對之進行分類……并從中推斷其譜系和親緣關系。”1812年,法語史學家A. G. Henry(1753—1835)在《法蘭西語言史》中兩次使用了“語言學”(Linguistique)這一術語;1826年,意大利裔法國學者A. Balbi(1782—1848)在《全球民族志地圖集導論》中使用了該詞;1827年,Par Quatre Professeurs de L’université編撰的《法語經典詞典》將“Linguistique”這一詞條收錄其中,釋義為“語言的科學”(Science des Langues)。根據Auroux(1987)的考證,以上這些線索表明法語已經從德語中接受了“語言學”這一術語。英語也同樣接受了這一術語,具體線索包括:①linguistic(adj.)最早見于1824年,其義為“關于語言研究的”,來自德語的 linguistisch(1807);②linguistics(n.)最早見于1847年,其義為“語言的科學”。3. 給“語言學”加限定詞1801—1803年,德國語言學家Bernhardi(1768—1820)的專著《語法學》出版,其中第一卷名為“純粹語法學”(Reine Sprachlehre),第二卷名為“應用語法學”(Angewandte Sprachlehre)。這樣的劃分方式顯然是受到了數學家的啟發。1870年,波—俄語言學家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在彼得堡大學開設“語言學導論”課程,他在講稿《關于語言學和語言的若干原則性看法》中提出:“首先,很有必要區分純粹語言學(чистое языковедение)與應用語言學(прикладного языковедения)。前者即語言學自身,其主題是把語言自身視為某種同質性事實的概括,將之歸因于所謂人類生活表征范疇的普遍性;后者的主題則是把純粹語言學的資料應用于其他學科領域。”(Куртенэ,1963a:62)18世紀以前,語言學研究主要與文獻學、歷史學、民族學交融在一起。而19世紀時,語言研究先后受到生物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的影響,這表明語言學家逐步認識到語言的生物性、心理性和社會性。例如,德國語言學家W. von Humboldt(1767—1835)認為語言具有一切有機體的本性;其友人F. Bopp(1791—1867)也贊同語言有機體學說;K. F. Becker(1775—1849)著有《語言的有機體:德語語法引論》一書;Bopp的學生Müller發展了語言有機體學說;A. Schleicher(1821—1868)更自認為是von Humboldt 學說的繼承人,他提出了語言研究的自然主義。盡管這些學者的理論觀點可被視為“第一代生物語言學”,但他們都沒有為自己貼上“生物語言學”的標簽。1950年,美國科學家C. L. Meader和J. H. Muyskens的《生物語言學手冊》中第一次出現了“生物語言學”(Biolinguistics)這一術語。德國心理學家H. Steinthal(1823—1899)在《語法、邏輯和心理》(1855)及《心理學和語言學導論》(1871)兩部著作中,深入地探討了歷史、心理、民族與語言之間的關系,建立了基于心理的語言學理論。他的理論觀點可謂“第一代心理語言學”,但他也沒有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新的術語名稱。Steinthal的追隨者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在《語言科學的任務》(1889)中指出:“語言的基礎純粹是心理的(即大腦中樞的),因此語言學應歸結為心理科學。然而,由于語言只能在社會中實現,并且由于個體心智通常只能在與他人的交往中得到發展,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語言學是心理—社會科學”(Куртенэ,1963a:217)。1903年,奧地利心理學家O. Dittrich(1865—1951)在《語言心理學基礎》中使用了“語言心理學”(Sprachpsychologie)。1936 年,美國心理學家J. R. Kantor(1888—1984)在《語法的客觀心理學》中使用了“心理語言學”(Psycholinguistics)。受法國社會學家D. É. Durkheim(1858—1917)的影響,法國語言學家A. Meillet(1866—1936)在《普通語言學的研究現狀》中指出,“由于語言是一種社會制度,因此語言學就是一門社會科學,并且可以用來解釋語言變化的唯一可變因素就是社會變化”(Meillet,1906:307)。1909年,G. de La Grasserie(1839—1914)發表了《論語言社會學》,文中使用了“sociologie linguistique”這一術語。1910年,A. Dauzat(1877—1955)在《語言的生命》中闡述了Meillet的學說,并提出了“社會語言學”(linguistique sociale)這一術語。20世紀時,隨著linguistics這一術語的不斷傳播,19世紀通稱的“比較語法”“比較語文學”有了新的名稱:1924年,丹麥語言學家O. Jespersen(1860—1943)在《語法哲學》中使用了“比較和歷史語言學”(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1941年,美國語言學家B. L. Whorf(1897—1941)在《語言與邏輯》中明確了“比較語言學”(Comparative Linguistics)和“對比語言學”(Contrastive Linguistics)之間的區別。
從“某種語言學”觀照體認語言學的理論性“某種語言學”意味著:①一種理論的標簽;②該理論與其他理論有別。繼而,我們可以推斷:這種理論應是以某種語言的事實為基礎的(即受限的),不可能有某種理論是建立在人類所有語言的事實的基礎上的;這種理論對語言研究具有一定價值(但也是受限的),不可能有某種理論對人類所有語言的事實都具有同樣的普遍價值。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推測:在該理論的背后,即在其提出者的語言觀的背后,可能存在某種哲學思想作為支撐。換言之,當我們說“某種語言學”時,指的是一種可能基于某種哲學思想、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普遍價值的語言學理論。1. 歐洲語言研究的傳統術語1777年以前,歐洲學者稱其語言研究主要來自古希臘的兩個術語。一個是grámmatiké(即讀寫知識,通常譯為“文法學/語法學”),該詞來自grámmatikós(即讀寫者),而其中的grámmat(即字母)來自gram(即書寫)。Dionysius Thrax(公元前170—公元前90)的Téchnē Grámmatiké(《讀寫技藝》,亦譯為《文法技藝》)被視為歐洲語法學原典。另一個術語是philologia(通常譯為“語文學”)。公元前3世紀,古希臘學者對亞歷山大里亞圖書館收藏的書稿進行研究,并將這種活動稱為“philologia”(philo 愛好 logia語言知識)。Eratosthenes of Cyrene(公元前274—公元前194)曾經擔任亞歷山大里亞圖書館的館長,他也是最早自稱“philologos”(語文學家)的學者。這兩個術語都與語言研究相關,但grámmatiké與“讀寫”的關系更密切,而philologia與“文獻”的關系更密切。盡管不同學者的研究各有側重,但19世紀以前的歐洲語法學或語文學就已經囊括了語言研究的方方面面(邱雪玫、李葆嘉,2020)。1574年,日內瓦大學教授B. C. Bertram(1531—1594)在《希伯來語和阿拉米語的比較語法》中已經使用了“比較語法”(comparatio grammaticæ)一詞。17世紀時,盡管荷蘭學派中語言親緣比較的理論和方法(Boxhorn,1654)已經成熟,但是“比較語法”并未得到正式定名。直到19世紀初,比較解剖學風靡一時,德國學者才為這門學科加冕。首先是J. S. Vater(1771—1826)在《試論普通語法學》(1801)中提出應建立“比較語法”(vergleichende Sprachlehre),兼指親緣比較和結構對比;之后,A. W. von Schlegel(1767—1845)在《本哈迪〈語法學〉評校》(1803)中提出專指語言親緣關系的“比較語法”(vergleichende Grammatik);再后來,F. von Schlegel(1772—1829)在《論印度人的語言和智慧》(1808)中沿用了其兄 A. W. von Schlegel 的術語。德裔俄國學者 F. von Adelung(1768—1843)在《凱瑟琳大帝對比較語言學的重要貢獻》(1815)中最早使用了“比較語言學”(vergleichende Sprachenkunde)這一術語,德裔英國學者 F. M. Müller(1823—1900)則在《論印歐語比較語文學與人類早期文明的關系》(1849)中最早使用了“比較語文學”(Comparative Philology)這一術語。2. Linguistik 的出現和傳播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一大批記錄異邦語言的字母表、詞表、語法書和會話手冊等紛紛面世。1777年,奧地利神父J. M. Denis(1729—1800)創造了“Linguistik”(語言學)這一術語:“德文的語言學(Sprachenkunde)或拉丁文的語言學(Linguistik)包括以下書籍:①關于語言術語的小冊子或論文;②關于文字和字母圖形的小冊子或論文;③語言教材或語法書;④詞典或字典”(Denis,1777:274)。1808 年,該術語出現在J. S. Vater 主編的《民族志和語言學總體檔案》中,Auroux(1987:450)指出,當時對“Linguistik”的定義是:“調研不同語言的特點,對之進行分類……并從中推斷其譜系和親緣關系。”1812年,法語史學家A. G. Henry(1753—1835)在《法蘭西語言史》中兩次使用了“語言學”(Linguistique)這一術語;1826年,意大利裔法國學者A. Balbi(1782—1848)在《全球民族志地圖集導論》中使用了該詞;1827年,Par Quatre Professeurs de L’université編撰的《法語經典詞典》將“Linguistique”這一詞條收錄其中,釋義為“語言的科學”(Science des Langues)。根據Auroux(1987)的考證,以上這些線索表明法語已經從德語中接受了“語言學”這一術語。英語也同樣接受了這一術語,具體線索包括:①linguistic(adj.)最早見于1824年,其義為“關于語言研究的”,來自德語的 linguistisch(1807);②linguistics(n.)最早見于1847年,其義為“語言的科學”。3. 給“語言學”加限定詞1801—1803年,德國語言學家Bernhardi(1768—1820)的專著《語法學》出版,其中第一卷名為“純粹語法學”(Reine Sprachlehre),第二卷名為“應用語法學”(Angewandte Sprachlehre)。這樣的劃分方式顯然是受到了數學家的啟發。1870年,波—俄語言學家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在彼得堡大學開設“語言學導論”課程,他在講稿《關于語言學和語言的若干原則性看法》中提出:“首先,很有必要區分純粹語言學(чистое языковедение)與應用語言學(прикладного языковедения)。前者即語言學自身,其主題是把語言自身視為某種同質性事實的概括,將之歸因于所謂人類生活表征范疇的普遍性;后者的主題則是把純粹語言學的資料應用于其他學科領域。”(Куртенэ,1963a:62)18世紀以前,語言學研究主要與文獻學、歷史學、民族學交融在一起。而19世紀時,語言研究先后受到生物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的影響,這表明語言學家逐步認識到語言的生物性、心理性和社會性。例如,德國語言學家W. von Humboldt(1767—1835)認為語言具有一切有機體的本性;其友人F. Bopp(1791—1867)也贊同語言有機體學說;K. F. Becker(1775—1849)著有《語言的有機體:德語語法引論》一書;Bopp的學生Müller發展了語言有機體學說;A. Schleicher(1821—1868)更自認為是von Humboldt 學說的繼承人,他提出了語言研究的自然主義。盡管這些學者的理論觀點可被視為“第一代生物語言學”,但他們都沒有為自己貼上“生物語言學”的標簽。1950年,美國科學家C. L. Meader和J. H. Muyskens的《生物語言學手冊》中第一次出現了“生物語言學”(Biolinguistics)這一術語。德國心理學家H. Steinthal(1823—1899)在《語法、邏輯和心理》(1855)及《心理學和語言學導論》(1871)兩部著作中,深入地探討了歷史、心理、民族與語言之間的關系,建立了基于心理的語言學理論。他的理論觀點可謂“第一代心理語言學”,但他也沒有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新的術語名稱。Steinthal的追隨者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在《語言科學的任務》(1889)中指出:“語言的基礎純粹是心理的(即大腦中樞的),因此語言學應歸結為心理科學。然而,由于語言只能在社會中實現,并且由于個體心智通常只能在與他人的交往中得到發展,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語言學是心理—社會科學”(Куртенэ,1963a:217)。1903年,奧地利心理學家O. Dittrich(1865—1951)在《語言心理學基礎》中使用了“語言心理學”(Sprachpsychologie)。1936 年,美國心理學家J. R. Kantor(1888—1984)在《語法的客觀心理學》中使用了“心理語言學”(Psycholinguistics)。受法國社會學家D. É. Durkheim(1858—1917)的影響,法國語言學家A. Meillet(1866—1936)在《普通語言學的研究現狀》中指出,“由于語言是一種社會制度,因此語言學就是一門社會科學,并且可以用來解釋語言變化的唯一可變因素就是社會變化”(Meillet,1906:307)。1909年,G. de La Grasserie(1839—1914)發表了《論語言社會學》,文中使用了“sociologie linguistique”這一術語。1910年,A. Dauzat(1877—1955)在《語言的生命》中闡述了Meillet的學說,并提出了“社會語言學”(linguistique sociale)這一術語。20世紀時,隨著linguistics這一術語的不斷傳播,19世紀通稱的“比較語法”“比較語文學”有了新的名稱:1924年,丹麥語言學家O. Jespersen(1860—1943)在《語法哲學》中使用了“比較和歷史語言學”(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1941年,美國語言學家B. L. Whorf(1897—1941)在《語言與邏輯》中明確了“比較語言學”(Comparative Linguistics)和“對比語言學”(Contrastive Linguistics)之間的區別。
體認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的本土化研究 作者簡介
王寅,四川外國語大學語言哲學研究中心主任、資深教授,國家二級教授,現任中西語言哲學研究會會長。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語言哲學、認知語言學、體認語言學、英漢對比等。共出版專著和教材40多部,發表論文300多篇。曾主持過三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三項省級社科項目,其中一項為省級重點項目,并有十幾項成果獲獎。
主要代表作品有:《認知語言學》《語言哲學研究一一21世紀中國后語言哲學沉思錄》《語義理論與語義教學》《構式語法研究》《中西語義理論對比研究》《語義符號象似性》《語義學辭典》《西哲第四轉向的后現代思潮一一探索世界人文社科之前沿》等。
- >
史學評論
- >
月亮虎
- >
羅庸西南聯大授課錄
- >
苦雨齋序跋文-周作人自編集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
- >
大紅狗在馬戲團-大紅狗克里弗-助人
- >
伯納黛特,你要去哪(2021新版)
- >
詩經-先民的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