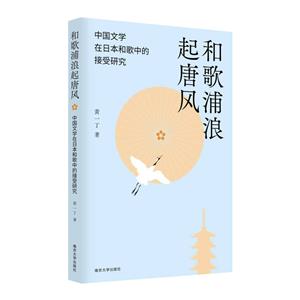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和歌浦浪起唐風 中國文學在日本和歌中的接受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5273278
- 條形碼:9787305273278 ; 978-7-305-27327-8
- 裝幀:平裝-膠訂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和歌浦浪起唐風 中國文學在日本和歌中的接受研究 內容簡介
和歌是日本獨有的文學形式,歷來被日本人視為其民族文學中*核心的詩歌體裁。它對后世日本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甚至直接決定了日本民族的文學審美基調。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日本民族文學的和歌,在其起源與發展過程中始終受到中國文學的持續影響。中國文學的影響貫穿了和歌發展的始終,并在其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本書聚焦的《古今集》至《新古今集》時代,是和歌發展史上*為重要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和歌作品不僅是日本文學的核心組成部分,也堪稱東亞“漢文化圈”文學的瑰寶。該時期大約對應中國的五代十國至南宋時期,在該時期的和歌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中國六朝至唐代文學的影子。本書詳細梳理了中國文學進入日本文學后,與日本文學相互碰撞所激發的火花,旨在拋磚引玉,期待更多學者投身于中國文學對海外文學的影響研究中。
和歌浦浪起唐風 中國文學在日本和歌中的接受研究 目錄
目 錄
序論 001
**節 中華文明對日本文學的影響 001
第二節 日本古典文學與中日比較文學的三段論 004
第三節 中國古代文學影響的日本化 010
第四節 “國風文化”時代的歷史背景 012
**章 “國風文化”時代文學思辨 020
**節 “唐風文化”的特征與歷史背景 020
第二節 “國風文化”的歷史背景與對“唐風文化”
的繼承 024
第三節 “國風文化”時代的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學 028
第二章 中國古代文學對“國風文化”時代前和歌的影響 035
**節 《萬葉集》與中國古代文學關系綜述 035
第二節 《萬葉集》文學史斷代與中國古代文學的
日本化 038
第三節 《萬葉集》的文學遺產與其后的和歌斷層 049
第三章 和歌與中國古代文學體裁的日本化 051
**節 中國古代文學體裁的日本化與句題和歌 052
第二節 句題和歌史斷代與歷史背景 054
第三節 句題和歌與中國古代文學表達的接受 060
第四節 句題和歌與典故的接受 065
第五節 句題和歌與文化觀念的接受 069
第六節 中國古代文學對《千里集》中四季部結構的
影響 073
第七節 《千里集》之后半部分與中國古代文學 092
本章結語 099
第四章 中國古代文學意象對“國風文化”時代和歌的
影響機制 101
**節 中國古代文學與和歌意象的產生 101
第二節 和歌中菊花意象的產生與中國古代文學
意象的影響 104
第三節 菊花的長生不老意象與中國古代文學的
影響 108
第四節 菊花意象在戀愛和歌中的流變現象 117
第五節 元稹詩對菊花意象的再影響 124
本章結語 126
第五章 中國典故的日本化對和歌文學的影響 128
**節 典故運用于“國風文化”和歌中的普遍性 128
第二節 中國文獻影響與和歌中的祥瑞之龜 131
第三節 中國祥瑞意識的影響與長壽之龜 135
第四節 中國祥瑞意識在典故中的流變 140
第五節 中國典故的日本化與和歌中的蓬萊山傳說 142
第六節 中國典故的流變與積土成山典故 146
第七節 《法華經》“盲龜浮木”典故在和歌中的影響 149
第八節 “盲龜浮木”典故在和歌中的流變 154
第九節 曳尾涂中典故對日本文學的影響 158
本章結語 160
第六章 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日本化 161
**節 《千五百番歌合》判詞與和歌判詩 162
第二節 和歌物候觀的中日文學依據 166
第三節 物候觀的日本化現象 172
第四節 和歌判詩中所見中日物候觀的融合 182
本章結語 193
第七章 歌合活動與中國文學日本化 197
**節 《陽成院歌合》的背景 198
第二節 白居易詩對《陽成院歌合》的影響 203
第三節 漢語“虛度”“空度”對《陽成院歌合》的影響206
第四節 惜春詩表達的流變 210
本章結語 216
第八章 “逆國風化”芻議 219
**節 日本惜秋文學之源流與傳統 221
第二節 惜秋文學的“逆國風化”與中國典故 224
第三節 惜秋文學的“逆國風化”與中國文學物候觀 230
第四節 惜秋文學的“逆國風化”與中國惜春文學 238
本章結語 242
本書結語 244
后記 247
和歌浦浪起唐風 中國文學在日本和歌中的接受研究 節選
試 讀
**章“國風文化”時代文學思辨
日本平安時代(794—1192)的文化史往往以公元900年左右為分水嶺,將整個平安時代劃分為前后兩個不同的時代,即自桓武天皇遷都至平安京至公元9世紀后半葉的“唐風文化(弘仁貞觀文化)”時代,與公元900年以后開始的“國風文化(攝關文化)”時代。而11世紀后半葉開始的“院政期文化”與此后的“鐮倉文化”均脫胎于“國風文化”,特別是在和歌文學中,院政期與鐮倉時代的和歌文學發展與“國風文化”時代的和歌一脈相承,不可分割,因此自平安中期至鐮倉時代結束,和歌文學的審美傾向都屬于廣義的“國風文化”。本章從文學史的角度對“國風文化”時代的日本文學作品進行梳理,旨在明確“國風文化”時代文學作品的基本文化屬性。
**節
“唐風文化”的特征與歷史背景
在“唐風文化”時代,日本朝廷延續了奈良時代的外交傳統,在繼續向唐朝派遣遣唐使與留學生(僧)的同時,還積極吸納唐代文化,以此為契機,長安的方音、以白居易為代表的中唐詩歌、以真言宗與天臺宗為代表的唐代佛教等新文化在這個時期進入日本,并扎下根基,為日后日本平安中后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試 讀
**章“國風文化”時代文學思辨
日本平安時代(794—1192)的文化史往往以公元900年左右為分水嶺,將整個平安時代劃分為前后兩個不同的時代,即自桓武天皇遷都至平安京至公元9世紀后半葉的“唐風文化(弘仁貞觀文化)”時代,與公元900年以后開始的“國風文化(攝關文化)”時代。而11世紀后半葉開始的“院政期文化”與此后的“鐮倉文化”均脫胎于“國風文化”,特別是在和歌文學中,院政期與鐮倉時代的和歌文學發展與“國風文化”時代的和歌一脈相承,不可分割,因此自平安中期至鐮倉時代結束,和歌文學的審美傾向都屬于廣義的“國風文化”。本章從文學史的角度對“國風文化”時代的日本文學作品進行梳理,旨在明確“國風文化”時代文學作品的基本文化屬性。
**節
“唐風文化”的特征與歷史背景
在“唐風文化”時代,日本朝廷延續了奈良時代的外交傳統,在繼續向唐朝派遣遣唐使與留學生(僧)的同時,還積極吸納唐代文化,以此為契機,長安的方音、以白居易為代表的中唐詩歌、以真言宗與天臺宗為代表的唐代佛教等新文化在這個時期進入日本,并扎下根基,為日后日本平安中后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政治上,模仿中國政治制度建立的律令制度在該時代日臻成熟,達到了*穩定的巔峰期。值得注意的是,下令遷都平安京的桓武天皇本身就具有大陸渡來人的血統,而其遷都平安京的根本目的也在于排除平城京(今奈良)既存的舊貴族舊宗教勢力,將統治中心轉移到歷來渡來人勢力強大的山背國地區,以之為新都,這顯示出桓武天皇親近大陸勢力的政治姿態。除此之外,中國傳統政治制度中受到中國傳統宗教影響而產生的“郊祭”制度在“唐風文化”時代初期也開始影響日本政治,桓武天皇在重新修整伊勢神宮的同時,還于平安京以南的河內國(今大阪一帶)舉行了類似“郊祭”的祭祀活動,此后,還將自己的父親光仁天皇以昊天上帝的身份進行祭祀,這些政治活動無一不顯示出“唐風文化”時代日本政壇對大陸文化的憧憬。究其根源,壬申之亂時更一度迭至天武系的皇統,幾經波折,終于在光仁天皇時又回歸到天智系一側,而統治根基未穩的桓武天皇自然要采取新的意識形態來鞏固自身統治,壬申之亂中敗北的大友皇子對中國文化頗為憧憬,這從奈良時代編纂的漢詩集《懷風藻》中收錄的大友皇子的詩作就可窺見一斑,天智系皇族對大陸文化理應保有較強的親近感,而此時盛唐中唐時期產生的絢爛文化又源源不斷地輸送到日本列島,這樣的外來先進文化天然地成為天智系新政權構建意識形態與文化統治的不二選擇。
桓武天皇后,平城京舊貴族保守勢力依舊強大,他們以平城天皇為政治核心,與以嵯峨天皇為代表的新貴族勢力展開了激烈的政治斗爭,其中以“平城太上天皇之變”(又稱藥子之變)*具代表性。平城天皇退位后成為太上天皇,在舊都平城京另立中央政權,*后甚至下令廢止平安京,在嵯峨天皇的武力圍剿下,平城天皇引咎出家,尚侍藤原藥子被剝奪官位,而原本在嵯峨天皇后有望繼承皇位的平城天皇之子高岳親王也被廢黜太子之位,皇位失去了在平城與嵯峨兩統間迭立的可能性。“平城太上天皇之變”以嵯峨天皇方的勝利而終結,這一歷史事件標志著平安京新貴族徹底穩固了政權,而為其后數十年“唐風文化”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此后,在文化的諸多方面,日本社會都顯示出了濃厚的中國特色。
宗教上,“南都六宗”在奈良時代的平城京擁有強大勢力,進入平安時代后,其勢力開始逐漸衰弱,取而代之的則是真言宗與天臺宗的平安二宗,在“平城太上天皇之變”中,這兩宗的勢力倒向嵯峨天皇一方,以此為契機,平安二宗成為日本朝廷認可的主流佛教宗派。天臺宗的開祖*澄入唐求法,甚至在入唐前已經是當時日域知名僧人。真言宗的開祖弘法大師空海曾隨*澄一道入唐求法,*澄原以弟子之禮相待,空海在學習中國先進的佛教文化后,與*澄的宗教思想出現分歧,創立了真言密教,日后成為日本佛教史與文化史上*重要的僧人之一。可以說平安二宗的誕生及繁榮與“唐風文化”時代的政治背景緊密相關。
美術上,平安二宗在帶來佛教思想的同時,還為日本列島帶來了絢爛多彩的佛教美術,形成了美術史上定義的“貞觀美術”(貞觀美術)。這一時代的曼陀羅與佛教造像吸收了大量源于大陸的藝術表現技法,體現出濃厚的大陸文化特征,成為該時代美術史上*顯著的特色。
語言上,平安時代以前傳入日本列島的漢字音被稱為“吳音”。漢字傳入日本列島至奈良時代為止的較長一段歷史時期內,“吳音”的性質本身也是多源的:有的源于傳入朝鮮半島的漢字音,有的源于上古漢字音末期的南朝方音。而進入平安時代以后,日本貴族開始集中系統地學習屬于中古漢字音的長安方音,以此為基礎形成了“漢音”。吳音與漢音在音韻上的對立是十分顯著的。該現象體現出平安初期漢字音的更新。
書法上,“唐風文化”時代的書法在理念上以尊重中國書法,特別是晉唐風為要義,并孕育出以模仿中國書法晉唐風特色見長的“日本三筆”,即空海、嵯峨天皇以及橘逸勢。其中空海受到王羲之與顏真卿書法的影響較大,而嵯峨天皇又受到了空海風格的影響,橘逸勢相傳在渡唐期間學習書法,其受到了唐代書法的巨大影響應是不爭的事實。書法方面亦能體現出“唐風文化”時代中國文化在日域的盛行。
在本書所聚焦的文學方面,“唐風時代”的文學更加凸顯出強烈的中國古代文學特征。在體裁上,以漢語文言文書寫的中國詩取代了自古墳時代開始的和歌,成為日本宮廷文學的主流。在文學思想上,嵯峨天皇下令編纂敕撰漢詩集《凌云集》,于日域踐行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文章經國”思想,實現其政治抱負,同時還開創了日本朝廷敕撰詩歌集的先河,成為數百年間層出不窮的敕撰文學之濫觴。而后編纂的《文華秀麗集》以及《經國集》亦是中國古代文學“文章經國”思想影響下的產物。如前文所述,以小島憲之為代表的日本文學學者甚至將“唐風文化”時代稱為“國風暗黑時代”,這一稱呼足以體現該時代日本傳統文學在發展上的蟄伏與中國古代文學體裁在日域的繁榮。“唐風文化”時代的一系列文學現象體現出儒家思想中的文學政治化理念已經影響日本,并對日本政治與文學產生了巨大的改造。
總體來說,在天智系的光仁—桓武皇統掌握政權的背景下,平安京的新貴族為鞏固文化統治,采取了積極吸收唐代先進文化的策略,在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走上了模仿唐朝文化的道路。這樣的現象與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社會全盤西化、脫亞入歐的場景頗為相似。事實上,在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傾倒于某一外國文化的現象,在日本歷史上似乎十分普遍,例如奈良時代的“天平文化”與平安時代的“唐風文化”皆出自對中國文化的憧憬,近代的明治維新源于日本民族對西方文明的崇拜,戰后的諸多思潮則體現出日本民族對發達的美國現代文化之推崇。了解到這樣的歷史事實,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日本文化形成的特點與規律。
第二節
“國風文化”的歷史背景與對“唐風文化”的繼承
嵯峨天皇退位后讓位于其弟淳和天皇,并持續以太上天皇的身份控制著朝廷實權。公元842年,嵯峨上皇駕崩后,其長達三十余年的安定統治畫上句號,隨之而來的是嵯峨天皇之子仁明天皇。他與新貴族藤原氏聯手,一舉消滅了淳和天皇之子,以及當時擁有皇太子身份的恒貞親王勢力,史稱“承和之變”。至此,正如“平城太上天皇之變”中嵯峨天皇一方的勝利避免了兩個皇統之間的迭立一般,仁明天皇與藤原氏北家在“承和之變”中的勝利同樣避免了嵯峨與淳和皇統的兩統迭立,此后的文德、清和以及陽成天皇三代,皇位均安穩地掌握在嵯峨—仁明皇統的皇族手中。安定的政治環境則為持續的文化政策提供了安定的土壤,自嵯峨天皇至陽成天皇,日本繼續派遣遣唐使,不斷學習中國大陸的先進文化,“唐風文化”時代得以持續。然而,自飛鳥時代開始至“唐風文化”時代結束,正如序章中所述,大量源自中國的政治制度與文化藝術漸漸表現出水土不服,其與日本社會實際之間的矛盾齟齬日益凸顯,舊的文化政策亟須新的文化政策替代。
新政策的政治契機源于陽成天皇的幼年即位與藤原氏北家的內部斗爭。自“承和之變”,藤原氏北家的勢力開始抬頭,依靠自身外戚的身份逐漸凌駕于其他貴族之上,到陽成天皇即位時,陽成天皇之母藤原高子成為皇太后,而高子之兄藤原基經亦被淳和上皇委任為攝政,權傾朝野。然而,基經與其妹高子之間不和,藤原氏北家的內部斗爭逐漸演變為日本朝廷的政治斗爭,其結果便是,公元884年,陽成天皇成為基經與高子政治斗爭的犧牲品,被迫讓位于祖父輩的仁明天皇之子光孝天皇,成為太上天皇,自此,天皇皇統再次發生更迭,由文德系變為光孝系。55歲高齡即位的光孝天皇4年后駕崩,而基經與高子的不和再次左右了繼承皇位的人選,光孝天皇生前將自己的子嗣全部降為臣籍,以表明身后將皇位歸還至清和天皇之子、陽成天皇之弟貞保親王的意圖,然而,貞保親王與陽成天皇同出于高子之腹,為遏制高子的政治勢力,基經及其朝中擁躉不惜將已經降為臣籍的光孝天皇之子源定省推上皇位,是為宇多天皇。宇多天皇即位后不久在基經就任關白的問題上又與之發生了矛盾,史稱“阿衡紛爭”。這一系列的政治事件表明,直到基經去世,光孝—宇多皇統都沒有牢固地掌握朝廷實權。公元891年基經去世,宇多天皇終于迎來親政的機會。至此,從桓武天皇以來的文化政策也出現了轉變的契機。
宇多天皇在位期間,和歌文學逐漸通過“歌合”(即具有競爭性、定勝負的歌會)的形式回歸至宮廷文學中,并留下了一批成書于該時代的歌合文獻。此外,公元630年以來持續了250多年的遣唐使制度在宇多天皇時期被廢止。雖然廢止遣唐使有晚唐時期中國社會動蕩、經濟凋敝的外在原因,但宇多天皇親政后在文化政策上急于探索新的思路,是廢止遣唐使的內在原因。這一系列現象表明,在光孝—宇多皇統的統治下,日本朝廷的新文化政策正在逐漸形成。公元897年,宇多天皇退位,其子醍醐天皇即位。901年,醍醐天皇為掃清父親宇多太上天皇等舊政治勢力,選擇了與藤原氏北家聯盟,與適時的重臣基經之子時平合謀將父親的寵臣——菅原道真流放出京,之后又敕令編纂假名文學《古今和歌集》,與此同時,醍醐天皇還對律令制度的實施細則進行了修正與重編,在嵯峨天皇的《弘仁格》與《弘仁式》以及清和天皇的《貞觀格》與《貞觀式》的基礎上,編纂了《延喜格》與《延喜式》,從而進一步規范朝廷的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以鞏固自身的統治穩定。此外,醍醐天皇還下令繼續編纂因宇多天皇退位而中斷的正史《日本三代實錄》,以彰顯光孝—宇多皇統在皇統更迭歷史中的正統性。自宇多天皇至醍醐天皇的這一連串歷史事件釋放出重要的政治信號——醍醐天皇統治集團的文化政策或將有別于自桓武天皇以來注重中國文化的傾向,而轉為弘揚本土文化。
此后的文學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這一觀點。公元900年以后,以假名為文字、用大和語言書寫的假名文學開始出現,在詩歌文學方面,自宇多天皇時期開始復興的和歌文學在經歷了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的高光時刻后并沒有停下發展的腳步,逐漸成為公元10世紀日本宮廷文學的主流。而在敘事文學方面,以假名書寫的日記文學與物語文學開始出現,并依托后宮的女性在宮廷內廣泛傳播,成為深受平安貴族喜愛的文學形式。基于這樣的文學現象,自20世紀30年代起,日本的古典文學研究界出現了解釋平安時代文學的基本理論“國風文化”論,以之為基礎,又結合戰后小島憲之的“國風暗黑時代”學說,從而形成了“唐風文化—國風文化”論。這一理論不僅在文學研究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在日本文化史、工藝美術史等領域亦為通行理論。“唐風文化—國風文化”論以公元9世紀末至10世紀初的數十年為分水嶺,將平安時代文化史劃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即崇尚中華文化的“唐風文化”時代與注重日本本土文化的“國風文化”時代,對此本章開頭一段已有敘述。
事實上,在平安文學研究領域,日本文學的學者們已經證實,“國風文化”時代產生的假名文學中的確存在著諸多中國古代文學要素,然而,這些論據并沒有被系統地組織起來用于反駁“國風文化”論。“國風文化”存在于平安時代文學的基本論據主要是假名文學的誕生與流行。通過在平安時代的假名文學中找到的為數眾多的中國古代文學要素,可以探明其在早期假名文學的誕生與流變中所起到的具體作用,可更加接近所謂“國風文化”時代文學的真相以及本質。如上文所述,假名文學主要包含和歌、物語、日記等文學體裁。根據現有的研究,這些文學體裁中存在著大量中國古代文學要素已是不爭的事實。
第三節
“國風文化”時代的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學
現存*早的和歌文學是日本古墳時代天皇所詠的和歌,但不能排除這些和歌為后世附會的可能性,但至少在飛鳥時代,和歌文學就已經成為日本朝廷的主流宮廷文學形式,并出現一批宮廷文學的御用歌人。自古墳時代到奈良時代數百年間的和歌文學都收錄于《萬葉集》中,但我們有理由相信,除了收錄于《萬葉集》的四千余首和歌,還有更多的產生于該時代的和歌已經散佚于歷史長河之中。《萬葉集》時代產生的和歌中就已經可以窺見許多中國古代文學的影響,這一問題我們將作為“國風文化”時代文學的前奏在第二章中進行系統探討。《萬葉集》中收錄的和歌在奈良時代中期戛然而止,此后的一百多年間或許存在過一些記錄和歌的文獻,但現今皆不存于世,究其原因,正是“唐風文化”造就了一個“國風文化”的“暗黑時代”,因此,“國風文化”時代伊始的和歌,面臨的是和歌已經式微一百多年的局面,而這樣的“國風文化”斷層就決定了“國風文化”時代伊始的和歌必須要從中國文學傳統中汲取營養,以彌合一百多年的斷層所帶來的內容空洞,而“唐風文化”時代傳入日域的唐代文學便成了不二之選。早在平安時代末期到中世,《古今集》的古注釋書中就已經注意到該時代的和歌中存在著一些借鑒唐代文學的內容,而符合近代學術規范的研究始于20世紀上半葉。前文所引述的日本戰前學者金子彥二郎就曾經系統地研究了傳入日本的白居易詩歌集《白氏長慶集》與“國風文化”時代初期的和歌文學之間的關系,并指出白居易的詩歌對《古今集》前夜的和歌文學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并直接在和歌古今風的形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古代文學特別是唐代文學對“國風文化”時代和歌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下列幾個方面。從文學體裁上來說,《古今集》前夜的一部分歌人選擇了直接借鑒唐詩的表達方法來豐富和歌的內涵,其具體體現便是以一句或一聯唐詩為題,將之翻譯成對應的和歌,進行吟詠欣賞。這樣的文學形式在后世被稱為“句題和歌”,而這個時期出身儒學門第的歌人大江千里所詠的《大江千里集》(又稱《句題和歌》,簡稱《千里集》)被后世視為該種文學形式的濫觴,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在體裁上影響日本文學的典型例證,這一問題將在后文中進行詳細論述。
從素材上來說,大量中國古代文學中使用的文學意象在該時代直接為和歌所借鑒,例如和歌中菊花的意象就與中國古代文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菊”是自中國傳入的觀賞植物,在日語中甚至沒有對應的和語訓讀。而和歌作為大和民族的傳統文學,原本天然排斥漢語詞匯。將源于漢語的“菊”入歌而詠,體現出“國風文化”時代和歌吸收中國古代文學意象的新動向。本書將在第四章系統分析“國風文化”時代中國古代文學中所使用的文學意象進入和歌文學的這一特殊現象。
此外,大量的中國古代文學典故在“國風文化”時期進入和歌文學。小島憲之在注釋《古今集》時探尋了大量源于中國古代文學的內容,其成果直接反映在由巖波書店出版的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古今和歌集》的注釋中。在他與新井榮藏的注釋中,甚至可以窺見《古今集》歌人對《史記·項羽本紀》中“錦衣夜行”典故的使用。除此之外,《古今集》時代的歌人對六朝文學中所見的典故也偏愛有加,例如《古今集》的編纂者之一紀友則就曾經化用過六朝文學任昉《述異記》中所見的“爛柯”典故;而同為《古今集》編纂者之一的凡河內躬恒則使用過六朝文學張華《博物志》中的“浮槎”典故。這些記載于中國文獻中的中國典故在“國風文化”時代進入和歌文學,為歌人活學活用,豐富了和歌的表達技法,并深刻了和歌文學的文化內涵,該現象無疑凸顯出“國風文化”時代初期的和歌對中國古代文學的依賴性。
除了文學體裁、文學意象以及文學典故三個方面,“國風文化”時代的和歌文學在文學思想上也受到了中國古代文學的顯著影響。例如渡邊秀夫從該時代和歌的意象與思想性出發,首先探索了唐詩中用語對《古今集》前后的和歌文學中歌語意象的影響,進而又提出了中國古代的禮樂思想對《古今集》編纂在思想上的影響,并指出敕撰和歌集編纂的根本意圖依然是源于中國古代的“文章經國”思想與禮樂意識。在這一觀點上,李宇玲與渡邊秀夫的觀點不謀而合。她系統地解釋了《古今集》編纂受中國禮樂思想影響的內在邏輯,為從思想根源探尋《古今集》的編纂原因提供了一個頗具建設性的思路。此外,筆者在《古今集》時代歌人的季節觀念中也找到了受到中國古代文學特別是唐代詩人白居易的物候觀影響的部分,可以說,唐代詩人的物候觀在整個和歌文學中自然事物的季節意識的生成與流變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這一問題將在本書的第五章進行詳細的論述。
綜上所述,“國風文化”時代的和歌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學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和歌文學中存在著大量中國古代文學要素。而傳統的“國風文化”論一味強調這個時期文學體裁上的變化,認為使用假名文字書寫的和歌文學必然是排斥中華文化的純粹國風文學,這樣的觀點在今天的研究視角下顯得有失客觀。至少在日本文學領域,所謂“國風文化”時代是否真的是排斥中華文化而弘揚日本本土文化的時代,這一問題值得商榷。
敘事文學方面,與詩歌文學一樣,“國風文化”時代中由假名文字所書寫的敘事文學中依然可以窺見大量的中國古代文學要素。對此,筆者將按照敘事文學的體裁分日記文學與物語文學進行闡述。但在此之前,我們需要厘清日本敘事文學的源流,為以后的行文做好準備。
日本的敘事文學與中國的敘事文學在起源上存在某種相似性,即敘事文學的起源都晚于詩歌文學且發展緩慢。中國古代文學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才在佛教傳入的影響下發展出了真正意義上的敘事文學——志人志怪小說,而日本文學亦然。除去上代因為政治統治與外交活動需要所編纂的《古事記》《日本書紀》以及《日本風土記》三部史書,日本文學中真正意義上的敘事文學發軔于“唐風文化”時代撰寫完成的《日本靈異記》。該書由奈良藥師寺僧人景戒編纂,收集了包括日本著名僧人行基事跡在內的諸多佛家故事,用以傳播佛教思想。該書用變體漢文書寫,因此屬于廣義的漢文學范疇。而以和文體書寫文獻的先例雖已見于上代文學中的《古事記》,但真正意義上用和文體書寫的敘事文學則要一直下溯到“國風文化”時期誕生的以假名書寫的早期物語與日記文學。這里必須辨析兩個概念,一個是文學作品的書寫文字,一個是文學作品的文體。此二者的區別在日本古典文學研究中頗為重要。在我國,很多多年從事日本文學研究工作的學者依舊無法弄清楚日本古典文學中文字與文體之區別。自日本古典文學伊始至院政期和漢文體合流形成和漢混淆文體為止,日本古典文學中存在著和文體與漢文體兩種截然不同的文體。和文體是利用大和民族自己的語言書寫的,漢文體則是模仿中國古代文言文書寫的,經典的漢文體可直接視為漢語文言文,而一些帶有日域用語特色的漢文體則被稱為變體漢文,與標準的漢語文言文存在一定語法與詞匯上的出入。在平安時代,漢文體一般由男性貴族掌握,而和文體主要由女性使用,二者的對立統一促進了日本古典文學的發展。與之相對,日本古典文獻的文字情況則有所不同。日本特有的文字假名誕生于平安時代前期,在此之前則使用漢字作為文字。在假名誕生以前,無論是和文體還是漢文體均由漢字記錄。當漢字用于記錄和文體的文獻時稱為萬葉假名,而用于記錄漢文體的文獻時則稱為漢字。例如上代文學中,《古事記》與《萬葉集》為漢字記錄和文體書寫的文獻,而《日本書紀》《日本風土記》以及《懷風藻》則為漢字記錄漢文體書寫的文獻。真正意義上的和文體假名敘事文學主要是“國風文化”時出現的假名日記以及物語這兩種文學體裁。
一般認為,假名日記文學脫胎于男性貴族用漢文體與漢字記錄的公卿日記。而現存*早的假名日記《土佐日記》的開頭也印證了這一觀點:“男人寫的日記,女人也試著寫寫。”一般認為《土佐日記》是《古今集》的編纂者之一紀貫之假托女性口吻所寫,此后成書于公元10世紀后半葉的《蜻蛉日記》則繼承了《土佐日記》的衣缽,此后假名日記主要由女性書寫。日記文學中存在的中國古代文學要素已被學界所認知。例如紀貫之在《土佐日記》中多次引用或化用李白與賈島等唐代詩人的詩歌。除此之外,小島憲之弟子之一的北山圓正也曾指出,《土佐日記》的結尾在結構與語言描寫上受到了《述異記》等魏晉南北朝文學的影響。而在《蜻蛉日記》中,我們可以窺見其作者藤原道綱母的漢學素養。大谷雅夫曾經指出本作品化用了李白的詩句,張陵則揭示了《蜻蛉日記》對以白居易詩歌為代表的諸多中國古代文學的借鑒。至此,日本假名日記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學之間的關系日漸明朗起來。
“國風文化”時代物語文學的誕生有兩個截然不同的源流,其一是源自漢文體的敘事文學,其二是源自和歌集中的題詞。前者稱為“作物語”,后者稱為“歌物語”。“作物語”的鼻祖《竹取物語》很有可能就是從一部漢文體的文學翻譯為和文體的假名物語的,因此其與中國古代文學的關系不言而喻。其后,物語的篇幅開始逐漸變長,到10世紀后半葉誕生了諸如《宇津保物語》一類的長篇假名物語。《宇津保物語》描寫了主人公清原俊蔭西渡唐朝學習琴術,學成歸國后出世發達的故事,這樣的故事情節本身就涉及諸多中國描寫,因此也必然受到中國古代文學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余鴻燕曾經指出,《宇津保物語》中可見多處中國孝悌思想的影響,這說明中國古代文學不僅在語言表達上對早期物語產生了諸多影響,更在深層次的思想方面對早期物語有著滲透。其后誕生的物語集大成者《源氏物語》與中國古代文學的關系更加緊密。新間一美主張《源氏物語》是在元稹作品《鶯鶯傳》影響下產生的文學,而其中的卷名又有源于中國古代文學的部分。這樣的說法未免有些標新立異而大膽,但紫式部在《源氏物語》中大量化用了白居易詩歌與中國古代文學典故是不爭的事實。例如化用白居易“兩千里外故人心”一句以及《漢書》中“白虹貫日”的典故都是紫式部受到中國古代文學巨大影響的實例。另一方面,歌物語中所見的中國古代文學影響研究則方興未艾,其中以小山順子的研究*具代表性。她指出了唐代傳奇對《伊勢物語》第69段的影響。又由于歌物語脫胎于和歌文學,其中包含了許多和歌。如前文所述,這些和歌本身就受到了中國古代文學的巨大影響,因此,總體來說,歌物語與中國古代文學的關系可以說十分緊密。
綜上所述,“國風文化”時代的文學種類中均可以窺見中國古代文學的諸多影響。假名文學的誕生并不意味著文學創作的主體階層拋棄了中國古代文學與中華文化,而是嘗試將“唐風文化”時代吸收的中國文化內化并改造,以假名文學的形式所表達出來,這樣的過程便是中國古代文學的日本化。中國古代文學的日本化是中國古代文學影響日本文學的重要機制,也是“國風文化”時代文學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書后續章節將從若干角度對“國風文化”時代和歌文學中所見中國古代文學的日本化現象進行系統闡述。
和歌浦浪起唐風 中國文學在日本和歌中的接受研究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黃一丁 1991年生,湖北武漢人。本科畢業于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外語學院日語系,碩士與博士畢業于日本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日本語言學日本文學專業,文獻文化學博士。現任教于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研究方向為日本古典文獻學與中日比較文學,主要關注日本平安與鐮倉時代的和歌文獻。在日本古典文獻學、中日比較文學以及域外漢籍研究等領域撰寫過相關論文。
- >
煙與鏡
- >
人文閱讀與收藏·良友文學叢書:一天的工作
- >
史學評論
- >
月亮與六便士
- >
詩經-先民的歌唱
- >
姑媽的寶刀
- >
朝聞道
- >
伊索寓言-世界文學名著典藏-全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