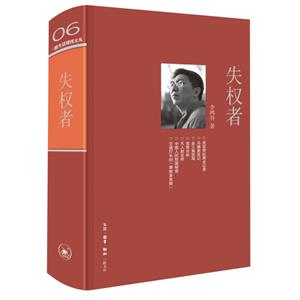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精裝)三聯(lián)生活周刊文叢:失權者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8031242
- 條形碼:9787108031242 ; 978-7-108-03124-2
- 裝幀:精裝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精裝)三聯(lián)生活周刊文叢:失權者 內(nèi)容簡介
來到新聞現(xiàn)場,記者面臨什么?他將如何選擇?三聯(lián)生活周刊主編李鴻谷對犯罪領域的進入以及對高位失權者的報道,不僅讓我們得見新聞事實的魅力,更獲得了新聞方法論的啟迪。這些視角獨特的故事,綿密的邏輯與平時白描的文字讓我們得以平靜、公正地把這些采訪對象當做人來分析,這些新聞事件提供給我們的信息價值,不單是一個犯罪事實,還有他們的人生故事。
(精裝)三聯(lián)生活周刊文叢:失權者 目錄
序
貪官
貪官李紀周全記錄
廣西貪官網(wǎng)
李真:秘書的權力
李真:秘書的網(wǎng)絡
馬德賣官記
毒品
新生代毒梟
冰毒網(wǎng)
金三角變局
劉招華:欲望與死亡游戲
罪犯
溫嶺黑社會
危險的財富
刑警隊長的罪與罰
張君分析
江湖
緋聞時代的女主角
凡人趙忠祥
債務人牛群
徐明是誰
財富
誰是有錢人
中國人的財富秘密
煤炭資本家的財富秘史
社會
交通廳長的“事故多發(fā)期”
人命與仕途
青基會的贏與虧
新聞筆記
調(diào)查李真
敘述馬德
觀察權力
新聞的方法論
三聯(lián)的知識生產(chǎn)
后記
(精裝)三聯(lián)生活周刊文叢:失權者 相關資料
“你見過李紀周嗎?”
“沒有。”
“哦。他腿有點瘸,很明顯。所以,這就有點奇怪了,他先當兵,然后進公安,這都是要健全的身體的啊……”
坐在公安部原治安局局長高旭家里,我們的采訪就這樣開始了。如果對記者這個職業(yè)有點感嘆,稍微喝點酒后,不免自得見過的陌生人多。采訪過程中見過的大量交換過名片的陌生人,真正能夠留下印象的,不多。不過,高旭是不會忘記的一位,多精彩的一個開頭……李紀周任治安局副局長時,高旭是正局長,李的直接上司。一個半小時,和藹的老先生有條不紊地講述下來,清清楚楚,干干凈凈,差不多都是可以引證的材料。講完了,老先生問,你還有什么問題嗎?沒有了。很簡單,能夠講的,他都講了,不能講的,問也沒用。
陽光挺好的那個初冬的下午,離開南露園小區(qū),站在街邊,我點燃一枝煙,想到那個詞 :核心信息源。所有有關李紀周眾多片斷的、零碎的信息,因為高旭而被證實或證否,李紀周的人生邏輯也因而清晰。
從事任何職業(yè)或許都有一個被“點燃”的時刻,這種戲劇性或隱或彰,各人自是不同。想起來,未來這份我還將繼續(xù)的新聞職業(yè),真正啟動我的,是那本《萬歷十五年》——不是黃仁宇的敘述與史觀,而是它書后附錄的七頁的參考書目。我一頁頁翻完這些書目,棄書而嘆 :真正的識見緣于此啊。沒有每周閱讀一冊《明實錄》(共 133 冊)以及眾多奏疏筆記、各地方志、新舊著作,黃先生又如何能從容講述 :“當日四海升平,全年并無大事可敘……”這種種,于我,借用佛語,大約就是:覺悟。因此機緣,再讀那本講述美國大媒體的厚書《掌權者》,很容易被忽視的細節(jié) :參加過越戰(zhàn)戰(zhàn)地報道的著者,贊嘆的不是他的職業(yè)對手獲得了普利策獎,而是對方每天采訪人數(shù)與所記錄的筆記(素材)比他更多——便有了職業(yè)性的醒悟,這才是這個職業(yè)的正當狀態(tài)。如此一脈貫通而來,最終是布羅代爾給予了我對新聞職業(yè)的根本性定義,很簡單,你擁有多少材料?——材料決定一切!
10 多年后,我來北京做記者,站在南露園小區(qū)外的街邊,我有了點發(fā)現(xiàn)與進步 :信息源其實是有級差的。這跟財富、知識與權力一樣,信息掌握的多少,是有等級的。所以,有效率的職業(yè)方式就是,迅速地判斷誰是核心信息源,同時找到機會去接觸并最終開掘它。所謂新聞的方法論,其建構的基點在此,舍此,如何討論與言說?當然,擁有足夠或更多材料之后,借用歷史研究的套語,你最終是“史料”的編輯者,還是發(fā)明自己的“史觀”,在于你有什么樣天分。
自然,覺悟是有分別的。
“你見過李紀周嗎?”
“沒有。”
“哦。他腿有點瘸,很明顯。所以,這就有點奇怪了,他先當兵,然后進公安,這都是要健全的身體的啊……”
坐在公安部原治安局局長高旭家里,我們的采訪就這樣開始了。如果對記者這個職業(yè)有點感嘆,稍微喝點酒后,不免自得見過的陌生人多。采訪過程中見過的大量交換過名片的陌生人,真正能夠留下印象的,不多。不過,高旭是不會忘記的一位,多精彩的一個開頭……李紀周任治安局副局長時,高旭是正局長,李的直接上司。一個半小時,和藹的老先生有條不紊地講述下來,清清楚楚,干干凈凈,差不多都是可以引證的材料。講完了,老先生問,你還有什么問題嗎?沒有了。很簡單,能夠講的,他都講了,不能講的,問也沒用。
陽光挺好的那個初冬的下午,離開南露園小區(qū),站在街邊,我點燃一枝煙,想到那個詞 :核心信息源。所有有關李紀周眾多片斷的、零碎的信息,因為高旭而被證實或證否,李紀周的人生邏輯也因而清晰。
從事任何職業(yè)或許都有一個被“點燃”的時刻,這種戲劇性或隱或彰,各人自是不同。想起來,未來這份我還將繼續(xù)的新聞職業(yè),真正啟動我的,是那本《萬歷十五年》——不是黃仁宇的敘述與史觀,而是它書后附錄的七頁的參考書目。我一頁頁翻完這些書目,棄書而嘆 :真正的識見緣于此啊。沒有每周閱讀一冊《明實錄》(共 133 冊)以及眾多奏疏筆記、各地方志、新舊著作,黃先生又如何能從容講述 :“當日四海升平,全年并無大事可敘……”這種種,于我,借用佛語,大約就是:覺悟。因此機緣,再讀那本講述美國大媒體的厚書《掌權者》,很容易被忽視的細節(jié) :參加過越戰(zhàn)戰(zhàn)地報道的著者,贊嘆的不是他的職業(yè)對手獲得了普利策獎,而是對方每天采訪人數(shù)與所記錄的筆記(素材)比他更多——便有了職業(yè)性的醒悟,這才是這個職業(yè)的正當狀態(tài)。如此一脈貫通而來,最終是布羅代爾給予了我對新聞職業(yè)的根本性定義,很簡單,你擁有多少材料?——材料決定一切!
10 多年后,我來北京做記者,站在南露園小區(qū)外的街邊,我有了點發(fā)現(xiàn)與進步 :信息源其實是有級差的。這跟財富、知識與權力一樣,信息掌握的多少,是有等級的。所以,有效率的職業(yè)方式就是,迅速地判斷誰是核心信息源,同時找到機會去接觸并最終開掘它。所謂新聞的方法論,其建構的基點在此,舍此,如何討論與言說?當然,擁有足夠或更多材料之后,借用歷史研究的套語,你最終是“史料”的編輯者,還是發(fā)明自己的“史觀”,在于你有什么樣天分。
自然,覺悟是有分別的。
在 2001 年,把李紀周做成《三聯(lián)生活周刊》的一個封面故事,或許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它的轉載之多,至少于這本雜志是少見的。我的同事當時有疑問 :你的李紀周,想說明一個什么問題呢?這樣的疑問也困擾過我。按提問者的話語體系,李紀周這個故事,對現(xiàn)代化進程的價值何在?在民主的進程里又有什么意義呢?這顯然是疑問。
簡單地解釋一下,是必要的。武斷一些來做個判斷,新聞的操作其實一直在兩個問題框架里游移 :事實與價值。每個媒體都有不同形式的選題討論會,相信每個有報道任務的記者對這樣會議的苦惱,是職業(yè)的基本經(jīng)驗。我有時不免奇怪,這人人都頭痛過的選題會,為什么就沒有被充分地討論過它為何會讓大家如此痛苦不堪。回到選題會現(xiàn)場,記者所申報的選題,多數(shù)是剛剛發(fā)生的事件,常態(tài)是基本的事實說不夠5句話;但是,這個時刻編輯必須做出判斷,我們是否在這個選題給予投入。對雙方而言,這都是一個充滿考驗的時刻。記者呈述的是不完全的“事實”,編輯必須做出確鑿的“價值”判斷,這就是新聞這一職業(yè)永恒的悖論。如果失去對此的體察,從事這個職業(yè),將長期處于蒙昧而痛苦狀態(tài)。
那么,如果我們再細心一點,先來探究編輯如何作“價值”判斷。20 多年前,我進入黨報系統(tǒng),一般而言,當時編輯主要由那些資深而成功的記者晉升而來,他們的經(jīng)驗構成了判斷的來源。現(xiàn)在可能像我當年那樣聆聽前輩記者講述報紙對權力人物排名順序安排的機巧的機會不多了,很快,就我眼見著,他們 30 多年來“宣傳”所積累的技術套路,被另一種“價值”觀所超越。80 年代有著高等教育背景的新一代編輯成長起來了,這是新一波浪潮。這一代編輯來自“新啟蒙”所獲知識及其價值觀,承接的思想資源是“五四”以來的文人辦報書生議政理念。個案總是比綜述精彩。在 80 年代,書生議政甚至有“行政”的機會。我
在香港大學讀當年一位報告文學家的自傳,這位供職于《人民日報》的記者,所津津樂道的是當時自己在黑龍江如何對省委書記拍桌而起,寫出轟動一時的大作。但重讀當年的大作,那個計劃經(jīng)濟時代的投機倒把,在如今這個市場經(jīng)濟社會,兩廂錯位,人妖俱滅,生死相隔,感嘆造化弄人之際,不免對此等價值觀生疑。當然,把記者這一職業(yè)做到仿佛欽差大臣的角色,對于當事人,自是人生快事。榜樣是用來垂范的,書生議政一路下來,漸成潮流。這一路價值觀與前述宣傳之套路,看似反正,其實一路,都執(zhí)著于媒體的權力,硬幣的兩面而已。稍后,都市報系列興起,媒體的權力動機之外,多了甚至更占主導的商業(yè)動機,新一輪的受眾至上價值觀潮流亦由此生發(fā)。
我們很難將這三種價值觀理解為替代,迄今,它們?nèi)匀皇枪泊妫饔蟹秶煌O嘈琶襟w從業(yè)者如有真誠檢討,我們各自的 C PU,大概不脫上述價值觀籠罩。
編輯的價值觀潮流如此,自然任何新聞,都可以用這個標尺測量一下。李紀周?對現(xiàn)代化進程的價值何在,在民主的進程里又有什么意義?自不意外。我初進三聯(lián),聽眾位同事報選題,難免驚異,怎么個個都跟主編一樣,高調(diào)意義不止。其實這只不過是一種言說策略而已,好讓自己的選題能夠速速通過,最后成稿是否如此,另說。
前述悖論,如此彌漫,我們應當更細心一些。仍回到選題會現(xiàn)場,其間悖論便會相對分明。那些尚且講不夠 5 句話的新聞事實,被迅速地高空作業(yè)給予了價值判斷,結果難免時常會一腳踏空,事實怎么可能只是用來證明編輯的想象呢?聰明的記者或許會實現(xiàn)編輯的意圖,事實如此之豐富,由編輯建構的那條邏輯線索,找到基本事實層的支持并不困難。但是,選題會仍然如此之痛苦,為什么?簡單說,中國30年,特別是最近 10 年變化如此之迅猛,記者接觸的是最為日常的變化,而我們一再用其實是曾經(jīng)潮流的標尺,當然可能失效而形成沖突。再則,新聞之核心是“新”,如果是真正的“新”聞,那么它必然不會受拘于我們的標尺。這是這個職業(yè)的悖論關鍵。
改造編輯的“價值”觀,如此說來,是不是言之成理呢?也許。但這不是我的興趣所在。很簡單,事實與價值之悖論,是這個行業(yè)基礎性事實,兩者相互沖突才可能促進媒體進步。單單指責一方,很幼稚,換個角色你來試試?
回到我自己的新聞現(xiàn)場,當年去做李紀周這個選題,是朱偉給我的要求,于我是挑戰(zhàn),卻也是一個機會。我們觀察記者編輯這對權力結構,往往注意權力上端的編輯及其價值選擇,如果將注意力投射于權力下端的記者,能否另開新面?職業(yè)角色其實沒有絕對的上下,決定性的因素往往是看誰更有力量,權力是可以流變的啊。如果還用“覺悟”那個詞,慢慢我認定,如何做記者,是我的興趣與責任所系。真正去到現(xiàn)場的記者,一定不會去想這個材料有什么可垂之恒遠的價值 ;這正如球員起腿射門,一定不會想到這將是改變歷史的一腳一樣。那么,記者面臨什么?他將如何選擇呢?
從武漢到北京入三聯(lián)來做記者,基本的原因是覺得自己記者沒有做夠。現(xiàn)在想起來,變成真正周刊的《三聯(lián)生活周刊》一度被戲謔為“法制文學”,亦實非偶然。當時我是真的對罪犯有興趣。勉強說來,這或許跟那本《劊子手之歌》有關,但激發(fā)我的興趣的并非它的文學性和被稱為“新新聞主義”的標簽,而是一種奇怪的好奇心 :一般而言,我們正常人努力求上進,獲得各種功名利益,是一種正向的作用力 ;但罪犯則不然,他們越是“成功”,可能離刑罰與死亡越近。對此,他們豈無自知?如果有此知覺,在這種負向作用力下,他們會呈現(xiàn)什么樣的心理與行為狀態(tài)?這個東西,遠遠超出我們正常人生邊界,我好奇。
如果閱讀意大利人龍勃羅梭與加羅法洛兩本同名的《犯罪學》也能當成一種知識準備的話——龍勃羅梭的精華是他的實證認定“生來犯罪人”定律 :“他們的犯罪性與生俱來,是由他們的生物特征所決定。”這類人的比例多少?龍氏后期將其降至 33%。這些準備,我所獲取的“教條”,不是現(xiàn)代化與民主那些虛詞,而是實在的 :“犯罪無法簡單歸因”。既此,那些罪犯究竟由什么因素構成?這當然是對智力的一個重大挑戰(zhàn)。進三聯(lián)后,看南方某周末報寫張君,將其犯罪歸因為貧窮,自然訕笑。好,我也下場來競技,表演一點有難度也有智力的報道吧!在這種沖動之下,有報道李紀周的機會,是一種幸運。
當時,我希望進入的領域倒也好玩,是禁毒。那些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毒梟們,是我實踐尋找多因致果(犯罪)的好題材。大約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成本”,我終于有了信息源,可以去云南報道被捕的大毒梟譚曉林。這次沒有見著譚本人,第二年我再去云南,去到看守所吃飯,剛坐定舉筷,進來一個瘦小的四川人,眼神靈活,警官介紹說 :“他就是譚曉林。”一切風淡云輕,自然而正常。我們一道吃了頓飯,單獨談了三個多小時。離開看守所,警官問感覺如何?我認同作為職業(yè)對手的那些警官們對譚的天分的贊美。這個領域在譚曉林平靜的敘述里,你有機會得窺其真實狀況。這一長時間的“投資”以及最終對譚曉林的報道,方便我有機會拿到高旭的電話號碼,電話打過去,說明意圖,對方稍加思索,便答應 :來吧。這又使我有了進入報道那些高位失權者的機會。饒舌幾句,將那些失權者稱之貪官更準確,但這一詞語在現(xiàn)實境況下所意味的俯視與仇視過甚,如果揭去這一標簽,我們可能能夠更平靜也更公正地把他們當做人來分析。雖然他們比之正常,是負向的。非此,又如何擴大我們對人與人類的了解、理解與認識邊界?
譚曉林的報道,很難說得上是成功的稿件。采訪者與被采訪者的信任建立,同樣需要時間成本。在昆明的小飯館里跟警員們搳拳喝猛酒,還去曖昧的小舞廳……第二天,這隊警員們將與毒販接貨,雙方都有武器,這一夜才是真正漫長的一夜。如何排遣內(nèi)心的壓力?這個時候你才有機會真正體會他們的緊張。用命去搏的職業(yè),任何輕薄都是罪過,后來譚曉林的預審者跟我一道喝酒,幾杯下去,大哭 :我工作 5 年,大學同班同學已犧牲三位。如果毒梟們以及他們犯罪的多因是我的興趣,那么這些警員們的工作,對毒梟們構成什么呢?當然是一種壓力,如果更克制一些,將其稱為“環(huán)境”,也是恰當?shù)摹?/p>
做完譚曉林報道后,第二年我又去了趟云南,去那個被描述成神秘而恐怖的“金三角”呆了 7 天。這是我們理解這些毒梟更重要的環(huán)境啊。犯罪的“多因致果”,環(huán)境——罪犯生長的環(huán)境、發(fā)生犯罪行為的環(huán)境以及組織結構的環(huán)境種種,在“多因”里實在占據(jù)大多比重。這才是認知最關鍵的橋梁。自然,如果我們將罪犯這個特定概念取消,任何新聞主角,當然亦可用同樣的方式切入。我的采訪經(jīng)驗與思考達成合格的報道結果,毒梟是劉招華,而貪官是馬德。
這些報道俱在,無須多言。但這些報道出臺的背景,卻值一說。90年代后期,都市報系列興起,媒體整體市場化趨向明朗。《三聯(lián)生活周刊》2001 年真正成為周出雜志,當然可以認定是這一趨勢的結果。這一輪商業(yè)主導的媒體變化,受眾至上壓力之下編輯的價值判斷又呈何種面目?看上去,它以一種去價值化的方式作為開始。“現(xiàn)場”——那些災害、事故與兇案的新聞現(xiàn)場成為新的動力來源,宣傳以及對體制的挑戰(zhàn)的權力價值觀,似乎暫隱。站在當下這個時刻點來回溯,這種商業(yè)化趨向使媒體相對意外地進入了新聞更為本源的意義。舉凡戰(zhàn)爭、災害、暴力、情色、貪官瀆職以及領導人更迭……這些人類所面臨的未可確定的意外與沖突,才是新聞的起源啊。任何一種新聞敘事,如果沒有“沖突”作為結構基礎,其意義與價值建構,其實可疑。
那個時刻,一場空難,最快到達現(xiàn)場的除了國家民航局的官員,可能更多的就是各路記者,這其中當然也會有《三聯(lián)生活周刊》的記者。“現(xiàn)場”所代表的事件新聞,成為最大宗的新聞產(chǎn)品。在這一背景下,“核心信息源”的概念被理解與接受,變得容易而迅速。然后,這一輪突進之后,再進半步,媒體步履亦顯艱難。唉,思想或者價值觀,那有那么容易產(chǎn)生的。之后,都市報媒體發(fā)育出一個叫“時評”的東西,過去的雜文家都成了時事評論員了。這再一輪強化了“現(xiàn)場”的重要性——那些碎片式的信息一經(jīng)刊布,即成評論家想象的根基,看上去,我們的輿論日益豐富 ;代價是,我們離事實越來越遠。
如此大劑量而同質(zhì)的事件新聞產(chǎn)品及其衍生物的供給,按經(jīng)濟學說法,邊際效應迅速遞減。加之,互聯(lián)網(wǎng)日趨成熟,其發(fā)布時間之迅猛,使紙質(zhì)媒體危機感成為話題。我同意一個說法,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核心信息源的價值也大打折扣,網(wǎng)絡的“人肉搜索”以及可以隨即發(fā)布的便利,那些艱難的尋找變得輕薄。速度壓倒一切,新聞還沒有開始,“時評”加上口水事實上已經(jīng)將它結束。好萊塢的歌舞片《芝加哥》,早已將這一故事演過一遍。
記者面臨什么?他將如何選擇?在有了新聞現(xiàn)場這個開始后,它的答案 :去盡量獲取材料,材料決定一切——似乎已經(jīng)確鑿。但在這個時間壓縮的年代,同質(zhì)化產(chǎn)品、過度“口水”、網(wǎng)絡的速度及其技術擠壓,種種疊加現(xiàn)實下,材料真的還是決定一切的力量?
選擇往往出之偶然。我進入三聯(lián)之際,賴昌星幾乎成為跨年度,而且是若干個年度的重要新聞,大家都是玩猜謎游戲,誰是賴式多米諾骨牌里倒下的最大一個官僚……這個時候,李紀周案審理開始了,雖然李被雙規(guī)甚至早于賴昌星事發(fā),但結果他卻是賴氏官人代表最顯赫的一個。在“現(xiàn)場”成為新一輪新聞生產(chǎn)方式之際,對于《三聯(lián)生活周刊》,更需資源與成本的諸如李紀周、譚曉林調(diào)查,提供了另一種路徑。所以,報道李紀周是一個機會,斷非客套之詞。
這是一個可以帶來新聞方法論創(chuàng)新的機會。當所有媒體都奔赴“現(xiàn)場”,用最快速度去爭奪李紀周的起訴書與判決書的時候,我們轉過身去尋找高旭。李紀周能夠提供給我們的信息價值,不單是一個犯罪事實,還有他的人生故事。這個主角的悲劇,戲劇的高潮在那里?這當然好玩。而當人物亦逐漸成為媒體發(fā)現(xiàn)的新的產(chǎn)品類型,眾多以“人物”為名目的媒體登場之際,我們發(fā)現(xiàn)其實那些故事的主角,比如譚曉林所處的金三角是有意思的,環(huán)境即使不能決定人,也是影響人的選擇與行為的核心要素。當然,在這種種行為選擇之下,更細致的方法與路徑,也有機巧,好在我有機會時常去大學報告一下我們工作的進展,這讓我有條件將其整理成文字,這些文字也在,放下不表。
沖突以及沖突背后的人物、環(huán)境,當你作為一個記者到達新聞的現(xiàn)場,這些是你去獲得比你的同行更多材料的方向。這是我的答案。周正龍“周老虎”那么熱鬧,但你去鎮(zhèn)坪呆上一周,看看這個沸騰的縣城各色人等,因為老虎的瘋狂,相信也是有價值的,至少比一個科學家發(fā)布的陰謀想象要有趣味得多。所以,材料決定一切,問題不在于它是否成立,而是你是否有基本的智力分辨你的材料構成及其方向。宣傳、體制批判、受眾至上……種種,其實,超越這一切遮蔽的關鍵在于你擁有了材料之后有沒有智慧,有了,新聞便成為一種工具,認知世界的工具。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你擁有足夠的資質(zhì),發(fā)明你的“史觀”,并不是件困難的事情。
最后,如果從記者本位稍稍換位,來重新思考一下編輯的“價值”觀,我自己更傾向認定,編輯的偉大與否其實不取決于他是否擁有思想,而在于他能否向他的時代提出正確的問題。所有的記者從本質(zhì)上講,都是去尋找事實解答問題的人。很偶然,有一兩個,發(fā)明了自己的“史觀”。那么,他就能講出一個傳之久遠的好故事。
后來,我專程去拜訪過一次高旭先生,表示我的感謝。他的安詳與淡定,已經(jīng)顯示我的感謝,太過庸常。再后來,我聽說李紀周假釋,打過一次電話問詢,他想了想說,從李的刑期看,不太可能這么快假釋……之后,就沒有了聯(lián)絡。這個職業(yè)見過的那些陌生人,其實多數(shù)對媒體無所欲求,只是出自基本的責任與道德感,幫助記者完成了他們的工作。而新聞這份職業(yè)卻相對功利,因為他們馬上又要奔向另一個新聞現(xiàn)場,那許許多多的信息源,還來不及感謝,便已擦身而過,也許再無碰面可能。那些信息的供給者,比如高旭先生,才是這份職業(yè)應當從內(nèi)心保持感激與感恩的對象。
人生何嘗不也是一個故事,是不是一個精彩故事,因人而異。如果也套用前述沖突、人物與環(huán)境結構,來看我自己微觀的職業(yè)環(huán)境,我的幸運在于,我碰著了一個天才的編輯朱偉,他對新鮮東西狂熱的追求并非修煉而是天性,這對像我這樣記者本位,以為記者才是主角的職業(yè)人而言,豈只一個榮幸可以概括。因此機緣,那些想象與思考,最終有機會變成一個個的報道。當然,天性之外,作為主編,朱偉的鑒賞能力才是值得真正尊重與贊美的。每一個人的成長,都是一個試錯的過程,朱偉的情緒與臉色是對錯之反饋,這才是精彩的編輯記者關系,至少你會因此而自省。除此,沒有他的督促,相信我們大多數(shù)人會因自己的惰性而放慢腳步。如此種種,《三聯(lián)生活周刊》終成一份讓才華表現(xiàn)的平臺——這是我的描述,而我經(jīng)常的感嘆則是,關鍵是因為朱偉,他鞭趕著你 :快快寫出你的好故事!
與此同時,在有截稿時間壓力下的工作,合作是必須的,如果沒有我的那些智力超群的同事們的合作,這里所收集的報道,多數(shù)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所以,對于朱偉還有我的同事們,單單一聲感謝,太過菲薄。所謂人生故事,在職業(yè)上,你們構成并決定了我啊!
當然,論及人生故事,家庭自是不可或缺。我的職業(yè)壓力,沒有妻子以及兒子七七的平衡與紓緩,相信會嚴峻許多。所以,將這本小書獻給他們,理所當然。
(精裝)三聯(lián)生活周刊文叢:失權者 作者簡介
李鴻谷,1987年,《長江日報》體育記者;1998年,《武漢晨報》編委;2000年進入《三聯(lián)生活周刊》社會部,任主筆,現(xiàn)為《三聯(lián)生活周刊》主編。
- >
我從未如此眷戀人間
- >
伊索寓言-世界文學名著典藏-全譯本
- >
唐代進士錄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裝共3冊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qū):歷史與人類學概述
- >
大紅狗在馬戲團-大紅狗克里弗-助人
- >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實旅程
- >
新文學天穹兩巨星--魯迅與胡適/紅燭學術叢書(紅燭學術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