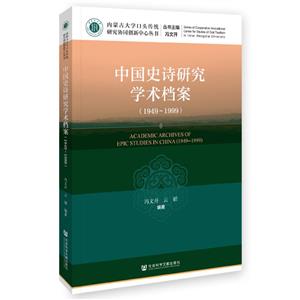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中國史詩研究學術檔案(1949-1999)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2827070
- 條形碼:9787522827070 ; 978-7-5228-2707-0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史詩研究學術檔案(1949-1999) 內容簡介
總序“口頭傳統”譯自英文oral tradition,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口頭傳統指口頭交流的一切形式,狹義的口頭傳統則特指傳統社會的溝通模式和口頭藝術(verbal art)。活形態的口頭傳統在中國蘊藏之宏富、形態之多樣、傳承之悠久,在當今世界上都是不多見的。基于國內當時對于口頭傳統的學術研究,以及對于相關資料的數字化與信息化的處理較為落后的狀況,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經充分醞釀,于2003年9月16日成立了“口頭傳統研究中心”。此后,該口頭傳統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口頭傳統的搜集整理與研究,在形成自身學術集群效應和研究論域的同時,也為從事各民族口頭傳統研究的學者提供了一個更為廣闊的學術空間和一個更有活力的學術平臺。總之,這一學術共同體有志于引領國內口頭傳統研究的發展,推進國內口頭傳統研究朝向學科化進階,將中國口頭傳統研究推向國際學術的舞臺。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口頭傳統研究中心成立以來,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便與該中心在學術研究、項目合作、人才培養等諸多方面有著密切的學術聯系。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擁有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和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形成了本科、碩士、博士三個層次的學科體系。經過多年的努力,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在中國民族文學研究、史詩學與口頭傳統研究方面具備了較好的學術積累,民族文學、史詩學與口頭傳統成為該學院擁有特色和優勢的專業方向。2019年8月13日,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口頭傳統研究中心成立了內蒙古大學口頭傳統研究協同創新中心。這個協同創新中心大體可以說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口頭傳統研究中心和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在多年合作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研究機構,立足“服務內蒙、創新機制、匯聚隊伍、整合資源、培養人才”的原則,通過跨機構橫向合作,助推學術資源共享和思想生產。經過充分的討論,本著推精品、推優品的學術宗旨,口頭傳統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向內蒙古大學申請“內蒙古大學一流學科建設”經費,以資助出版一批質量較高的學術著作。我們將這批著作命名為“內蒙古大學口頭傳統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叢書”,**期擬推出《中國史詩研究學術批評(1949~2019)》《中國史詩研究學術檔案(1840~1949)》《草原文化中的馬母題意象研究》三部著作。我們后續將著手啟動第二期的出版規劃,期待將該叢書做成一個長線的項目,以提升內蒙古大學口頭傳統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的科研實力和影響力。“內蒙古大學口頭傳統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叢書”的作者主要是該中心的中青年學者們。在此,我代表內蒙古大學口頭傳統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的各位同仁,感謝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對這個項目的支持,感謝內蒙古大學一流學科建設經費的資助。由于能力和條件所限,叢書難免會有種種瑕疵,切望各位讀者方家批評指正。我們深知,叢書的出版并不意味著工作的終結。內蒙古大學口頭傳統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的工作將在已有的基礎上穩步展開,也期待各位讀者今后給予持續關注。朝戈金2020年6月8日前言1949~1999年,以中國少數民族史詩為研究主體的中國史詩學術格局奠定,中國史詩研究有了它特有的研究對象、基本問題、理論結構、不斷演進的方法體系以及其他學科難以取代的功能,而且20世紀在史詩研究領域具有深遠影響的諸多中國學者,如仁欽道爾吉、郎櫻、楊恩洪、劉亞虎等也已悉數登場。1949~1989年,中國學者以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和美學觀為主要理論支撐探討中國少數民族史詩的特征、價值以及思想性和藝術性,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績。20世紀80年代之后,各種與史詩有關的外國理論開始陸續被介紹到國內,幾十年里被擱置的學術觀點也被重新提出。一時間,滿園花開,中國的史詩研究變得熱鬧非凡,中國少數民族史詩、荷馬史詩、印度兩大史詩和其他世界史詩都得到了熱烈的討論,其中又以中國三大史詩的研究*為突出。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黑格爾、伏爾泰和維柯等對史詩的論述開始被頻頻引用,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和國外其他各種與史詩相關的論述并存的研究局面。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學術事件是20世紀90年代海西希對蒙古史詩母題、類型的研究和弗萊的原型批評理論傳到中國,國內史詩研究者開始把它們運用到對中國少數民族史詩的主題、類型、母題的結構特征及其文化歷史意蘊的研究中。當然,除了理論譯介,還有一些重要的國際史詩研究著作被介紹到中國,如涅克留多夫的《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詩》、石泰安的《西藏史詩和說唱藝人》等。這些國際史詩研究理論和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給中國學者認識和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史詩提供了理論利器和研究范式。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學者開始突破西方的古典文藝理論及經典作家史詩概念的框架,從“英雄史詩”的范疇中拓展出“創世史詩”和“遷徙史詩”兩種史詩類型,豐富了世界史詩寶庫,使得史詩在文類的界定上具有了一種新的維度。為了在21世紀能夠更好地砥礪前行,回顧和總結1949~1999年中國史詩研究的歷程是史詩研究的題中之義。這也是我們編著《中國史詩研究學術檔案(1949~1999)》的學術初衷。這里僅擇其犖犖大者,對1949~1999年的中國史詩研究進行粗線條的梳理和述評,并總結與反思其間得失。一 發現與搜集:1949~1966年的史詩研究1950年,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在北京成立,將民間文學的搜集和整理作為工作宗旨:“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國民間的文學、藝術,增進對人民的文學藝術遺產的尊重和了解,并吸取和發揚它的優秀部分,批判和拋棄它的落后部分,使有助于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建設。”自此,中國學人開始對全國的民間文學展開搜集,中國各民族史詩作為中國民間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被納入了搜集的范疇。1956年,老舍作為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理事長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上作了《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高度評價《格斯爾的故事》是“優美的富有神奇性的人民文學著作,應當列入世界文化寶庫”,并對民族文學的搜集、整理和翻譯等提出了應該遵循的原則、方法以及其他應該注意的相關事項。1958年,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制訂了編選“中國歌謠叢書”和“中國民間故事叢書”的計劃,由中共中央宣傳部下發給各省、區、市黨委宣傳部,其中劃入民間故事范疇的史詩有《格薩爾》《苗族古歌》《梅葛》等,內蒙古自治區、青海省、貴州省和云南省分別負責《格斯爾》《格薩爾》《苗族古歌》《梅葛》的定稿及寫序工作。由此,中國學人開始對國內各民族史詩展開有目的、有計劃的搜集,《格薩爾》《江格爾》《瑪納斯》《苗族古歌》《阿細的先基》《梅葛》等諸多史詩被相繼發現,對它們的搜集、整理以及出版等工作有了一定的規模。至20世紀60年代,青海地區已經搜集《格薩爾》19部74個異文本,由藏文漢譯過來的《格薩爾》有29部53個異文本。華甲收藏的《格薩爾王傳》(貴德分章本)由王沂暖、華甲漢譯出來,發表在《青海湖》雜志上。1962年,青海省民間文學研究會翻譯整理的《格薩爾4·霍嶺大戰上部》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是當時專享公開出版的漢譯本《格薩爾》。蒙古族英雄史詩的搜集整理成果較多。琶杰演唱的近80小時的《格斯爾》被記錄下來,而且謄寫成了文字。1959年,其木德道爾吉將琶杰演唱的《英雄格斯爾可汗》整理出來,交由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安柯欽夫將琶杰演唱的《英雄格斯爾可汗》漢譯出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這是當時公開出版的**部《格斯爾》漢譯本。1960年,桑杰扎布將北京木刻本《格斯爾傳》漢譯,交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50年,邊垣編寫的《洪古爾》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又于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再版。1958年,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13部回鶻式蒙古文《江格爾》。1964年,13部《江格爾》以托忒蒙古文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1960年,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英雄史詩集》,收入《鎮壓蟒古思的故事》《巴圖烏力吉巴托爾》《忠畢力格圖巴托爾》等5部小型蒙古族英雄史詩。隨后幾年,內蒙古蒙古語言文學研究所編印了內部資料《英雄史詩(一)》和《英雄史詩(二)》。《瑪納斯》的搜集整理成果也不少。1955~1957年,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調查組和中央民族學院的工作組先后兩次深入柯爾克孜族地區進行語言調查,搜集了《瑪納斯》的許多片段。1961年,《賽麥臺依》中的“賽麥臺依與阿依曲萊克”一章由中國作家協會新疆分會民間文學組和中央民族學院柯爾克孜語實習組合作翻譯,在《天山》雜志的第1、2期上刊發出來。1961年春,新疆《瑪納斯》工作組成立,集合了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語言文學研究所、中央民族學院等諸多單位的學人。至1961年底前,他們對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的史詩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搜集,記錄了《瑪納斯》的各種變體,約有25萬行。1961年,新疆文聯將居素普·瑪瑪依**次演唱的《瑪納斯》口頭文本譯成漢文,作為內部資料使用。1961年12月14日、15日的漢文版《新疆日報》發表了居素普·瑪瑪依演唱的片段《闊闊托依的祭奠》。1962年,新疆《瑪納斯》工作組搜集翻譯整理了居素普·瑪瑪依演唱的《凱耐尼木》中的一節,刊發在《民間文學》第5期上。南方各民族史詩的搜集整理成果也被陸續出版。1955年,仰星將在貴州清水江一帶搜集到的《蝴蝶歌》整理出來,發表在《民間文學》第8期上。1958年,中國作家協會貴州分會內部編印了《民間文學資料(第四集)·黔東南苗族古歌(一)》,包括了《開天辟地》《鑄撐天柱》《造日月》《種樹》《砍楓木樹》《十二個蛋》《兄妹開親》等13首古歌。以潘正興演唱的材料為主,綜合其他歌手的演唱材料,云南省民族民間文學紅河調查隊整理翻譯了《阿細的先基》,于1959年將它交給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59年9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云南省民族民間文學楚雄調查隊搜集整理翻譯的《梅葛》。1960年3月,云南省民族民間文學麗江調查隊將翻譯整理的《創世紀》交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貴州省民間文學工作組將楊芝、馬學明等歌手演唱的《洪水滔天歌》整理出來,刊發在《民間文學》1960年第10期上。1964年5月,以藍海祥唱譯的《密洛陀》為基礎,以后來搜集到的材料為輔,莎紅整理出了《密洛陀》,于1965年將它刊發在《民間文學》第1期上。20世紀50~60年代中國各民族史詩的搜集整理存在不關注史詩歌手的相關情況以及演唱語境等現象,對中國各民族史詩做出了增添、刪除、改動等諸多不科學、不規范的格式化行為。**,按照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原則對各民族史詩的內容進行改編。如云南省民族民間文學麗江調查隊在整理納西族《創世紀》時刪掉了宣揚東巴“消災禳禍”威力的詩行,云南省民族民間文學紅河調查隊刪掉了《阿細的先基》中祭神拜佛等一些混雜著迷信色彩的內容。第二,剔除重復的詩行和內容,認為它們是不必要的重復,有損史詩的藝術性。在整理流傳在貴州清水江一帶苗族地區的古歌《蝴蝶歌》時,仰星刪除了他認為不必要的重復的詩行,使詩歌前后銜接更為緊湊。云南省民族民間文學紅河調查隊認為重復的詩行妨礙突出作品的主線,延緩了情節的發展和推進,因此在整理過程中對許多重復的詩行進行了刪節。第三,對同一首史詩展開多次搜集記錄,然后將這些材料進行綜合整理,匯編出整理者認為完整的一首史詩,如云南省民族民間文學麗江調查隊搜集整理的納西族《創世紀》。有時,一些中國學人以某一次搜集記錄的史詩演唱材料為底本,綜合與這首史詩相關的其他材料,整理出一首史詩,如云南省民族民間文學紅河調查隊搜集整理的《阿細的先基》。雖然在搜集整理等諸多工作環節上存在不少問題,但是不可否認,20世紀50~60年代中國各民族史詩搜集整理的成果是顯著的。鐘敬文曾說:“建國后,我們這方面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但是,不可諱言,它也存在著明顯的缺點或不足之處。在搜集、整理方面我們有較大的成就,特別是發現和刊行了許多兄弟民族的民族史詩。這是世界文學目前的一宗收獲。但是,在記錄、整理的忠實性方面始終存在著一些問題。”也就是說,這一時期中國各民族史詩搜集整理的學術實踐值得我們借鑒和總結。而且中國各民族史詩的發現與搜集打破了以前言必稱希臘史詩和印度史詩的囿限,有力地反駁了黑格爾提出的關于中國沒有民族史詩的論斷。20世紀50~60年代是中國史詩研究的資料建設時期,學術性的論文較少,大多是搜集者在“文藝從屬于政治,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文藝政策下對搜集工作的感想和為出版的史詩撰寫的序言,較為重要的學術論文有徐國瓊的《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黃靜濤的《〈格薩爾〉序言》、劉俊發等的《柯爾克孜族民間英雄史詩〈瑪納斯〉》、云南省民族民間文學楚雄調查隊的《論彝族史詩〈梅葛〉》等。二 史詩的起源研究:20世紀80年代的史詩研究“”期間,中國各民族史詩的搜集工作停滯了。“”結束后,黨和國家高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旗幟,提出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文藝工作方向。在這種文藝政策和思想潮流的推動下,中國少數民族史詩的搜集工作很快得到了恢復和重視,中國各民族史詩的搜集整理迎來了新的契機,呈現良好的發展勢頭,取得了許多可喜成績。與此相應,在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和美學觀的理論框架下,中國各民族史詩的研究也逐步展開,其中對史詩起源的討論較為熱烈。20世紀50年代以來,《格薩爾》的產生年代問題一直是《格薩爾》研究的主要話題之一,但是因為缺乏足夠翔實而可靠的文字證據,要確切地說出《格薩爾》究竟產生在什么年代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雖然如此,許多學者還是從史詩《格薩爾》的內容入手,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不過因為解讀的角度和出發點不同,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也是眾說紛紜。徐國瓊在《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中推測*初的格薩爾故事*有可能產生于11世紀末。毛星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認為《格薩爾王傳》約產生于11世紀前后。許多學者根據史詩所反映的歷史內容,將其產生時間推定為13世紀。由此,“宋元時期說”成為20世紀80年代討論《格薩爾》產生年代的一種主要觀點。黃文煥的《關于〈格薩爾〉歷史內涵的若干探討》提出“吐蕃時期說”,認為“《格薩爾》基本上是吐蕃人按照吐蕃時期的基本史實創作來的長篇詩體作品”。“吐蕃時期說”忽視了《格薩爾》作為民間文學自身所特有的生成規律,贊同者不多。王沂暖的《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提出“明清時期說”,指出要動態地考察《格薩爾》的形成過程。《格薩爾》的產生、流傳、演變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有著自身特有的內在規律。“吐蕃時期說”“宋元時期說”“明清時期說”對《格薩爾》產生年代給出了各自的解答,但都有著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都很難說一勞永逸地解決了這個有爭議的學術話題。隨后幾年,學界對《格薩爾》在漫長的不斷積累過程中逐步發展的觀點達成了共識,有意識地將《格薩爾》放在其自身的歷史、地理以及口頭傳統的語域里討論其形成過程。對于《江格爾》的產生年代,國內學人的見解各異。阿爾丁夫提出《江格爾》產生于13世紀以前的觀點。《江格爾》沒有反映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的歷史事實,沒有反映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西征的歷史事實,也沒有提及蒙古汗國建立的萬、千、百、十戶制度。據此,阿爾丁夫推定《江格爾》的產生和基本形成年代不可能晚于13世紀初,即不晚于1206年。齊木道吉等編著的《蒙古族文學簡史》采納了這種觀點。色道爾吉也推測《江格爾》產生于四部衛拉特中的土爾扈特部,然后流傳于國內外蒙古族民眾聚居地。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江格爾》產生于13世紀以后。寶音和西格在《關于史詩〈江格爾〉創作于何時何地的問題》里提出《江格爾》產生于衛拉特蒙古部落遷徙到新疆阿爾泰山建立四衛拉特聯盟時期,即脫歡和也先統治的15世紀。仁欽道爾吉主張《江格爾》產生于13世紀以后。他從文化淵源、社會原型、詞匯和地名、衛拉特人的遷徙史、宗教形態、流傳情況等方面綜合闡發,指出《江格爾》成為長篇英雄史詩的上限是15世紀30年代早期四衛拉特聯盟建立以后,下限是17世紀20年代土爾扈特部首領和鄂爾勒克率部眾西遷以前,在這200年內《江格爾》的主要部分業已形成。仁欽道爾吉還否定了《江格爾》的“烏孫起源說”,批評了劉嵐山在沒有掌握任何材料的情況下,僅根據色道爾吉《江格爾》漢譯本中的“昆莫”便推斷《江格爾》有烏孫歷史的影子的做法,駁斥了格日勒扎布通過字形、字音、字義把《江格爾》與烏孫歷史聯系起來的假設,認為劉嵐山的觀點“忽視蒙古族本身的歷史和文化發展,忽視中央亞細亞地區整個蒙古和突厥英雄史詩的發展規律,企圖把《江格爾》同現有衛拉特人和蒙古民族分開”。同時,仁欽道爾吉反對那種把四衛拉特人和蒙古民族分開而否認新疆衛拉特人對《江格爾》的創作權的觀點,進而否定了《江格爾》產生于13世紀以前的觀點。對《瑪納斯》產生年代的討論也是眾說紛紜。陶陽的“成吉思汗時代形成說”闡述了《瑪納斯》消化和吸收了成吉思汗時代前后柯爾克孜族的歷史事實。胡振華認為《瑪納斯》于10~12世紀形成。張宏超的“10~16世紀形成說”認為《瑪納斯》產生于柯爾克孜人遷徙到天山地區以后,下限是柯爾克孜人伊斯蘭化之前,即形成年代不會超過16世紀。這個學術論爭一直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白多明和張永海的“遼代形成說”指出《瑪納斯》大約產生于11世紀,史詩中的“北京”即契丹首都臨潢。郎櫻依據居素普·瑪瑪依和艾什瑪特的《瑪納斯》唱本內容,結合柯爾克孜族的歷史發展情況,推斷《瑪納斯》**部基本形成于13~16世紀,而《瑪納斯》的其他七部基本形成于16~18世紀。這些對史詩生成年代的討論大多從各民族的歷史、史詩的基本內容等方面出發推斷史詩的產生年代。孰是孰非,一時之間難以給出一個定論,而在接下來的20世紀90年代乃至21世紀初期,對史詩生成年代的討論逐漸轉向對史詩生成過程的討論,側重考察史詩形成、發展與演變的內在規律,如巴·布林貝赫的《蒙古英雄史詩的詩學》、仁欽道爾吉的《蒙古英雄史詩源流》和陳崗龍的《蟒古思故事論》。在20世紀80年代的史詩研究過程中,格薩爾其人也成為當時學術論爭的焦點。較早對格薩爾其人展開歷史研究的中國學人應該是任乃強。參證《宋史·吐蕃傳》、西夏史等典籍的記載,任乃強推定格薩爾是林蔥土司的先祖,即唃廝啰。1979年,王沂暖肯定了格薩爾是一個歷史人物,批評了格薩爾的關羽說和外借說,對任乃強提出的格薩爾是唃廝啰的觀點進行了論證和闡發。1982年,開斗山和丹珠昂奔對格薩爾其人的“歷史人物說”、“外族說”和“先有模特兒,后成文學形象說”進行了述評,將《格薩爾》內容與史料互相參證,傾向于支持格薩爾是唃廝啰的觀點,但沒有對唃廝啰是否為林蔥土司的祖先給予學術論證。上官劍璧提出了格薩爾是林蔥土司祖先的觀點,根據《格薩爾》的內容和流傳區域以及藏文典籍等多方面的資料論證了格薩爾與林國的關系。隨后,王沂暖支持上官劍璧的說法,認為格薩爾應該是林國的首領。1984年,吳均否定嶺·格薩爾是唃廝啰的觀點,提出了格薩爾是以林蔥地方的首領為模特兒發展而來的觀點。格薩爾是藏族民眾創作出來的藝術形象,將他與藏族歷史上的人物過分比附是不科學的,不能將他與藏族歷史上的英雄人物等同起來,他應該是一個綜合了藏族歷史上諸多英雄人物特征的典型人物。對格薩爾其人的探討,應該將歷史研究與文學藝術形象的創作規律結合起來。另外,20世紀80年代,以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從內容與形式的對立統一出發,結合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依據文學具體形象地反映社會生活的觀念,寶音和西格的《談史詩〈江格爾〉中的〈洪格爾娶親〉》、色道爾吉的《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王沂暖的《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索代的《試談〈格薩爾王傳〉的社會內容》、劉發俊的《論史詩〈瑪納斯〉》、周作秋的《論壯族的創世史詩〈布洛陀〉》等許多研究成果對中國各民族史詩展開了美學分析,闡釋其思想性和藝術性,挖掘其社會文化內涵。這一時期,中國學人還拓寬了國際學界的史詩概念,提出了“創世史詩”的史詩類型,豐富了世界史詩的寶庫。三 情節類型研究與比較研究:20世紀90年代的史詩研究在“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的文藝政策下,國外的各種詩學理論陸續被引入國內。一時間,中國的史詩研究變得熱鬧非凡,巴·布林貝赫、仁欽道爾吉、郎櫻、楊恩洪、劉亞虎等中國學人悉數登場,挑起了20世紀90年代史詩研究的大梁,開創了90年代中國史詩研究的新局面。在尼·波佩、海西希的蒙古英雄史詩母題研究的影響下,情節結構類型的研究成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史詩研究的一個重要學術話題。以海西希的母題分類法為指導,仁欽道爾吉創造了“英雄史詩母題系列”的概念。“英雄史詩母題系列”是蒙古英雄史詩中共有的基本情節,它們“各有著自己的結構模式,都有一批固定的基本母題,而且那些母題有著有機的聯系和排列順序”。仁欽道爾吉從眾多的蒙古英雄史詩中抽繹歸納出婚姻型母題系列和征戰型母題系列兩種基本的英雄史詩母題系列。他觀察到所有蒙古英雄史詩都是使用不同數量的母題在這兩種母題系列的統馭下以不同的組合方式構成的,并根據母題系列的內容、數量和組合方式的不同把蒙古英雄史詩分為單篇史詩、串連復合型史詩和并列復合型史詩三大類型。在確立婚姻型母題系列和征戰型母題系列是蒙古英雄史詩核心情節單元的基礎上,仁欽道爾吉探討了整個蒙古英雄史詩情節結構的發展規律和人物形象的發展規律。他對在中國境內記錄的全部中小型英雄史詩及其異文共113種文本進行了研究,闡釋這些史詩文本的共性和特性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及其形成過程。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前提下,仁欽道爾吉把這些材料作為一個整體來探尋它們的內在聯系,從中抽繹出兩種帶有普遍意義和規律性的母題系列,以它們為核心分析研究蒙古英雄史詩的各種發展形式,由此使蒙古英雄史詩情節結構的發展規律在空間性和時間性上得到了一種整體性的解釋。英雄再生母題的一種特殊類型——英雄入地母題不僅廣泛存在于突厥語族的民間敘事文學中,還存在于許多民族的民間文學作品中。郎櫻的《英雄的再生——突厥語族敘事文學中英雄入地母題研究》推定這個母題的原型是“英雄追趕妖魔入地,鷹馱英雄返回地面”,并對它的文化內涵和象征意義進行了較為科學的闡述。她分析了“英雄入地是由于朋友或兄長的背叛”和“英雄斬蟒救鷹雛,大鷹報恩將馱英雄歸返地面”兩個英雄入地母題的亞母題類型,指出它們是英雄入地這一古老母題不斷擴充、發展和派生的結果。郎櫻的《瑪納斯形象的古老文化內涵——英雄嗜血、好色、酣睡、死而復生母題研究》揭示了英雄嗜血母題、英雄好色母題、英雄酣睡母題、英雄死而復生母題的文化內涵與象征意義,以及初民崇信順勢巫術與交感巫術的原始思維方式和思維邏輯,闡述了以柯爾克孜族民間文化為根基的《瑪納斯》文化源流的悠久性與古老性。這些母題的研究對于正確分析瑪納斯形象,深入研究《瑪納斯》的歷史文化內涵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此外,卻日勒扎布的《書面〈格斯爾〉的故事情節與結構類型》利用世界各地收藏的《格斯爾》手稿或抄本,特別是近年來中國搜集到的藏文、蒙文《格薩(斯)爾》的豐富資料,對書面《格斯爾》的故事情節與結構類型做了深入的探討。斯欽巴圖的《蒙古英雄史詩搶馬母題的產生與發展》闡述了蒙古族游牧社會的歷史、經濟、政治、軍事、信仰等與搶馬母題的聯系,指出搶馬母題是蒙古族古代氏族部落間經濟掠奪及經濟軍事雙重性掠奪的反映,同時分析了搶馬母題的符號化及其象征意蘊。烏日古木勒的《蒙古史詩英雄死而復生母題與薩滿入巫儀式》指出蒙古族史詩中英雄死而復生母題起源于薩滿入巫儀式或成年禮。史詩母題的研究雖然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是主要集中在蒙古族英雄史詩、柯爾克孜族史詩以及其他突厥語族的史詩上,南方各民族史詩的母題研究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視,不同史詩傳統的母題索引尚待編制,史詩母題蘊藏的社會、歷史、文化的深層含義有待進一步挖掘。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學界專注于從比較研究的角度對藏族《格薩爾》和蒙古族《格斯爾》的產生時代、流傳過程、情節內容、藝術特點等進行綜合研究。實際上,對這一話題的研究可以回溯到20世紀50~60年代。1959年,徐國瓊就簡要地指出了《格薩爾》與《格斯爾》的異同點,但沒有明確兩者的源流問題。1960年,桑杰扎布明確提出了先有藏族《格薩爾》,后有蒙古族《格斯爾》的觀點。而后,王沂暖認為,蒙文本《格斯爾》既有從藏文本《格薩爾》翻譯過去的東西,也有根據藏文本《格薩爾》部分情節發展創作的內容。對這一話題的討論一直延續到20世紀90年代,徐國瓊、烏力吉、降邊嘉措、王興先、斯欽孟和、卻日勒扎布、趙秉理等許多學人都對《格薩爾》和《格斯爾》的關系問題發表了自己的見解。經過一系列的討論,學界基本形成了一個共識,即《格薩爾》*早在藏族民眾中流傳,后來在流傳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格斯爾》等諸多其他文本。《格薩爾》和《格斯爾》比較研究為《格薩(斯)爾》的傳承與發展做出了可貴的探索,論述了藏族《格薩爾》和蒙古族《格斯爾》的文化內涵及其承載的獨立價值、民族精神與審美理想,進而揭示了藏族和蒙古族文化的相互關系及其內在規律,這些對于正確理解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下蒙藏文化的互動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還需要提及的是“中國史詩研究”叢書,它包括《〈格薩爾〉論》《〈江格爾〉論》《〈瑪納斯〉論》《南方史詩論》《〈江格爾〉與蒙古族宗教文化》等。這套叢書對中國史詩的總體面貌、重要文本以及重要的史詩歌手等進行了較為系統的闡述,對許多較為重要的史詩理論問題展開了深入的探討,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反映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各民族史詩研究的成就和水平。此外,卻日勒扎布的《蒙古〈格斯爾〉研究》(1992)、扎格爾的《史詩〈江格爾〉研究》(1993)、楊恩洪的《民間詩神——格薩爾藝人研究》(1995)、賈木查的《史詩〈江格爾〉探淵》(1996)等許多學術價值較高的研究成果相繼問世,它們對中國史詩研究的某些專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系統的探討。簡而言之,1949~1999年的史詩研究奠定了中國史詩學的基本格局,為中國史詩研究理論體系的創建打下了扎實的基礎,標志著中國史詩研究逐步走向成熟。本書擇選了撰寫于1949~1999年的11篇具有代表性的、產生過較大影響的關于史詩討論的文章,不僅涉及中國三大史詩《格薩(斯)爾》《瑪納斯》《江格爾》,還涉及南方各民族史詩以及域外史詩。其中,有的專論史詩的人物形象,有的專論史詩的說唱藝人,有的專論史詩的母題和類型,有的著力于史詩的比較研究,等等。對于這些文章,本書或以全文轉載的形式,或以節錄的形式,將原作忠實地呈現,并附有“評介”。出于種種考慮,本書對佟錦華的《格薩爾王與歷史人物的關系——格薩爾王藝術形象的形成》和季羨林的《〈羅摩衍那〉在中國》做存目處理。在整理學者們文章的過程中,為了方便檢索,本書在每一篇學者原作的結尾都注明了文章的出處。其中,饒宗頤、季羨林、陶陽和鐘秀的文章節選自其著作,其余學者的文章均依據其首發期刊版本整理。為了充分尊重原作,也為了讓讀者更好地了解原作的原貌,本書除了對個別訛錯明顯又影響文意的地方稍作改動外,原作中人名、地名、書名、譯名、注釋,彝文、藏文、希臘文等單詞,以及部分脫、衍、訛、倒之處,皆一仍其舊。原文有拿捏不準的地方,因編者學識有限,一律保持原文。原作中雙引號和書名號之間的頓號亦保持原狀。凡排印漏誤、容易引起歧義的文字,在不影響原意的基礎上均徑改,不出校記。同時,為方便當代讀者閱讀,本書對原作中的個別標點符號、異體字等進行了規范處理。當然,受各種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的,本書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不完善之處,還請眾方家不吝指正!*后,需要特別感謝的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編輯工作者們!趙娜女士作為責編,在本書的編校出版過程中貢獻了專業的學術智慧和大量的辛勤勞動,她的愛崗敬業令人敬佩!同時還要感謝內蒙古大學口頭傳統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的各位同仁和領導的支持和幫助!預祝各位讀者有愉快的閱讀體驗!
中國史詩研究學術檔案(1949-1999) 目錄
中國史詩研究學術檔案(1949-1999) 作者簡介
馮文開,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史詩學與口頭傳統研究。 云韜,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博士,長期從事20世紀中國文學與文論、民族民間文學研究。
- >
【精裝繪本】畫給孩子的中國神話
- >
煙與鏡
- >
羅曼·羅蘭讀書隨筆-精裝
- >
史學評論
- >
山海經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
- >
有舍有得是人生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歷史與人類學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