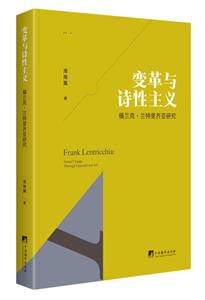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變革與詩性主義:福蘭克·蘭特里齊亞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1742292
- 條形碼:9787511742292 ; 978-7-5117-4229-2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變革與詩性主義:福蘭克·蘭特里齊亞研究 本書特色
系統評述美國文學批評家、意大利裔作家福蘭克·蘭特里齊亞(Frank Lentricchia)的文學觀和文學批評思想
變革與詩性主義:福蘭克·蘭特里齊亞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系統評述美國文學批評家、意大利裔作家福蘭克·蘭特里齊亞(Frank Lentricchia)的文學觀和文學批評思想,探討其文化政治詩學和詩性主義的特征,分析其小說創作實踐與風格,闡明他對美國意大利裔文學與文化研究的貢獻。蘭特里齊亞強調文學與文學批評的歷史性、政治性和社會功能,但他也反對將藝術過分政治化,強調藝術詩性主義。他的小說將文化政治與詩學巧妙結合在一起,小說被賦予對抗各種形式的權力、改變大眾意識、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具有浪漫主義色彩。蘭特里齊亞的文化政治詩學,對當今文學創作及研究具有啟示作用。
變革與詩性主義:福蘭克·蘭特里齊亞研究 目錄
目錄
引言 / 1
**章藝術的文化政治學 / 12
**節形式主義美學批判 / 12
一、文學學科的自主性與歷史性 / 14
二、二元對立傳統的消解 / 22
三、作為終極解釋的福柯與歷史意識 / 27
第二節批評與社會變革 / 32
一、文學批評的社會功能 / 32
二、挑戰文化傳統和霸權 / 37
三、作為政治力量的修辭 / 42
第三節藝術的精靈與詩性主義 / 46
一、福柯權力論和新歷史主義視野下的主體 / 47
二、新舊實用主義與理論視野下的個體性和獨特性 / 51
三、詩性主義的精靈 / 57
第二章文化政治學的藝術表述 / 62
**節蘭特里齊亞小說的暴力敘事 / 62
一、顯性暴力敘事的文本表征 / 65
二、隱性暴力敘事中的壓制與反抗 / 68
三、文學藝術家越界的渴望 / 76
00|
變革與詩性主義:福蘭克·蘭特里齊亞研究
目錄|00
第二節美國意大利族裔性的書寫與超越:《煉獄之聲》 / 81
一、美國意大利裔的族裔符號與顛覆 / 83
二、書寫與改寫美國意大利族裔性 / 91
三、美國意大利族裔性的超越 / 96
第三節父權文化下男性身份的書寫與跨界:《臨時抬棺人》 / 104
一、父權文化下男性“被女性化”的文化塑造過程 / 105
二、男性“被女性化”現象在意大利族裔問題上的象征寓意 / 109
三、身份解構下男性“被女性化”文化現象的藝術改寫 / 115
第四節女性書寫中的多元交集、賦能與反抗 / 120
一、男性政治中打破沉默的母親 / 122
二、消費社會中拒絕被物化的繆斯 / 126
三、多元交集下反抗暴力的女俠 / 130
第三章文化政治詩學的主體 / 138
**節文學創作中的藝術家:《盧凱西與白鯨》 / 138
一、文學創作與自我 / 139
二、文學創作與現實生活 / 142
三、文學創作的自主性 / 149
第二節后現代空間里的藝術家:《路得記》 / 151
一、后現代網絡關系下的空間流動 / 153
二、后現代空間網絡中的藝術家 / 158
三、后現代空間里藝術家的主體性 / 163
第三節現代傳媒技術與消費文化中的藝術家:《意大利
女演員》 / 166
一、歷史文本創造的圖像 / 168
二、現代傳媒技術下圖像社會創造的神話 / 171
三、視覺消費文化中藝術家的社會責任 / 177
第四章文化政治詩學的文本藝術 / 182
**節蘭特里齊亞小說的文類與語言策略 / 182
一、蘭特里齊亞小說中的戲劇 / 183
二、文類的轉換 / 187
三、多元化的語言風格 / 191
第二節《刀手》的敘事技巧與策略 / 194
一、《刀手》的敘事結構和時空轉換 / 195
二、《刀手》的敘事視角與轉換 / 206
三、《刀手》的人物設計與象征含義 / 212
第三節《盧凱西與白鯨》的文學批評 / 217
一、以小說人物詮釋《白鯨》 / 219
二、以小說敘事結構詮釋《白鯨》 / 222
三、小說中的文學評論文本 / 224
第四節《安東尼奧尼的憂傷》的電影元素 / 236
一、閃前和閃回突出回憶敘事 / 239
二、長鏡頭和跳切表現時限性 / 244
三、場景畫面強調獨特性 / 248
第五章超越自我:一位充滿反叛激情的批評家和詩性的藝術家 / 257
**節從反叛的激情到詩性的自我 / 257
第二節文學悟性、創新與超越 / 260
引用文獻 / 264
后記 / 284
變革與詩性主義:福蘭克·蘭特里齊亞研究 節選
引言 福蘭克?蘭特里齊亞(Frank Lentricchia,1940— )是美國著名文學評論家、小說家,在研究詩歌、現代主義、批評理論史以及小說創作等領域頗有建樹。他的文學評論著作引起批評界的熱烈討論,被許多美國大學列為研究生的必讀參考書。他本人被認為是與愛德華?賽義德(Edward Said)一樣帶有對抗性的知識分子式批評家(Salusinszky, 1987; Xu,1992),與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一樣,都是帶著叛逆傾向、追求自我塑造和自我表征的知識分子(Fjellested 863—874),躋身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弗列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杰拉爾德?格拉夫(Gerald Graff)等新左派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之列(楊仁敬653—661)。他的小說創作深受美國著名作家唐?德里羅(Don DeLillo)和紐約文學圈著名的編輯和評論家格爾登?利什(Gordon Lish)等人的好評,喜歡他的粉絲更是奉之為美國重要文學潮流里的硬通貨,是必讀作品(Jackson 13)。 蘭特里齊亞出生于美國紐約州尤蒂卡(Utica)的一個意大利移民家庭,無論在文學和批評理論研究方面,還是文學創作上,都深受其家庭、教育環境及其意大利裔身份的影響。蘭特里齊亞的父母都是意大利南部移民二代,為維持家庭生計,八年級后就都離開學校到工廠工作,生活艱辛。他們自身文化程度不高,但非常重視對蘭特里齊亞的教育,他的母親常以自己為反面例子,鼓勵他一定要上大學。1962年,蘭特里齊亞從尤蒂卡大學畢業后,懷著對文學的熱愛來到杜克大學深造,1963年獲得碩士學位,1966年獲得博士學位,由此開始文學批評之路。他*具影響力的批評著作包括《新批評之后》(After the New Criticism,1980)、《批評與社會變革》(Criticism and Social Change,1983)、《精靈與警察:米歇爾?福柯、威廉?詹姆斯、華萊士?斯蒂文斯》(Ariel and the Police: Michel Foucault, William James, Wallace Stevens,1988)、《藝術的犯罪與恐怖》(Crimes of Art and Terror,2003,合著)等。蘭特里齊亞的批評理論受到美國學界的肯定,也引起爭議,甚至被新保守派唾罵。 00| 變革與詩性主義:福蘭克?蘭特里齊亞研究 引言|00 追溯蘭特里齊亞的學術生涯可以發現,他在很多方面算得上是美國文學研究傳統的反叛人物,但從中也看到一條反叛和回歸的有趣軌跡。可以說,蘭特里齊亞以形式主義美學的視角開始文學之旅。他從大學時代起就對現代詩歌產生興趣,在碩士畢業論文里評述美國對詩人拜倫的文學評論,并在博士畢業論文里研究葉芝和斯蒂文斯的詩歌。然而,在批評理論盛行之前,蘭特里齊亞就開始涉足批評理論,將文學批評放置在歐洲哲學語境里。早在20世紀60年代中葉,他深受喬治?布萊(George Poulet)、現象學(phenomenological) 或“意識”批評學者(“consciousness” critics)及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早期著作的影響,與他們的思想產生共鳴,渴望批評界能夠重新重視文學中的“人”。他的**部著作《語言的狂歡:葉芝與斯蒂文斯的激進詩學》(The Gaiety of Language: An Essay on the Radical Poetics of WBYeats and Wallace Stevens,1968)具有強烈形式主義美學特點,他不僅從形式主義美學角度分析葉芝和斯蒂文斯的詩學,而且追溯康德與后康德哲學思想對19世紀文學產生的影響。 這部書體現了貫穿蘭特里齊亞學術生涯的兩大元素:語言帶來的愉悅和藝術家的激進主義傾向。他在書中說:我們理性的頭腦知道詩歌是成年人的童話,更知道童話與否并不重要,于是放縱“沉浸在詩歌媒介的狂歡里”(Gaiety 192)。這種思想的形式主義美學特點過于濃厚,他后來對此也漸漸產生懷疑。然而,質疑并不等于完全推翻。即便在他后來反思形式主義美學并且反叛這一傳統時,他仍然在心里存留它的重要性。他在1987年的一次訪談里表示,我們不可能完全擺脫形式主義美學,也不應該完全拋棄它。盡管文本與歷史密不可分,不應將文本和歷史割裂開,但形式主義美學仍可以起作用,它為我們“描寫語言文字的細微發展變化,密切觀察這些發展變化所包含、表達或涉及的歷史”(Salusinszky 187)。形式主義美學像平衡桿的另外一頭,一直牽制著蘭特里齊亞的激進主義批評意識,并且在他后來發現批評理論的發展局限時起到一定作用。這就是蘭特里齊亞對“沉浸在詩歌媒介的狂歡里”的發展性解釋,與形式主義美學批評有一定差異,包含他后來激進主義文化政治詩學的傾向。 蘭特里齊亞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加利福尼亞大學歐文分校擔任助理教授期間,出版著作《羅伯特?弗羅斯特:現代詩學與自我的景觀》(Robert Frost: Modern Poetics and the Landscapes of Self,1975)。蘭特里齊亞的研究比其他人提早幾十年回歸到美國現代文化的主體及其歷史淵源上,他在書中將弗羅斯特與艾略特、斯蒂文斯和葉芝相提并論,特別關注自我與主體性、創造性、“意識的特殊藝術行為”(16)或塑造行為,以及個人內在與外在的互動關系。這部書與《語言的狂歡》一樣,滲透著現象學和存在主義思想。然而,這部著作體現了蘭特里齊亞此后一直反復思考的主題:一方面,詩人受到歷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教育影響,上述種種因素不斷塑造詩人,并對詩人產生壓迫;另一方面,詩人以其創造性想象力對外界實施改變和影響作用。在這個過程中,蘭特里齊亞從原來關注詩人的“激進詩學”,發展為關注詩人激進的自我:他特別聚焦詩人在實施變革和暴力沖擊等方面的能動性。但*終,他必須面對的問題是:詩人誕生于塑造詩人自我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語言)等因素,置身這個框架體系里面,該如何突破種種限制和影響因素,反過來去改變它們。在書中,蘭特里齊亞使用一些含義相近的詞,反復強調驅動詩人的是創造力和想象力,若要更深入追問,則驅動詩人超越限制的,是某種根本的力量或創造性的能量、原始沖動和能量、創造性的意識等。蘭特里齊亞受斯蒂文斯的影響頗大,在這部著作里首次提到斯蒂文斯的觀點,即詩人內心存在一種與“外在的暴力”相稱的“內在的暴力”(149)。 蘭特里齊亞常常反思并質疑自己的思想,發現自己作品中的不足之處。他會從相反的角度思考問題,有時甚至推翻以前的思考。他在一次訪談中承認,“這是我生命中的一個主題; 我一發現自己總在重復某個相同的寫作方式,就一定要去找別的事情做,才能保持濃厚的興趣”(Depietro 16)。其實,與其說他是為了讓頭腦持續保持高度敏銳,不如說是他那富于批評性思維的頭腦在工作。 在歐洲理論對美國產生重大影響時,蘭特里齊亞開始深入反思形式主義美學的強大影響,對新批評之后的批評理論展開批判。20世紀70年代的學術氛圍為蘭特里齊亞的思想提供了背景。現代語言協會(MLA)主席路易斯?坎普(Louis Kampf)曾在1971年年會講話中聲稱:文學如果沒有直接與政治行動聯系起來,就只是一種“消遣”,“小把戲”或“游戲”,他號召大家起來參與到“激進的社會變動”中 (Strandberg 1)。似乎是響應坎普的呼吁,70年代中葉,文學理論在美國迅速發展起來。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歐文分校,穆瑞?克利格(Murray Kreiger)與哈澤德?亞當斯(Hazard Adams)創立了批評與理論學院(School of Criticism and Theory),吸引大批批評界人士前來任教。批評界一片繁榮,關于結構主義和德里達(Derrida)的書不斷出版。蘭特里齊亞開始預見未來十年批評理論的發展和繁榮,同時也敏銳地看到,對于批評理論學科的現狀和發展,批評界似乎缺乏共時性和歷時性的整體把握。因此,有必要將時興的批評理論,放置在一個歷時性框架里予以審視,1980年出版的批評論著《新批評之后》就誕生于這一思考。 《新批評之后》是在歐洲哲學語境下研究當代美國批評理論的開山之作,不僅為后來的理論研究者提供新思路,也標志著蘭特里齊亞在理論學科取得成功。蘭特里齊亞將批評理論放置在思想發展史的框架里,與過去建立聯系,批評美國文學批評界普遍存在割裂文學與社會現實的傾向,對美國學界根深蒂固的形式主義美學提出批判。可以說,這是**部綜述和評價美國當代批評理論史的著作,也是**部對二戰后批評理論的發展進行全面評論的著作,為未來的批評理論策略指出方向,極大地促進了批評理論在美國學術界的體系化。它的思想高度在美國批評界遙遙領先,該書出版之后很久,解構主義和其他包括新批評在內的許多理論流派才開始將其核心觀點與政治性和歷史性聯系起來(Salusinszky 185),紛紛撰文表明它們并非不關注政治和歷史。 將文學與政治行動聯系起來的做法,跟蘭特里齊亞的家庭背景、社會背景有關。蘭特里齊亞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來自意大利南部。意大利南部*大特點是赤貧和剝削,跟北部形成鮮明對比。他們移民美國后,都在工廠里做工,屬于典型的勞動者階層。一方面,蘭特里齊亞的祖父會寫詩,外祖父擅長講故事,蘭特里齊亞很可能繼承他們的基因,走上文學批評之路乃至后來的文學創作之路。另一方面,出身勞動者階層,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他的關注點和思維方向。他身處大學機構,研究西方經典作品,卻也深切地感到自己與學院那些出身比較好的人之間存在差異。他不僅看到自己跟別人的階層差異性,也看到作家們的階層差異性,看到作家們的種族、族裔和性別差異。他敏銳地認識到,有些文學理論是在“規避不可回避的差異性”,因此他不僅“對這類文學理論保持警惕”(182),而且刻意要將這種階層、族群差異性呈現出來。這也促使他在《新批評之后》里挑戰主流文學理論流派的霸權地位,號召文學和文學批評要積極投入改變美國社會經濟文化現狀的活動當中。可以說,在美國各族裔或群體紛紛起來為平權發聲的20世紀80年代,他以自己敏銳的思考和觀察加入這場社會文化變革大潮,成為*早將文學批評與文化批評結合的批評者之一,也促使學術界將他列為馬克思主義“新左派”文學批評家。 蘭特里齊亞到萊斯大學任職之后,于1982年出版《批評與社會變革》。這部著作深受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的影響。蘭特里齊亞在著作里強調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功能是推進社會變革。他反對文學批評脫離社會政治語境的做法,高唱文學與文學批評的政治作用,以階級、性別、族裔、文化研究顛覆傳統的經典敘事,也預見了美國文化同化進程與多元文化歷史淵源之間的矛盾。 蘭特里齊亞在探討文化、社會和知識分子的力量時,他的族裔和階級背景仍然起很大作用。他首先承認自己曾逃避和壓抑自己的社會和族裔背景,但他表示,作為一個出身于勞動者階層的知識分子,面對充滿社會、種族、族裔、階級和性別偏見的主流文化,他要重拾自己的局外人經歷,對主流文化提出批判;他要把人文主義學術理念作為一個平臺,從事“激進主義研究,引起爭議的研究,從事有目的、有隱秘政治目標的研究,承認美國文化多元性的研究,代表受貶低者、被踐踏者的研究”(Depietro 17)。顯然,蘭特里齊亞決意將意識形態和文化批評引入美國學術界,堅信文學工作者在推動變革方面能夠起到極大的影響作用。該書因再次打破學術與政治之間的界限、表現出強烈的馬克思主義傾向,受到里根時代文化右派的強烈批判,使他飽受爭議,被評論界稱為“引起文化紛爭的人”(18)。美國記者、作家和文學評論家莫林?克里根(Maureen Corrigan)在1984年初《村聲》(Village) 《村聲》是美國**個新聞周刊。作為一類著眼于文化和藝術的報紙,它是紐約市眾多作家和藝術家的平臺。 中為他起了一個綽號,稱他為“當代文學理論界的流氓哈利”。雜志還配上他的照片,他穿著緊身高爾夫球衫,兩只胳臂交叉在胸口,露出強壯的肱二頭肌,被美國意大利裔評論家認為是典型的意大利街頭硬漢形象,生動地詮釋了《批評與社會變革》的作者挑戰主流文化霸權的反叛精神。 1984年,蘭特里齊亞回到母校杜克大學任教,后來出版《精靈與警察》,與之前的兩部著作構成“批評三部曲”。在這部著作里,蘭特里齊亞關注藝術的主體在福柯和詹姆斯思想中的位置,不僅討論斯蒂文斯詩歌中體現的性別意識和經濟差異意識,而且推出詩性主義思想。正如評論者所說,“《精靈與警察》的亮點,是覆蓋和超越《新批評之后》所闡釋的哲學意義,也超越《批評與社會變革》所捍衛的批評的政治價值。這部書與其說代表批評家蘭特里齊亞的終結,不如說代表作家蘭特里齊亞的開始”(DePietro 20)。蘭特里齊亞關注“作為主體的人”,強調從事藝術創作的主體能夠在社會變革方面發揮主觀能動性,因為藝術主體的詩性主義具備活潑、自由的氣質,總在挑戰資本主義權力及機構的壓迫,在創造歷史中起到積極的建設作用。蘭特里齊亞回答了前兩部著作留下的問題:文學工作者究竟如何推動社會變革,為他將來的寫作轉向埋下伏筆。 此后短短幾年內,蘭特里齊亞相繼出版《唐?德里羅述評》(Introducing Don DeLillo, 1991)、《〈白噪音〉新論》(New Essays on White Noise, 1991)和非常暢銷的《文學研究中的批評術語》(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1990),繼續探索文學批評甚至是文學創作之路。 與此同時,蘭特里齊亞的學術生涯和個人生活危機不斷,讓他從中發現改變自己道路的契機。一方面,自1982年以來,蘭特里齊亞一直在撰寫弗羅斯特、斯蒂文斯、龐德和艾略特批評著作《現代主義四重奏》(Modernist Quartet,1994),但在寫作過程中遇到瓶頸,一直找不到理論突破,時隔12年才得以成書出版。蘭特里齊亞在著作中仍然發揮優秀的批評素養和文學悟性,對四位現代主義詩人的作品進行精彩的文本解讀;在理論觀點上,他強調四位藝術家抵制權力壓迫的反叛激情:詩人抵制文化霸權和父權文化,抵制資本主義消費文化,詩性自我及其藝術表達在推動社會變革上能夠發揮積極作用。至于如何將他所提倡的付諸實踐,要等到蘭特里齊亞自己從事藝術創作,才算是解決這個問題。 另一方面,婚姻破裂令他深受中年焦慮的困擾,渴望內心的平靜。受托馬斯?默頓(Thomas Merton)著作的影響,1991年夏,蘭特里齊亞往南卡羅來納州熙篤會修道院麥普金修道院(Mepkin Abbey)小住,尋求掙脫自我困擾的方法。離開修道院時,他受一位修道士的啟發,將自傳和一些思考記錄下來,他的自傳體小說《夜晚之畔:告白書》(The Edge of Night: A Confession,1994)也因此誕生。他撇開過去20年所做的,進入“一個全新的文學空間”,并從中看到希望,因為他感到他既是在寫“真實發生的”,又“不必拘泥于事實”,這樣就“可以探索自己的各種情感反應,可以在這一階段反思自己,探索這對我自己來說有什么意義。這很誘人,我非常享受這個過程”(21—22)。這種自傳性質的寫作促使蘭特里齊亞開始轉變寫作思路,也讓他獲得寫作的自由、自我的自由。對于他來說,寫作不僅僅是很治愈的一件事,而且讓他從智識上獲得新生,他個人也開始新的生活,——這個新生活以他和杜克大學戲劇學教授喬迪?麥考利夫(Jody McAuliffe)結婚為起點。 此時的蘭特里齊亞也開始反思文學批評界過分政治化的傾向,加快了他轉向小說創作的進程。時值20世紀90年代中葉,整個批評理論界的政治活動仍如火如荼地開展,與新保守派的辯論也在繼續。僅僅20多年,文學批評就越來越集中在批判文學中的“霸權話語”與“權力關系”上,女權主義、后殖民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在研究文學時,無論什么樣的文本,無須細讀,一律提出標準化問題,然后得出可以預測的答案(Edmundson 163)。 蘭特里齊亞深感憂慮,在1996年9、10月合刊的《通言》(Lingua Franca)雜志上發表文章《一個前文學評論者的遺愿和遺訓》(“Last Will and Testament of an Exliterary Critic”),反對文學研究中無視美學研究、過分政治化、過分夸大文學批評政治作用的勢頭,批評這場幾乎可以說是由他倡導、引領并振興的文學政治活動,在中外文學評論家界引起轟動。他在文章中提到一個給他極大觸動的事件。在一次研討會上,一個研究生的陳述使他認識到當時文學批評的嚴重問題。那個白人男學生聲稱“我們首先要明白,福克納是種族主義者”(23),由此引發熱議,也激怒蘭特里齊亞。他認為發言者對福克納作出狹隘解讀,還自以為是,表明文學研究已經被某類評論家主導,學生模仿教員,站在道德制高點上評判文學作品,將“政治正確”奉為圭臬(DePietro 154)。 蘭特里齊亞在文章中明確指出:文本解讀程序化普遍存在,其弊端在于“文本不是被閱讀,而是被預先閱讀。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X,文學研究就是揭示那個X,X即帝國主義、性別歧視主義、厭惡同性戀等等”。究其原因,許多文學批評者格外努力刻意地證明文學在世界各種權力關系的組織上扮演戰略角色(“Last Will” 59—67)。他們舍棄審美,專注于政治與文化研究,掩蓋了對文學作品品格高下的甄別,對文學與文學批評都是不利的。 此后,蘭特里齊亞有意回避鋒芒畢露的文學批評理論活動。他不再給研究生上課,開始教本科生;不談批評理論,卻以文本細讀法為起點,與學生一起體驗文字解讀并從中獲得思想的愉悅。1996年后,蘭特里齊亞一邊致力于小說創作,將自己多年的理論思想融入創作中,一邊進一步思考批評理論。2003年,他與斯坦利?豪爾沃斯(Stanley Hauerwas)共同編輯出版《來自家鄉的異見:“9?11”之后的散文》(Dissent from the Homeland: Essays after 911),與喬迪?麥考利夫合著出版《藝術的犯罪與恐怖》。他還和安德魯?杜布瓦(Andrew DuBois)共同編輯出版《文本細讀:讀者》(Close Reading: The Reader)。這三本書成為他在文學評論領域的收山之作。這位曾經以文學為政治工具的文學批評家,*終對脫離文學文本的文學批評感到非常不滿,在文學創作實踐中推行他的藝術理論。 20多年里,蘭特里齊亞在文學創作上碩果累累,體現了他的創作才華和創作激情。除了《夜晚之畔:告白書》,他的小說還包括兩部小說合集的《約翰?克利泰里/刀手》(John Critelli/The Knifemen, 1996),《煉獄之聲》 (The Music of the Inferno,1999)、《盧凱西與白鯨》(Lucchesi and The Whale,2001)、《路得記》(The Book of Ruth, 2005)、《意大利女演員》(The Italian Actress,2010)、《安東尼奧尼的憂傷》(The Sadness of Antonioni,2011)。此后,蘭特里齊亞創作了具有強烈大眾小說風格的作品,包括艾略特?孔德偵探小說三部曲《臨時抬棺人:艾略特?孔德偵探故事》(The Accidental Pallbearer: An Eliot Conte Mystery,2012)、《尤蒂卡殺狗人》(The Dog Killer of Utica,2014)和《莫雷利往事》(The Morelli Thing,2015),以及《黑暗中的位置/惡之迷惑》(A Place in the Dark/ The Glamour of Evil,2020),《曼哈頓崩盤》(Manhattan Meltdown,2021)。評論界對于蘭特里齊亞的小說創作依然是毀譽參半。有人認為蘭特里齊亞的思想和創作實踐轉向是出于一種經濟學考量(唐小兵,1997)。更多人則認為他飽含強烈的藝術激情,帶著新穎而尖銳的創作聲音,在探討族裔性、自我、地方與現代性、藝術的本質等主題上具有深度和廣度(DePietro, 2010; Gardaphé, 2003; 2006)。
變革與詩性主義:福蘭克·蘭特里齊亞研究 作者簡介
周南翼,1998年至2001年,獲得英語語言文學專業的博士學位。2001年至2003年參加楊仁敬教授主持的200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美國后現代派小說論》。2003年8月至2004年8月國家留學基金資助往美國杜克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4年至2019年主持并完成國家社科基金一般課題《福蘭克·蘭特里齊亞的文學觀與小說創作研究》。2018年1月-?2019年1月福建省留學資金資助往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訪問學者2019年6月17日-2019年7月5日在意大利羅馬參加“羅馬2019年意大利裔流散研究夏季學習研討班”。
- >
山海經
- >
企鵝口袋書系列·偉大的思想20:論自然選擇(英漢雙語)
- >
大紅狗在馬戲團-大紅狗克里弗-助人
- >
我與地壇
- >
羅庸西南聯大授課錄
- >
煙與鏡
- >
新文學天穹兩巨星--魯迅與胡適/紅燭學術叢書(紅燭學術叢書)
- >
李白與唐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