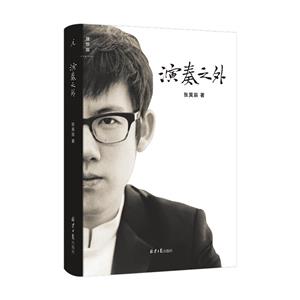-
>
東洋鏡:京華舊影
-
>
東洋鏡:嵩山少林寺舊影
-
>
東洋鏡:晚清雜觀
-
>
關(guān)中木雕
-
>
國(guó)博日歷2024年禮盒版
-
>
中國(guó)書法一本通
-
>
中國(guó)美術(shù)8000年
演奏之外 版權(quán)信息
- ISBN:9787547742723
- 條形碼:9787547742723 ; 978-7-5477-4272-3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cè)數(shù):暫無(wú)
- 重量:暫無(wú)
- 所屬分類:>>
演奏之外 本書特色
★ 青年鋼琴演奏家張昊辰首部音樂(lè)哲學(xué)隨筆 本書是青年鋼琴演奏家張昊辰寫在“演奏之外”的音樂(lè)哲學(xué)隨筆。張昊辰作為一位“90后”鋼琴演奏家,多次獲得國(guó)際大獎(jiǎng),與諸多國(guó)際著名樂(lè)團(tuán)合作,是享譽(yù)世界的中國(guó)青年鋼琴家。同時(shí),他“好讀書,善思考”,在本書中,他記錄了自己二十多年來(lái)與古典音樂(lè)為伴的思考和感悟,展現(xiàn)了當(dāng)代藝術(shù)家誠(chéng)摯而深邃的精神世界。 ★ 發(fā)現(xiàn)古典音樂(lè)背后的文化脈絡(luò),探討音樂(lè)與人的關(guān)系 在本書中,作者探討了關(guān)于古典音樂(lè)的諸多命題,包括古典音樂(lè)在歷史和社會(huì)變遷中具有的角色和地位,音樂(lè)和藝術(shù)審美的變遷及其背后的哲學(xué)意涵,以及貝多芬、勃拉姆斯、肖邦、舒伯特等重要作曲家在音樂(lè)史上留下的深遠(yuǎn)影響,還有個(gè)人在藝術(shù)與科技交織發(fā)展的時(shí)代中對(duì)新趨勢(shì)的思考……所有這些問(wèn)題,都關(guān)乎音樂(lè)與人的關(guān)系,作者作為古典音樂(lè)的“信徒”也是“使者”,想要為我們呈現(xiàn)的是一種由內(nèi)向外的思考,極度個(gè)人化又努力接近核心,引人深思。 ★ 鋼琴教育家但昭義、藝術(shù)家陳丹青、樂(lè)評(píng)家焦元溥推薦 中國(guó)著名鋼琴教育家但昭義稱,本書中張昊辰“個(gè)人獨(dú)到之見(jiàn)解,同時(shí)代中難有人可與之比肩”。藝術(shù)家、文藝評(píng)論家陳丹青則稱,“一位90后天才鋼琴家,能在演奏之外寫下這樣的思考、領(lǐng)悟、見(jiàn)解,令我驚異”。樂(lè)評(píng)家焦元溥指出,張昊辰所獲得的成就,“舞臺(tái)上的恢宏背后,更深厚的土壤還在演奏之外”。本書得到音樂(lè)、藝術(shù)領(lǐng)域?qū)I(yè)人士的推薦和認(rèn)可,為大眾讀者提供了一個(gè)走進(jìn)古典音樂(lè)的窗口。
演奏之外 內(nèi)容簡(jiǎn)介
這是一部青年鋼琴演奏家張昊辰寫在“演奏之外”的音樂(lè)哲學(xué)隨筆。在古典音樂(lè)與大眾審美存在距離的今天,作者試圖講述的是自己心目中鮮活而又深刻、細(xì)膩而又廣闊的屬于古典音樂(lè)的完美世界。從古典音樂(lè)與哲學(xué)、美學(xué)、歷史、社會(huì)的關(guān)系,到在音樂(lè)目前留下重要印跡的作曲家們的藝術(shù)人生,再到作者本人在與鋼琴對(duì)話的生涯中感知到的共鳴和張力,書中的隨筆思考看似斷章,實(shí)際上連貫地呈現(xiàn)了既是青年也是鋼琴演奏家的張昊辰對(duì)古典音樂(lè)和演奏舞臺(tái)的理解、熱愛(ài)、依戀與期待。
演奏之外 目錄
肉體與雪
聆聽(tīng)的三種空間
歷史與回歸
康德的矛盾
看不見(jiàn)的博物館
敘事的神話
失落的真相
個(gè)人與歷史
言說(shuō)背后
異鄉(xiāng)的世界
肖邦與鋼琴
維也納的孩子
機(jī)器復(fù)制時(shí)代的音樂(lè)
就此一別
訪談
天生喜歡復(fù)雜感
模仿與刻意
音樂(lè)之外
流行與批判
演奏之外 節(jié)選
肖邦與鋼琴 年幼學(xué)琴,腦中沒(méi)有“人物”。初學(xué)那些年,全然不知作曲家的相貌。后來(lái)母親買了一本《鋼琴藝術(shù)博覽》,悉數(shù)介紹史上名家的生平大作,并附上他們的漫畫像——當(dāng)然,那都是“前影像時(shí)代”的事了。但我已如獲珍寶:?jiǎn)眩@就是貝多芬,這就是肖邦啊。 15歲赴美后,正式學(xué)習(xí)“西方音樂(lè)史”。柯蒂斯音樂(lè)學(xué)院的必修課上,翻開(kāi)厚厚的書頁(yè),還是那些人,但配上了“嚴(yán)肅”的油畫圖片。從古希臘到文藝復(fù)興,幾乎只見(jiàn)史實(shí),進(jìn)入巴洛克,“人”才漸而凸顯。維瓦爾第、亨德?tīng)枴秃铡⒑nD、莫扎特……篇幅均等,唯貝多芬稍長(zhǎng)。至浪漫一代,肖像驟然密集:舒伯特、柏遼茲、門德?tīng)査伞⑹媛⑿ぐ睢⒗钏固亍⑼吒窦{、柴可夫斯基、勃拉姆斯、德沃夏克…… 我隨即發(fā)現(xiàn),這之中,肖邦所占的篇幅*短——甚至過(guò)短——僅僅簡(jiǎn)述了他作為“鋼琴作曲家”的“特殊身份”。課后詫異之余,與同為鋼琴專業(yè)的好友交換意見(jiàn),他也大為不解。 這不解、這詫異,好不難說(shuō)。自年幼起,無(wú)數(shù)鋼琴學(xué)童就是憑借肖邦,漸漸塑成他們心中“鋼琴家”的主體形象:孤獨(dú)、詩(shī)性、憂郁……汗水、表?yè)P(yáng)、訓(xùn)斥、掌聲;在無(wú)數(shù)成敗無(wú)數(shù)苦樂(lè)的時(shí)光里,波蘭人的名字深深刻入每一個(gè)琴童的心里。心理記憶、肉體記憶,共同凝結(jié)為難以磨滅的情緒記憶:對(duì)于任何日后成人的鋼琴家,無(wú)論喜厭,肖邦始終占據(jù)著無(wú)法撼動(dòng)的位置。但在那天、那堂音樂(lè)史課上,這一位置被過(guò)于輕易地撼動(dòng)了。 課后再讀:寥寥數(shù)筆,絲毫不提他的創(chuàng)作高度,簡(jiǎn)直是侮辱。難道鋼琴史與音樂(lè)史之間,存在著未被我等所了解的嫌隙?我與同學(xué)決定一問(wèn)究竟。找來(lái)其他幾位非鋼琴專業(yè)的同學(xué)討論,結(jié)果更是詫異。他們都不以為然:肖邦是一個(gè)“不會(huì)寫交響樂(lè)”的作曲家,鋼琴之外,他一無(wú)所成。這近乎“客觀事實(shí)”,于是困惑轉(zhuǎn)為憤懣,我們繼而逼問(wèn):拋開(kāi)樂(lè)器形式不談,這樣的音樂(lè)難道不夠獨(dú)一無(wú)二?對(duì)方回答,在他們聽(tīng)來(lái),那只是“好聽(tīng)”的旋律,與其他人筆下的其他好聽(tīng)旋律并無(wú)不同;至于偉大,更沾不上邊了。我們駁斥:他在旋律方面的天分高過(guò)了任何其他作曲家。對(duì)方仍不為所動(dòng)。甚至,其中一位還挑釁地說(shuō),論地位,肖邦還不及李斯特——畢竟,后者還寫過(guò)交響詩(shī)。 多年以后回看這事,不禁笑嘆年少時(shí)代的可愛(ài)。但對(duì)那時(shí)的我,當(dāng)真是挫敗的經(jīng)驗(yàn):好像從未想過(guò),某種觀念上的差異一直存在。(其實(shí)對(duì)這個(gè)差異,我本不應(yīng)感到陌生的。初來(lái)美國(guó),就有一位小提琴同學(xué)對(duì)我談及勃拉姆斯時(shí)感嘆:肖邦只是通俗,勃氏才真的偉大。當(dāng)時(shí)未較真,一部分原因,也因自己同樣鐘愛(ài)后者。數(shù)年后,某位我敬重的指揮又對(duì)我說(shuō),肖邦的協(xié)奏曲就是對(duì)指揮的羞辱。我笑了,心里不服:莫扎特后,還有誰(shuí)19歲便能寫出這樣的協(xié)奏曲嗎?)——但那天、那堂課后的當(dāng)真,只因它真的被“權(quán)威”的立場(chǎng)證實(shí)了——并且這個(gè)立場(chǎng),也似乎為鋼琴圈外的廣大專業(yè)群體所認(rèn)同。 現(xiàn)在想來(lái),鋼琴演奏確實(shí)是一件私事:臺(tái)上臺(tái)下,我們向來(lái)獨(dú)處。自我校正、自我總結(jié)、自我批判,匱乏如管弦樂(lè)手在室內(nèi)樂(lè)、交響樂(lè)中相互聆聽(tīng)交流的體驗(yàn)。我們的耳朵是“向內(nèi)”的,或許,我們的見(jiàn)識(shí)也同樣。昔時(shí)的挫敗于是成為必然:那天,我詫異于鋼琴在樂(lè)器界的孤立處境—同時(shí),詫異于肖邦在音樂(lè)史的邊緣事實(shí)。 不曾料到,自己對(duì)管弦作品的鐘愛(ài),也始自那天的挫敗。此后聽(tīng)勃拉姆斯,幾乎全是交響樂(lè)、室內(nèi)樂(lè),對(duì)他的鋼琴作品倒不如從前那樣關(guān)注了;再聽(tīng)貝多芬,驚覺(jué)他的弦樂(lè)四重奏較之鋼琴奏鳴曲更為神妙;對(duì)舒曼的熱情,也更多轉(zhuǎn)向了他的藝術(shù)歌曲。這是全新的快感:遠(yuǎn)離熟悉的鋼琴語(yǔ)境,我更能跳離演奏的立場(chǎng),直入“作品”本身。管弦樂(lè)的世界何其廣博,只消流連其中,無(wú)須顧及自我,反倒更忘我。猛地返回鋼琴,再?gòu)椥ぐ睿l(fā)現(xiàn)我對(duì)他的喜愛(ài)依舊未變。唯變的,我想,是自己漸漸會(huì)站在某段距離之外看他了——坦白說(shuō),較之彈,我發(fā)覺(jué)自己更愛(ài)“讀”他的作品。我這樣,是否更合他意?肖邦一生不愛(ài)公開(kāi)演奏,時(shí)常抱怨李斯特演奏他作品時(shí)的“隨興發(fā)揮”。偶然看到Y(jié)ouTube上一則視頻,題曰:“肖邦是一個(gè)偉大的作曲家嗎?”點(diǎn)開(kāi)看,某位加拿大鋼琴家正奮力為波蘭人正名,邊彈邊講,言辭懇切。我又感嘆:肖邦,你還是需要宣傳啊。 但他早已被過(guò)度宣傳。我是說(shuō),在社會(huì)的層面:其人、其事、其形象,早就深入大眾文化記憶里了。愛(ài)國(guó)、憂郁、多病、早逝,那就是浪漫主義、民族主義的經(jīng)典符號(hào)。且看他的肖像吧:多具符號(hào)性的一張臉!音樂(lè)照亮了這張矜貴的面龐,同時(shí),也被它背后的象征力量所輕易收編——談?wù)撔ぐ睿兊眠^(guò)于簡(jiǎn)單,也過(guò)于困難。 說(shuō)簡(jiǎn)單,是因?yàn)閷?duì)他的一切表述都可輕易附身于某種符號(hào)式的解讀,或以“主義”(浪漫、民族、愛(ài)國(guó)),或以“精神”(懷想、孤獨(dú)、高貴、悲情……) 誰(shuí)不是從這些角度切入肖邦的呢?說(shuō)難,則是類似表述霸道地壟斷了有關(guān)他的一切。我似乎明白了:這正是肖邦在古典樂(lè)界權(quán)威史書中,和在大眾以及琴童心中的極端反差所在。在“正史”看來(lái),他總是某種名片式的人物,是古典音樂(lè)面對(duì)市場(chǎng)打出的迷情牌,擅長(zhǎng)鋼琴小品與安可曲,通俗易懂、取悅?cè)诵摹5牵柰瑢W(xué)的話說(shuō),“與偉大不沾邊”。 是否是某種“交響為大”的意識(shí)所致?西方音樂(lè)的萬(wàn)神殿里,居于主位的,總是那些龐大體裁、繁重結(jié)構(gòu)的締造者。勃拉姆斯直到中年才敢發(fā)表交響曲,就連舒曼在他生命末期也逐漸轉(zhuǎn)向大型作品:“我們現(xiàn)在需要的,是交響曲、四重奏……”這與其說(shuō)是對(duì)大結(jié)構(gòu)的迷戀,毋寧說(shuō),是某種對(duì)重量感、深沉感的“陽(yáng)性崇拜”。它一面指向“自然”——自浪漫主義開(kāi)始,沒(méi)什么比大自然更能喚起對(duì)崇高之物的向往,從而引致對(duì)宏偉音響的訴求(這在浪漫晚期愈加明顯);另一面,它指向“高處”:對(duì)古典遺跡的追溯。作為歷史的巔峰,古典的成就已成神話;對(duì)它的向往,與其說(shuō)是源于自發(fā),毋寧說(shuō),是人對(duì)神話的喃喃致敬…… 乍一看,肖邦與這些立場(chǎng)皆各錯(cuò)開(kāi)。首先,他的作品不涉自然——他從不開(kāi)掘標(biāo)題化、文學(xué)化的音響敘事,只表達(dá)鋼琴的聲音;再者,他似乎也無(wú)心于歷史。其*富個(gè)人性的體裁:瑪祖卡、波蘭舞曲、夜曲等,不僅屬小結(jié)構(gòu),也非古典正統(tǒng)(按中國(guó)老話,有點(diǎn)“庶出”的意思);而那些有著古典淵源的體裁:幻想曲、諧謔曲、回旋曲、前奏曲、變奏曲、圓舞曲等,又經(jīng)過(guò)了極度個(gè)人化的翻新,以至難于認(rèn)祖歸宗。他似乎不事整體、癡迷瞬間,其中所影射的“女性主義”意味(一如他過(guò)于傷感、脆弱的形象),必然為“陽(yáng)性崇拜”的交響世界所邊緣化。 我到底想說(shuō)什么呢?也許,我也有自己的苦衷。每讀到前人對(duì)肖邦的比喻,一如舒曼:“他是藏在花叢中的大炮,向全世界宣告:波蘭不會(huì)亡”;或傅聰:“肖邦至少是像李后主那樣……”;或木心:“肖邦,就是一部分的俄耳浦斯……”;我暗暗想:也許,不去談?wù)撍谩5@些年反復(fù)重讀樂(lè)譜,我越來(lái)越看到了另一個(gè)肖邦。如果能重新回到少年時(shí),我好想對(duì)我的同學(xué)說(shuō):我錯(cuò)了,你們錯(cuò)了,比喻錯(cuò)了,“音樂(lè)史”也錯(cuò)了。 * * * 這錯(cuò),首先得“歸咎”于肖邦自己:他確實(shí)是史上獨(dú)一無(wú)二的旋律天才。“好聽(tīng)”的旋律,不僅遍布其所有主題,也貫穿他作品的每個(gè)角落——即便過(guò)渡段、炫技處、內(nèi)聲部也無(wú)一例外。似乎在他筆下,一切織體皆旋律。如此,移開(kāi)旋律的視角來(lái)看肖邦幾乎不可能。你幾乎看不到:他是繼巴赫、貝多芬之后,*偉大的結(jié)構(gòu)天才。 將肖邦比作“藏在花叢中的大炮”的舒曼,在聽(tīng)完其《第二鋼琴奏鳴曲》后大為困惑,至于原因,自然是其中備受爭(zhēng)議的終樂(lè)章:“它令人入迷。它可以是任何東西,但恰恰不是音樂(lè)。”作為同代*先鋒的作曲家,這一批評(píng)即使出自舒曼也不難理解:悲沉的第三章“葬禮進(jìn)行曲”后,緊隨的末樂(lè)章似一場(chǎng)陰風(fēng)迅疾刮過(guò),何止結(jié)構(gòu)、布局、整體,便是細(xì)節(jié)也難于捕捉;一切古典的聽(tīng)覺(jué)習(xí)慣在此消解。 肖邦在此,看似摒棄了兩個(gè)他創(chuàng)作中*顯明的元素:旋律、和聲。全樂(lè)章只以一條單聲部左右手平行疊加而成:沒(méi)有“花叢”,也沒(méi)有“大炮”;與其說(shuō)是樂(lè)章,更像是一段莫名的尾聲。未經(jīng)仔細(xì)辨聽(tīng),你很難洞察:其實(shí)它嚴(yán)格地遵照古典的雙段式寫成,有著清晰的主題、副題、再現(xiàn);只是它們這般不經(jīng)意地淡出穿插,以至于音樂(lè)的“形式感”“儀式感”被倏然抹去了。但注意:通篇的單聲部并非意味著“去和聲化”;正相反,和聲的存在獲得了*大程度的強(qiáng)調(diào)——只是它并非通過(guò)浪漫的處理,而是巴洛克的復(fù)調(diào)藝術(shù)。 相較浪漫主義以和聲“渲染”旋律,巴洛克則以線條“影射”和聲。和聲在后者那里是藏去的:復(fù)調(diào)聲部的交縱如同網(wǎng)狀的“血管”系起聲響;而非如古典之后,使和聲作為塊狀的“肌肉”凸顯出來(lái)。但在此曲中,肖邦更進(jìn)一步,連巴洛克的傳統(tǒng)復(fù)調(diào)形態(tài)也一并棄之,僅一條聲線便暗中把控住全曲的走勢(shì),使和聲以“隱喻”的形式即勾勒出迷人的浪漫意象——意象,真的只是意象——在深處驅(qū)動(dòng)一切的,是對(duì)古老對(duì)位法*嫻熟的掌握、*大膽的創(chuàng)新。 巴洛克與浪漫,雖形式迥異,但兩者都關(guān)乎“線條”(一個(gè)視覺(jué)的術(shù)語(yǔ));而在其間的古典時(shí)期,線條則被切割、打斷,成為短小的單位:動(dòng)機(jī)(一個(gè)純音樂(lè)的定義)。它不僅生成主題,也構(gòu)成其余一切織體,使局部與局部時(shí)刻保持著有機(jī)的關(guān)聯(lián)。這就是古典的遺產(chǎn);*宏觀的結(jié)構(gòu),來(lái)自*微小的分子。小單位的運(yùn)動(dòng)使織體隨時(shí)處在變化中,因而賦予整體以不斷的驅(qū)力。這種“小”的技術(shù),在浪漫派初期(準(zhǔn)確地說(shuō),在貝多芬后)神秘地遺失了。以此造成的后果,是奏鳴曲式在浪漫一代的全面衰退。 在舒伯特、勃拉姆斯等人的諸多鋼琴奏鳴曲中,我們常常看到僵挪硬移的古典框架,卻獨(dú)獨(dú)看不到對(duì)形式基因(小單位的互動(dòng)、對(duì)立)的活用。浪漫的慣性難以更改:一代進(jìn)入某個(gè)織體,它便自成一個(gè)語(yǔ)境,使作者難于,也不愿脫身其外。于是,結(jié)構(gòu)的動(dòng)力沉陷其中、難以自拔——體裁越大,這個(gè)癥結(jié)就越暴露。* 肖邦如何應(yīng)對(duì)這個(gè)問(wèn)題?且不談他的《第三奏鳴曲》(形式上*近于古典),只聽(tīng)其《第二奏鳴曲》開(kāi)篇小動(dòng)機(jī)的構(gòu)架,主、副題織體的無(wú)縫焊接,發(fā)展部不同動(dòng)機(jī)變體的貫穿:你何時(shí)在浪漫派同輩所作的奏鳴曲中,照見(jiàn)如此“復(fù)古”的風(fēng)范?! 一樂(lè)章主題前的兩小節(jié)引子:一個(gè)刺耳的異調(diào)和聲打破沉默,接著以某種決絕的意志推倒阻力——主題高昂地挺進(jìn)。正是這個(gè)突兀的引子,埋伏著整曲的原動(dòng)機(jī),并以此“逼出”主題;而那個(gè)刺耳的和聲,其實(shí)是之后副題音響的伏筆:動(dòng)機(jī)直接影射結(jié)構(gòu),因此更富戲劇深度。 將整曲根植于引子,為貝多芬首創(chuàng)——它源自對(duì)結(jié)構(gòu)*強(qiáng)烈的訴求。這首奏鳴曲的開(kāi)篇,也依稀存有貝多芬*后一首鋼琴奏鳴曲Op. 111引子的回響(肖邦也曾提及對(duì)此曲的鐘愛(ài))。當(dāng)然,兩者是迥然不同的音樂(lè),但我們?nèi)阅軓闹懈Q見(jiàn)什么。這是關(guān)鍵的訊息:唯有以“奏鳴曲”作為切入點(diǎn),我們或許能撕開(kāi)一個(gè)缺口——肖邦的光芒,使其天才真正鶴立于同輩的,并非僅僅在抒情小品,而是在中大型的古典體裁中,何以使舊有形式煥發(fā)出如此有機(jī)的生命。 ……
演奏之外 作者簡(jiǎn)介
張昊辰,1990年出生于上海。五歲在上海音樂(lè)廳舉辦首場(chǎng)鋼琴獨(dú)奏會(huì)。幼時(shí)師從林恒、吳子杰、王建中,2001年起師從著名鋼琴教育家但昭義,2005年進(jìn)入柯蒂斯音樂(lè)學(xué)院,師從時(shí)任院長(zhǎng)加里·格拉夫曼。2009年獲范·克萊本國(guó)際鋼琴比賽金獎(jiǎng),是首位獲得這一頂級(jí)賽事冠軍的亞洲人;2017年獲艾弗里·費(fèi)舍爾音樂(lè)職業(yè)大獎(jiǎng)。 張昊辰曾與諸多國(guó)際著名樂(lè)團(tuán)合作,包括琉森音樂(lè)節(jié)管弦樂(lè)團(tuán)、紐約愛(ài)樂(lè)樂(lè)團(tuán)、費(fèi)城交響樂(lè)團(tuán)、慕尼黑愛(ài)樂(lè)樂(lè)團(tuán)、倫敦交響樂(lè)團(tuán)、倫敦愛(ài)樂(lè)樂(lè)團(tuán)、法國(guó)廣播交響樂(lè)團(tuán)、法蘭克福廣播交響樂(lè)團(tuán)、舊金山交響樂(lè)團(tuán)、洛杉磯愛(ài)樂(lè)樂(lè)團(tuán)、以色列愛(ài)樂(lè)樂(lè)團(tuán)、悉尼交響樂(lè)團(tuán)、華沙愛(ài)樂(lè)樂(lè)團(tuán)、馬林斯基交響樂(lè)團(tuán)、中國(guó)愛(ài)樂(lè)樂(lè)團(tuán)等;其巡演足跡遍布美洲、亞洲、歐洲,在BBC逍遙音樂(lè)節(jié)、琉森音樂(lè)節(jié)、韋比耶音樂(lè)節(jié)、阿斯本音樂(lè)節(jié)等頂尖音樂(lè)節(jié)中均有亮相。 本書記錄作者習(xí)琴近三十年的部分思考、感悟,以一位演奏者的視角看“演奏之外”古典音樂(lè)的種種話題及人物。
- >
人文閱讀與收藏·良友文學(xué)叢書:一天的工作
- >
詩(shī)經(jīng)-先民的歌唱
- >
回憶愛(ài)瑪儂
- >
推拿
- >
伯納黛特,你要去哪(2021新版)
- >
史學(xué)評(píng)論
- >
莉莉和章魚
- >
中國(guó)人在烏蘇里邊疆區(qū):歷史與人類學(xué)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