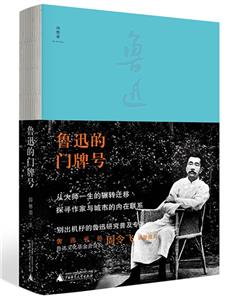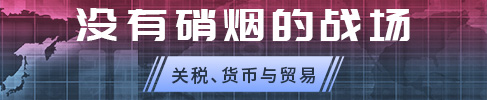-
>
魯迅全傳:苦魂三部曲-增訂版(全三冊(cè))
-
>
大家精要- 克爾凱郭爾
-
>
尼 采
-
>
弗洛姆
-
>
大家精要- 羅素
-
>
大家精要- 錢穆
-
>
白居易:相逢何必曾相識(shí)
魯迅的門牌號(hào) 版權(quán)信息
- ISBN:9787559847591
- 條形碼:9787559847591 ; 978-7-5598-4759-1
- 裝幀:一般輕型紙
- 冊(cè)數(shù):暫無(wú)
- 重量:暫無(wú)
- 所屬分類:>
魯迅的門牌號(hào) 本書特色
作家和城市的關(guān)系一直是令人尋味的一個(gè)話題,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彼得堡的關(guān)系、巴爾扎克和雨果及巴黎的關(guān)系、喬伊斯和都柏林的關(guān)系等等。本書以魯迅居所為切入點(diǎn),探尋魯迅與其所居住的城市的種種關(guān)系,角度新穎,發(fā)現(xiàn)頗多,是一本值得細(xì)讀的隨筆文本。
魯迅的門牌號(hào) 內(nèi)容簡(jiǎn)介
《魯迅的門牌號(hào)》是學(xué)者薛林榮繼《魯迅草木譜》《魯迅的飯局》《魯迅的封面》之后,“微觀魯迅”系列的第四部,也是本系列的收官之作。魯迅一生在多個(gè)地方求學(xué)、工作和生活,不同的地方在魯迅生命中留下了不同的印記,他所居住的地點(diǎn)也因此具有某種特殊的精神文化價(jià)值。本書按時(shí)間順序,以魯迅不同時(shí)期的居所為線索,切入魯迅的生活史、創(chuàng)作史和心路史,展現(xiàn)了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的人文、教育風(fēng)貌與政壇、文壇風(fēng)云。同時(shí),書中收錄的許多珍貴歷史照片,將給讀者帶來(lái)更為真實(shí)立體的閱讀感受。
魯迅的門牌號(hào) 目錄
紹 興
003 東昌坊口新臺(tái)門(1881年—1898年)
南 京
031 南京江南水師學(xué)堂和礦路學(xué)堂(1898年 4月—1902年 3月)
日 本
047 仙臺(tái)“佐藤屋”公寓(1904年 9月—1904年 11月)
063 仙臺(tái)宮川宅(1904年 11月—1906年春)
075 東京伏見館公寓(1906年秋—1907年夏)
081 東京中越館(1907年秋—1908年 4月 8日)
086 伍舍(1908年 4月 8日—1909年 2月)
095 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號(hào)(1909年 2月—1909年秋)
浙 江
099 浙江兩級(jí)師范學(xué)堂(1909年秋—1910年 7月)
110 紹興府中學(xué)堂(1910年秋—1911年冬)
116 浙江山會(huì)初級(jí)師范學(xué)堂(1911年冬—1912年 2月)
北 京
123 紹興會(huì)館(1912年 5月 5日—1919年 11月 21日)
157 八道灣 11號(hào)(1919年 11月 21日—1923年 8月 2日)
173 磚塔胡同 61號(hào)(1923年 8月 2日—1924年 5月 25日)
188 宮門口西三條胡同 21號(hào)(1924年 5月 25日—1926年 9月)
廈 門
225 廈大生物樓(1926年 9月 4日—1926年 9月 25日)
231 廈大集美樓(1926年 9月 25日—1927年 1月 16日)
廣 州
257 中山大學(xué)大鐘樓(1927年 1月 18日—1927年 3月 29日)
284 白云樓 26號(hào)二樓(1927年 3月 29日—1927年 9月 27日)
上 海
299 景云里 23號(hào)(1927年 10月 8日—1928年 9月 9日)
310 景云里內(nèi) 18號(hào)、17號(hào)(1928年 9月 9日—1930年 5月 12日)
313 施高塔路 11號(hào)內(nèi)山書店
318 拉摩斯公寓 194A3樓 4號(hào)(1930年 5月 12日—1933年 4月 11日)
346 大陸新村 9號(hào)(1933年 4月 11日—1936年 10月)
370 魯迅未能離開的上海
389 附錄:魯迅的門牌號(hào)不完全記錄
394 主要參考書目
396 后記
魯迅的門牌號(hào) 節(jié)選
白云樓26號(hào)二樓 (1927 年 3 月 29 日— 1927 年 9 月 27 日) 一 1927年3月29日,魯迅搬出中山大學(xué)的標(biāo)志性建筑大鐘樓,搬進(jìn)了珠江東堤上的白云樓。 欲訪白云樓,先尋白云路。 “白云”是廣州市的文化符號(hào),無(wú)論白云路、白云樓,還是白云機(jī)場(chǎng),都與廣州東北部的南粵名山白云山有關(guān)。秦末高士鄭安期隱居白云山采藥濟(jì)世,晉人葛洪在此煉丹,唐宋以后,杜審言、韓愈、蘇軾等文人登山吟詩(shī),寓情于物,豐富了嶺南文化。明清羊城八景中,“白云晚望”居其一。羊城新八景中,“白云松濤”居其一。白云樓所在的白云路建于 1912年,當(dāng)時(shí)路北段東川橋一帶稱川龍口,是源于白云山的水道,故名。這條路一直是建國(guó)前廣州*寬的馬路,且首次試驗(yàn)性建成中間有綠化帶的復(fù)式馬路,有“模范馬路”之稱。 現(xiàn)在,當(dāng)年試驗(yàn)性的復(fù)式馬路早已成為天下馬路的基本樣式,白云路上也是綠意森森,一棵棵遒勁的榕樹立在路邊,盤曲扭結(jié)的枝干透著南方式的倔強(qiáng)。道路的盡頭,一幢土黃色的舊式洋樓在周圍的環(huán)境中顯得極其醒目,并且氣度不凡,這就是白云樓。 白云樓建于 1924年,是一座鋼筋混凝土結(jié)構(gòu)的二層樓房(目前的三樓是后來(lái)加蓋的),圓形立柱有羅馬建筑韻味,門窗裝飾富巴洛克風(fēng)格,透露出富麗堂皇的感覺。據(jù)說(shuō)此樓西南和 北面墻壁上原懸掛木刻“白云樓”橫匾,后改為水泥,今已不存,只看到西段**道門上方浮雕有“郵局”二字。原來(lái)新中國(guó)成立后,白云樓曾為郵電部門職工宿舍。外墻上釘著一白一黑兩塊石碑,其中顯示白云樓魯迅故居早在 1985年就成為廣東省文物保護(hù)單位。 當(dāng)年,魯迅租賃了白云樓西段**道門二樓的北室,計(jì)有1廳 3房,與許壽裳、許廣平合居。 白云樓底層是郵局,二樓中間是樓梯,一梯兩戶,分為北室和南室。北室“一廳三房一廚房一廁所”,共五六間房。南室共十間房,包括一個(gè)八角亭。歷來(lái)將南室定為魯迅故居,事實(shí)上不然。1963年當(dāng)廣州魯迅紀(jì)念館館長(zhǎng)張競(jìng)先生詢問(wèn)許廣平魯迅故居位置時(shí),她當(dāng)場(chǎng)手繪了白云樓故居的方位圖,確認(rèn)了北室才是魯迅故居。 許廣平在《我所敬的許壽裳先生》中說(shuō):“租了廣九車站的白云樓,除了廚房、女工住房、飯廳兼會(huì)客廳之外,我們每人有一間房子,但魯迅先生首先挑選那個(gè)比較大而風(fēng)涼朝南的給許先生住,寧可自己整天在朝西的窗下書寫。”魯迅的《朝花夕拾·后記》文末所署是:“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寫完于廣州東堤寓樓之西窗下。” 魯迅給許壽裳讓出來(lái)的是北室*大的一間,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說(shuō):“后來(lái)搬出學(xué)校,租了白云樓的一組,我和魯迅、景宋三人合居。地甚清靜,遠(yuǎn)望青山,前臨小港,方 以為課余可以有讀書的環(huán)境了。” 據(jù)何春才回憶,“白云樓是一所很大的洋房,魯迅先生只賃了其中二樓的一幢有一廳二房一廚房一廁所的房子。他的書房、寢室兼會(huì)客廳的房子是入門的**間,面積相當(dāng)寬闊,當(dāng)中的一邊,安置著一張板床,對(duì)面是一個(gè)放滿了書的架子,西窗下有一張書桌,此外還有幾張?zhí)僖巍K臅郎辖?jīng)常放著一盆青蔥可愛的水橫枝”。a 何春才此文編入《魯迅生平史料匯編》時(shí),有一條注,說(shuō)“一廳二房”應(yīng)為“一廳三房”,這也是北室的結(jié)構(gòu)。 何春才回憶: 我常去見他的時(shí)候,正是南方特有的悶熱的時(shí)候。他喜歡在深夜趁著風(fēng)涼寫作,甚至有時(shí)寫到天亮,白天是起得很遲的,會(huì)客的時(shí)間大半在下午。這時(shí)強(qiáng)烈的陽(yáng)光從西窗射入,我往往走得滿頭大汗到了他那里去時(shí),他總是很關(guān)懷地說(shuō):“把大衣脫下來(lái)吧。”我便把中山裝解下,穿著沒有袖的薄背心,起初很不自然,以后也就習(xí)慣了。他也很怕熱,經(jīng)常穿著半袖的底衣,有時(shí)將席鋪在飯廳的花磚上困覺,這多半當(dāng)他身體有些不舒服的時(shí)候。 何春才還說(shuō),魯迅自奉薄而待人厚。比方他抽的香煙是彩鳳牌之類的次等貨,而給朋友或?qū)W生抽的卻往往是美麗牌之類較好的香煙。另外,平時(shí)吃的菜蔬很隨便,款待熟人時(shí),肴饌則頗豐厚。 白云樓“地甚清靜,遠(yuǎn)望青山,前臨小港”,非常適合寫作,看得出,魯迅對(duì)此處環(huán)境是很滿意的。 即便如此清幽,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魯迅在《而已集·小雜感》中這樣描寫白云樓周圍的環(huán)境:“樓下一個(gè)男人病得要死,那間隔壁的一家唱著留聲機(jī);對(duì)面是弄孩子。樓上有兩人狂笑;還有打牌聲。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著她死去的母親。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我只覺得他們吵鬧。” 在清幽又吵鬧的白云樓上,魯迅開始著手整理《小約翰》譯稿。 魯迅在《小約翰》引言中談到了與齊宗頤(齊壽山)翻譯《小約翰》的過(guò)程,*初是在北京中央公園一間紅墻的小屋里譯成草稿,然后魯迅把草稿帶到廈門大學(xué),又帶到中山大學(xué),“想在那里抽空整理,然而又沒有工夫;而且也就住不下去了,那里又來(lái)了‘學(xué)者’。結(jié)果是帶著逃進(jìn)自己的寓所——?jiǎng)倓傋舛ú坏揭辉碌模荛煟欢軣岬姆孔印自茦恰薄?白云樓外是什么風(fēng)景呢?魯迅寫道: 滿天炎熱的陽(yáng)光,時(shí)而如繩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幾只蜑戶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談笑哭罵,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歡。也仿佛覺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淪亡,或者正被殺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經(jīng)營(yíng)腐爛事業(yè)”和作這事業(yè)的材料。然而我卻漸漸知道這雖然沈[沉]默的都市中,還有我的生命存在,縱已節(jié)節(jié)敗退,我實(shí)未嘗淪亡。只是不見“火云”,時(shí)窘陰雨,若明若昧,又像整理這譯稿的時(shí)候了。于是以五月二日開手,稍加修正,并且謄清,月底才完,費(fèi)時(shí)又一個(gè)月。 (《小約翰》引言) 白云樓西窗下,不僅天氣炎熱,還常有暗探盯梢,有人甚至冒充訪問(wèn)者闖入居室,魯迅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堅(jiān)持寫作和戰(zhàn)斗的。 魯迅由于常常曬在白云樓西窗下,渾身長(zhǎng)滿了痱子,他為此還在致友人的信中如此調(diào)侃:“我諸事大略已了,本即可走,而太古公司洋鬼子,偏偏罷工,令我無(wú)船可坐;此地又漸熱,在西屋中九蒸九曬,煉得遍身痱子。繼而思之,到上海恐亦須擠在小屋中,不會(huì)更好,所以也就心平氣和,‘聽其自然’,生痱子就生痱子,長(zhǎng)疙瘩就長(zhǎng)疙瘩,無(wú)可無(wú)不可也。”(書信 270817致章廷謙) 北伐節(jié)節(jié)取勝的時(shí)期, 4月 10日,魯迅在白云樓寓所聽到了廣州民眾上街慶祝北伐軍攻克上海南京的歡呼聲,于是寫下了《慶祝滬寧克復(fù)的那一邊》,提醒人們防止革命精神“浮滑, 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復(fù)舊”。僅僅兩天后,魯迅的預(yù)言就應(yīng)驗(yàn)了,上海發(fā)生了“四一二”政變。緊接著,廣州發(fā)生了“四一五”政變,國(guó)民黨在廣州開始“清黨”,中山大學(xué)遭到大搜捕。這一天,魯迅頂著狂風(fēng)暴雨,從白云樓趕回中大,以教務(wù)主任的名義召集各系主任開會(huì),設(shè)法營(yíng)救被捕學(xué)生。但他的主張未能得到中大校務(wù)實(shí)際主持者朱家驊的支持,會(huì)議無(wú)果而終,魯迅憤怒退席。中山大學(xué)圖書館前貼出開除數(shù)百名學(xué)生學(xué)籍和教職員工職務(wù)的布告后,魯迅憤而辭去中山大學(xué)一切職務(wù)表示抗議。校方三番五次自上而下進(jìn)行挽留,其中刊登在《中山大學(xué)校報(bào)》上的《挽留周樹人教授》一文寫道:“本校革新伊始,主理教務(wù),正賴?guó)欓啵慰慑嵊枭崛ァ3惺救諆?nèi)歸 里,悵望至殷,切希查照前函早日返校,共策進(jìn)行云云。”其中不乏恭維意味。當(dāng)然,魯迅之于教務(wù)工作之重要,似乎也是事實(shí)。1927年 5月,魯迅在致章廷謙的信中說(shuō):“我在此只三月, 竟做了一個(gè)大傀儡——現(xiàn)在他們還挽留我,當(dāng)然無(wú)效,我是不走回頭路的。”顯示出非走不可、無(wú)可商量的決心。 魯迅去意已決,特別是對(duì)中大擬聘請(qǐng)顧頡剛來(lái)校任教之事,魯迅反應(yīng)比較激烈。魯迅和顧頡剛在廈門大學(xué)時(shí)期即已交惡,魯迅到廣州中山大學(xué)任職后,“不是冤家不聚首”,顧頡剛隨后也來(lái)到中山大學(xué)。魯迅當(dāng)然是很不痛快的,宣稱“鼻來(lái)我走”。 “四一五”事件使魯迅“既悲且憤,復(fù)又感到落寞,這一段時(shí)間精神上是很為痛苦的”。但同時(shí),魯迅也學(xué)會(huì)了如何保護(hù)自己。如致電《循環(huán)日?qǐng)?bào)》要求澄清流言,聲明他在廣州的事實(shí),*后未能如愿;同時(shí),他寫信給廣州市公安局長(zhǎng)報(bào)告自己的住址,“表示隨時(shí)聽候逮捕”,雖然公安局長(zhǎng)回信安慰他,又有些有力者保證他的安全,而他似乎仍不免有些憤懣煩躁。(林賢治《人間魯迅》) 雖然被鮮血嚇得目瞪口呆,但魯迅還是選擇留在廣州。他從中山大學(xué)辭職后并沒有馬上離開廣州,他說(shuō):“他們不是造謠說(shuō)我已逃走了,逃到漢口去了嗎?現(xiàn)在到處都是烏鴉一般黑,我就不走,也不能走。倘一走,豈不正好給他們?cè)熘{?”他既能夠自我保護(hù),同時(shí)又選擇以相對(duì)安全的方式針砭現(xiàn)實(shí)。比如 7月份的夏期演講會(huì)“魏晉風(fēng)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guān)系”,借魏晉間的知識(shí)分子的遭遇和苦悶來(lái)對(duì)照他自己目前的遭遇和苦悶。正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 1927年 5月 1日,無(wú)官一身輕的魯迅在白云樓上,難得地寫到了他居住的環(huán)境及其時(shí)的心境: 廣州的天氣熱得真早,夕陽(yáng)從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強(qiáng)穿一件單衣。書桌上的一盆“水橫枝”,是我先前沒有見過(guò)的:就是一段樹,只要浸在水中,枝葉便青蔥得可愛。看看綠葉,編編舊稿,總算也在做一點(diǎn)事。做著這等事,真是雖生之日,猶死之年,很可以驅(qū)除炎熱的。 這段文字非常精彩,頗富張力,但正如朱崇科先生在論及魯迅的精神焦慮時(shí)所言,其中也藏匿著魯迅的一種中年心境:在現(xiàn)實(shí)與理念之間、綠葉的生機(jī)盎然與自己的混天度日編舊稿之間,顯出淡淡的不甘與無(wú)奈。 紀(jì)念館復(fù)原的魯迅書桌上,就放著一盆著名的水橫枝,果然只是將一段樹枝浸在清水中便綠意盎然。這種無(wú)土栽培法,不知道在北方的氣候中是否可以效仿。 資料載,白云樓的陳設(shè)是這樣的:會(huì)客廳在入門處,陳設(shè)簡(jiǎn)樸,椅子是竹制的;魯迅的房子、窗戶正對(duì)馬路。樓下西側(cè)是走廊,面對(duì)東濠涌,螺旋式樓梯,可通二、三樓。但目前白 云樓大門緊閉,木門油漆剝落,拉手銹跡斑斑,看不出有人進(jìn)出的痕跡。 至此,魯迅的國(guó)內(nèi)住處的門牌號(hào),我基本尋訪到了。從網(wǎng)上看到,廣州魯迅紀(jì)念館原館長(zhǎng)張競(jìng)老先生稱,介紹白云樓的碑文曾出現(xiàn)過(guò)幾處錯(cuò)誤,修改過(guò)后現(xiàn)仍有一處錯(cuò)誤。而魯迅住過(guò)的房間現(xiàn)仍為民居,多年以前他們?cè)蚴∥幕瘡d打過(guò)報(bào)告,打算與郵局方面磋商,將白云樓收歸文物部門管理,市人大也提過(guò)議案,但終因住戶安置等棘手問(wèn)題無(wú)法解決。因此,不少慕名而至的遠(yuǎn)近游客頂多只能在魯迅先生住所的西窗之下望而卻步。 我在白云樓外面徘徊的時(shí)候,一位戴著紅袖章在附近巡邏的“越秀群眾”警惕地走過(guò)來(lái)。在向我說(shuō)明了這處故居暫未開放之后,她又用吃力的普通話對(duì)我說(shuō):你可以給政府寫信讓早 點(diǎn)開放! 白云路*東段的街角,還有一個(gè)魯迅主題公園。魯迅塑像前居然擺著三個(gè)空飲料瓶。如此莊重之地,豈容小子撒野!我一邊生著氣,一邊將飲料瓶清理掉了。 二 魯迅回歸創(chuàng)作,是他在廣州做出的抉擇。從骨子里說(shuō),魯迅更擅長(zhǎng)自由創(chuàng)作。 魯迅此前一直生活在要學(xué)術(shù)還是要?jiǎng)?chuàng)作的糾結(jié)中。早在廈大時(shí)期,他就在思考:“兼作兩樣的,倘不認(rèn)真,使兩面都油滑淺薄,倘都認(rèn)真,則一時(shí)使熱血沸騰,一時(shí)使心平氣和,精神便不勝困憊,結(jié)果也還是兩面不討好……或者還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則于余暇時(shí)做,不過(guò)倘使應(yīng)酬一多,可又不行了。”1927年 7月 16日在廣州知用中學(xué)演講時(shí),他又重提此話題:“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靜的,而創(chuàng)作須情感,至少總得發(fā)點(diǎn)熱,于是忽冷忽熱,弄得頭昏,——這也是職業(yè)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處。苦倒也罷了,結(jié)果還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證據(jù),是試翻世界文學(xué)史,那里面的人,幾乎沒有兼作教授的。” 1927年 7月 17日,魯迅致信章廷謙,告知其通信地址將發(fā)生變化: 這里的“北新書屋”我擬于八月中關(guān)門,因?yàn)殓娋次模ū侵埽┮獊?lái)和我合辦,我則關(guān)門了,不合辦。此后來(lái)信,如八月十日前發(fā),可寄“廣九車站旁,白云樓二十六號(hào)二樓,許寓收轉(zhuǎn)”,以后寄喬峰收轉(zhuǎn)。 廣州期間,由于事務(wù)繁雜,魯迅幾乎停止了他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完成于廣州的《眉間尺》其實(shí)早在廈門時(shí)期就構(gòu)思和準(zhǔn)備好了。魯迅在廣州時(shí)期的絕大部分作品屬于機(jī)動(dòng)靈活的雜文, 其中不乏對(duì)困頓、挫敗的書寫。魯迅把在廣州所寫的一批雜文輯為《而已集》,可以看作他對(duì)自己在廣州的小結(jié):“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淚揩了,血消了;屠伯們逍遙復(fù)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連‘雜感’也被‘放進(jìn)了應(yīng)該去的地方’時(shí),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他曾經(jīng)批評(píng)廣東文藝氛圍淡薄,可讀之書甚少,于是他接過(guò)孫伏園租過(guò)的芳草街 44號(hào)創(chuàng)辦了北新書屋,而且累計(jì)自掏腰包 60元付房租。該書屋于 3月 25日開業(yè),在魯迅離開前的8月 15日停業(yè),不但沒有賺到錢,魯迅還倒貼上了 80元左右。但該書屋對(duì)當(dāng)時(shí)廣州的文藝青年而言,是一個(gè)不可替代的好去處。“青年們像蜜蜂飛進(jìn)花叢一般,盡情地采擷著珍貴的養(yǎng)分……魯迅為了讓生活在沉悶中的青年呼吸到一點(diǎn)新鮮空氣,絲毫不計(jì)較自己付出的代價(jià)。”(李江《魯迅與中山大學(xué)》) 在廣州,魯迅見證了革命策源地到反革命策源地的轉(zhuǎn)換,被淋漓鮮血嚇得失語(yǔ),他也受了“紅中夾白”的廣州“革命”的欺騙,感受到政治背后的骯臟。他不得不為和許廣平的生活尋找更合適的安置空間。此時(shí),國(guó)際化大都市上海可以為魯迅的安全提供更好的屏障。上海有租界,并且由于國(guó)共的對(duì)抗、國(guó)際勢(shì)力的介入,在混亂之中魯迅反倒相對(duì)安全。據(jù)曹聚仁分析,魯迅在上海“那十年間,有驚無(wú)險(xiǎn),太嚴(yán)重的迫害,并不曾有過(guò)”。魯迅完全可以靠稿費(fèi)和版稅體面生存,并且給許廣平一個(gè)名分。 1927年 9月 3日,即將離開廣州的魯迅致信李小峰,談及他對(duì)廣州生活的小結(jié):“訪問(wèn)的,研究的,談文學(xué)的,偵探思想的,要作序,題簽的,請(qǐng)演說(shuō)的,鬧得不亦樂乎。我尤其怕 的是演說(shuō),因?yàn)樗兄付ǖ臅r(shí)候,不聽拖延……事前事后,我常常對(duì)熟人嘆息說(shuō),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來(lái)做洋八股了。” 這已經(jīng)預(yù)示著魯迅不得不逃離廣州。 四年多后的 1932年 4月 24日夜,編完《三閑集》的魯迅,在該書的序言里回首往事,更加坦率地說(shuō)到了離開廣州的根本原因:“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shuō)的話,都載在《而已集》里。” 魯迅是這樣評(píng)介廣州的:“那時(shí)我于廣州無(wú)愛憎,因而也就無(wú)欣戚,無(wú)褒貶。我抱著夢(mèng)幻而來(lái),一遇實(shí)際,便被從夢(mèng)境放逐了,不過(guò)剩下些索漠。我覺得廣州究竟是中國(guó)的一部分,雖然奇異的花果,特別的語(yǔ)言,可以淆亂游子的耳目,但實(shí)際是和我所走過(guò)的別處都差不多的。倘說(shuō)中國(guó)是一幅畫出的不類人間的圖,則各省的圖樣實(shí)無(wú)不同,差異的只在所用的顏色。 黃河以北的幾省,是黃色和灰色畫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綠,廈門是淡紅和灰色,廣州是深綠和深紅。我那時(shí)覺得似乎其實(shí)未曾游行,所以也沒有特別的罵詈之辭,要專一傾注在素馨和香 蕉上。” 他還說(shuō):“廣東還有點(diǎn)蠻氣,較好。” 在廣州短短的8個(gè)多月時(shí)間內(nèi),魯迅整理了膾炙人口的《野草》《朝花夕拾》《唐宋傳奇集》和《小約翰》等著譯,寫下《而已集》《三閑集》中的不少名篇,世界觀、人生觀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 1927年 9月 27日,焦慮的中年人魯迅攜他的愛人許廣平登上“山東號(hào)”輪船,離開廣州去上海。 一代文豪與廣州的緣分終結(jié)了。這不是單純的個(gè)人選擇, 而是時(shí)代風(fēng)云和個(gè)人命運(yùn)淘洗的必然結(jié)果。
魯迅的門牌號(hào) 作者簡(jiǎn)介
薛林榮,1977年生,甘肅秦安人,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著有長(zhǎng)篇?dú)v史小說(shuō)《疏勒》,散文集《一個(gè)村莊的三種時(shí)間》,隨筆集《魯迅草木譜》《魯迅的飯局》《魯迅的封面》《閱人記》《處事記》等。作品散見于《散文》《北京文學(xué)》《散文選刊》《南方周末》等刊物。曾獲黃河文學(xué)獎(jiǎng)等多個(gè)獎(jiǎng)項(xiàng)。現(xiàn)居甘肅天水。
- >
龍榆生:詞曲概論/大家小書
- >
企鵝口袋書系列·偉大的思想20:論自然選擇(英漢雙語(yǔ))
- >
二體千字文
- >
我與地壇
- >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實(shí)旅程
- >
回憶愛瑪儂
- >
大紅狗在馬戲團(tuán)-大紅狗克里弗-助人
- >
名家?guī)阕x魯迅:朝花夕拾
-
¥27.3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