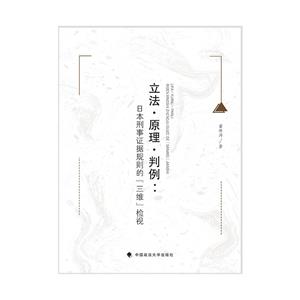-
>
法律的悖論(簽章版)
-
>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
>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
-
>
私人財富保護、傳承與工具
-
>
再審洞穴奇案
-
>
法醫(yī)追兇:破譯犯罪現場的156個冷知識
-
>
法醫(yī)追兇:偵破罪案的214個冷知識
立法·原理·判例:日本刑事證據法要義 版權信息
- ISBN:9787562098140
- 條形碼:9787562098140 ; 978-7-5620-9814-0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立法·原理·判例:日本刑事證據法要義 內容簡介
《立法·原理·判例:日本刑事證據規(guī)則的“三維”檢視》從法律規(guī)定、基本原理、司法判例(解釋)三個維度向國內讀者展示日本刑事證據規(guī)則與相關程序的多重樣態(tài)。寫作過程中,《立法·原理·判例:日本刑事證據規(guī)則的“三維”檢視》筆者并不滿足于對以上三方面內容的細致梳理、詳盡羅列,而試圖以此為依托展開對刑事證據規(guī)則相關問題的深入分析、延伸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觀點或者主張,在提升《立法·原理·判例:日本刑事證據規(guī)則的“三維”檢視》自身學術價值的同時,也為我國刑事證據規(guī)則體系的建構與完善提供域外智識和經驗教訓。
立法·原理·判例:日本刑事證據法要義 目錄
一、證據的含義與種類
(一)事實認定與證據
(二)證據種類
二、證據能力與證明力
三、證據裁判主義
(一)證據裁判主義的含義
(二)嚴格證明與自由證明
(三)證明對象:嚴格證明抑或自由證明
四、證明的必要
第二章 證據關聯性
一、關聯性的意義
二、寫實證據
(一)照片
(二)錄音帶、錄像帶
三、科學證據
四、不良品格與類似事實
(一)不良品格的證明
(二)余罪與量刑
第三章 傳聞法則
一、傳聞法則概述
(一)傳聞法則的根據
(二)《憲法》第37條第2款與傳聞法則
(三)傳聞證據的定義
(四)傳聞與非傳聞
(五)傳聞法則的例外體系
二、傳聞文書
(一)被告人以外之人的陳述代用文書
(二)被告人的陳述代用文書
(三)特信性文書
三、傳聞陳述
四、傳聞證據的相關問題
(一)任意性調查
(二)同意文書
(三)合意文書
第四章 違法收集證據排除法則
一、違法收集證據排除法則概述
二、違法收集證據排除的理論根據
三、違法收集證據排除的判斷標準
(一)違法收集證據排除的理論標準
(二)違法收集證據排除的判例標準
(三)違法收集證據排除的例外情形
四、違法收集證據排除法則的實務運用
(一)程序存在輕微違法的場合
(二)程序存在重大違法的場合
(三)證據收集程序違反與令狀主義無關之其他法規(guī)的場合
(四)程序違法與證據收集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的場合
(五)先前偵查行為違法對后續(xù)證據收集行為產生影響的場合
五、毒樹之果
六、其他問題
(一)對違法收集證據的同意
(二)違法收集證據排除的申請適格
(三)違法收集證據之實質證據外使用
(四)私人違法收集的證據
第五章 自白法則
一、自白與自白法則
二、自白的證據能力
(一)自白法則的根據
(二)自白法則的具體適用
三、自白的證明力
(一)自白的信用性評價
(二)自白補強法則
四、共同被告人的陳述
(一)概述
(二)共同被告人陳述的證據能力
(三)共犯者陳述(自白)的證明力
第六章 審判前整理程序
一、審判前整理程序概述
(一)審判前整理程序的含義
(二)爭點、證據整理與證據開示的基本構想
(三)與預斷排除、審判公開原則的關系
二、審判前整理程序的內容
(一)程序開始
(二)程序參與者
(三)程序內容
三、審判前整理程序的流程
(一)預定證明事實明示、證據調查請求與證據開示
(二)類型證據開示
(三)被告人或者辯護人的主張明示、證據請求、證據開示
(四)被告方主張關聯證據開示
(五)預定證明事實、主張的追加、變更等
(六)爭點、證據整理結果的確認
(七)關于證據開示的裁定
(八)開示證據目的外使用的禁止
四、審判前整理程序的特例
(一)必要辯護
(二)被告人、辯護人必要的開頭陳述
(三)審判前整理程序結果的公布
(四)審判前整理程序終結后證據調查請求的限制
第七章 證據調查程序
一、證據調查程序概覽
二、開頭陳述
(一)開頭陳述的意義與功能
(二)開頭陳述的范圍與限度
(三)被告方的開頭陳述
三、證據調查請求
(一)請求權人與請求對象
(二)請求時期與請求順序
(三)證據調查的請求方式
(四)請求的取消(撤回)
四、證據裁定
五、證據調查范圍、順序、方法的裁定
六、證據調查的實施
(一)證人詢問
(二)鑒定、口譯、筆譯
(三)證據文書的調查
(四)證據物的調查
(五)勘驗
(六)被告人質問
七、爭辯證明力的機會
八、有關證據調查的異議
九、證據調查完畢后證據的處置
十、被害人等的意見陳述
十一、法院職權調查
十二、審判期日外的證據調查
(一)證人詢問
(二)勘驗
(三)扣押、搜查
第八章 證據評價與心證形成
一、自由心證主義
(一)自由心證主義的含義
(二)自由心證主義的例外
(三)合理心證主義
二、心證程度(證明標準)
三、舉證責任
(一)舉證責任的概念
(二)舉證責任的分配
(三)舉證責任的轉換
四、推定
參考文獻
參考判例
立法·原理·判例:日本刑事證據法要義 節(jié)選
《立法·原理·判例:日本刑事證據規(guī)則的“三維”檢視》: 在一般情況下,上述觀點對于傳聞證據的判斷是相同的。但是,進一步考量會發(fā)現,它們也存在著微妙的差別。以下結合具體情形進行分析。情形一:目擊證人甲未到庭,而乙出庭作證言稱“甲對我說丙拿槍射殺了被害人”。根據間接來源說或形式定義說,乙的當庭陳述為傳聞證據;而根據實質定義說,甲的庭外陳述則為傳聞證據。情形二:在法庭上回答完主詢問的證人甲因死亡等理由無法接受反對詢問的。根據實質定義說,甲的證言屬于明顯的傳聞證據,應當根據申請將其排除。根據間接來源說或形式定義說,甲的證言不是傳聞證據。但是,依然不能以此直接肯定其證據能力,而應進一步區(qū)分。如果甲為控訴方證人,無法接受反對詢問意味著剝奪了被告人的反對詢問權,除非控訴方為保證甲出庭作證盡了*大努力而*終未果,否則應當否定甲在主詢問環(huán)節(jié)所作陳述的證據能力。如果甲為被告方證人,由于與《憲法》第37條第2款的規(guī)定不產生關聯,可以證人進行了宣誓、法官對證人陳述態(tài)度進行了觀察為理由,承認其陳述的證據能力。情形三:被告人甲在法庭上所作關于共同被告人乙的陳述。根據第三種觀點,甲的陳述則構成傳聞證據:而根據前兩種觀點,甲的陳述不構成傳聞證據,“但是,這僅限于被告人乙通過質問被告人的方式對共同被告人甲進行質問,以達到與反詢問類似之實質效果的場合”。 (四)傳聞與非傳聞 《刑事訴訟法》第320條第1款原則上禁止將陳述代用文書與傳聞陳述作為證據。在諸如用以推論庭外陳述存在的場合,雖然在形式上符合該款的規(guī)定,但是實質上并無傳聞法則的適用空間。這一般被稱為“非傳聞”。以庭外陳述為內容的同一份證據,是否適用傳聞法則(傳聞抑或非傳聞),取決于該證據所欲證明的對象是什么(立證事項)。當然,以庭外陳述為內容的陳述或者文書是否能夠用作非傳聞,還取決于在特定使用方法上是否具有自然關聯性。即使用于證明原陳述存在,如果這對于該當案件的事實認定并無任何意義(證據價值)的話,該陳述或者文書將因無自然關聯性而被否定證據能力。從類型上看,非傳聞包含兩種類型:一為用以證明庭外陳述的存在。在此場合,證明對象并非陳述內容的事實真實性,原陳述的陳述過程也不會成為問題,因此屬于純粹的非傳聞(庭外陳述的非言詞證據用法)。二為雖用于證明原陳述內容所包含事實的真實性,但是該陳述的陳述過程不完整的,可以此為理由,將其視為非傳聞。具體而言,非傳聞主要包括下列具體情形: **,原陳述為待證事實的場合。以甲在法庭上作出的“乙曾說過:‘A是小偷’”的證言為例。在用甲的證言證明A實施了盜竊行為的場合,需要對甲進行反對詢問以檢驗其發(fā)言的真實性,因此甲的證言為傳聞證據。在用乙的證言證明甲實施了誹謗行為的場合,對直接聽過甲上述發(fā)言的乙進行反對詢問則是可能的。此時,乙的證言為非傳聞證據。也就是說,在原陳述本身成為證明對象時,所需要驗證的并非原陳述內容的真實性,而是原陳述者是否發(fā)表過相關言論。此時,對作為實際體驗者的證人進行詢問即可,無需適用傳聞法則加以排除。 第二,原陳述為行為的言詞部分的場合。所謂行為的言詞部分,是指與行為相伴而生并賦予其以法律意義的言詞。在用以評價行為屬性的場合,此類言詞原則上應被作為非言詞對待。例如,傳遞現金的同時說“還你錢”。單從現金傳遞行為本身無法判斷該行為的屬性,但是結合“還你錢”的言詞我們可以認定該行為屬于債務償還行為。此時,在現場的第三者對于該言詞的轉述,實際上是該債務償還行為的目擊證言,為非傳聞證據。鑒于自身的言詞性質,對原陳述是否構成行為的言語部分要結合三個條件進行綜合判斷:一是行為作為爭點的重要性;二是行為屬性的模糊性與言詞的有用性:三是言詞與行為的伴隨性。當然,在有必要對行為人的真實意思進行確認的場合,目擊證人的證言則為傳聞證據。 第三,原陳述為情況證據的場合。在將原陳述本身而非陳述內容的真實性作為推定其他事實之基礎事實(也即情況證據)的場合,包含原陳述的言詞證據為非傳聞證據。一般認為,將原陳述作為情況證據使用的情形有三:其一,證明原陳述對聽者所造成影響的。例如,在機動車肇事案件中,證人在法庭上作證:“事發(fā)前,汽修廠工人曾經告訴車主:‘這輛車的剎車系統(tǒng)故障’”。在證明對象為該車的剎車系統(tǒng)存在故障的場合,因需要確認汽修廠工人陳述內容的真實性,此時該證人證言為傳聞證據。但是,在證明對象為車主曾經收到汽修廠工人關于剎車系統(tǒng)故障的提示,并將證人證言作為情況證據之一推定車主已經意識到剎車故障的場合下,因證明對象與汽修廠工人的陳述內容真實性無關,該證人證言為非傳聞。其二,證明原陳述者精神狀態(tài)異常的。例如,在法庭上,證人言稱:“曾經多次聽到甲說:‘我是織田信長轉世’”。在用甲的陳述證明甲精神狀態(tài)異常的場合,因為該陳述并非被用來證明陳述內容的真實性,而只是作為證明陳述自身存在這一間接事實的情況證據,所以該證人證言為非傳聞證據。其三,證明原陳述者認知的。例如,機動車肇事案件中,證人陳述:“在事發(fā)當日、事故發(fā)生之前,車主曾跟我說過:‘剎車好像不怎么靈了’”。在證明對象為車輛剎車系統(tǒng)失靈這一事實時,需要確認車主陳述內容的真實性,因而證人證言為傳聞證據。但是,當該證人證言用以證明車主知曉剎車系統(tǒng)故障這一事實時,車主的主觀認知可以由本人的言論進行推論,而該言論是否存在可以通過對證人進行詢問加以確認。是故,此種場合下的證人證言為非傳聞證據。 ……
立法·原理·判例:日本刑事證據法要義 作者簡介
董林濤,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后研究人員)、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法律職業(yè)倫理研究所講師。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學士,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碩士、博士,日本九州大學訪問學者。主持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等多項省部級科研項目,在《政法論壇》《中國刑事法雜志》《法學雜志》等期刊發(fā)表學術論文30余篇。
- >
月亮與六便士
- >
我從未如此眷戀人間
- >
龍榆生:詞曲概論/大家小書
- >
隨園食單
- >
有舍有得是人生
- >
山海經
- >
羅庸西南聯大授課錄
- >
羅曼·羅蘭讀書隨筆-精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