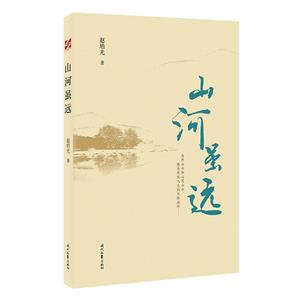-
>
百年孤獨(dú)(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guó)”系列(珍藏版全四冊(cè))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jiǎn)⒊視?shū)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guó)大家筆下的父母
山河雖遠(yuǎn) 版權(quán)信息
- ISBN:9787538765991
- 條形碼:9787538765991 ; 978-7-5387-6599-1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cè)數(shù):暫無(wú)
- 重量:暫無(wú)
- 所屬分類:>
山河雖遠(yuǎn) 本書(shū)特色
作者趙培光曾獲得冰心散文獎(jiǎng)、孫犁報(bào)紙副刊編輯獎(jiǎng)、第十五屆長(zhǎng)江韜奮獎(jiǎng)、中國(guó)散文優(yōu)秀編輯獎(jiǎng)等。 本書(shū)為作者的散文集,收錄其《草原深處的石城》《阿勒泰的惦念》《大地上的恩澤》《真實(shí)的碎片》《與年齡有關(guān)》《記憶芬芳》《所謂新知》《1994:暑中札記》等作品,以饗讀者。
山河雖遠(yuǎn) 內(nèi)容簡(jiǎn)介
這是一本散文集,收錄了冰心散文獎(jiǎng)獲獎(jiǎng)作者趙培光近年來(lái)創(chuàng)作22篇散文隨筆作品,其中絕大部分的內(nèi)容是作者的采風(fēng)瑣記和思想評(píng)述,或抒發(fā)了作者彼時(shí)彼刻的見(jiàn)聞感受,或表達(dá)了作者對(duì)某些事件的看法和意見(jiàn),內(nèi)容平實(shí),情感真摯。
山河雖遠(yuǎn) 目錄
找上海 / 001
獨(dú)自出行 / 014
面孔 / 020
草原深處的石城 / 027
阿勒泰的惦念 / 036
到白山去 / 043
回鄉(xiāng)記 / 053
大地上的恩澤 / 065
真實(shí)的碎片 / 071
關(guān)于廣告 / 075
與年齡有關(guān) / 079
忽然六十 / 082
草莓偶寄 / 096
旅伴 / 100
序或跋 / 105
所謂新知 / 116
記憶芬芳 / 126
1994:暑中札記 / 134
記這個(gè)春天 / 161
裝修記 / 169
字里流年 / 182
山河雖遠(yuǎn) 節(jié)選
找??上??海 一 國(guó)中的城鎮(zhèn)鄉(xiāng)村,散落在山水,傳說(shuō)于民間,去哪里放情看一時(shí)的興致,而我,興致之上,魂纏兮,夢(mèng)繞兮,恐怕只有上海了。 于是,得機(jī)會(huì)便去上海。一次又一次,不厭不倦,著魔中蠱了一般。 去上海干嗎? ……找上海。對(duì),找上海! 找母親咿呀學(xué)語(yǔ)的上海,找母親風(fēng)姿綽約的上海;找父親蹣跚學(xué)步的上海,找父親壯志凌云的上海;找父親母親結(jié)識(shí)的、戀愛(ài)的上海;找父親母親告別的、思念的上海。 毫無(wú)疑問(wèn),這是我找上海的初衷。 已經(jīng)十分久遠(yuǎn)了。 往往始于一粒城隍廟五香豆、一塊大白兔奶糖、一把張小泉剪子、一件開(kāi)開(kāi)牌羊毛衫、一臺(tái)永久牌自行車(chē),以及父母二人之間經(jīng)常性的吳儂軟語(yǔ)。 恍然三十五載,別夢(mèng)依稀。此后,火車(chē)、輪船、飛機(jī),我得以陸、海、空三種方式反復(fù)地出入上海,只為找我關(guān)心的上海,連同我期望的上海。或蒼茫,或明麗;或通透,或昏昧;或誠(chéng)摯,或婉約;或粗樸,或細(xì)膩。父母年紀(jì)輕輕便把自己交給了吉林,而我要把年紀(jì)輕輕的父母還給上海。明知道,諸多的想象來(lái)源于我的自作多情,譬如,那個(gè)不遜于許文強(qiáng)的男人便是父親,那個(gè)不輸于馮程程的女人便是母親。回憶的空間里,父親少年時(shí)跟著做保姆的奶奶過(guò)著窮日子,而母親經(jīng)常是一襲旗袍,搖曳在繁華的街頭與外灘。尤其是母親,一腦子電影和小說(shuō),字寫(xiě)得漂亮,毛衣織得漂亮,講故事也繪聲,唱越劇也繪色,榮耀了平房院落的左鄰右舍。 生活之余,多是時(shí)光遺漏的那些細(xì)碎記憶。晚飯后,燈光下,母親給兒女們講老家舊事,講她的手足弟妹。*令她放心不下的是大弟,也就是我的大舅。大舅學(xué)習(xí)很努力,苦苦拼爭(zhēng),卻沒(méi)能考上高校,致使神經(jīng)錯(cuò)亂,毀掉了前程。二姨遠(yuǎn)嫁西安,在國(guó)棉六廠上班。三姨哪也沒(méi)去,隨長(zhǎng)輩過(guò)著油鹽醬醋的日子。再就是四姨、五姨和小舅了,同父異母所生,感情不近不疏的,維系著親人的關(guān)系。上世紀(jì)70年代,我們家一時(shí)困窘,母親寫(xiě)信求助于二姨,借二十元錢(qián)。這件事,深深烙在我的心頭,直至今天,直到永遠(yuǎn)。 還有一個(gè)結(jié),不,一個(gè)謎,似乎永遠(yuǎn)也解不開(kāi)了。1953年,父母為什么放棄黃浦江畔的大上海而落戶在松花江畔的吉林?據(jù)說(shuō),是來(lái)參加“三大化”建設(shè):101、102、103,即染料廠、化肥廠、電石廠。將近六十年,風(fēng)霜雨雪,苦辣酸甜,然后被合葬在距“三大化”不遠(yuǎn)的南山陵園。也快十年了,我每次去祭掃,佇立墓前,都禁不住想,要不要把二老的骨灰盒捧回上海,尋一片清靜安息。終究是,念念而已,想想則罷。 二 不錯(cuò),從神游上海到行走上海,我整整花掉了童年、少年及青年,時(shí)光夠漫長(zhǎng)的。 1985年4月29日,風(fēng)香日暖,開(kāi)啟婚旅。按照方便的路線圖,先是北京、南京、蘇州、杭州,然后便落腳上海了。 上海有著我的一系列親戚,*親的是三姨和三姨父及其一雙兒女。此前,母親給我一個(gè)地址:中山南一路944弄。舟車(chē)勞頓,待到弄口張望,方知:弄,相當(dāng)于胡同,卻比胡同還小。七拐八彎,在狹窄的深處,摸到了三姨家。親戚好,好親戚,笑臉相迎,酒菜相待,讓我們很快就不把自己當(dāng)外人了。幾天里,備受照料,好不熱鬧。可好歸好,不便之一是,解手要到一百五十米以外的公廁,盡管屋里有馬桶,但不習(xí)慣。 上海足夠誘惑,白天轉(zhuǎn)不夠,晚上接著轉(zhuǎn),主要是圍著南京路轉(zhuǎn)。大世界、大光明電影院、和平飯店、外灘等從概念中一一呈現(xiàn),不失時(shí)機(jī)地促發(fā)我對(duì)父母當(dāng)年原貌原聲出入其中的聯(lián)想。莫名其妙的是,自己也仿佛孩子般跟隨著他們哼起了《夜上海》:“夜上海,夜上海,你是個(gè)不夜城。華燈起,車(chē)聲響,歌舞升平……”仿周璇唱的那種聲調(diào),凄切,曖昧,如夢(mèng)初醒。 我們順道去了三姨家新分的房子。哦,實(shí)際是舊房,在上海電視臺(tái)附近。進(jìn)去看,跟車(chē)庫(kù)差不多,已經(jīng)搭起了二層隔斷,準(zhǔn)備住人的。說(shuō)心里話,房子不怎么樣,但三姨一家卻樂(lè)開(kāi)了花。他們還慶幸呢,不用去浦東了。盡管浦東可以分到寬敞些的,但不想去,不愿意去,太遠(yuǎn),也太不方便。住浦西住慣了,浦東像漁村,剛剛傳出開(kāi)發(fā)的消息。當(dāng)時(shí),民間流傳一句話: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套房。 還是浦西好。怎么個(gè)好?一條南京路演繹著無(wú)盡的繁華,蔓延到上海的四處。哪怕?lián)頂D,哪怕逼仄,哪怕放眼望去人頭攢動(dòng),樓窗支出的鐵架上飄動(dòng)著晾曬的被褥和衣服…… 三 爾后,再去上海的時(shí)候,跟著欲望走,由南京路擴(kuò)展到河南中路、陜西南路、西藏東路、洋涇邦路、淮海路、衡山路、福州路、漕寶路、宛平路……如果把上海比作一棵樹(shù),路便是它的枝,房就是它的葉。路可以盡情地走,想乘涼嗎?大樹(shù)底下不太好乘涼,即使是片刻的涼。 父母養(yǎng)育了五個(gè)兒女,始終寄望著晚輩有朝一日回上海,回他們的上海,綿長(zhǎng)且柔韌,柔韌且綿長(zhǎng)。大哥參加工作后,超常規(guī)地發(fā)奮圖強(qiáng),讀吉林醫(yī)學(xué)院學(xué)士五年,讀白求恩醫(yī)科大學(xué)碩士三年,讀北京醫(yī)科大學(xué)博士三年,讀上海醫(yī)科大學(xué)博士后三年,又去美利堅(jiān)合眾國(guó)鉆研尖端醫(yī)學(xué)十年,光陰荏苒,幽夢(mèng)飄浮,*后終于落戶到上海。 上海好嗎?前塵往事今猶在,風(fēng)雷激蕩更精神! 公務(wù)或者私游,我一次次到上海逗留,心下不免思及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何止是想,還付諸行為。我把我的愿望說(shuō)給上海的同學(xué),還把求職簡(jiǎn)歷交給上海的朋友。左難右難,左右為難,直至我解甲歸田。這也不算完,等我更老一些的時(shí)候,就在上海租住,寧肯舊房、小房、邊緣房。終究成為一片枯葉,落下來(lái),化為泥土。 上海,位于長(zhǎng)江中下游平原,傍蘇州河,濱黃浦江,外向遼闊的大海。海納百川的胸懷及眼光,讓這座城市突飛猛進(jìn),煊赫東西半球。 近、現(xiàn)兩代史,租界是沉重的,孤島是沉郁的,江水滔滔東去,流走了屈辱,遍地是城市的光榮與夢(mèng)想。一步一步地,揮汗瀝血,上海成為奮斗者的樂(lè)園,而融入上海的*好方式是人才的如魚(yú)得水。福哉,幸哉,上海托起了人才,人才托起了上海,相輔復(fù)相成。 也不是順風(fēng)順?biāo)敲春?jiǎn)單,天下蕓蕓人才,何以在上海安家立業(yè)? 大地上,腳步匆匆,人心茫茫。 機(jī)會(huì)與難點(diǎn)同在,過(guò)盡千帆,顧慮一片一片,多少人才留也留不住,位子、票子、房子、孩子,壓得八方匯聚的人才直不起腰、喘不勻氣,奈何依依不舍地放棄。放棄,并且期望重新回來(lái)。 房子是庇佑人才的前提。2000年,同學(xué)在黃浦區(qū)買(mǎi)了一套102平方米的舊房,每平方米6480元,據(jù)說(shuō)現(xiàn)在總房?jī)r(jià)早已突破千萬(wàn);2004年,大哥在楊浦區(qū)買(mǎi)了一套105平方米新房,每平方米12000元,據(jù)說(shuō)現(xiàn)在總價(jià)也接近千萬(wàn)了。歲月追趕著歲月,生活壓迫著生活,時(shí)至今日,房產(chǎn)市值基本上漲了10倍左右,200萬(wàn)勉強(qiáng)交個(gè)首付,還算不上理想的房源。外鄉(xiāng)人,隔岸觀火,偶爾幽它一默,道:房子安好四輪,推到上海去賣(mài)。 古人居長(zhǎng)安,不易,不易,無(wú)關(guān)房?jī)r(jià);今人居上海,不易,不易,無(wú)非房?jī)r(jià)。 還是很小的時(shí)候,常聽(tīng)父母說(shuō)到上海大廈,二十四層,獨(dú)高無(wú)二,那份“唯我獨(dú)尊”的氣概,令很多人口口傳誦。到今朝,早已嬰孩兒般淹沒(méi)在橫無(wú)際涯的樓海中了。走在它的身邊,我覺(jué)得自己如同潛水員,需要笨拙地?fù)潋v。 從父母,找上海,有些落葉歸根的意思。九泉之下,父母不能了,而我要繼承二老的遺愿,好好活著,好好找。 四 上海不是古都,卻很會(huì)懷舊。憑借一首詩(shī),憑借一幅畫(huà),憑借一片云,憑借一陣風(fēng)。我如果替上海來(lái)一次煙雨蒙蒙的懷舊,*好的方式是弄一部電視劇,五十集。名字我都已經(jīng)想好了,就叫《黃浦江的女兒》。卻始終未敢動(dòng)筆,沒(méi)底氣。 畢竟,上海是有格調(diào)、有性情的,就是所謂城市的調(diào)性。
山河雖遠(yuǎn) 作者簡(jiǎn)介
趙培光,筆名野馬。詩(shī)人,散文家。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中國(guó)散文學(xué)會(huì)理事,中國(guó)記者協(xié)會(huì)理事。吉林省作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吉林省散文委員會(huì)主任,吉林省雜文學(xué)會(huì)副會(huì)長(zhǎng)。《吉林日?qǐng)?bào)》社高級(jí)編輯(二級(jí))。曾獲得冰心散文獎(jiǎng)、孫犁報(bào)紙副刊編輯獎(jiǎng)、第十五屆長(zhǎng)江韜奮獎(jiǎng)、中國(guó)散文優(yōu)秀編輯獎(jiǎng)等。已出版詩(shī)集、散文集、小說(shuō)集等十六部著作。
- >
自卑與超越
- >
煙與鏡
- >
人文閱讀與收藏·良友文學(xué)叢書(shū):一天的工作
- >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實(shí)旅程
- >
中國(guó)人在烏蘇里邊疆區(qū):歷史與人類學(xué)概述
- >
詩(shī)經(jīng)-先民的歌唱
- >
回憶愛(ài)瑪儂
- >
羅庸西南聯(lián)大授課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