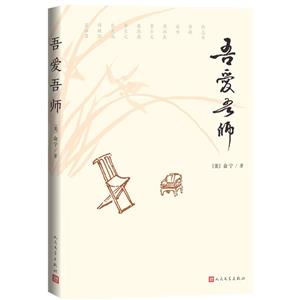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吾愛吾師 版權信息
- ISBN:9787020167135
- 條形碼:9787020167135 ; 978-7-02-016713-5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吾愛吾師 本書特色
他當學徒工時的師傅,作研究生時的老師,還有*讓他念茲在茲的父親“俞師傅”和朝夕相處的“啟大爺”……他們的一句話,一個眼神兒,一個動作,哪怕當初叫他難堪,很不高興,而今,“卻話巴山夜雨時”,又會變成一種溫馨的記憶。——劉躍進
吾愛吾師 內容簡介
《吾愛吾師》是一部作者回憶、懷念親人長輩們的隨筆集。作者是著名學者俞敏之子,青少年時期,他與父執啟功、包桂濬、柴德賡、李長之等先生生活交集較多,并且曾得到這些人無私的關愛與教誨。文章所寫皆是作者自己親身聞見的日常生活瑣事,事情雖然都是細枝末節,但從中我們卻能夠領略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風貌,以及他們高貴的品質和高尚的情操。作者去國三十余載,平時很少使用母語寫作,但是一旦下筆回憶故國故人,便不自覺地流露出濃濃的京味兒,極具特色。
吾愛吾師 目錄
近乎本色的記憶·1·
*憶師恩·8·
鳴謝·20·
天使的香味——回憶陸志韋校長生平片段·1·
少年印象——我的父親俞“師傅”·11·
母親與“抖須”·21·
啟大爺·28·
三十年無改父之道——和父親的約法三章·40·
震災中的“秀才人情”·47·
兩位師傅·57·
曼倩不歸花落盡——發現元白先生墨寶一件·69·
元白先生說“不”的藝術·76·
濃贈迎曦滿室香——和元白先生聊美國華裔女作家水仙花·89·
元白先生的人格與風格·102·
元白先生背后的章佳氏家族·114·
柴青峰先生出北平記·128·
柴青峰先生逃婚記·140·
遲來的謝意——懷念李長之先生·155·
月光皎潔只讀書——懷念既專且通的包天池老伯·167·
吾師“周公”·183·
只緣身在此山中——懷念傅璇琮先生·200·
懷念吳谷茗老師·207·
附錄:
元白先生論元、白·223·
論詩兼論人——從“明代苦吟”到“分香賣履”·233·
金牌得主李愛銳·243·
印度才子白春暉·253·
近乎本色的記憶
□ 緩之
吾愛吾師 節選
母親與“抖須” 我從2016年暑假開始重新用漢字寫文章,沒想到一發而不可收,竟寫了二三十篇。2020年暑假開始,給自己定了一個規矩,準備暫時封筆。干什么吆喝什么。我一個教英文的,不能一味寫漢字文章。沒想到此時《南方周末》約稿,題目是“影響我*深的三本書”,觸發了我的回憶,竟然引我“破戒”。 要說影響我*長久的,當數唐詩。我四五歲的時候,母親從韶關的外婆家把我接回北京。外婆送我們繞過一個水塘,母親彎下腰對著我耳朵說:“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阿婆送我情。”回到北京,夏夜院子里,坐在父母中間乘涼。那時的市中心還有螢火蟲飛來飛去,我用大蒲扇去拍打,扇出的風讓它們飄得更遠了。母親說:“輕羅小扇撲流螢。”從濕熱的廣東來到北京,我*能體會“天階夜色涼如水”的滋味。對我來說,唐詩不是一本書,是一種聲音——母親的聲音,清柔如暑天的微風。父親問我:“你怎么把‘撲(pū)流螢’念成‘瀑(pù)流螢’呢?”我說:“‘撲流螢’不好聽,‘瀑流螢’好聽。”父親搖搖頭,說:“怪來哉!‘撲’是入聲一屋。仄平平。”我一頭霧水。唐詩不是書,是一個謎——父親的謎,神秘如夏夜的流螢。 我的生日比法定開學日期晚九天,要再等上一年才能入學。母親不甘心。她領著我到大翔鳳小學,從校長室到教務處到教室,走了好幾個地方,游說老師們:“這孩子怪,沒人教過他漢語拼音,他自己就會拼。”說罷讓老師隨便指個什么東西,然后讓我拼出聲母和韻母:之喔桌,依蟻椅,吃汪窗,喝霧戶。校長和教務主任點了頭。出了校門,母親囑咐我,上了學不能和小朋友打架,要好好“抖須”。我在外婆家,聽不懂外人的廣東話,聽得懂家人的湖南話。 抗戰期間母親在重慶的國立女子師范學院國語專修科讀書,勝利后跟隨她的老師魏國光先生到臺灣推行國語,普通話極標準。那天她故意用家鄉話把讀書說成“抖須”,是為了一番緊急的學前教育:“你看蟋蟀平時抖動它的長須,多威風、多漂亮!再看它打架時張開大牙,與對手掰來擰去的,多暴力、多難看!你上學以后不要做難看的事情。”我們住的那條胡同叫大翔鳳胡同,那里的學校叫大翔鳳小學。我知道,那原來叫“大墻縫”胡同,有人嫌它不好聽,改成了大翔鳳。我想,我要真是母親所說的蟋蟀,那么“大墻縫”倒是我應該去的地方。加上她領我奔走求情,讓我感到爬進“大墻縫”“抖須”是費力氣爭來的機會,很寶貴。 于是我就努力認字,為了早點兒“抖須”。到了二年級的寒假,我在課里課外認了不少字,趴在舊沙發上竟讀完了一本大約二百頁的“厚字兒書”,叫作《藺鐵頭紅旗不倒》,而在那之前,所看的都是我們叫作“小人兒書”的連環畫。因為是**本,所以印象特別深。不知道為什么,它影響我*深的,不是書里寫的戰斗故事,而是書里沒寫、我想象出來的那個孤單的、趴在箱子上的人。這使我早早就懂得,讀書與寫書,都不是湊熱鬧的事。還有一件得意的事,是連我哥哥都不認識的“藺”字,我卻認得。 我所讀的第二本影響深刻的書是《儒林外史》。我對周進的理解與同情,遠勝于對范進的嘆息與搖頭。但一部大書*給我震撼的,竟是那些不惹人注目的小人物。比如蕪湖甘露庵里的老和尚,見詩人牛布衣客死他鄉,不但在他柩前念“往生咒”,而且忙碌著“煮了一鍋粥,打了一二十斤酒,買些面筋、豆腐干、青菜之類到庵”,請眾鄉鄰一起祭奠牛布衣。他說:“出家人不能備個肴饌,只得一杯水酒,和些素菜,與列位坐坐。”眾人答道:“我們都是煙火鄰居,遇到這樣的大事,理該效勞。”于是老和尚請了吉祥寺八眾僧人替牛布衣拜了一天的《梁皇懺》。自此之后,老和尚早晚課誦,開門關門,一定到牛布衣柩前添些香,灑幾點眼淚。小人物里有真君子,無論出家的還是在家的,都讓我聞到了一股生活本身的“煙火氣”。 還有開香蠟店的牛老爹和間壁開米店的卜老爹,他們日常的交往寒素而溫暖:“卜老爹走了過來,坐著說閑話。牛老爹店里賣的有現成的百益酒,燙了一壺,撥出兩塊豆腐乳和些筍干、大頭菜,擺在柜臺上,兩人吃著。”我十四五歲時讀到這里,無來由地覺得這樣的溫情小酌,遠勝大觀園里“饕餮王孫應有酒,橫行公子竟無腸”式的狂歡豪宴。他們經營小本生意,勉強度日都難,卻肯互相幫襯著為孫子、外孫女完婚。卜老爹說:“一個外甥(孫)女,是我領來養在家里,倒大令孫一歲,今年十九歲了,你若不嫌棄,就把與你做個孫媳婦。你我愛親做親,我不爭你的財禮,你也不爭我的妝奩,只要做幾件布草衣服。況且一墻之隔,打開一個門就攙了過來……”我看到小人物在生活的重壓下仍然保持了一種素樸的尊嚴,在窘困中盡力安排自己的生活。其言行舉止,無意中流露出人性溫柔的光。可惜牛老爹的孫子牛圃郎不學好,把“三討不如一偷”之類的奸詐當作智慧,“捵開”老和尚的箱子,偷出已故牛布衣的詩集,冒充牛布衣到社會上招搖撞騙,作廉價的“名士”。我在學校里、社會上聽到很多“做人要誠實”的說教,但都不如這段故事有效。我不能騙人,不能像牛圃郎那樣對不起他祖父那溫柔敦厚的人品。 1978年,我考上大學,成了英語專業的學生。三年級時來了一位美國教授“老白”(Eric White)。一天他把一本書扔到我課桌上,說:“寧,你翻翻(thumb it through),如果喜歡,咱們抽印一部分,作課本。”我一看,是Walden and Other Writings(《瓦爾登湖和其他作品》),美國十九世紀作家梭羅寫的。我這一翻可不要緊,好像找到了文學的新大陸。沒翻幾頁,我就不由自主地朗誦起來:“近來哲學教授多得很,哲學家卻一個沒有。現在我們羨慕授課,因為過去我們曾經羨慕生活。作為哲學家,僅有微妙的思想,甚或建立一個學派,都是不夠的;應該熱愛智慧,并按照智慧的吩咐去過一種簡樸、獨立、大氣、信任的生活。”①我少年時跟父親讀《論語》,曾經非常崇尚“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那種高風崇義。現在讀了梭羅的話,大有他鄉遇故知的感覺。后來還發現他從法文譯本里讀到孔夫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段話,不知是法文譯者的主意,還是梭羅本人的“妙計”,總之,英文譯本是用哥白尼名言代替了孔夫子的語錄:“To know that we know what we know, and to know that we do not know what we do not know,that is true knowledge.”我試著把它再譯回中文,感覺頗為好玩:“知道我們知道我們所知道的,也知道我們不知道我們所不知道的,這才是真知。”這種奇妙的語言變化,把一個倫理學陳述,變成了一個認識論的陳述;把孔夫子的話用哥白尼的話來替代,而讀者又不能說它完全錯誤,使我初次感受到語言學習和文化交叉的深層樂趣。 梭羅關于讀書的論述也讓我心生喜悅:“文字是*精美的文物……它是貼著生活*近的藝術品。”而經典作品的著者“在每個社會里都是自然的、無法抗拒的貴族”。他提倡讀者讀書應該像著者寫書一樣的認真而慎重。*好的書房不是大學的圖書館,而是他在樹林里自己搭建的木屋,因為不用交學費,不用付租金,成本*低,因此干擾*少、精力*為集中。讀書是精神上的新生。他挑戰性地設問:“有多少人能夠用讀了某一本書來記錄自己生命又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呢?”我因此想到了《禮記˙大學》里的名言:“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正是因為讀了梭羅,我才心里打定主意,此生不妨在研讀英美文學中度過。同時產生了到瓦爾登湖游游泳的想法。若干年后,我帶著兒子橫渡瓦爾登湖的時候,忽然產生了幻覺,仿佛在我身旁奮力劃水的不是十四歲的男孩,而是四十歲的梭羅。古人說“一個人不能兩次涉足同一條河”,但我覺得托我浮起的那湖清水,也曾承載過梭羅簡單明快的思想:人生本不復雜,我們把它極簡化,是為了把只有一次的生命用在我們覺得*有意思的地方。 1982年徐遲先生翻譯的《瓦爾登湖》出版了。我買了一本送給母親。她反復閱讀,在上面畫了許多著重的橫線,并在扉頁寫了幾句話: 兀兀不修善 騰騰不造惡 寂寂斷見聞 蕩蕩心無著 我問她什么意思。她說:“參。”我參不透,也不太在乎。反正在參透之前,我還可以繼續“抖須”。參透以后是不是就不“抖”了呢?那也未必。 老白教授離開中國的時候,把那本書送給了我。我至今還保存著。我每次教十九世紀美國文學課,一定用它,絕不新買一本。它現在卷邊破角,看上去像一只疲倦的老狗。但我把它看得比魯迅那只“金不換”毛筆還珍貴。狗是人類*忠實的朋友,這本老狗似的舊書,是我*心愛的伙伴。老白在科羅拉多大學英文系教書,我在西華盛頓大學英文系教書。我們聯系不多,也沒斷。他知道我還在“抖”著他當年送給我的“須”。
吾愛吾師 作者簡介
俞寧,1955年出生,1986年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英文系獲英美文學碩士學位,1993年在美國康乃迪克大學畢業獲英美文學博士學位。現任美國西華盛頓大學英語言文學系教授(終身職)。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中國歷史的瞬間
- >
二體千字文
- >
隨園食單
- >
苦雨齋序跋文-周作人自編集
- >
自卑與超越
- >
經典常談
- >
龍榆生:詞曲概論/大家小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