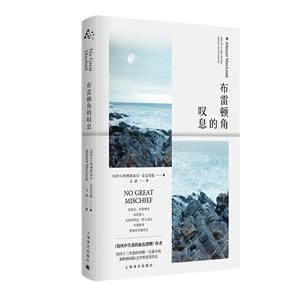-
>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茨威格短篇小說集
-
>
女人的勝利
-
>
崇禎皇帝【全三冊】
-
>
地下室手記
-
>
雪國
-
>
云邊有個小賣部(聲畫光影套裝)
-
>
播火記
新書--布雷頓角的嘆息 版權信息
- ISBN:9787532785384
- 條形碼:9787532785384 ; 978-7-5327-8538-4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新書--布雷頓角的嘆息 本書特色
《海風中失落的血色饋贈》作者阿利斯泰爾?麥克勞德唯一長篇小說 歷時十三載創作,被譽為“加拿大大西洋省份*偉大的小說” 都柏林文學獎、達特茅斯圖書獎、加拿大三瓣花圖書獎等多項國際大獎得主,一部縮小版的蘇格蘭移民史
新書--布雷頓角的嘆息 內容簡介
兩百多年前,蘇格蘭高地麥克唐納家族的紅頭發卡隆帶領妻兒跨越千山萬水,從蘇格蘭來到遙遠的新大陸,在那片擁有茂密森林與漫長冬季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后來,紅頭發卡隆的后裔們陸續離開布雷頓角這座海島,散落在加利福尼亞的海灘、南美洲的礦區、非洲的沙漠……但無論走多遠,布雷頓角始終是縈繞在他們心頭永恒的牽掛。那對著巨頭鯨歌唱的夏日,少年追逐彩虹的背影,那些有關忠誠與背叛的傳說,在歲月的狂風暴雨中,幻化為一聲溫存而沉重的嘆息: “當我們被愛著的時候,我們就會變得更好。” 《布雷頓角的嘆息》故事穿梭于“現在”和“過去”之間,主人公亞歷山大?麥克唐納早已離開家鄉,對往事的記憶也已模糊,但與哥哥、妹妹的交集卻讓他時常在不經意間回想起童年生活和祖輩的故事,他*終理解了血脈情深與那超越一切傷痛苦難的故土情懷。 這也是一部有關文化溯源的作品,是一部縮小版的蘇格蘭移民史。透過個人成長與家族變遷,阿利斯泰爾?麥克勞德展現了兩個世紀以來動蕩的加拿大文化版圖,探索了不同語言、文化之間相斥共生的歷程。
新書--布雷頓角的嘆息 節選
1 我和你說啊,那個時候,安大略省的西南部正是金秋九月的好季節。美妙的秋日陽光照耀豐饒的土地,令人目眩神迷,好像再現了濟慈詩中的美景。3 號公路的兩旁堆滿了一籃籃農作物和一筐筐花草。路邊的招牌邀請人們來田里“采摘果子”。有幾家人正在摘果子,他們的腰彎了又直,直了又彎,有的人踩著梯子,伸手去夠蘋果和梨,有的人提著裝滿的籃子,腳步蹣跚。 在幾個大農場里,大部分采摘工作由外來工人干。他們也是一家人齊上陣,不過摘下的果子并不屬于他們,能拿走的只有應得的那點薪水。這片土地也不是他們的故土,工人們有的來自加勒比地區,有的是墨西哥的門諾派基督教徒,還有新不倫瑞克和魁北克的法裔加拿大人。 收割完的土地變得暗淡無光,農夫開著拖拉機將一片片老莊稼推倒,給新莊稼騰出位置。一大群海鷗滿懷希望地跟在后面,粗聲粗氣地叫嚷,仿佛感激涕零。有一年,我奶奶恰好這時過來做客。當她經過利明頓郊外,見到一堆不合格的爛西紅柿被推平碾碎,眼淚一下子涌了出來。她為這“可恥的浪費”哭泣,差一點沒跑到地里去,將那些西紅柿“救出”犁溝,免遭厄運,只可惜她與自家的儲藏箱相隔了一千五百英里。奶奶幾十年如一日,在春夏時節為那幾株生長在石頭地里的寶貝疙瘩施肥,到了秋天,便摘下寥寥幾個好不容易存活下來的仍是青綠色的西紅柿,將它們擺放在窗臺上,盼著斜射進來的微弱陽光能將它們催熟。對她 而言,那幾顆西紅柿就是稀罕的寶貝,十分難得。所以,當她在利明頓的郊外見到那些西紅柿被丟棄,著實抑郁了好一陣子。我猜她根本抑制不了這種感情,就像我們在*不恰當的時機總是抑制不住去想煩心事。 這樣,我一邊回憶往事,一邊開車沿金黃富饒的公路駛向目的地多倫多。每逢周六,我便踏上這段旅程,每次都是一大早出發,盡管沒有任何必要趕這個早。在春秋兩季,我會走一條風光更好的長路,比如2 號公路和3 號公路,有時也走98 號公路和21 號公路。這幾條路曲折蜿蜒,令人心情暢快,不時還能見到狗兒跑到路邊朝過路車的輪胎狂吠,這對于漫長的旅程而言是個極好的安慰。似乎在它們眼里,這些車也算得上一件大事。而在酷熱的夏天和嚴寒的冬天,我一般走401 公路。401 公路,不少人一聽就知道,它起源于美利堅,筆直而忠實地通往魁北克的邊界——也許有些人認為那里是另一個國家。這條公路為*大限度 地運送人和貨物而修建,它是*快捷的選擇,也是*平庸、*無趣的選擇。在我看來,它是一個標志,就算不是*快*窄的路,也算得上是*直截了當的路,或者說,是“唯一的一條近路”。 401 公路有特定的入口,若是你要去的地方就在這條路上,它會像運送西紅柿的傳送帶一樣,干凈利落地把你送到目的地。只要你忠實于它,它便會忠實于你,讓你永遠、永遠都不會迷路。 不提這條公路的入口怎么找,我們先說說多倫多城——它總是奇跡般出現在你眼前。車流越來越多,你需要重新協調神經去適應汽車的停停走走,若想去到目的地還真得費點腦筋。 央街沿線以及往西的繁華地帶,反核人士們正手舉招牌游行,高喊:“一二三四五,反對造核武!六七八九十,遠離核輻射!”街對面并行的是另一隊同樣堅決的人馬,令氣氛更加劍拔弩張。只見他們舉著的告示牌上寫著:“反戰人士,你們是紅黨的*愛。”“不挺加拿大,不要賴在這。”“不愛加拿大,統統滾出去。 ” 行至位于央街和士巴丹拿大道之間的皇后西街,我漸漸放慢速度,觀望四周,盼著能在這條街上看見他,盼著他會在這里迎接我,不管我從哪條道過來。然而這次我并沒有如愿。我驅車拐進一條小巷,那兒有幾個上鎖的垃圾桶,偶爾還有條狗拴在旁邊。玻璃碴已被壓平碾碎,對輪胎不再構成威脅。逃生通道和樓梯橫七豎八地插在樓房后面,各種聲響從虛掩的門窗里傾瀉直下,有來自不同國家的音樂聲和歌聲,有大到好像吵架的說話聲,以及不斷傳來的玻璃破碎的聲音。 秋日的陽光下,我把車停在午后的小巷,沿圍墻走上人潮涌動的大街。街上到處是討價還價的買家,吆喝的老板,撿垃圾的人。店鋪骯臟的窗戶上掛著手寫的招牌,出售的商品簡直應有盡有,而且看上去都十分劃算。 這些鋪子之間,有幾扇門是那么普通,總是被人忽視。它們大多漆成棕色,有的門牌上掉了一兩個數字,在釘子上搖搖欲墜,有的甚至連門牌都沒有。推開這些門,你會見到一排信箱,有的信箱用灰色膠帶貼著姓名。門里大多有一段陡峭的木頭樓梯,徑直通往頂樓。頂樓的走道亮著昏暗的白熾燈光,兩邊房間都住著人,有的頂樓還不止一層。房間就在那些店鋪的樓上。和料想的不同,這里的住戶幾乎都不是店鋪的老板,而是身無長物的窮光蛋。就連屋里的家具大多都不是他們的,所以在搬家時——他們總在搬家——也不用翻黃頁找搬家公司幫忙。 住戶之中只有幾對夫妻,更多的是形單影只的人,大多是已過中年的男人。有時候,一整條走廊的房間住的全是男人。由一兩個小單間組成的公寓樓里*常出現這種情況。走廊里只有一個小小的衛生間設在盡頭,供整層樓的住戶使用。這些衛生間的門永遠也鎖不上,坐在里面必須用一只腳頂住門。不時能聽見內急的人站在關著的門前大聲詢問“里面有人嗎”,像是一大家子人起床后搶著用廁所。衛生間內,廁紙用一團精心纏繞的線掛著,發出昏暗光芒的燈泡也套了一層鐵絲網,以免被人偷去裝在自己房間。污漬斑斑的水池里,有個龍頭永遠關不緊,不斷滴落的水珠留下一條黃色的污跡。熱水幾乎用不上,再上一層樓更是見不到它的存在。 那些緊閉的門后依然會傳出模糊的聲響。*好辨認的是男人咳嗽和吐痰的聲音。這兒幾乎所有人都是老煙槍,有人只穿條內褲坐在床邊,自個卷煙卷兒。還能聽見收音機和便攜式小型電視機的聲響,這些器件就擱在桌上或是空空如也的冰箱上。畢竟這兒吃得豐盛的人著實太少。大多數房間都沒有爐灶和可用的烤箱,泡著餅干的西紅柿湯得放在熱金屬板上加溫。空氣中常年飄著面包的焦煳味,窗臺和銹跡斑斑的暖氣片上隨處放著裝速溶咖啡的罐子、裝茶包的紙盒,以及袋裝的曲奇餅干。這些添加了大量防腐劑的食物像是幾個月都不曾有人動過。 我走進一條這樣的走廊,把街上的陽光拋在了身后,又爬上了一段這樣的樓梯,來到了頂樓的大廳。這已經是他幾年來第三次住在這個地方了。兜兜轉轉,*后又回來和這里的房東簽合同——他還為房東打過雜呢。房東一次次答應他回來住的請求,看中的就是他還算可靠,以及他們好幾年的交情。房東以前用棕色紙袋裝酒賣給租客,他有很多煩惱想找愿意聽的人傾訴。他說生意不好做,租客們要不就欠著房租趁黑夜偷偷搬走,要不就把他和老婆買來的家具偷走賣掉,要不就配上好幾把鑰匙讓朋友住進來。他還說世道艱難,晚上在家看電視看得好好的,總會接到警察的電話。有時是租客們又打架了,有時是喝高了的人拿餐刀互捅,有時是有人屎尿橫流地死在床上,被堵在喉嚨里的嘔吐物活活憋死。遇到這種情況,他都不知道該聯系誰。他說這些尸體一般都“捐給科學事業”了,又補充道:“這就能顯出你的好處。 萬一他有個閃失,我還知道該聯系誰。”房東是個矮胖男人,年幼時從歐洲過來,后來發了些財。他的幾個孩子都讀了大學,他們在他錢包里的照片上微笑著,露出潔白整齊的牙。他為他們感到驕傲。 我走在樓道里,心里照例有些不平靜,總擔心出什么事。要是敲門沒人應,門又鎖著,我會把耳朵貼上鑰匙孔,看看能不能聽到他急促的呼吸聲。要是沒聽到動靜,我就返回街上,到隔壁的小酒館看看。那兒的啤酒杯下面永遠都有一攤不干不凈的水漬,一滴一滴往地上淌;那兒的酒客們搖搖擺擺從衛生間走出來時,總是拉不上褲子拉鏈。 而這次,我一敲門,他的聲音就響了起來。“進來吧。” 我推了推門,推不動。“門鎖著呢。” “那你等等,”他答應道,“等一下。”里面傳來三聲忽快忽慢的腳步聲,接著聽見砰的一響,就沒動靜了。 “你沒事吧?”我問。 “嗯,沒事。”他回答說,“等等,馬上就給你開門。 ” 門鎖一轉,門開了。我走進去,他站在一旁,兩只大手撐在門把上,身體隨著門的開合而搖晃。他穿著短襪,棕色工作褲,系一條同色的寬皮帶,上身只穿了一件泛黃的白色羊毛內衣。這件衣服他一年到頭都穿在身上。 “啊,”他說的英語混雜著蓋爾語,“啊,紅頭發男孩,你終于來了。”他后退幾步,把門往里拉開,手依然撐在門把上。他左邊眉骨上有一道傷疤,很可能是剛才絆倒那會兒磕在了床墊角落凸起的鐵架上。血順著他的臉往耳后流淌,流到下巴上,脖子上,*后消失在內衣下面的胸毛中,幾乎要滴在地上,但沒有,也許全被褲管口接住了。鮮血沿著他臉上的溝壑流淌,如同山澗小溪蜿蜒流入大海。 “你磕傷了嗎?”我說著,想找紙巾給他擦掉那條血的小溪。 “沒有啊,”他不解地問,“怎么了?”他順著我的目光,抬起撐在門把上的左手去摸臉,然后驚訝地看著手指上的血跡。“哦,沒事,擦傷了而已。”他說。 他放開門把,蹣跚著退后,跌坐在亂七八糟的床上,彈簧發出一聲抗議的聲響。他的手一放開門把,便開始劇烈地顫抖。坐下來后,兩只手垂在身旁,牢牢抓住鐵制的床架。他抓得那么牢,布滿傷痕的粗大指節都開始發白,不過手終于是不抖了。 “只要我能抓著點什么,”他晃動身體,自我解嘲地說,“就好得很。 ” 我看看四周,這個熟悉的小房間依舊簡單得要命。房間里見不到任何食物,看來他今天還沒吃過東西。水池邊的垃圾桶里有一個琥珀色的瓶子,是那種甜得發膩的廉價酒的包裝。瓶子是空的。 “你想吃點什么嗎?”我問他。 “不用,”他回答得很干脆,停頓一下,又補充了一句,“沒東西可吃。”他重重說出*后一個字,笑了。他的眼睛和我一樣黑,他的頭發曾經也是黑的,現在已經變成了一蓬透亮的白色。這頭發是他身上僅有的仍然充滿生機的東西,從額頭上源源不斷地冒出,因為沒有修剪,已經漫過了耳朵,淹沒了頸脖。這種跡象表明這個人吃得太少、喝得太多。酒精是一種奇怪的養料,它讓頂端的葉子繁盛豐茂,卻令整棵植物麻木枯萎。 ……
新書--布雷頓角的嘆息 作者簡介
阿利斯泰爾·麥克勞德(1936-2014),加拿大著名小說家。他生于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北貝特爾福德市,但在十歲時隨父母搬回世代居住的老家、位于加拿大大西洋省份新斯科舍省的布雷頓角島定居。他早年從新斯科舍師范學院畢業后成為一名教師,后來,他相繼在新斯科舍省的圣方濟各?沙勿略大學和新不倫瑞克大學攻讀學士和碩士學位,1968年在美國圣母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年輕時為了維持學業,他做過伐木工、煤礦工人和漁夫。 1969年,在印第安納大學英語系執教三年之后,他回到加拿大,在安大略省的溫莎大學教授英文和寫作,直至退休。麥克勞德一生只出版了兩部短篇小說集《海風中失落的血色饋贈》(1976)、《當鳥兒帶來太陽》(1986)和長篇小說《布雷頓角的嘆息》(又譯《沒什么大不了的》(1999)。2000年,他的加拿大出版社McClelland & Stewart將他早年兩部短篇集加上兩個新的短篇小說,出版短篇小說合集《島嶼》。 2014年4月,麥克勞德在溫莎病逝。 《布雷頓角的嘆息》是麥克勞德唯一的長篇小說,歷時十三年完成,獲得包括都柏林國際文學獎在內的多個文學圖書獎。2009年,該書在“加拿大大西洋地區100部最佳作品”評選中名列榜首。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推拿
- >
自卑與超越
- >
人文閱讀與收藏·良友文學叢書:一天的工作
- >
朝聞道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
- >
新文學天穹兩巨星--魯迅與胡適/紅燭學術叢書(紅燭學術叢書)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裝共3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