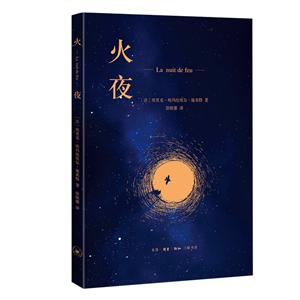-
>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茨威格短篇小說集
-
>
女人的勝利
-
>
崇禎皇帝【全三冊】
-
>
地下室手記
-
>
雪國
-
>
云邊有個小賣部(聲畫光影套裝)
-
>
播火記
火夜 本書特色
l 作者用詩意和情感飽滿的語言,與我們分享了他在撒哈拉沙漠令人驚嘆的非凡經歷。 —— 《生活》雜志 l 在這本書里,埃里克-埃馬紐埃爾·施米特先生向我們透露了改變他一生的那個神奇之夜。 ——《瑞士星期日晨報》 l 本書是作者一份滾燙的記憶,是他帶給我們的一份驚喜。 ——加拿大《蒙特利爾日報》
火夜 內容簡介
二十八歲的巴黎薩瓦大學哲學系教師埃里克接受了一項劇本創作的任務,要寫一部有關在撒哈拉沙漠圖瓦雷克人中傳教的傳教士——夏爾?德?福科的電影劇本。為了更好地理解這個人物,他和導演一起去探訪福科的舊跡。在艱難的沙漠行程中,尤其是與虔誠的穆斯林、圖瓦雷克人向導阿貝格的朝夕相處中,埃里克感受到自然生活的本真之處及所謂現代文明的缺失所在,他不斷追問自身存在之謎,但仍以哲學的理性智慧抗拒超越性的上帝,直到一次遠足時夜晚迷路,在肉體的靠前虛弱之中,他有了一次變身火焰并靠近光的體驗之后,一切都改變了……
火夜 節選
從撒哈拉沙漠那次長途跋涉到我今天的敘述,整整過去了二十五年。我的信仰經受住了環境變遷、時間流逝的,仍在不斷生長。沙漠中的娟娟細流,已寬闊為湯湯大河。這,就是源頭的力量。
長久以來,我一直秘密持有這份信仰,它在無聲改變著我。當信仰開挖自己的河床,我對世界的感受也日趨豐富:我閱讀靈性撥動者們的書籍,無論東方的還是西方的;我從院子深處隱秘的小門進入宗教大花園,那是神秘詩人的門,那些生活在野外的人們,遠離教條和機構,他們的感受遠勝他們的表達。以人文主義看待民眾信仰,更增添了那種內在火焰,我愿與所有時代、所有地區的人們分享那種火焰。博愛被編織,世界被拓寬。
從霍加爾回來后,自童年時代就沉睡于我體內的作家幼蟲,在書桌前蠢蠢欲動,成為它所經歷故事的 謄寫人。我出生了兩次:一次是1960年在里昂,一次是1989年在撒哈拉。
從此,長篇小說、戲劇、中篇小說、短篇小說接踵而至,在祥和的天空下從我筆端流淌,有時寫得有點難,大部分時候很容易,總是飽含激情。接受神啟的那個夜晚協調了我我額的一切:我的身體、心靈、理性同心協力而非各行其道。這份體驗賦予了我一種正當性:如果才華僅用來服務自己,除了想著被承認、被欣賞和被鼓掌外,沒有其他目標,這樣的才華是虛妄的。真正的才華應該傳遞一些超越才華、引領價值觀的東西。如果說我有幸在某個夜晚成為某種啟示的接受地,那在我眼里我就有權說幾句。
我很害怕人們會誤解我的心里話……不,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先知或是被神啟的人;不,我從不認為自己是上帝的代言者。相反,我自認有愧于我所得之恩澤,為此貢獻我全部的余生,都不足以讓我配得上這份恩賜。
然而,像每一個正真的人,我不弄虛作假:我從我的靈魂出發,生活和寫作。而我的靈魂見過光明——并且還在繼續見著,包括穿過*幽深的黑暗時刻。
我一直守著那一夜的秘密,直到有一天,一名記者著實惹煩了我:“為什么你的作品中總是洋溢著對生活的如此之愛和如此平和?”她反反復復問道,“你可以把一些悲劇性的題材處理得既無奉承,也無夸張,更無絕望。是什么奇跡讓你做到這樣?”我認識這位女記者,也很認可她,知道她是新教教徒。在她鍥而不舍的追問下,我終于承認我在塔哈特山腳下認識了上帝。
“你還會重返那里嗎?”她試探道。
“重返……為什么?
一次,足矣。
一份信仰,也足矣。
當人們遭遇不可見事物的召喚時,人們試著應對這份禮物。
在神啟中*讓人意外的是,盡管啟示顯而易見,但你仍可以保持自由。自由地對所發生之事視而不見,自由地回放事件,自由地繞開,自由地遺忘。
在遇見上帝之后,我從未感覺如此自由,因為我依然擁有否認它的權利。在被命運操縱過后,我從未感覺如此自由,因為我仍可以躲避到對于偶然性的迷戀中。
一次神秘體驗也是一種矛盾體驗:上帝的力量并沒有摧毀我自己的力量;我與上帝的接觸并不妨礙后來自我的呈現;不容置疑的強烈情感絲毫不會抹去理性的慎思。
“理性的*后步驟就是承認存在超越理性的無窮性。理性如果沒有達到那一步,它就是虛弱的。”但理性不會主動謙卑,必須推它一把。*出色的理性主義者、哲學家、數學家,智慧超群的帕斯卡[1],也不得不在1654年11月23日,繳械投降:在接近子夜時分,上帝擊中了他,從此他的一切存在被揭開了意義。他把有關這個夜晚的晦澀記錄稱為《火夜》,隨身攜帶并藏在外套夾層中。
“信仰與見證不同,一個屬于人類,另一個來自上帝的饋贈。是心靈感受上帝而非理性感受上帝;上帝對心靈敏感而不是理性,這就是信仰。”
在我的那個撒哈拉之夜,我并沒有得知什么,我只是信。
提及信仰,現代人必須表現得十分嚴謹。如果有人問我:“上帝存在嗎?”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因為在哲學上,我屬于不可知論者,這是對于理性唯一站得住腳的部分。不過我會補充一句:“我想可能是存在的。”信仰與科學根本不同,我不會將二者混淆。我所知的并非我所信的,我所信的永遠不會成為我所知。
面對上帝是否存在這樣的疑問,有三種誠實的人。信主的人會說:“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上帝存在”;無神論者會說:“我不知道,但我不相信上帝存在”;無所謂的人說:“我不知道,我才不去操這份心。”
而欺詐始于那些聲稱 “我知道!”,言之鑿鑿 “我知道上帝存在”或者“我知道上帝不存在”的那種人。他突破理性的能力,陷于原教旨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或無神論原教旨主義,選取災難性的狂熱之路和死亡前景。這種確信只會留下一地尸體。
我們的時代與過去一樣,人們以上帝的名義殺戮,所以千萬別混淆了信仰者與招搖撞騙者:上帝的朋友是那些尋找上帝的人,而不是那些聲稱找到了上帝并以上帝名義說話的人。
信仰者的信心提供了一種安放神秘的方式。就如無神論者的焦慮一樣……神秘,也會繼續存在下去。
隨著年齡漸長,我越來越意識到不可知論處于被多數人拒絕的位置。人們總想著要知道!然而只存在有信仰的不可知論者、無神論的不可知論者以及冷漠的不可知論者。無數人執意于混淆信仰與理性,拒絕精神世界的復雜性,簡單化諸事萬物,將非常個人化的情感轉換成普遍真理。
我們應該承認和培養我們的無知,和平的人文主義值得這個代價。我們所有人,只有在無知的時候才是兄弟姐妹,而不是在有信仰的時候。只有以共同的無知的名義,我們才能容忍區分我們的那些信仰。對于他人,我首先應該尊重他與我相同的部分,即他想知而不得知的那部分;然后,以相同部分的名義,我尊重他的不同部分。
在經歷了我的那個火夜,回到我們在沙漠枯河的露營地后,我非常糟糕地解讀了塞戈萊娜向我承認她向上帝祈禱解救我出困境一事。我感到氣憤的是(現在依然會)在出現不公或有災難時,上帝并不對每個人都出手相救!因此上帝并不是人類的拯救者,他只是建議人類思考自己的永福。
如果說這篇敘述動搖了某些人,但不會說服任何人……我對此有清醒認識,并為此而難過……有多少次我想把滾燙著我的信心傳遞出去?面對困惑著的朋友或絕望的陌生人,我多么希望向他們展示我的說服力!可惜,我沒有傳染性……唯有理性證據才能讓人心悅誠服,而不是經驗。我只能讓人感受,我無法證明,我滿足于見證。
在書寫這些篇章時,我顫抖、狂喜、迫不及待、屏息靜氣、興奮喊叫,激動到行動困難,以至于寫這本書讓我進了兩次醫院……那一夜的火取之不盡,繼續重塑著我的身體、靈魂、生活,就如一位至尊的煉丹術士,不會拋棄他的杰作。
在大地上的一夜,讓我的整個存在充滿喜悅。
在大地上的一夜,讓我預感到了永恒。 [1] 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年,法國數學家、物理學家、哲學家和散文家,1653年提出了著名的“帕斯卡定律”。
火夜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埃里克-埃瑪紐埃爾??施米特(Eric-Emmanuel Schmitt),法國知名作家、導演。1960年出生于法國里昂,畢業于巴黎高等師范學院,哲學博士。他的作品被譯成四十多種語言,戲劇在五十多個國家上演,深受讀者和觀眾喜愛,是當代法語作家中讀者最廣、作品被改編次數最多的作家之一。短篇小說集《紀念天使協奏曲》榮獲2010年龔古爾短篇小說獎;《來訪者》在1994年獲得三項莫里哀戲劇大獎;《看不見的周期》使他在世界范圍內獲得聲譽。他也執導了據小說《我們都是奧黛特》《奧斯卡與玫瑰夫人》改編的同名電影等多部影片。 譯者簡介: 徐曉雁 早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第一屆法文班,后在法國留學、工作十余年,巴黎十二大生命科學碩士。曾任職于瑞士和法國企業,2004年起涉足法國文學翻譯。迄今已翻譯出版近二十部法國文學作品,其中包括本書作者埃里克-埃馬紐埃爾·施米特的《奧斯卡與玫瑰奶奶》、《我們都是奧黛特》、《諾亞的孩子》、《紀念天使協奏曲》、《看不見的愛》、《奧斯坦德的夢想家》等多部作品。
- >
煙與鏡
- >
回憶愛瑪儂
- >
伊索寓言-世界文學名著典藏-全譯本
- >
姑媽的寶刀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朝花夕拾
- >
大紅狗在馬戲團-大紅狗克里弗-助人
- >
詩經-先民的歌唱
- >
新文學天穹兩巨星--魯迅與胡適/紅燭學術叢書(紅燭學術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