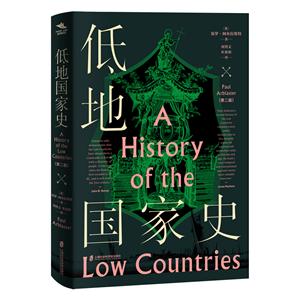-
>
ŪÕ═©Ķb(╚½╦─āį)(Š½čb)
-
>
├„═©Ķb(╚½╚²āį)(Š½čb)
-
>
┐ń╠½ŲĮč¾Ą─╚A╚╦Ė─┴╝┼cĖ’├³ 1898-1918
-
>
╠ņėąČ■╚šŻ©║×├¹ŌjėĪ╠žčb▒ŠŻ®
-
>
ÜWų▐ų┴░ĄĢr┐╠Ż©1878-1923Ż®Ż║ę╗æ(zh©żn)×ķ║╬▒¼░l(f©Ī)╝░æ(zh©żn)║¾╚ń║╬ųžĮ©
-
>
(Š½čb)ŖW═ąĪż±TĪż ┘┬╦╣¹£┼cĄ┬ęŌųŠĄ█ć°Į©┴ó
-
>
╚A╬─╚½Ū“╩Ę:ųąć°╬─├}
┤¾īWå¢Īżč┼└Ēūgģ▓:░l(f©Ī)├„éĆ¾w--╚╦į┌╣┼ĄõĢr┤·┼cųą╩└╝oĄ─Ąž╬╗(Š½čb)
[ėó]└Ł└’Īż╬„ĄŪ═ąŲš ų°Ż¼┘RŪń┤© ūg¥57.3¥88.0
Ą═Ąžć°╝ę╩Ę ░µÖÓą┼Žó
- ISBNŻ║9787552032772
- Ślą╬┤aŻ║9787552032772 ; 978-7-5520-3277-2
- čbļŻ║ę╗░Ń─z░µ╝ł
- āįöĄŻ║Ģ║¤o
- ųž┴┐Ż║Ģ║¤o
- ╦∙ī┘ĘųŅÉŻ║>>
Ą═Ąžć°╝ę╩Ę ▒ŠĢ°╠ž╔½
▒Ż┴_.░ó▓╝└Ł╦╣╠žųv╩÷┴╦Ą═Ąžć°╝ęÅ─╣┼ų┴Į±Ą─╔ĒĘ▌▐DūāŻ║Å─╣┼┴_±RĢrŲ┌Ą─▀ģŠ│╩ĪĘ▌č▌ūā?y©Łu)ķ╚ńĮ±Ą─╚²éĆŠ²ų„┴óæŚųŲć°╝ęŻ¼ÅŖš{┴╦┘xėĶ▀@ę╗Ąžģ^(q©▒)ć°ļHųžę¬ąįĄ─╔ńĢ■ĪóĮøØ·ĪóŠ½╔±║═╬─╗»▀\äėĪŻ▀@éĆą▐ėå░µ▒ŠĄ─ā╚╚▌Ė³×ķžSĖ╗Ż¼║Ł╔w┴╦Ū░čžÜv╩Ę蹊┐│╔╣¹┼cųžę¬╩┬╝■Ż¼╠ß╣®┴╦Ą═Ąžć°╝ęėąĻPęŲ├±ĪóČÓį¬╬─╗»ų„┴x║═├±ūÕų„┴xÅ═┼dĄ─*ą┬ą┼ŽóŻ¼║åČ╠Ąžėæšō┴╦╩└╦ūų„┴xį┌╬„ÜWĄ─ß╚Ų╝░Ųõī”▒╚║╔▒RĄžģ^(q©▒)Ą─ė░ĒæŻ¼Ė┼╩÷┴╦Ą═Ąžć°╝ęĮ³╚šĄ─ĮøØ·│╔öĪŻ¼ą┬į÷┴╦1918─ĻęįüĒĄ─š■³h║═š■Ė«ę╗ė[▒ĒĪŻ ╚¶Žļ═©▀^║å├„ęūČ«Ą─╬─ūų┴╦ĮŌĄ═Ąžć°╝ęĄ─▀^╚źŻ¼▒ŠĢ°¤oę╔╩Ūę╗éĆ║▄║├Ą─▀xō±ĪŻ
Ą═Ąžć°╝ę╩Ę ā╚╚▌║åĮķ
ÄūéĆ╩└╝oęįüĒŻ¼Ą═Ąžć°╝ꯩ▒╚└¹ĢrĪó║╔╠m║═▒R╔Ł▒żŻ®ę╗ų▒╬╗ė┌╬„ÜWĄ─╩«ūų┬Ę┐┌Ż¼╦³éāĄ─ć°═┴├µĘeļm╚╗ŽÓī”▌^ąĪŻ¼Ą½ī”ÜWų▐ĮøØ·Īóū┌Į╠║═╦ćągĄ─░l(f©Ī)š╣Š∙ėąŠ▐┤¾žĢ½IĪŻį┌ć°ļHīė├µŻ¼įōĄžģ^(q©▒)═∙═∙╝╚│õ«öų▄▀ģ┤¾ć°╚ńĘ©ć°Īóėóć°║═Ą┬ć°Ą─š{═Żš▀Ż¼ėų│õ«öŠÅø_ģ^(q©▒)ĪŻ╚²ć°ų«ķg═∙üĒ├▄ŪąŻ¼┼cÓÅć°Ą─Į╗═∙ę▓╩«ĘųŅlĘ▒Ż¼ļxķ_┴╦ŲõųąĄ─╚╬ę╗ć°╝ęŻ¼▒╚║╔▒RĄ─Üv╩ĘČ╝¤oÅ─šäŲŻ╗Č°╚¶║÷ęĢ┴╦Ą═Ąžć°╝ęŻ¼ÜWų▐Ą─Üv╩Ęę▓¤oÅ─šäŲĪŻ į┌Üv╩Ę╔ŽŻ¼Ę©ć°▒▒▓┐Ą─║═Ą┬ć°╬„▓┐Ą─▓┐ĘųĄžģ^(q©▒)ę▓į°▒╗Üw×ķĄ═Ąžć°╝ęŻ¼ę“┤╦Ī░Ą═Ąžć°╝ęĪ▒▀@éĆągšZĄ─Č©┴x▒žĒÜ▒Ż│ųīÆĘ║║═ņ`╗ŅąįŻ¼╦³Š═Ž±ę╗éĆĘĮ▒Ń╩╣ė├Ą─ś╦║ׯ¼║▄╔┘┤·▒Ēę╗éĆ╣╠Č©Ą─ĪóĮy(t©»ng)ę╗Ą─š¹¾wĪŻį┌Ė³įńĄ──Ļ┤·Ż¼▓┐┬õ║══§ć°öUÅłĄĮ│¼│÷¼FĮ±║╔╠mĪó▒╚└¹Ģr║═▒R╔Ł▒żĄ─ÅVķ¤ģ^(q©▒)ė“Ż¼─Ū├┤Š═Ė³ļyĮo▀@ę╗Ąžģ^(q©▒)įOČ©ś╦£╩Ż¼╩╣Ųõ─▄ē“Ę┤ė││÷ÜWų▐╩Ūę╗éĆš¹¾wĪŻų▒ų┴Į±╚šŻ¼Ą═Ąžć°╝ęį┌š■ų╬║═╬─╗»╔Ž╚į│╩¼F│÷Ė▀Č╚ČÓį¬╗»Ż¼─Ū└’Ą─Šė├±ųvČÓĘNšZčįŻ║║╔╠mšZĪóĘ©šZĪóĖź└’╬„üåšZ║═Ą┬šZŻ¼▀@éĆ’LŠ░ąŃ├└Ą─Ąžģ^(q©▒)Ę┬Ę╩ŪÜWų▐Üv╩ĘĄ─├į╚╦┐sė░ĪŻ▒╚└¹Ģr║═║╔╠mätįĮüĒįĮČÓĄžģó┼cĖ³ÅVĘ║Ą─ÜWų▐ę╗¾w╗»▀M│╠Ż¼╦³éā┐é╩Ū╣▓ŽĒ└¹ęµŻ¼▓ó▓╔╚ĪŽÓ╦ŲĄ─š■▓▀Ż¼į┌Į±╚šÜWų▐╚į╚╗░l(f©Ī)ō]ų°ųžę¬ū„ė├ĪŻ
Ą═Ąžć°╝ę╩Ę ─┐õø
į┘░µą“
Ū░čįŻ©**░µŻ®
ę²čį
**š┬ Å─«ÉĮ╠═ĮĄĮ╩«ūų▄Ŗæ(zh©żn)╩┐Ż║╣½į¬Ū░57Ī¬╣½į¬1100─Ļ
Ą┌Č■š┬ ÖÓ┴”║═“»š\Ą─ą╬╩ĮŻ║╣½į¬1100Ī¬1384─Ļ
Ą┌╚²š┬ Ą═Ąžć°╝ęĄ─Įy(t©»ng)ę╗║═Ęų┴čŻ║1384Ī¬1609─Ļ
Ą┌╦─š┬ Å─┤·Ā¢Ę“╠ž╠šŲ„ĄĮ┤╔Ų„Ż║1609Ī¬1780─Ļ
Ą┌╬Õš┬ ūįė╔ų╚ą“Ą─┼d╦źŻ║1776Ī¬1914─Ļ
Ą┌┴∙š┬ ╩└Įń┤¾æ(zh©żn)┼c╩└Įń║═ŲĮŻ║1914Ī¬2011─Ļ
Ą═Ąžć°╝ę┤¾╩┬ėø
═§│»┼cĮy(t©»ng)ų╬š▀
1918─Ļ║¾ų„꬚■³h╝░š■Ė«ÖCśŗ
čė╔ņķåūxų°ū„
Ą═Ąžć°╝ę╩Ę ╣Ø(ji©”)▀x
▒╚└¹ĢrĪó║╔╠mĪó▒R╔Ł▒ż╩Ūų°├¹Ą─Ī░╚╦įņĪ▒ć°╝ęŻ¼╦³éāĄ─▀ģĮńų╗╩Ūęį═∙═ŌĮ╗║═▄Ŗ╩┬╗ŅäėĄ─«a╬’ĪŻį┌▀@ę╗ģ^(q©▒)ė“ā╔Č╦Ż¼Ę©ć°║═Ą┬ć°š╝ŅI┴╦╦∙ėą─▄š╝ŅIĄ─═┴ĄžŻ¼ėÓŽ┬ųąķg▓┐ĘųŻ¼Ę©Ą┬ļpĘĮČ╝¤oĘ©Į©┴óĮy(t©»ng)ų╬Ż¼ą╬│╔┴╦▒╚Īó║╔Īó▒R╚²ć°ĪŻį┌─│ą®╚╦Ż¼└²╚ńĘ©ć°Ū░┐éĮy(t©»ng)Ž─Ā¢· ┤„Ė▀śĘŻ©Charles de GaulleŻ®┐┤üĒŻ¼▀@ę╗Ūķør╩╣▒╚Īó║╔Īó▒R│╔┴╦ę╗ĘN«É│Ż╗“ČÓėÓĄ─┤µį┌ĪŻĄ½į┌19╩└╝oĄ═Ąž╚²ć°Ą─╩ĘīW╝ęč█ųąŻ¼▀@Ę┤Č°ūī▒╚Īó║╔Īó▒R│╔┴╦Ż©ŅAŽ╚Ż®┤_Č©Ą─ąę┤µš▀ĪŻ╚ń╣¹Ī░▀ģĮńĪ▒▓╗╩ŪųĖø▄╬╝Ęų├„Ą─ĘųĮńŠĆŻ¼Č°╩ŪųĖŽÓ╗źū„ė├ĪóŽÓ╗źųž»BĄ─ģ^(q©▒)ė“Ż¼─Ū▀@ēK═┴Ąž*ŪĪ«öĄ─ĘQų^æ¬╩Ū▀ģĮńĄžģ^(q©▒)ĪŻ▓╗╩ŪšfĘ©ć°ĪóĄ┬ć°╗“ęŌ┤¾└¹Īó╚╩┐ī”▀@╚²éĆć°╝ęø]ėąė░ĒæŻ¼Č°╩Ūļmėąė░ĒæŻ¼ģsø]ėą╚╬║╬ę╗ĘĮ─▄ē“═Ļ╚½ų„ī¦▀@Ų¼ģ^(q©▒)ė“ĪŻ ČÓśėąį Ė„ĘNŅÉą═Ą─▀ģĮńŠĆīó▒╚└¹ĢrĪó║╔╠m║═▒R╔Ł▒żĘųĖŅķ_üĒĪŻę╗Č╚▒╗Ę©ć°╚╦ĘQ×ķĪ░╠ņ╚╗▀ģĮńŠĆĪ▒Ą─╚Rę║ėŻ©RhineŻ®Ż¼┤®▀^┴╦║╔╠mĄ─ą─┼KĄžÄ¦ĪŻ┴Ē═Ō▀Ćėą╚²ŚlšZčį▀ģĮńŠĆŻ║▒╚└¹ĢrŠ│ā╚Ą─║╔╠mšZĪ¬Ę©šZ▀ģĮńŠĆĪó▒╚└¹Ģr║═▒R╔Ł▒żŠ│ā╚Ą─Ę©šZĪ¬Ą┬šZ▀ģĮńŠĆęį╝░║╔╠mŠ│ā╚Ą─║╔╠mšZĪ¬Ėź└’╦╣╠mšZŻ©FrisianŻ®▀ģĮńŠĆĪŻ║╔╠m▀Ćėąę╗ŚläØĘų╠ņų„Į╠║═ą┬Į╠é„Įy(t©»ng)ų„ī¦ģ^(q©▒)ė“Ą─ĘųĮńŠĆĪŻ▒╚└¹ĢrĄ─░═└šĪ¬║Ż═ą║šµé(zh©©n)Ż©Baarle-HertogŻ®╦─├µ┼c║╔╠m─Ž▓┐╩ĪĘ▌▒▒▓╝└Ł░Ó═óŻ©North BrabantŻ®×ķĮńŻ¼▀Ć┼c║╔╠mĄ─░═└šĪ¬╝{ĮBŻ©Baarle-NassauŻ®ŽÓ▀BŻ¼▀@ĘNę╗éĆÜWų▐ć°╝ęĄ──│ę╗ā╚ĻæŅI═┴ģsį┌ÓÅć°Š│ā╚Ą─ŪķørŻ¼─┐Ū░ĘŪ│Ż║▒ęŖĪŻŠ═ŲõšZčįČÓśėĪóū┌Į╠Į╗┐Śęį╝░Ąž└Ē▀ģŠ│ĄžÄ¦Ą─ŪķørüĒ┐┤Ż¼Ą═Ąž╚²ć°┼cį┌Ę©ĪóĄ┬Į╗Įń╠Ä┴Ēę╗Č╦Ą─╚╩┐ŅH×ķŽÓ╦ŲĪŻ▓╗═¼Ą─╩ŪŻ¼╚╩┐Äū║§▓╗ģó┼c╬„ÜWĄ─ÅŖÖÓš■ų╬Ż¼Č°▒╚Īó║╔Īó▒R╚²ć°ÄūéĆ╩└╝oęįüĒę╗ų▒╩ŪÅŖÖÓš■ų╬Ą─ųąą─Ż¼╦³éā▀Ćį┌ÜWų▐ĮøØ·š■ų╬ę╗¾w╗»Ą─▀^│╠ųą░ńč▌┴╦ųžę¬ĮŪ╔½ĪŻ ╚╩┐┼cĄ═Ąžć°╝ęĄ─┴Ēę╗éĆģ^(q©▒)äeį┌ė┌Ż¼╚╩┐Ž“üĒ╩Ūę╗éĆ╦╔╔óĄ½śOŲõĘĆ(w©¦n)╣╠Ą─┬ō░Ņć°╝ęŻ¼ė╔Ė„éĆų▌ĮM│╔ĪŻČ°Ą═Ąžć°╝ęät┌ģŽ“ė┌▒╦┤╦Ęų┴čŻ¼1815Ī¬1830─Ļķgį°ėą╚╦ćLįć░čĄ═Ąžć°╝ęū„×ķę╗éĆå╬ę╗ųŲųąčļ╝»ÖÓć°╝ę▀MąąĮy(t©»ng)ų╬Ż¼ģs*ĮKī¦ų┬┴╦Ė’├³┼cæ(zh©żn)ĀÄĪŻ┴Ņ╚╦įī«ÉĄ─╩ŪŻ¼╚╬ę╗Ą═Ąžć°╝ęā╚Ż¼Č╝┤µį┌ų°╩Ī╝ē║═Ąžģ^(q©▒)ąįĄ─šZčį║═ė^³cĄ─▓Ņ«ÉĪŻ╔§ų┴į┌├µĘe*ąĪĪó╩╣ė├ļpšZĄ─▒R╔Ł▒żŻ¼ę▓ėą─ĖšZ╩ŪĘ©šZČ°ĘŪ▒R╔Ł▒żšZĄ─╚╦ĪŻ═¼ĢrŻ¼▒R╔Ł▒żĘų×ķ╬„▒▒▓┐Ą─┴ųśI(y©©)ģ^(q©▒)Īó¢|▓┐Ą─▐rśI(y©©)ģ^(q©▒)Īó╬„─Ž▓┐Ą─╣żśI(y©©)ģ^(q©▒)Ż¼ųąą─Ą─▒R╔Ł▒ż│Ūätė╔Ę■äšśI(y©©)ų„ī¦ĪŻ ╬─╗»▓Ņ«Éį┌╚š│ŻĮėė|ųąĘŪ│Ż├„’@ĪŻ║╔╠m╚╦Ą─┬╩ų▒Ģ■¤oęŌųą├░ĘĖ╦¹╚╦Ż¼Č°▒╚└¹Ģr╚╦Ą─║¼ąŅėųĢ■▒╗š`ĮŌ│╔╠ōé╬ĪŻ▒╚└¹Ģr╚╦Ģ■ųv║╔╠m╚╦ōĖķTĄ─ą”įÆŻ¼Č°║╔╠m╚╦ätĢ■š{ą”▒╚└¹Ģr╚╦ĘĖ┤└ĪŻųvą”įÆĄ─╚╦Ģ■ėXĄ├ėą╚żŻ¼ę“×ķ╦¹éāČ╝Ų┌┤²╦∙ųvĄ─ą”įÆĢ■«a╔·ę╗śėĄ─É║ĖŃą¦╣¹ĪŻ╬─╗»▓Ņ«É╔§ų┴▓╗═Ļ╚½ė╔ć°ĮńŽ▐Č©ĪŻę╗ć°ų«ā╚Ż¼▒╚└¹ĢrĄ─Ę╠mĄ┬╦╣╚╦Ż©FlemingsŻ®Ģ■│░ųS┴ų▒ż╚╦Ż©LimburgersŻ®Ī░Ól(xi©Īng)░═└ąĪ▒Ż╗║╔╠m╚╦ę▓Ģ■▀@śė│░ą”Ėź└’╦╣╠m╚╦Ż©FrisiansŻ®ĪŻį┌║╔╠mŻ¼┐±ÜgæcĄõ┴„ąąė┌╚Rę║ė╚²ĮŪų▐ęį─ŽĄ─é„Įy(t©»ng)╠ņų„Į╠│Ū╩ąŻ¼╚ń╦╣║ŻĀ¢═ą║Ó▓®╦╣Ż©Ī»s-HertogenboschŻ®Īó░Żę“╗¶£žŻ©EindhovenŻ®║═±R╦╣╠ž└’║š╠žŻ©MaastrichtŻ®Ż╗ų▒ĄĮĮ³─ĻŻ¼▀@ą®┴Ģ╦ū▓┼┴„╚ļĖ³╝ėŠąųö▒Ż╩žĄ─▒▒ĘĮŻ¼Ä¦╚ź┴╦«Éė“ų«’LĪŻ ▒╚Īó║╔Īó▒R│²┴╦į┌┴Ģ╦ūĪóšZčįĪóĘ©┬╔Īóū┌Į╠ĘĮ├µĘųĮń▓╗ŪÕŻ¼ęį╝░┼┼═Ōų„┴x║═¬M░»ų„┴xĄ─Ąžģ^(q©▒)▓ŅäeŻ¼╚²ć°Ą─╣½├±╔ńĢ■ÖCśŗę▓│╩¼FŲµ╣ųĄ─Ęų┴čĀŅæB(t©żi)ĪŻėóšZ╩ĘīWĮńšJ×ķŻ¼į┌19╩└╝o║═20╩└╝oŻ¼▒╚└¹Ģr║═║╔╠mĄ─╔ńĢ■ÖCśŗ│╩Ī░ų∙╗»Ī▒¼FŽ¾ĪŻų∙ūėĄ─ą╬Ž¾▒Ē╩Š╔ńĢ■Ė„éĆ▓┐Ęų╣▓═¼ų¦ō╬Ų╬▌ĒöŻ¼Ą½ø]ėąę╗éĆ─▄ŲĄĮøQČ©ąįū„ė├ĪŻą┬Į╠═ĮĪó╠ņų„Į╠═ĮĪóūįė╔Ī¬╩└╦ūų„┴xš▀Īó╔ńĢ■ų„┴xš▀ęį╝░ėąą®╣▓«aų„┴x╚╦╩┐Č╝╝Ŗ╝ŖĮ©┴óŲūį╝║Ą─ÖCśŗŻ¼▒ŻšŽŲõ│╔åTÅ─│÷╔·ĄĮ╦└═÷Ą─╔·╗ŅĘĮĘĮ├µ├µŻ║Į╠╠├║═ū┌Į╠ł÷╦∙Īóš■³hĪó╣żĢ■Īó▒ŻļU┬ō║ŽĢ■Īóā”ąŅŃyąąĪóßt(y©®)į║ĪóųąąĪīWĪó┤¾īWĪół¾╔ńŻ¼ėąĢr╔§ų┴▀Ć░³└©ÅV▓źĪóļŖęĢ╣½╦Šęį╝░╬─╗»Īó궜Ę║═¾wė²ÖCśŗĪŻ19╩└╝o─®20╩└╝o│§Ż¼╔ńĢ■ÖCśŗĄ─Ī░ų∙╗»Ī▒▀_ĄĮĒöĘÕŻ¼╔§ų┴┤¾ą═Ą─Ų¾śI(y©©)ę▓Ģ■Üwī┘ė┌─│ę╗Į╠┼╔╗“─│éĆĪ░╔·╗ŅĪ¬š▄īWĪ▒ĻćĀIĪŻ│╔×ķę╗├¹╠ņų„Į╠═Į╗“╝ėĀ¢╬─Į╠═Į▓╗āHāH╩Ūą┼č÷╔ŽĄ─│ąųZŻ╗═¼śėĄžŻ¼ą┼ĘŅūįė╔ų„┴x▀Ć╩Ū╔ńĢ■ų„┴xę▓▓╗å╬å╬╩Ūš■ų╬▀xō±ĪŻī”─│ę╗╩┬╬’Ą─ųęš\Ģ■ė░Ēæ╔·╗ŅĄ─ĘĮĘĮ├µ├µŻ¼ė░Ēæ╚╦éāĄ─Š±ō±Ż║╦═║óūė╔Ž──╦∙īWąŻŻ¼╚ź──╝ęŃyąąķ_įO┘~æ¶Ż¼į┌──└’▐k└Ēßt(y©®)»¤▒ŻļUŻ¼╝ė╚ļ──ę╗ūŃŪ“ŠŃśĘ▓┐╗“▄ŖśĘĻĀŻ©▓╗šō╦¹éā╩Ūʱį┌ų▄╚š╗ŅäėŻ®Ż¼ėåķå──ĘNł¾╝łŻ¼╔§ų┴╩Ū╚ź──éĆ╔╠ĄĻ▓╔┘ÅĪŻ╔╠╚╦╔ąŪęĢ■┼c║═ūį╝║╗∙▒Š╔·╗Ņė^─Ņ▓╗═¼Ą─╚╦üĒ═∙Ż¼Č°ŲõėÓ╚╦ät║▄╔┘ėąÖCĢ■ū▀│÷╔·╗ŅĪ░╚”ūėĪ▒╚źģó┼c═ŌĮńĄ─╔ńĢ■╬─╗»╗ŅäėĪŻ ═¼▒╚└¹ĢrĪó║╔╠mę╗śėŻ¼▒R╔Ł▒żĄ─Į╠Ģ■║═š■Ė«ų«ķgę▓┤µį┌ĀÄł╠(zh©¬)Ż¼Ą½╩Ū▒R╔Ł▒żĘŅąąūįė╔ų„┴xĄ─š■ų╬Š½ėóĖ³įĖęŌš■Ė«ų¦│ų╠ņų„Į╠Ą─Į╠ė²║═┤╚╔ŲÖCśŗĪŻČ°ŽÓī”ė┌Ųõ╦¹ĄžĘĮĄ─▓╗Ė╔╔µŻ¼Į╠Ģ■Š½ėóę▓ĘŪ│Ż┴ĢæTė┌ć°╝ęī”╦¹éāĖ³┤¾┴”Č╚Ą─▒O(ji©Īn)ČĮĪŻ▀@╩╣Ą├▒R╔Ł▒ż│╔┴╦Ė³╝ėĮy(t©»ng)ę╗Ą─╔ńĢ■║═š■ų╬š¹¾wĪŻĄ½į┌▒╚└¹Ģr║═║╔╠mŻ¼Ė„ĘĮČ╝▓╗įĖęŌį┌įŁät╔Ž═ūģf(xi©”)ĪŻį┌▒╚└¹ĢrŻ¼╩▄įōš■ų╬ę“╦žė░ĒæŻ¼Ī░ų∙╗»Ī▒ė░Ēæų°╔ńĢ■╔·╗ŅŻ©╝┤╝┘įOĄ─Ī░╬▌ĒöĪ▒Ż®Ą─ĘĮĘĮ├µ├µŻ¼║╔╠mę▓ę╗śėŻ¼ų╗╩Ū│╠Č╚Ė³ąĪę╗ą®ĪŻųT╚ńŠ»▓ņŠųĪóÓ]ŠųĪóĶF┬ĘŽĄĮy(t©»ng)└’žōėąÖÓž¤Ą─┬Ü╬╗Ż¼╔§ų┴╩Ū╦ŠĘ©╣┘åT║═ČYāx╣┘åTĄ─╚╬├³Ż¼Č╝į┌▓╗═¼Ą─Ī░ų¦ų∙Ī▒ķgĘų┼õĪó╠µōQĪŻ▀@śėĄ─¼FŽ¾─┐Ū░╔ąėąÜł┴¶Ż¼Ą½ų„ę¬╩Ūį┌▒╚└¹ĢrĪŻ ▒╚└¹ĢrĄ─Ęųļx┌ģä▌▀Mę╗▓Į╝ė╔ŅŻ¼▀@³cį┌║╔╠m║═▒R╔Ł▒ż▓ó▓╗├„’@ĪŻ▒╚└¹ĢręčĮø┬ō░Ņ╗»┴╦Ż¼įSČÓš■ų╬║═ĮøØ·ÖÓ┴”ęŲĮ╗Įo┴╦╚²┤¾Ī░ŅIģ^(q©▒)Ī▒Ż║ųv║╔╠mšZĄ─Ę╠mĄ┬╦╣ģ^(q©▒)Ż©FlandersŻ®Ż¼Ę©šZĄ─═▀┬Īģ^(q©▒)Ż©WalloniaŻ®ęį╝░╣┘ĘĮļpšZŻ©║╔╠mšZ║═Ę©šZŻ®Ą─▓╝¶ö╚¹Ā¢╩ūČ╝ģ^(q©▒)Ż©Brussels Capital RegionŻ®ĪŻ╬─╗»š■▓▀║═Į╠ė²š■▓▀į┌╚²éĆ▓╗═¼šZčįĪ¬Ī¬║╔╠mšZĪóĘ©šZĪóĄ┬šZĪ¬Ī¬Ą─Ī░╔ńģ^(q©▒)Ī▒ķg╦∙╣▓ėąĪŻŲõųąŻ¼Ę╠mĄ┬╦╣ģ^(q©▒)║═║╔╠mšZģ^(q©▒)Ė▀Č╚╬Ū║ŽŻ¼═▀┬Īģ^(q©▒)║═Ę©šZģ^(q©▒)ę▓Ė▀Č╚╬Ū║ŽŻ¼Ą½╩ŪĄ┬šZģ^(q©▒)╬╗ė┌═▀┬Īģ^(q©▒)ā╚Ż¼▓óŪęĘ©šZģ^(q©▒)║═║╔╠mšZģ^(q©▒)į┌ļpšZĄ─▓╝¶ö╚¹Ā¢╩ūČ╝ģ^(q©▒)Š∙ėąūį╝║Ą─ä▌┴”ĪŻ▀@ĘN╔ńģ^(q©▒)╔ŽĄ─ĘųļxŻ¼╩╣Ą├ų¦ō╬ć°╝ęĄ─╦∙ėąĪ░ų¦ų∙Ī▒Ż¼▓╗šō╩Ūš■ų╬Īó╔ńĢ■Īó╬─╗»╗“╩ŪĮøØ·ÖCśŗŻ¼į┌├┐éĆšZčį╔ńģ^(q©▒)ųąŠ∙ėąųžÅ═ĪŻ▓╗═¼╔ńģ^(q©▒)ķgŻ¼▒╦┤╦▓╗ūāĄ─┐╠░ÕėĪŽ¾ą╬│╔┴╦ć└ųžĄ─ęŌūR▓Ņ«ÉŻ¼╔§ų┴ŽÓ╗źī”┴óŻ¼▀@▓╗āH¾w¼Fį┌╔ńĢ■║═╬─╗»╔ŽĪŻ╔§ų┴Į±╚šŻ¼ę╗ą®ĻPė┌Ī░╚šČ·┬³šZĪ▒ĘNūÕ║═Ī░┴_┬³šZĪ▒ĘNūÕĄ─║·čįüyšZ▀Ć┐╔ęį┬ĀĄĮŻ¼▒M╣▄┬ĀŲüĒėą└Ēėąō■Ż¼Ą½Ė³ČÓ╩Ū╠ōśŗ│÷üĒĄ─Ī░╬─╗»▓Ņ«ÉĪ▒ĪŻėąĻPÜWų▐╚╦æB(t©żi)Č╚║═ārųĄė^Ą─š{▓ķę╗į┘▒Ē├„Ż¼Ę╠mĄ┬╦╣╚╦║══▀┬Ī╚╦ų«ķgĄ─ŽÓĮ³│╠Č╚│¼▀^┴╦╦¹éā┼c║╔╠m╚╦╗“š▀Ę©ć°╚╦Ą─ĻPŽĄŻ¼į┌─│ą®ŪķørŽ┬╔§ų┴Ė³ĮėĮ³Ą┬ć°Ą─╚Rę╠m╚╦Ż©RhinelandersŻ®ĪŻ╦¹éā║▄╔┘į┌╔Ē▓─ĪóķLŽÓĪó┤®ų°╗“ąą×ķ╔Žėą╩▓├┤ĘųäeŻ¼╬©ę╗─▄ģ^(q©▒)ĘųĄ─╩Ū╦¹éāĄ─Č·ČõĪŻųv║╔╠mšZĄ─╚╦ę▓Ģ■ŲŽ±Ę©šZĄ─├¹ūųŻ¼ųvĘ©šZĄ─╚╦ę▓Ģ■ŲŽ±║╔╠mšZĄ─├¹ūųĪŻ├┐«ö▒╚└¹Ģr╚╦šäŲ╦¹éāĄ─▓╗═¼ĢrŻ¼æ¬įōŃæėø─ŪŠõĖ±čįŻ║įĮ╩ŪŽÓ╦ŲĄ─Ż¼įĮÅŖš{▓Ņ«ÉĪŻ │²┴╦šZčįĄ─ĘųļxŻ¼╗∙ČĮ═Į║═╩└╦ūų„┴xš▀į┌ą┼č÷╔ŽĄ─ĘųŲńĖ³╝ėć└ųžŻ¼═¼ĢrĘų┴čų°▒╚└¹Ģr╔ńĢ■ĪŻ19╩└╝oĄ─Ę┤Į╠ÖÓų„┴xė░Ēæ┴”ÅVĘ║ĪŻ╝o┬╔Ė„«ÉĄ─╣▓Ø·Ģ■Ģ■╦∙į┌ūįė╔³h║═╔ńĢ■³hĄ─╣½╣▓╔·╗Ņųą░ńč▌ų°┼eūŃ▌pųžĄ─ū„ė├Ż¼▀@į┌ėóć°╚╦┐┤üĒĘ╦ę─╦∙╦╝Ż¼Ą½─½╬„Ėń╚╦ģs║▄╩ņŽżĪŻį┌║╔╠mŻ¼╩└╦ūų„┴x║═ū┌Į╠ų«ķgĄ─ĘųŲńę▓║▄├„’@Ż¼ų╗╩Ūø]ėą▒╚└¹ĢrĘ┤Į╠ÖÓų„┴x─Ū░Ń╝ż┴ęĪŻ┤╦═ŌŻ¼▒╚└¹ĢrĄ─ą┬Į╠═ĮöĄ┴┐║▄╔┘Ż¼╔┘ĄĮ┐╔ęį║÷┬įŻ╗Č°║╔╠mĄ─ą┬Į╠═ĮöĄ┴┐ģs║▄²ŗ┤¾Ż¼į┌ū┌Į╠╗ŅäėųąĘeśO╗Ņ▄SĪŻ│²┴╦ą┬Į╠═ĮŻ¼║╔╠m▀Ćėąę╗éĆ╗∙ĄAłįīŹĪóĮM┐Ś┴╝║├Ą─╠ņų„Į╠╚║¾wū„×ķ╔┘öĄ┼╔Ż¼╦¹éā┤¾ČÓöĄ╝»ųąį┌╚Rę║ė╚²ĮŪų▐─Ž▓┐Ż¼Ą½▓╗ŠųŽ▐ė┌┤╦ĪŻ║═╦∙ėą╬„ÜWć°╝ęę╗śėŻ¼Ą═Ąž╚²ć°┤µį┌ęčŠ├Ą─╬─╗»Īóą┼č÷║═╔ńĢ■╠ž┘|š²į┌┬²┬²Ž¹£pŻ¼ųØu═¼╗»ė┌ę╗éĆĘČć·Ė³ÅVĪóĖ³×ķ│╔╩ņĄ─╔ńĢ■Ż¼įō╔ńĢ■ī”│²ę┴╦╣╠mĮ╠═ŌĄ─╚╬║╬ū┌Į╠Š∙▒Ż│ųųą┴óŻ¼═¼ĢrŻ¼ę▓į┌īżŪ¾Ė„ĘN▐kĘ©░▓ų├Å─ÜWų▐ęį═Ōė┐╚ļĄ─┤¾┼·ęŲ├±ĪŻ ▒M╣▄Ą═Ąž╚²ć°┤µį┌ų°Į╠ģ^(q©▒)Ą─ĪóĄžĘĮĄ─Īó├±ūÕĄ─ĪóšZčįĄ─╝░ą┼č÷Ą─ĘųŲńŻ¼Ą½╦³éāķLŲ┌ęįüĒČ╝╩Ū├±ų„Ą─ĪóČÓ³hģf(xi©”)╔╠Ą─š■ų╬ĄõĘČŻ¼▓╔ė├┴╦┤¾┴┐ÖCųŲĘ└ų╣Ė„╔ńĢ■ÖCśŗ░l(f©Ī)╔·╬─╗»æ(zh©żn)ĀÄŻ¼ŠÅĮŌ┴╦╔ńģ^(q©▒)ķgĄ─ŠoÅłĘšć·ĪŻ20╩└╝o─®Ż¼▀@ą®ÖCųŲ╚šØu╩Į╬óŻ¼╔§ų┴ī”ć°╝ę║═╔ńĢ■Ą─łFĮYĦüĒ┴╦žō├µė░ĒæĪŻ21╩└╝o│§Ż¼╚╦éāķ_╩╝┘|ę╔▀@ą®ÖCųŲ╩Ūʱėą▒žę¬└^└m(x©┤)┤µį┌Ż¼Ė³ČÓ╝Ü╣Ø(ji©”)Ģ■į┌*║¾ę╗š┬šäĄĮĪŻĄ═Ąž╚²ć°├µ┼RĄ─*┤¾═■├{üĒūįę╗éĆ▓╗öÓēč┤¾Ą─ęŌęŖ░l(f©Ī)┬Ģ╚║¾wŻ¼╦¹éāīŻūóė┌├±ūÕ▀@éĆ╔±įÆŻ¼ČÓöĄ╚╦ī”╬┤═¼╗»Ą─ęŲ├±╚║¾w▒¦ėąö│ęŌĪŻ ╦«║═’L▄ć │²┴╦Ī░╚╦įņĪ▒Ą─ć°╝ę▀ģĮńų«═ŌŻ¼║╔╠mį┌┴Ēę╗ĘĮ├µę▓ęįĪ░╚╦įņĪ▒┬ä├¹ė┌╩└ĪŻŲõ▒▒║╔╠m╩ĪŻ©North HollandŻ®Īó─Ž║╔╠m╩ĪŻ©South HollandŻ®ĪóĖź└’╦╣╠m╩ĪŻ©FrieslandŻ®ĪóĖ±┴_īÄĖ∙╩ĪŻ©GroningenŻ®║═Ėź╚RĖŻ╠m╩ĪŻ©FlevolandŻ®Ą─┤¾ČÓöĄĄžģ^(q©▒)Ą═ė┌║ŻŲĮ├µĪŻ│Ū╩ąų«═ŌĄ─ų„╔½š{╩Ū┤¾ĄžĄ─ŠG║═╦«╠ņę╗╔½Ą─╗ęĪŻėóć°įŖ╚╦┐┬└š┬╔ų╬Ż©ColeridgeŻ®į┌ę╗╩ūļS╣PįŖųąŻ¼╩ū┤╬ėøõøŽ┬Ųõ║╔╠mų«┬├Ą─ėĪŽ¾Ż║ ╦«║═’L▄ćŻ¼ØMč█Ą─ŠGŻ¼ŠG╔½Ą─ŹuÄZŻ╗Ī¬Ī¬ ŚŅ┴°┤╣┤╣Ż¼×óŽ┬ę╗Ų¼ŠG╩aŻ¼ĖŻØ╔┴╦šėĄžŻ╗Ī¬Ī¬ ķgķg▐r╔߯¼╦Ų╩Ū═Ż▓┤į┌─Ū╠ņ┐šĄ─Ą╣ė░Ż¼ Ė▀┬¢Ą─╦■╝ŌŻ¼īóØŌņF┤®═ĖĪ¬Ī¬ ╦«░ĪŻ¼╩Ū─Ū├┤Ą─īÆÅVŻ╗ĄĮ╠ÄŻ¼╩ŪŠG╔½Ą─╔·ÖCŻ¼ ├└║├’L╣ŌŻ¼▒M╩šč█ĄūĪ¬Ī¬ ō■é„Ż¼Ę©ć°š▄īW╝ęĄč┐©Ā¢į°šf▀^Ż║Ī░╔ŽĄ█äō(chu©żng)įņ┴╦╩└ĮńŻ¼Ą½║╔╠m╚╦äō(chu©żng)įņ┴╦║╔╠mĪŻĪ▒├┐«ö║╔╠m╚╦╠ߥĮūµć°ą─╔·ūį║└ĢrŻ¼▒ŃĢ■Ę┤Å═╠ß╝░▀@ŠõįÆŻ¼Ą½▀@ę▓▒®┬Č┴╦║╔╠mĄ─╚▒Ž▌ĪŻį┌║╔╠mŻ¼┤¾ūį╚╗½I╔Ž┴╦╦³Ą─ę╗▒█ų«┴”ĪŻ─Ž▒▒║╔╠m╩Ī║═Ø╔╠m╩ĪŻ©ZeelandŻ®Ą─═┴Ąžų«╦∙ęįĖ╔į’Ż¼Ą├ęµė┌║ė┴„║═│▒Ž½▓╗öÓĦüĒ─Ó═┴ą╬│╔│┴ĘeŻ¼▒▒║Ż░ČĄ─╔│Ūę▓╩Ūę╗Ą└╠ņ╚╗Ą½śO▓╗┐╔┐┐Ą─Ų┴šŽĪŻ║Żč¾║═║ė┴„Ą─Į╗ģR╠ÄĄžä▌Ą══▌Ż¼×ķ╚╦éāĦüĒ┴╦┘Qęū║═žöĖ╗Ż¼Ą½═¼Ģrę▓ĦüĒ┴╦║ķ╦«Ņl░l(f©Ī)Ą─╬ŻļUĪŻ┤¾ūį╚╗Įo▀@└’Ą─╚╦éā╠ß╣®┴╦ę╗éĆ┴óūŃų«ĄžŻ¼Č°╚╦ŅÉĄ─ą┴Ū┌Ż¼īó▀@Ų¼¹}šė┤“įņ│╔┴╦┘ćęį╔·┤µĄ─╝ęł@ĪŻ ║▄Š├ęįŪ░Ż¼į┌ĶFŲ„Ģr┤·─®Ų┌Ż¼╦«╬╗Ą─▓╗öÓ╔Ž╔²Ų╚╩╣╚╦éāą▐Į©╚╦╣ż═┴Ą╠Ż¼─Ūą®čė└m(x©┤)ūµ▌ģ╔·╗Ņ┴¶į┌─Ó╠┐šėĄžĄ─╚╦Ż¼ļpūŃę“┤╦┐╔ęį▒Ż│ųĖ╔į’ĪŻ┴_±RĄž└ĒīW╝ęūóęŌĄĮĄ─Ųµ╚żęŖ┬äų«ę╗╩ŪĖź└’╦╣╠m╚╦Ą─╔·╗ŅĪŻ╦¹éāŠėūĪį┌ų╗ėą═╦│▒Ģr▓┼─▄Ąų▀_Ą─ąĪŹuŻ¼ęį¶~║═╦«▀ģĄ─ę░Ū▌×ķ╔·Ż¼Č°ĘŪĻæĄž╔ŽĄ─╦«╣¹║═ę░½FĪŻė├Ė╔į’Ą──Ó░═╔·╗ĪŻÅ─ĶFŲ„Ģr┤·═ĒŲ┌ĄĮųą╩└╝o╩óŲ┌Ż¼│╔Ū¦╔Ž╚féĆ═┴Ą╠ČčĮ©ŲüĒŻ¼ėąĄ─╩Ū×ķ┴╦▒Żūo╦Į╚╦▐rŪfŻ¼ėąĄ─╩Ū×ķ┴╦▒Żūoš¹éĆ┤ÕŪfŻ¼▀Ćėąę╗ą®│╔×ķ║¾üĒ│Ū╩ąĄ─╗∙ĄAŻ¼▒╚╚ń░ó─Ę╦╣╠žĄżŻ©AmsterdamŻ®ĪŻ ═┴Ąžķ_ē©į┌ÄūéĆ╩└╝o└’ę╗ų▒╩Ūčž║ŻĄžģ^(q©▒)Ą─╠ž³cĪŻį┌ųą╩└╝oĄ─Ę╠mĄ┬╦╣Ż¼╚╦éā═©▀^ų■Ą╠║═┼┼╦«Ż¼īó║ŻŲĮ├µęįŽ┬Ą─═┴Ąžūā?y©Łu)ķ┴╝╠’Ż¼│╔×ķ«öĢrĄ─Ž╚“īĪŻĄ½ČĪĄ─ĪČ╔±Ū·ĪĘųą├Ķīæ▀^Ż¼Ęą“vĄ─č¬║ėį┌Ąž¬zĄ─Ą┌Ų▀īė▒╗ę╗├µē”ūĶō§Ż¼▀@ūī╚╦ŽļŲ┴╦Ż║ ĪŁĪŁĘ╠mĄ┬╦╣╚╦ĖąĄĮ▓╗░▓ į┌▓╝ģ╬║š║═ŠS╔Żų«ķgų■Ų┴╦īÆÅVĄ─Ą╠ē╬ ╬©┐ų║Ż╦«Ūų╚ļ 12╩└╝oŻ¼ć·Ą╠įņ╠’Ą─╝╝ągį┌║╔╠męčĮøĘŪ│ŻŲš╝░ĪŻ17╩└╝oŻ¼ļSų°║╔╠m╚╦╩╣ė├Ą╠ē╬Īó╦«ķlęį╝░┼┼Ė╔█ū╠’Ą─’L┴”▒├Ż©Ī░’L▄ćĪ▒Ż®Ż¼╝╝ąg▓╗öÓ═Ļ╔ŲĪŻų■Ą╠Ųš╝░║¾Ż¼┤¾ČÓöĄĮ©įņį┌Ę┐╬▌║═╗©ł@Ž┬ĘĮĄ─▓╗į┘┐╔ė├Ą─╣┼┤·Ą╠ē╬▒╗ķ_Š“Ż¼Ųõ═┴╚└ė├ū„Ąžä▌Ė³╝ėĄ══▌Ąžģ^(q©▒)Ą─Ę╩┴ŽĪŻ 20╩└╝oŻ¼╚╦ŅÉš╣ķ_┴╦ī”╦«Š░*ĻPµIĄ─Ė─įņĪŻ1927Ī¬1932─ĻŻ¼║╔╠m╚╦ą▐Į©┴╦ę╗ŚlķL▀_╝s32╣½└’Ą─┤¾ē╬Ż¼ĘųĖ¶ķ_┴╦ĒÜĄ┬║ŻŻ©Zuider ZeeŻ®┼c▒▒║ŻŻ©the North SeaŻ®ĪŻÅ──ŪĢrŲų┴1968─ĻŻ¼═©▀^┼┼│÷ĒÜĄ┬║Ż║Ż╦«Ż¼╚╦éā½@Ą├┴╦│¼▀^16╚f╣½ĒĢĄ─═┴ĄžŻ¼Ųõųą▀^░ļĄ─═┴ĄžĮM│╔┴╦ę╗éĆ╚½ą┬Ą─╩ĪĪ¬Ī¬Ėź╚RĖŻ╠m╩ĪĪŻØ╔╠mĄ─Ī░╚²ĮŪų▐╣ż│╠Ī▒åóäėė┌1953─Ļ┤║╠ņę╗ł÷ܦ£ńąįĄ─║ķ×─ų«║¾Ż¼įō╣ż│╠╩╣╚Rę╚²ĮŪų▐Ą─┤¾▓┐Ęų╦«ė“ūā│╔┴╦ĄŁ╦«║■ĪŻ▀@╩Ūę╗ĒŚśOŲõÅ═ļsĄ─╣ż│╠Ż¼╦³▓╗āH░³└©į┌╚²ĮŪų▐Ąžģ^(q©▒)ų■ē╬Ż¼▀ĆąĶ꬚{╣Ø(ji©”)║ė┴„╔Žė╬Ą─┴„┴┐Ż¼ęįĘ└ĮŌøQ┴╦│▒Ž½║ķ╦«Ą─å¢Ņ}Ż¼ėų╩▄ĄĮ║ė╦«Ę║×EĄ─═■├{ĪŻ20╩└╝o60─Ļ┤·Ż¼įŁ╣ż│╠Ą─ŅAŲ┌─┐ś╦│÷¼F┴╦å¢Ņ}Ż¼ė┌╩ŪėŗäØėą┴╦ą▐Ė─ĪŻ×ķ┴╦░▓ōßØO├±║═Łh(hu©ón)▒Ż╚╦╩┐Ą─▓╗ØMŻ¼ę╗Śl3╣½└’ČÓķLĄ─ör║ķē╬ę“┤╦Č°ą▐Į©ĪŻ╦³▒Żūo┴╦¢|╦╣║ŻĀ¢Ą┬║ėŻ©Eastern ScheldtŻ®║ė┐┌ĄžÄ¦Ą─║Żč¾╔·╬’░³└©─ĄŽĀ║═░÷╚║Ż¼į┌Šo╝▒ŪķørŽ┬╦«ķl┐╔ęįĻPķ]ĪŻ1996─Ļ┐ó╣żĄ─┬╣╠žĄżör║ķē╬╩ŪĪ░╚²ĮŪų▐╣ż│╠Ī▒Ą─*Ė▀│╔Š═ĪŻį┌Ø╔╠mŻ¼▀Ćėąę╗ēK¬MķLĄ─═┴Ąž▒╗╦«ė“┼c║╔╠mų„¾w╦∙Ęųķ_ĪŻ╦³╬╗ė┌╬„╦╣║ŻĀ¢Ą┬Ż©Western ScheldtŻ®║ė║ė┐┌ęį─ŽŻ¼┼■ÓÅ▒╚└¹ĢrĄ─Ę╠mĄ┬╦╣Ż¼2003─Ļ═Ļ╣żĄ─ę╗Śl║ŻĄū╦ĒĄ└īóŲõ┼c║╔╠mŲõ╦¹▓┐Ęų▀BĮėŲüĒĪŻ▀@Śl║ŻĄū╦ĒĄ└╩Ū║╔╠m20╩└╝o*éź┤¾Ą─╣ż│╠ų«ę╗└’ŽÓī”Ųš═©Ą─ĖĮ╝ė╣ż│╠ĪŻę“┤╦Ż¼║╔╠mĄ─╣ż│╠ū╔įāį┌├└ć°ųžĮ©ą┬ŖWĀ¢┴╝Ę└║ķ╣ż│╠ųą░l(f©Ī)ō]┴╦ųžę¬ū„ė├Ż¼▀@ę▓Š═▓╗ūŃ×ķŲµ┴╦ĪŻ ╚╦ŅÉĄ─ųŪ╗█║═┼¼┴”╩╣Ą═Ąžć°╝ę▓╗āHę╦ŠėŻ¼Č°Ūę╩µ▀mĪóĖ╗ūŃĪŻ║╔╠mĪó▒╚└¹Ģr║═▒R╔Ł▒ż╚╦ė╚Ųõ╔Ųė┌ĮŌøQå¢Ņ}Īó┴Ēīż│÷┬ĘŻ¼║åčįų«Ż║ūīūį╝║╗ŅĄ├╩µĘ■ĪŻš■ų╬╔ŽŻ¼╦¹éāęį═ūģf(xi©”)║═║Žū„×ķ╠ž³cŻ¼Ųõ├▄Ūą│╠Č╚į┌Ųõ╦¹ĘĆ(w©¦n)Č©Ą─├±ų„ć°╝ęę▓▓╗ČÓęŖĪŻį┌Ą═Ąž╚²ć°ųąŻ¼╣½╣▓┐šķg║═░ļ╣½╣▓┐šķgĄ─╩µ▀mČ╚Ż©▓╗šō╩Ū╩ął÷ĪóķTļAĪó╣½ł@▀Ć╩Ū═źį║Ż®┼cĘ©ć°Ą─║Ļéź║═ėóć°Ą─└Ž┼fą╬│╔§r├„ī”▒╚ĪŻĻPė┌║═─└ŽÓ╠Ä╩Ū╚╦ŅÉ╗∙▒Š“īäė┴”Ą─▀@ę╗╝┘įOŻ¼ėąĢrĢ■įņ│╔▀^ė┌śĘė^Ą─┼ąöÓŻ¼šJ×ķį┌Ųõ╦¹ĄžĘĮŻ¼╚╦Ą─┼¼┴”ę▓┐╔ęįĦüĒ╔ńĢ■║═ųCĪóĘĆ(w©¦n)Č©┼cĘ▒śsĪŻį┌š¹éĆĮ³¼F┤·Ż¼║╔╠m║═▒╚└¹Ģręčį┌ę╗ĘĮ├µ╗“┴Ēę╗ĘĮ├µŻ¼╚ń╔ńĢ■ĪóĮ╠ė²Īóš■ų╬║═▐rśI(y©©)ŅIė“Ż¼│╔×ķŲõ╦¹ć°╝ęĖ─Ė’š▀ą¦Ę┬Ą─ĄõĘČĪŻ║╔╠m╚╦║═▒╚└¹Ģr╚╦į┌ę²ī¦╔ńĢ■ø_═╗Īóą┼č÷ø_═╗╝░╣▓«aų„┴xø_═╗ū▀Ž“║═ŲĮ░l(f©Ī)š╣Ą─Ą└┬Ę╔Ž│╔┐āņ│╚╗Ż¼╝żäŅ┴╦Ųõ╦¹Ąžģ^(q©▒)▓╔╚ĪąąäėŻ¼Ą½▀@ą®Įø“×╩╝ĮK¤oĘ©│╔╣”Å═ųŲĪŻ
Ą═Ąžć°╝ę╩Ę ū„š▀║åĮķ
▒Ż┴_.░ó▓╝└Ł╦╣╠ž”“ Paul Arblaster ┼ŻĮ“┤¾īWÜv╩ĘīW▓®╩┐Ż¼ų„ę¬čąŠ┐ĘĮŽ“×ķĄ═Ąžć°╝ę╩Ę║═įńŲ┌¼F┤·ÜWų▐╩ĘĪŻį°╚╬Į╠ė┌¶öŃļ┤¾īWÜWų▐蹊┐ųąą─╝░▒╚└¹Ģr─Ū─ĮĀ¢┤¾īWŻ¼¼F╚╬Į╠ė┌║╔╠m±R╦╣╠ž└’║š╠žĄ──ŽĘĮæ¬ė├┐Ų╝╝┤¾īWĪŻų„ę¬ū„ŲĘ░³└©ĪČ░▓╠žąl(w©©i)Ųš┼c╩└ĮńŻ║└Ē▓ķĄ┬.ŠS╦╣Ė∙╠ž┼c╠ņų„Į╠Ė─Ė’ĢrŲ┌Ą─ć°ļH╬─╗»ĪĘŻ©Antwerp and the World: Richard Versteg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e of Catholic ReformationŻ®ĪóĪČ┬├š▀Ą─║╔▒╚▒RÜv╩ĘĪĘŻ©A Traveller's History of the Netherlands, Belgium and LuxembourgŻ®Ą╚ĪŻ
- >
├¹╝ę?gu©®)¦─Ńūx¶öčĖ:│»╗©Ž”╩░
- >
²łė▄╔·Ż║į~Ū·Ė┼šō/┤¾╝ęąĪĢ°
- >
¤¤┼cńR
- >
ūį▒░┼c│¼įĮ
- >
ųąć°╚╦į┌ק╠K└’▀ģĮ«ģ^(q©▒):Üv╩Ę┼c╚╦ŅÉīWĖ┼╩÷
- >
Ų¾∙Z┐┌┤³Ģ°ŽĄ┴ąĪżéź┤¾Ą─╦╝Žļ20:šōūį╚╗▀xō±(ėóØhļpšZ)
- >
╔Į║ŻĮø
- >
į┬┴┴╗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