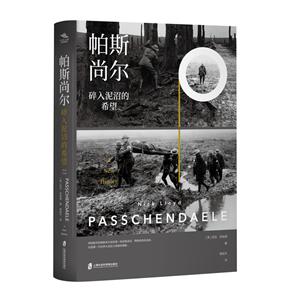-
>
清通鑒(全四冊)(精裝)
-
>
明通鑒(全三冊)(精裝)
-
>
跨太平洋的華人改良與革命 1898-1918
-
>
天有二日(簽名鈐印特裝本)
-
>
歐洲至暗時刻(1878-1923):一戰為何爆發及戰后如何重建
-
>
(精裝)奧托·馮· 俾斯麥與德意志帝國建立
-
>
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帕斯尚爾:碎入泥沼的希望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2031812
- 條形碼:9787552031812 ; 978-7-5520-3181-2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帕斯尚爾:碎入泥沼的希望 本書特色
【名人推薦】 這是一段相當寫實的歷史,清晰投射出一系列內容:從戰略規劃到對雙方而言都相當殘酷的戰役本身,再到戰役復雜的(zui)后階段對整場戰爭的影響,等等。 ——艾米麗·梅休博士(Dr. Emily Mayhew) 對1917年7—11月發生的事件進行一次全新的徹底審視是(zui)有必要的。尼克·勞埃德博士做到了這一點,他的敘述既具有學術性又極其引人入勝。 ——格林·哈珀教授(Professor Glyn Harper) 尼克·勞埃德的寫作簡潔、清晰、切中要害,讓我們不得不重新評價帕斯尚爾以及與帕斯尚爾有關的一切。 ——保羅·格羅斯,電影《帕斯尚爾》的導演兼影星(Paul Gross, director and star of the film Passchendaele)
帕斯尚爾:碎入泥沼的希望 內容簡介
伊普爾攻勢代表了現代人對次世界大戰的經典印象:炸碎的樹木、積水的溝壑、泥濘的彈坑。帕斯尚爾戰役作為其高潮,是兩次大戰中(zui)慘烈的戰役之一。對1917年的英國而言,它可謂是一場“失去的勝利”。 在這個比利時小村莊里,7—11月間死傷人數超過50萬,許多人尸骨無存。英軍付出慘重的代價才將帕斯尚爾攻下,但整個佛蘭德斯戰場的攻勢*終卻被叫停。 尼克·勞埃德在這本書中對此次戰役做了詳細的展示,而尤為難得的是,通過從前被忽視的德軍檔案等史料,他發現這場戰役并非毫無意義,英軍將士在戰斗中摸索出的戰術本可以幫助英軍卓有成效地在塹壕戰中打破僵局,但英軍卻在作戰過程中受到拙劣戰術的束縛,導致戰斗陷入僵局,錯失盡早結束大戰的機會。 作為新一代次世界大戰學者中的佼佼者,尼克·勞埃德對這場存在極大爭議的戰役做了全面有效的考察和嚴謹的研究,并以清晰和冷靜的敘述將這一戰爭故事展現在讀者面前。
帕斯尚爾:碎入泥沼的希望 目錄
導言
引子 尼韋勒攻勢
第1章 戰爭的調遣
第2章 黑格和“北部行動”
第3章 “一片火海”
第4章 “我們有時間完成嗎?”
第5章 “在持續的炮火下”
第6章 “真是個該死的詛咒”
第7章 “就像加爾各答黑洞”
第8章 “問題在于集中”
第9章 “艱苦作業的開始”
第10章“驚天大混戰”
第11章“重大的戰爭”
第12章“勢不可當的打擊”
第13章“欲速則不達”
第14章“不值得流一滴血”
第15章“沖向鐵盾”
尾聲
致謝
帕斯尚爾:碎入泥沼的希望 節選
《歷史必須做出裁決》 —— 蒂姆??哈林頓爵士 1917年11月11日,帕斯尚爾(zui)后的進攻結束后第二天,德國(zui)高統帥部(當時已遷往比利時蒙斯)舉行了一次絕密會議,討論下一年的行動計劃。11月7日,布爾什維克在圣彼得堡(當時稱“彼得格勒”)奪取政權,這意味著蘇俄現在事實上退出了戰爭,德國在東線的領土野心已無人遏制。問題仍然是西線這邊可以做些什么。德國是否應該接受和平妥協——這對一個多年來由勝利故事滋養起來的民族將造成巨大沖擊——還是要發起決定性的一擊。正如人們預料的,德國軍隊選擇了忠于自己的傳統。出席會議的赫爾曼?馮?庫爾以后指出:“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德國打算把一切都押在對西線的大規模進攻上,目的是在美國人進行武力干預之前摧毀協約國。潛艇戰已經失敗了。現在德國將再次把命運交到陸軍手中。 春季攻勢(zui)終于1918年3月21日在濃濃的晨霧中展開,這是英國軍隊歷史上(zui)糟糕的一天。魯登道夫大規模進攻的先頭部隊由70多個師組成,分布在3支集團軍中,有6000多門火炮支援,在充滿恐怖的一天里襲擊了英國防線。休伯特?高夫爵士的第5集團軍承擔了一項艱巨任務:在佩羅訥(Péronne)周圍守住前線的南部戰區。結果卻遭鐵蹄蹂躪。在那天據守前線的21個師中,有19個在第三次伊普爾戰役中參與了行動,它們失去了官方歷史學家所稱的“一大批(zui)優秀的士兵,他們的位置由未經訓練的新兵和轉調兵填補(如果真的能填補上)”。雖然高夫數月來一直警告說部隊防御能力差,后備力量太少,但他的陣地終歸是失守了。這需要一個替罪羊。4月3日黑格告訴高夫他將被解職,必須立即返回英國。 不久,這場災難的嚴重程度和德軍進攻的規模迫使人們重新思考,英國是否可能從伊普爾發起新一輪攻勢?赫伯特?普盧默爵士在意大利度過了一個冬天后,現又回到第2集團軍。他在傷痕累累的帕斯尚爾嶺上察看了英軍陣地,這里即使在(zui)好的天氣條件下也難以防守,他想知道該怎么辦。當蒂姆?哈林頓建議他們撤退時,普盧默走出了房間。 他所能說的只有:“我不同意。” 不久,這位將軍又返回,把手放在哈林頓的肩上。 “你說得對,”他心情沉重地說,“下命令吧。” 普盧默討厭這樣做。“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幕。”哈林頓回憶說:“有這樣一個人,他憑著堅定的決心和勇氣,多年來一直堅守著伊普爾突出部,打退了所有來犯者。他贏得了梅西訥戰役和帕斯尚爾戰役,現在卻被迫撤離。” 那天晚上,英國軍隊悄悄溜出了帕斯尚爾嶺。以如此代價贏得的陣地現在留給了德國人(如果他們想要的話),而第2集團軍則回到了千瘡百孔的伊普爾城附近,在那個熟悉的地方他們再次被鬼魅般的山嶺俯視。帕斯尚爾在沒有放一槍一彈的情況下丟失。從許多方面似乎可以總結出,1917年夏天伊普爾的整個戰役都是徒勞無功、毫無意義的。(zui)后,借用保羅?格羅斯(Paul Gross)2008年執導的劇情片《帕斯尚爾》中的一行文字概而言之:“1917年10月26日,加拿大軍卷入帕斯尚爾戰役。一周之內,他們以5000人的生命為代價占領了這座千瘡百孔的村莊……第二年春天,敵人不到一周的進攻又奪回了這片來之不易的陣地……”如果流了那么多鮮血去征服的山嶺這么快就能被放棄,那意義何在呢?倒不如一開始就別去奪取它,不是嗎? 對第三次伊普爾戰役的這種判定仍然司空見慣:一場徹底令人失望的悲劇戰役,一個完全徒勞的結局。但是對這個問題應該仔細考慮——那些德國指揮官斷不會這么認為,他們親眼看到了山嶺的意義所在。雖然這場戰役在德國并沒有引起特別的爭議,但人們普遍認為它是整場戰爭(zui)嚴峻的考驗之一。1917年12月5日當天,魯普雷希特王儲發布命令,向所有參加“迄今為止(zui)慘烈戰斗”的人致敬。86個師在佛蘭德斯進行了接替換防,其中22個師完成了兩輪作戰,同時大多數炮兵部隊也曾參戰。對魯普雷希特來說,戰爭結果是德國取得了完全勝利。“盡管敵人動用了大量的人員和物資,但他們卻一無所獲。”德國軍隊在佛蘭德斯的勇猛防御使德國軍隊能夠對俄國軍隊和意大利軍隊進行毀滅式打擊,令徹底的勝利近在咫尺。羅斯伯格同意這一說法,稱這場戰役為“大戰中(zui)可怕的防御戰”,并為德國軍隊的英勇行為感到自豪。他們在敵人飛機的監視下,在沼澤和彈坑的戰場上“頑強地戰斗”數月。 譜寫一段成功的防御戰傳奇(這是德國傳記作家熱衷宣傳的)離不開一個話題——對德國軍隊來說第三次伊普爾戰役有多么難打。歷史學家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英國(zui)高統帥部的錯誤和弱點上,有時會淡化“佛蘭德斯大屠殺”給守軍帶來的可怕經歷。然而,我們不應低估德軍的壓力,尤其是1917年9月和10月。在這樣潮濕的天氣里,露天作戰已經夠糟糕了,德軍士兵還不得不面對看起來無窮無盡的猛烈炮火、毒氣和低空掠過的飛機,同時只能依靠送到前線的微量食物和水來維持生存。即使是(zui)優秀的部隊,在戰場上待幾天后,也會變成步履蹣跚、虱子滿身的散兵游勇。當第465步兵團(第238師)于10月30日撤離時,沒有一個連的兵力超過30人。威爾克(Wilcke)少校望著細長的縱隊從身旁艱難走過,看到這些“瘦骨嶙峋、飽經風霜、骯臟不堪”的士兵,他情難自已。他顫抖著,眼含淚水,雙手摘下頭盔,向帕斯尚爾的英雄致敬。 1917年,對德軍來說,很少有戰役像佛蘭德斯戰役那樣對軍隊的精神和肉體提出了雙重挑戰。德軍的戰術在戰斗初期非常奏效,當時高夫試圖深入德軍防線,這種情況完全適合使用反應師。但普盧默在1917年9月和10月采取了有限的“咬住不放式”進攻,抵抗起來要困難得多。德軍指揮官在戰斗這一階段面臨的重大挑戰,長期以來要么不為英語世界作家所知,要么就被他們忽視,因而扭曲了我們對這場戰役的理解。德文資料來源(無論是部隊報告、個人日記還是公開發表的報道)非常清楚地表明,無論是抵抗普盧默的進攻,或是在英軍陣地鞏固后對其進行任何有意義的打擊,都是多么的困難。帕斯尚爾戰役揭示了自1914年以來,由防守者一方明顯占據的戰術優勢是如何轉移到進攻者一方的。 與德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對于這場勞合?喬治稱之為“爛泥戰役”的爭論在英國及其前自治領從未平息過。黑格于1928年1月去世。人們在倫敦為他舉行了一場紀念游行,并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舉行了悼念儀式。有數千名哀悼者到場,之后他被安葬在離祖籍貝爾斯德不遠的德萊布格大教堂。他似乎至死都沒有后悔,因為他確信已經盡力,別無他法。戰爭結束后不久,莫里斯?漢基舉行了一次小型宴會,黑格應邀出席。當晚,漢基一再詢問佛蘭德斯的戰況,以及進攻和持續進攻的決定是否正確,但黑格的反應從未動搖。漢基晚上走出來時確信“黑格心里完全沒有任何自責”。對黑格而言,正如他在1917年的作戰報告中所寫的那樣,盡管戰役令人失望,但是“我們已大大推動了敵人野戰部隊走向(zui)終毀滅”。赫爾曼?馮?庫爾1929年發表的報告強化了這一結論,該報告指出,如果英軍不進攻伊普爾,“德國人就會掌握主動權,從(zui)薄弱的地方進攻協約國”。 因此,英軍“緩解了法軍的危機”,吸引了德軍的預備隊力量,讓法軍的士氣有時間從春季的崩潰中恢復過來。 黑格將帕斯尚爾戰役合理化,形容為一場(jue dui )成功的消耗戰。事實上,這完全可以預見;畢竟,一年前他在索姆河也說過同樣的話。1916年,黑格精心籌劃的戰事未能取得突破,但這一失利被寥寥幾筆帶過,視作對預先計劃的適當而審慎的演練,并未被視為行動思路上的原則性錯誤。約翰?特瑞恩也同意黑格對第三次伊普爾戰役的評論,認為這是“疲憊不堪的斗爭”中(zui)關鍵的時刻。他也同樣認為德軍對進攻的反應(zui)能證明進攻的意義。(wei yi )的問題是,這種判斷只可能是事后做出的。黑格在佛蘭德斯的戰斗初衷不是為了粉碎德國軍隊,也不是為了奪取重要的山嶺(不管他后來怎么說),而僅僅是為了取得重大突破,解放比利時海岸。至于庫爾認為第三次伊普爾戰役阻止了德軍進攻,這似乎不太可能。很明顯,德國情報部門已了解到法軍出現了嚴重問題,但更大的戰略背景使他們不可能對貝當的部隊發起任何進攻——畢竟,貝當的部隊剛剛在西線進行了一次大規模撤軍。 休伯特?高夫的職業生涯在1918年4月中斷,他一直清楚地知道黑格多么想在伊普爾進行戰斗。“黑格一直夢想著騎兵部隊能推進到底,”戰后他寫信給詹姆斯?埃德蒙茲爵士,“從1915年的新沙佩勒戰役到索姆河戰役,他從未放棄過這個夢想”。這種以騎兵部隊為先鋒的大規模突破,并不只是一種空想,畢竟,黑格曾于6月在戰時內閣提出過使用“大規模騎兵部隊”作戰的誘人前景。他打仗依據的是參謀學院灌輸的那套對戰爭的理解,即打仗重在大膽的調遣、決定性攻勢和終極進攻。正如歷史學家羅賓?普賴爾和特雷弗?威爾遜所指出的那樣:“黑格的首要決心是充分利用假想中德軍開始瓦解的士氣,完成一次直達海岸線的大規模掃蕩,這種決心扭曲了每個階段的行動方針。”黑格的確在9月和10月同意在普盧默指揮下進行有限的行動,但他從未動搖過自己的信念,即遲早會取得重大突破。如果黑格愿意按照戰時內閣的指示,完全采用消耗性或“循序漸進”的方法進行戰斗,他很容易就能這樣做。 幾十年來,歷史學家都能指出黑格在第三次伊普爾戰役中的錯誤:他相信自己能掃清比利時海岸的敵軍,樂觀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梅西訥戰役之后致命的拖延;決定任命高夫這樣一名不合適的指揮官;未能研究好計劃的細節就命令高夫奪取葛路維高原;在取得決定性戰果的希望破滅后執意繼續進攻。科雷爾利?巴尼特(Correlli Barnett)在1964年BBC電視系列片《大戰》中與約翰?特瑞恩合作過,他發現特瑞恩對帕斯尚爾戰役的分析(載于1963年的著作《道格拉斯?黑格——受過教育的戰士》)可能是“一本優秀傳記中(zui)令人懷疑的一段”。對巴尼特來說,黑格決定“攻擊這場戰爭中(zui)強大的陸軍,自己卻只有一個集團軍群,而盟友之一處于解體狀態,另一個則因士氣問題而癱瘓”,這樣的決定是無謂且愚蠢的。“不僅僅是歷史的后見之明顯示出黑格思慮的不合理,”他寫道,“畢竟當時另有一位總司令正確地解讀了形勢,并采取了正確的政策——那就是貝當。” 也許第三次伊普爾戰役的真正悲劇不在于打了這場仗,也不在于英軍沒有取得突破,而在于他們并沒有發揮出全部實力。到1917年夏天,英國遠征軍已經發展出了一種能贏得戰斗的作戰方法:猛烈火炮輔以“咬住不放式”攻擊就可奪取陣地(盡管數量有限),并給任何不幸擋路的守軍造成沉重的傷亡。如果天氣好且時間充裕,英國人對敵造成的傷亡至少能和自己遭受的一樣多。普盧默將軍是“咬住不放”戰術(zui)偉大的締造者。然而黑格決定讓高夫牽頭,在7月31日首先發起高風險的突破性嘗試,接著還決定讓部隊在整個8月卷入一次又一次的小規模進攻。這些進攻逐漸削弱了各師的力量,卻幾乎沒有任何效果。犯下如此巨大的錯誤,這反映了**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的3年來,黑格幾乎從未反省過自身以及對下屬的選任問題。這與1916年他在索姆河戰役犯下的錯誤如出一轍(盡管那次涉及的是亨利?羅林森將軍,而不是高夫):尋求雄心勃勃的突破,而當突破未果時任由戰斗在組織缺乏和結構混亂的情況下坎坷推進。只有在行動瀕于失敗時,黑格才會被迫干預,改變做法。 當普盧默終于得到機會時,他牢牢把握住了。與高夫的手足無措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普盧默在突出部的指揮為**次世界大戰中的成功作戰提供了3個(zui)突出的范例:梅嫩路戰役、波勒岡樹林之戰和布魯德塞安德戰役(除此之外,還有早先在梅西訥嶺的勝利)。這些攻擊或許只奪取了少量地盤,但就連敵方也認為它們的價值(zui)高。這幾次重錘打擊的結果是粉碎性的:扭轉了德國人自戰爭開始以來(依靠縱深防御和反應師)占據的有利局面,并促使他們進行反復的浪費式反擊。事實上,人們很少意識到這些行動的效果,以及德皇的軍隊由此陷入的艱難處境。德軍指揮官很懊惱,正如他們所承認的那樣,實際上,他們無法阻止實施得當的有限攻擊。此外,在兩周內策劃一系列這樣的戰役不僅展現了英軍出色的后勤水平和組織管理能力,而且創造了(至少是暫時的)更快的作戰節奏,讓德國人措手不及。作為解決塹壕戰困境的一種方案,它幾乎和預期中一樣奏效。 整個機制當然還是崩潰了。當普盧默無法獲取成功的兩個關鍵要素——時間和好天氣時,不可避免就要恢復軍隊常態,暫停進攻。雖然他必須接受一些批評,因為他沒能更堅決地告誡黑格,把攻勢維持到10月和11月是徒勞的,但是普盧默已經指明了方向。如果這位第2集團軍指揮官從一開始就全權負責,如果進攻是在1個月前開始的,如果“咬住不放”成為英軍行動的指導原則,誰知道會取得什么成果呢?或許1917年夏末和秋天就能取得重大勝利。雖然比利時海岸未必會因此而徹底解放,但不難想象,英軍的持續施壓、德軍的更大損失,以及經常性的重擊,可能會迫使德國(zui)統帥部選擇止損。一旦德軍決定撤退到一個更適宜防御的位置,這意味放棄一些港口和魯萊斯的鐵路樞紐,那么他們對比利時西部的控制就會越來越不穩定,從而將一場重大勝利拱手讓與英國。這勢必會促使德國呼吁就比利時的狀況重啟談判,增加妥協和平的可能性。 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認為,第三次伊普爾戰役是1917年英國軍隊一次“失去的勝利”。普盧默在9月20日—10月4日間指揮的戰役從未得到應有的承認,未能在戰斗早期發起這些限制性攻擊,標志著失去了一個巨大的機會。黑格必須為此負責。在他眼里,重大突破勢在必行,“咬住不放”即使具備什么重要性,也只是用于暫時應付戰場條件。這便是黑格公認的形象:一位冷漠的指揮官,4年來毫無想象力地遵循陳腐的消耗戰理論。這一名聲掩蓋了他嗜賭成性的事實——賭徒心理使人習慣于輸錢之后一次又一次地追加籌碼。他確信,這一次的牌終會到位,他會大比分贏得勝利。悲劇的是黑格明白賭注有多高,而他的勝算又是多么渺茫。 ……
帕斯尚爾:碎入泥沼的希望 作者簡介
尼克??勞埃德(Nick Lloyd),軍事史博士,英國皇家歷史學會研究員、倫敦國王學院國防研究系軍事與帝國歷史方向高級講師,常駐威爾特郡施萊文漢姆英國國防學院聯合部隊指揮部和參謀系講學。主要研究方向為第1次世界大戰、現代戰爭發展和英帝國歷史。著有《盧斯,1915》《阿姆利則大屠殺:災難的一天》、《最后一百天》等。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朝花夕拾
- >
羅庸西南聯大授課錄
- >
巴金-再思錄
- >
我從未如此眷戀人間
- >
莉莉和章魚
- >
中國歷史的瞬間
- >
隨園食單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