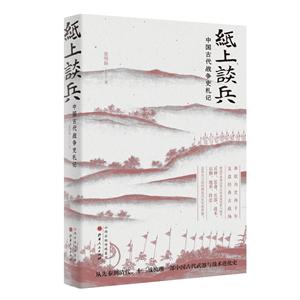-
>
清通鑒(全四冊)(精裝)
-
>
明通鑒(全三冊)(精裝)
-
>
跨太平洋的華人改良與革命 1898-1918
-
>
天有二日(簽名鈐印特裝本)
-
>
歐洲至暗時刻(1878-1923):一戰為何爆發及戰后如何重建
-
>
(精裝)奧托·馮· 俾斯麥與德意志帝國建立
-
>
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紙上談兵(中國古代戰爭史札記)(精)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3115007
- 條形碼:9787203115007 ; 978-7-203-11500-7
- 裝幀:一般輕型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紙上談兵(中國古代戰爭史札記)(精) 本書特色
張明揚就是史學界的“后浪”。他的作品是“接地氣的公眾史學”——有故事,有想法,有深度。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許紀霖 如果我們要討論軍事史的話,在這個過程當中是有非常多的細節值得我們去挖掘的。對于絕大多數軍事迷來說,這本書應該是一頓饕餮大餐了。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姜鵬 在張明揚這里,古代戰爭不再是平面的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而是兵器、后勤、軍事實力、戰術等一系列綜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上海博物館研究員 張經緯
紙上談兵(中國古代戰爭史札記)(精) 內容簡介
影視劇中常見的運籌帷幄、用兵如神,使觀眾對戰爭神話產生無盡的想象,但其中傳達的古代軍事信息并不一定準確。本書正是對中國歷代有名戰爭的多方面真實解析,精選從先秦到清代的十三場經典戰役,結合古代文獻記載與軍事理論,解讀決定戰爭勝負的多重因素與細節——兵種、裝備、兵器、戰術、后勤、地形、陣法等等,還原古代戰場實況,廓清后世演繹的兵家傳奇。 本書尤其關注中國古代政權間的競爭壓力對軍事革新的推動,梳理古代武器與戰術的歷次進化,是古代歷史文化愛好者與軍事迷不可錯過的一場盛宴。
紙上談兵(中國古代戰爭史札記)(精) 目錄
紙上談兵(中國古代戰爭史札記)(精) 節選
導論?古代的軍事競爭與武器、戰術革新 威廉?麥尼爾在其名著《競逐富強:公元1000年以來的技術、軍事與社會》中認為,歐洲長期的列國分立帶來激烈的軍事和政治競爭,由此產生的生存壓力迫使各國必須不斷進行軍事技術和軍事體制變革,從而造就了歐洲近代的軍事神話。 這一規律自然是“歐洲式”的,畢竟也只有歐洲在近代借此機會脫穎而出。但從中國古代戰爭史來看,這一規律也有其普世性的一面。在古代中國,來自周邊的軍事競爭壓力往往也會主動或被動地在中原王朝催生軍事革新。比如明清鼎革前長達二十余年的大規模軍事對抗,為兩大方營造出一個研發、裝備和應用新型火器的“絕佳”競爭環境。 軍事革新可能是物質性的,即新武器、新裝備的誕生,如大黃弩、如諸葛連弩、如甲騎具裝、如馬鐙、如陌刀、如神臂弓、如火銃…… 軍事革新也有可能是知識性的,即新戰術的革新,如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如項羽的騎兵長途奔襲,如衛青、霍去病的騎兵沖擊戰術,如劉裕的“卻月陣”,如李靖的“不停頓連續作戰”,如劉锜、岳飛的砍馬腿戰法,如明成祖的火器輪射戰術,如戚繼光的車營戰術,如袁崇煥的“憑堅城以用大炮”…… 并且,在大多數時候,武器技術革新和戰術革新并不是割裂的,而是互相激蕩、互相啟發的。技術革新促進戰術革新,新式裝備需要新戰術推動其戰力*大化。比如,隨著佛郎機在明軍中的大量裝備,戚繼光為其量身定制了車營戰術,還編練了中國騎兵史上*早的“騎炮兵”;戰術革新又對武器的進一步革新提出新的要求,比如騎兵正面沖擊這一戰術的發明,呼喚著一種讓沖擊騎兵更不易從馬背上跌落的“新馬具”——馬鐙就這么來了。 關于軍事競爭促進武器和戰術革新,在中國古代戰爭的語境內,有兩點特別值得關注。 **,草原騎兵對中原王朝上千年如一日的軍事壓力。在中國古代的軍事革新中,大多數動力和壓力都來自北方騎兵。如果細分的話,這種應對草原騎兵的軍事革新可以分三類:**類是“以騎制騎”,比如胡服騎射、漢武帝的騎兵革命、西晉后在中原王朝率先出現的馬鐙、唐高祖組建突厥化的輕騎兵軍團,都屬于此類;第二類是“以步制騎”,比如漢武帝時代的弓弩革新,李陵的“大車+弓弩”戰術,劉裕的“卻月陣”,由李靖率先裝備、李嗣業發揚光大的陌刀,北宋中前期的“彈性防御”戰術,宋神宗時代的神臂弓和斬馬刀,劉锜、岳飛的砍馬腿戰法;第三類是“以火制騎”,即以火器對抗騎兵,如朱元璋時代發明的銅制火銃,朱棣親自創建的神機營,正德、嘉靖時代引入的新式火器佛郎機,明末的紅夷大炮,袁崇煥的“炮騎協同”戰術。 第二,軍事革新的中西共振。從本質上,武器是一種商品,戰術是一種知識,都是可以在歐亞大陸或海洋貿易網絡中傳播的。馬鐙很可能就是由中國率先發明,然后傳播至中亞和西方的;在蒙古西征中,蒙古人將從金和南宋獲得的火器及其戰術帶往阿拉伯地區,再經由阿拉伯人傳播至歐洲;在明代中晚期,在火器制造技術上已超越中國的歐洲開始“反哺”,經由兩次大航海時代中的“西炮東傳”,先后將佛郎機和紅夷大炮傳至中國,幫助明軍面對滿蒙騎兵的軍事壓力。 自趙武靈王時代開始,到康熙時代,在從未停止過的軍事壓力下,特別是分裂時間不短于統一時間的軍事競爭之下,中國的軍事科技與戰術革新事實上從未真正停止過。 為了對抗機動靈活的北方胡族騎兵,趙武靈王拋棄了統治中國戰爭史上千年的笨重戰車,進行了“胡服騎射”改革,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支獨立作戰的騎兵軍團,這也讓趙武靈王成為中國騎兵之父。 但在長平之戰中,趙國騎兵暴露了前馬鐙時代騎兵的*大弱點,即只適合偵查、騷擾、追擊敗退敵軍和破襲糧道這些非核心任務,無法在大規模戰爭中正面對抗步兵軍陣,從而在長平之戰中“隱身”。當作為趙軍*大軍事強點的騎兵無法有效發揮作用,反而進入了*能彰顯秦軍紀律性和兵力優勢的步兵軍團戰斗模式時,趙國在長平之戰中的失敗也就不言而喻了。事實上,在戰車漫長的半衰期中,除了胡服騎射這一面向的軍事變革外,還有“毀車為行”,也就是變車兵為步兵軍陣的變革方向。在長平之戰時,趙國代表了變車兵為騎兵的變革,而秦軍的步兵軍陣則代言了變車兵為步兵。 事實證明,僅就軍事層面而言,毀車為行是比胡服騎射更接近當時戰爭本質的深刻變革。 長平之戰時,也正處于鋼鐵兵器與青銅兵器的激蕩更迭時代,相對而言,趙軍的鐵制兵器普及度要高于秦軍,但發展尚不成熟的鋼鐵兵器在戰場上,對于發展完備的青銅兵器并未取得明顯優勢,因此也不足以成為改寫長平之戰的變量。 在楚漢戰爭時代,劉邦在初期迅速占領關中后,就獲得了秦國在戰國時代擁有的國力體量優勢,在與項羽的戰爭中幾乎始終處于以眾擊寡的態勢。在彭城之戰中,為了對抗劉邦近60萬大軍的壓倒性兵力優勢,項羽親率三萬騎兵突襲彭城,以快制多,*大限度地發揮了騎兵的長途奔襲能力與機動性優勢,創造了騎兵**次大規模殲滅步兵集團的中國戰史記錄,成為中國騎兵史上繼胡服騎射之后的第二個里程碑。 為了對抗楚軍的騎兵優勢,劉邦戰后痛定思痛,以原秦軍騎兵為班底組建漢軍騎兵,以騎制騎,在垓下之戰中窮追不舍,逼得項羽烏江自刎的就是這支漢軍騎兵。 在漢武帝時代,為了對抗匈奴的騎兵優勢,漢武帝也采取了“以騎制騎”的大戰略,在“文景之治”積累的雄厚國力支撐下,傾全力發展馬政,很快具備了一次性數萬騎兵,甚至十萬騎兵出塞的能力。即使有了馬和騎兵,漢軍仍然直面著騎射能力遠不如匈奴騎兵的壓力。李碩在《南北戰爭三百年》一書中認為,為了對抗騎兵的騎射優勢,衛青和霍去病率先在漢軍中發起了騎兵戰術革新,不與匈奴人較量他們擅長的遠距離騎射,將中原步兵擅長的正面沖擊戰術移植到騎兵身上。 盡管依靠騎兵戰術革新,漢軍騎兵將匈奴騎兵一路從漠南打到漠北,但戰爭中損失的大量戰馬很快又讓漢帝國重新面臨缺馬的威脅。到了漢武帝后期,缺馬的現實成了李陵五千步兵出塞的時代注腳,李陵雖兵敗被俘,但這支精英步兵在絕對兵力劣勢下的頑強表現,卻顯示了漢軍“以步制騎”能力的提升。在匈奴騎兵的壓力下,帝國的制弩技術在漢武帝時代發生了一次技術革新,與秦弩相比,無論在射程、強度還是在射擊精度上都有著很大的提升,這也可以視作西漢軍工業對匈奴騎射優勢的一種極有針對性的回應。在李陵軍的*后時光里,弩成為他們*后的倔強,五十萬支箭射盡之后,李陵軍方才潰敗。 在三國時代,為了在北伐時應對曹軍的騎兵優勢,特別是曹軍的精銳騎兵部隊“虎豹騎”,諸葛亮發明了“諸葛連弩”,號稱“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在追擊蜀漢軍隊時被射殺的大將張郃,就有可能死于“諸葛連弩”;諸葛亮還編練了一套叫“八陣圖”的陣法,自稱“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八陣圖很可能是一種應對騎兵快速沖擊的步兵密集結陣;為了解決北伐時的后勤運輸問題,諸葛亮還發明了“木牛流馬”,如果撇去那些怪力亂神的包裝,簡單說就是木牛為車,流馬為舟,系統性升級了蜀漢的后勤運輸 體系。 在兩晉南北朝時代,作為騎兵歷史上*重要技術革新的馬鐙率先在中國出現,給了騎兵更大的平衡性,在高速沖擊中更不易從馬背上跌落。有論者稱,這也是中原王朝在北方游牧民族騎兵優勢壓力下的一種“回應式”創新,馬鐙可以減少中原騎兵掌握騎射技術的訓練時間,大大加快中原王朝編練騎兵軍團的效率。 馬鐙的發明是基于中原王朝的利益考量,但如同所有的軍事技術一樣,一旦發明出來,誰也不能控制它的流向與應用場景。馬鐙的出現讓中國騎兵正式進入了重騎兵時代,“甲騎具裝”成為北朝騎兵*鮮明的特點,這也讓騎兵**次具備了在正面決戰中突破步兵密集結陣的能力。 但在淝水之戰中,前秦騎兵并未成功扭轉前秦數十萬大軍的潰敗,反而成就了北府兵“以步制騎”的神話;在劉裕北伐的時代,兩千北府兵憑借其首創的卻月陣大敗三萬北魏重騎兵,號稱在戰國后就被淘汰的戰車在重騎兵大行于世的時代壓力下得到某種“復興”,成為步兵軍團防御騎兵沖擊*好的屏障。 到了唐開國時代,為了回應突厥輕騎兵的機動性優勢,李淵啟動了騎兵革新,告別了北朝以來盛行的重騎兵風潮,建立了一支以突厥為師的輕騎兵。而正是憑借這支“突厥化”的輕騎兵,唐軍成功掃平了中原群雄,而在李世民登基之后,唐軍輕騎兵又“以騎制騎”,以閃電戰的速度消滅了東突厥,成為東亞的新霸主,大唐帝國興盛于輕騎兵的馬背上。 而在盛唐時代,隨著邊境戰事的擴大,為了緩解戰馬不足的狀況,唐軍不得不重新續上“以步制騎”的中原軍隊傳統,將李靖率先裝備的新式武器陌刀與陌刀戰術發揚光大,李嗣業和他的陌刀軍,以其“人馬俱碎”的巨大威力,威震安西,成為那個時代游牧騎兵的終極噩夢。 在北宋,為了對抗遼國的騎兵優勢,如曾瑞龍在《經略幽燕》一書中所說,宋軍逐漸發展出了“彈性防御”戰術,放棄了五代時崇尚野戰和速決戰的進攻主義取向。到了宋神宗時代,為了對付西夏騎兵,宋朝軍工業連續貢獻了兩大軍備技術革新,發明了斬馬刀和神臂弓這兩個神兵利器,一近戰、一遠戰,豐富了宋軍步兵對戰敵國騎兵的武庫。 到了靖康時代,金軍憑借其騎兵,特別是重騎兵優勢,成就了“女真滿萬不可敵”的戰爭神話,為了回應這一壓力,岳飛一方面“以騎制騎”,建立了以岳云為核心的岳家軍騎兵;另一方面又在“以步制騎”的戰法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在郾城大戰中以砍馬腿戰術大破金軍*精銳的一支騎兵,也是中國歷史上*出名的超重裝騎兵——“鐵浮屠”。 到了蒙古崛起的時代,蒙古人將騎兵的機動性發揮到了人類騎兵史上的極致,如《世界歷史上的蒙古征服》一書所說,“機動性使蒙古人造就了一種不可復制的戰爭風格,直到二十世紀機動車輛應用于軍隊,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觀”。憑借無與倫比的機動性,蒙古騎兵也成為馬鐙時代騎兵戰術的集大成者,將騎射戰術和正面沖擊戰術結合得無懈可擊。 在蒙古騎兵的絕對優勢之下,原本以騎兵起家的金軍眼見在野戰中無力對抗蒙古人,便開始在防御上下功夫,將新生的火器引入守城戰,在金開興元年(1232年)三月的開封之戰中,金軍使用了當時威力*大的投擲火器——震天雷,“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炮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但就如初生的鐵制兵器并未扭轉趙國在長平之戰中的敗局一樣,新生的火器同樣未能拯救金國的亡國命運。 在蒙古滅宋的*關鍵戰役——襄陽之戰中,為了對付宋軍的堅城,蒙古軍中的伊斯蘭兵器專家改造了投石機的攻擊距離和準確率,建造了歷史上威力*大的投石機——“回回炮”,據說拋射的巨石重達150公斤,“聲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洶洶,諸將多逾城降者”,順利轟開了樊城,逼得襄陽也開城投降。不過,“回回炮”并不是火炮。 在明初,明成祖為了徹底解決蒙古問題,五次親征漠北。為了對抗蒙古騎兵,朱棣承繼了朱元璋時代的火器大飛躍,進一步完善了火銃技術,在完成“**次火器革命”后,明軍從冷兵器時代逐步邁向冷熱兵器混用時代。 也是在朱棣時代,明軍還進行了一次重大戰術革新。為了緩解火銃發射流程過慢,無法應對蒙古騎兵快速沖擊的狀況,明軍在此時升級了“疊陣”戰術,將火器部隊分為三行,雖然存在爭議,但這有可能被看作全世界*早的“輪射戰術”雛形。 在技術革命和戰術革新的同時,為了更好地發揮火器的效能,朱棣還進行了兵種配置上的改革。**次親征前,朱棣創建了神機營,這也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組建專用火器的部隊,比西班牙創建火槍兵還要早一百年左右。 明初的火銃代表了當時世界火器技術的*高水平。但在此后,歐洲在列國競爭的背景下,火器的研發制造進入了快車道,逐步超越了相對停滯的明朝。 而在嘉靖時代,蒙古人自土木堡時代以來又一次走向統一和強盛,給明軍北方邊防施加了極大壓力。為了對抗蒙古騎兵,明朝在嘉靖初年開始了對葡萄牙佛郎機的仿制工作,稍晚又引入了火繩槍,希望能夠借助這些比國產火銃更先進的歐洲火器挫敗蒙古騎兵的進犯。在“**次西炮東傳”中,戚繼光成為當時中國軍界*積極的應用者,戚繼光的部隊成為明軍中裝備西式火器*多的軍隊,甚至作為中國版火繩槍“鳥銃”的命名也很可能得自戚繼光的靈感。 邊患越嚴重,明軍對新式火器越保持學習的開放性。到了萬歷末年,隨著滿洲八旗的崛起,明軍在遼東的邊防壓力與日俱增,就在1619年薩爾滸之戰的慘敗過后,徐光啟等一批明朝士大夫深感包括佛郎機在內的明軍現有火器已無法應對八旗軍的強力挑戰,主動派人赴澳門采購更新一代的火炮——紅夷大炮,之后還開始了規模浩大的仿制工作,是為“第二次西炮東傳”。 在1626年的寧遠之戰中,袁崇煥首次攜紅夷大炮亮相便力挫努爾哈赤親率的后金大軍,幫助明軍取得了雙方開戰八年以來的首次大勝,有史料稱,寧遠之戰中的紅夷大炮“每炮所中,糜爛可數里”。為了將紅夷大炮的戰力發揮到極致,袁崇煥還圍繞大炮設計了兩套新戰術:“憑堅城以用大炮”和“炮騎協同”。前者的要義是在軍力處于弱勢的情況下,堅決避免野戰;后者的要義是關寧鐵騎“依城而戰”,在火炮火力的掩護下和清軍騎兵進行有限度的野戰。但紅夷大炮救得了寧遠城,卻救不了大明朝。 紅夷大炮的橫空出世警醒了以皇太極為代表的八旗精英們,讓后金做出了“以炮制炮”的應對措施。后金很快開始了對紅夷大炮的仿制,據說為避“夷”字之諱,改稱紅衣大炮。在吳橋兵變后,帶著幾十門紅衣大炮和制造技術的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率軍投降清軍,清軍的火器實力很快就后來居上,在東亞有史以來*大的火炮對戰——松錦之戰中,徹底壓制了明軍的炮兵,入關后紅衣大炮更成為關內各大堅城的噩夢。 正如學者黃一農所說,“徐光啟等天主教人士原本希冀能利用紅夷大炮幫助明朝救亡圖存,但歷史的發展往往事與愿違,這種新型火器*后卻轉成為清朝得以吞并大明的利器”。 在明亡清興的鼎革時代,清成為騎兵與火器均領先于同時代競爭對手的超級軍事強權。 在康熙時代,中國火器抵達了*后的巔峰時刻。在東北,清軍的大炮遭遇了俄國人堡壘戰術的挑戰,在紅衣大炮的基礎上,清朝研發出了如“神威無敵大將軍炮”這樣的攻城炮。俄國憑借西式造城法,將雅克薩城打造為一座具有歐式棱堡色彩的堅城,大大降低了清軍大炮的破壞力,迫使清軍只能圍而不攻。 在西北,清軍的大炮遭遇了噶爾丹“駱駝炮”戰術的挑戰。像準噶爾軍這種廣泛配備火器的騎兵軍團,是清軍在此前的歷次戰爭中前所未遇的勁敵。清準戰爭幾乎完全以野戰為主,清軍的重型火炮不僅缺乏機動性,更不利于遠征。初戰不利后,康熙開始為清軍大量配備適合遠征的子母炮等各種輕型火炮,為了對抗噶爾丹騎兵的快速沖擊,清軍還引入了鹿角木移動在前,火器部隊輪射在后的“連環本柵”戰術,*終在昭莫多之戰中取得了對噶爾丹的決定性勝利。 如果說清初的強敵環伺,成就了皇太極至康熙朝的火器發展,那么,正是從康熙平定噶爾丹開始,清帝國周邊再無可危及其政權生存的強力競爭對手,沒有敵人可以強大到倒逼清軍軍事創新,清軍縱然不勝,也沒有動力走出舒適區。中國火器發展在此之后徹底走向停滯,甚至有所倒退,鴉片戰爭時清軍使用的火炮在作戰效能上甚至有可能還不如康熙時代。 在《三體》中,三體文明用“質子”鎖死了地球基礎科學,從這個角度出發,鎖死清朝軍事科技發展的“質子”,就是“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這個答案或許過于淺薄,諸君不妨看完書后再嚴肅批評。
紙上談兵(中國古代戰爭史札記)(精) 作者簡介
張明揚,歷史寫作者,作家,非資深軍迷。出版有《此史有關風與月》《天命與劍》《非常之人》等。
- >
隨園食單
- >
大紅狗在馬戲團-大紅狗克里弗-助人
- >
推拿
- >
羅曼·羅蘭讀書隨筆-精裝
- >
人文閱讀與收藏·良友文學叢書:一天的工作
- >
有舍有得是人生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歷史與人類學概述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