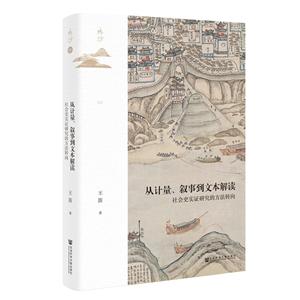-
>
清通鑒(全四冊)(精裝)
-
>
明通鑒(全三冊)(精裝)
-
>
跨太平洋的華人改良與革命 1898-1918
-
>
天有二日(簽名鈐印特裝本)
-
>
歐洲至暗時刻(1878-1923):一戰為何爆發及戰后如何重建
-
>
(精裝)奧托·馮· 俾斯麥與德意志帝國建立
-
>
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鳴沙從計量.敘事到文本解讀:社會史實證研究的方法轉向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0166966
- 條形碼:9787520166966 ; 978-7-5201-6696-6
- 裝幀:精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鳴沙從計量.敘事到文本解讀:社會史實證研究的方法轉向 本書特色
知名歷史學者王笛三十年學術探索的總結和研究方法的轉變軌跡。 產品賣點
1、作者王笛為知名歷史學者,師從著名學者羅威廉,系國內新文化史研究的代表人物,出版多種著作,口碑頗佳。
2、本書系作者對其三十年海內外學術生涯方法論總結,系作者首次對自己學術探索經歷的梳理。反映了作者在史學研究上的方法轉向和具體實踐,讀者可從中窺見三十年來史學研究的風云轉換。
3、作者的研究轉向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早期以計量史學為中心,中期以日常生活為中心,近期以文本解讀為中心。不僅反映了作者在方法上的探索和發展軌跡,具有方法論上的指導意義,同時反映了歷史研究的前沿和熱點。
4、作者兼及中西方學術環境的學習和研究經歷,對雙方學術傳統均有了解,并堅持用中英雙語進行寫作,這對于從事歷史研究的中青年學者和廣大讀者,具有極大的啟發意義。
鳴沙從計量.敘事到文本解讀:社會史實證研究的方法轉向 內容簡介
本書由作者不同時期的11篇文章構成。作為一個整體,展示了作者學術研究方法的轉變。這些文章涉及不同的主題,寫作于不同的時期,在方法上都有一定的特點,體現了作者方法上的自覺,可以說是作者三十年來學術探索的一個總結。從這本書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從計量、敘事到文本解讀的學術軌跡,從數據和社會結構的分析開始,到對下層民眾和日常生活的深描,很后致力于歷史文本的多角度闡釋,反映了作者從社會科學方法,到人文學方法的回歸,以及所采取的新文化史、微觀史和人類學的多學科交叉的研究取向。
鳴沙從計量.敘事到文本解讀:社會史實證研究的方法轉向 目錄
導言 三十年的學術探索
**編
早期研究:以計量史學為中心(1980~1990年代)
**章 計量歷史:清代四川人口、耕地及糧食問題
一 清初四川人口的恢復與移民
二 人口的數量考察
三 耕地面積的修正
四 糧食畝產和總產估計
五 清代四川的人口壓力
六 人口、耕地與糧食問題
第二章 施堅雅的影響:近代長江上游城市系統與市場結構
一 經濟區域與市場系統
二 高級市場與城鎮發展
三 集市的作用及其功能
四 市場密度與農民活動半徑
五 區域市場發展的局限
第三章 跨國研究:華人社區的沖突、控制與自治
——二戰前美國城市中的中國傳統社會組織
一 華人社區中的社會組織
二 華人社區組織的功能
三 組織間的沖突
四 華人社區內的控制和自治
五 華人組織在不成功的同化過程中的角色
六 融合還是同化
第二編
中期研究:以日常生活為中心(1990~2000年代)
第四章 從下往上看:晚清街頭文化、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
一 街頭與城市商業
二 街頭與民眾日常生活
三 謀生街頭
四 街頭的節日慶典
五 街頭改良
六 街頭控制
七 創造新的地方政治空間
八 從改良到革命
第五章 下層群體的考察:“茶博士”
——抗戰時期成都茶館的工人、職場文化與性別沖突
一 茶館業和雇工
二 “茶博士”
三 在男人的世界討生活
四 工會及會員問題
五 性別沖突與工會內部權力斗爭
六 暴力陰影下的茶館工人
七 男女茶房的社會形象
八 政府管控
九 下層民眾之間的沖突
第六章 詩歌作為歷史資料:城市之韻
——19世紀竹枝詞里的成都日常生活
一 竹枝詞及其作者
二 城市景觀與公共空間
三 節日、慶典和宗教儀式
四 大眾娛樂活動
五 對城市人的描述
六 階層、民族和性別
七 精英對民眾的批判
八 詩歌中的歷史
第七章 從微觀到宏觀:微觀世界的宏觀思考
——從成都個案看中國城市史研究
一 從沿海城市到內陸城市
二 進入城市的底層
三 茶館的微觀歷史
四 變化和延續
五 公共政治中的民眾和精英
六 “無意義”的小題目怎么變成有意義
第三編
近期研究:以文本解讀為中心(2000~2010年代)
第八章 圖像的解讀:圖像與想象
——都市歷史的視覺重構
一 什么是歷史的想象
二 想象和情感與歷史觀和方法論
三 想象的時間和空間
四 圖像的解讀
五 圖像與想象
六 圖像的局限
第九章 文本解讀:鄉村秘密社會的多種敘事
——1940年代四川袍哥的文本解讀
一 檔案中的敘事
二 社會學調查的敘事
三 小說的敘事
四 袍哥的個人敘事
五 文史資料的敘事
六 怎樣解讀不同的敘事
第十章 從語言看歷史:神秘的語言和溝通
——19世紀四川袍哥的隱語、身份認同與政治文化
一 聯絡的秘密政治
二 隱語與自我身份認同
三 飲茶吟詩中的力量角逐
四 從語言揭示隱秘的歷史
第十一章 社會學的啟發:社會學與1940年代的秘密社會調查
——以沈寶媛《一個農村社團家庭》為中心
一 沈寶媛與“農村工作者”
二 沈寶媛社會調查的學術淵源
三 調查者沈寶媛
四 沈寶媛的調查方法
五 沈寶媛對袍哥命運的認識
六 社會學調查怎樣成為歷史資料
后記
鳴沙從計量.敘事到文本解讀:社會史實證研究的方法轉向 節選
怎樣解讀不同的敘事 如果這五種敘事是講述同一人或者同一件事情,那是*理想的,我們可以比較不同敘事中對同一人和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或相同描述,但是這種資料是可遇不可求的。不過,至少本章所使用的資料涉及的是同一個群體——袍哥,這使我們能夠用五種資料的不同敘事來構建這個已經消失的秘密社會。這五種不同的敘事有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敘事方法、不同的政治背景,因此它們對袍哥的敘事存在較大差異是毫不奇怪的。 在這五種袍哥敘事中,前三種是當時人們留下來的記錄,是同時期(1940年代)人們對袍哥的三種不同角度的觀察。**種是官方的,第二種是社會學的,第三種是左翼知識分子的。第四種和第五種是1949年以后的記述,而且是1980年代完成的,離故事發生的年代已經有相當距離。第四種是袍哥個人親身經歷回憶,第五種是別人為袍哥撰寫的歷史。我想指出的是,上述五種資料,雖然都不能簡單地看作信史,但是它們對于我們了解袍哥提供了不同的視角,都是珍貴的記錄。認識歷史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每一種資料都提供了一個文本,它們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描寫方法,給我們提供了對袍哥的一種認識。它們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真實和虛構兩方面的因素,即使虛構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無意識產生的。因此它們在幫助我們認識歷史真實的同時,也可能誤導我們對歷史真實的探索。 這五種資料從哪些方面讓我們看到了袍哥的不同面相?其一,從官方的角度,我們看到雖然政府也的確采取一些措施限制袍哥活動,但收效甚微,直到中共1949年末接管成都,地方政府都未能阻止袍哥勢力的擴張。雖然民國政府公布了那么多禁止哥老會的禁令,但在檔案中看不到真正意義上的對這個組織進行打擊的運動,這和1949年以后的情況是截然不同的。應該認為,民國時期袍哥之所以能夠有如此巨大的發展,與地方政府的縱容態度是分不開的。當然,袍哥有如此巨大的發展,和民國時期四川的歷史有著密切的關系。我們知道,四川直到1935年才真正納入國民政府的管轄之下,正是在軍閥混戰時期,袍哥奠定了自己權力的堅實基礎。由于缺乏一個統一的強有力的政府,20世紀二三十年代,袍哥彌補了地方權力的真空,包括參與稅收和地方治安。如果沒有袍哥,社區的日常生活將會更加混亂。當國民政府在全面抗戰爆發前夕終于把四川置于中央統轄范圍之內時,袍哥已經發展到如此的規模,政府不但無法對他們進行有效的控制和打擊,而且必須更多地依靠這股社會力量。 其二,社會學的調查再次證明,在抗戰時期的四川,地方領袖幾乎都是袍哥成員,望鎮鄉保甲、治安的頭面人物便是*好的證明。這也印證了本章開始時所引用的廖泰初在《太平洋事務》上關于袍哥在四川成年男性中比例非常高的說法。從雷明遠捉匪的事跡中,我們看到袍哥是土匪的克星,袍哥在地方安全事務中扮演了一個活躍的角色。但在官方——從清朝到民國,再到共產黨——的歷史記述中(包括本章關于賀松的記述),他們卻與土匪聯系在一起。因此才有了《袍哥與土匪》這樣的題目出現。這個現象可以有若干種解釋:一是袍哥背景的復雜性,不可否認某些袍哥的土匪背景;二是官方話語的影響,使袍哥消極的方面被擴大;三是1949年以后紅色政權對袍哥形象的再創造。在現在的國家話語中,袍哥都是無惡不作的惡棍,但是從本章關于望鎮袍哥的故事中,我們卻看到一個年輕的女大學生和這個家庭建立的友誼,這是否暗示當時袍哥的形象并非那么可怕,或者說相當一部分的袍哥,看起來和一般人民也差不多?關于雷明遠失去佃田的事情是耐人尋味的。在我們的概念中,作為一個袍哥首領,他似乎可以輕易迫使地主繼續出租這些田地,但事實上并非如此。盡管他可以殺人,但是在佃田的問題上卻是無能為力的,*后導致了其權力的衰落。 其三,在這五種敘事中,可能對歷史研究者來說,小說是*上不了臺面的資料,其實,文學對于我們研究歷史,有著獨特的用處。正如德塞都所指出的,如果說“標準的歷史寫的是權威勢力的謀略”,那么那些“編造的故事”則提供了了解文化的基礎。沙汀所描述的故事離真實的歷史到底有多遠?如果我們了解沙汀的寫作方式和故事源泉,就會發現其創作的小說具有強烈的紀實性。沙汀的寫作類似另一位四川鄉土作家李劼人,李在1920年代寫了《市民的自衛》,30年代寫了《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等歷史小說,被文學批評者稱為歷史的“紀事本末”,缺乏革命的浪漫主義。同李劼人類似,沙汀的小說都是根據他對四川鄉場的個人觀察和親身經歷寫出來的。《在其香居茶館里》所涉及的茶館的茶客、討論的問題、文化、習俗等都是有所根據的,諸如聯保主任、壯丁、兵役科、吃講茶、喊茶錢、團總、哥老會、打醮、派款、收糧等。沙汀后來回憶《在其香居茶館里》的創作時,也承認這個故事基本上是寫實的,“聽來的故事就那么一點點,被擺在小說的*后,用來點題。虛構的是幾個人物爭吵的過程,一次不可開交的吃講茶場面。這一定是在一個鄉鎮的茶館里進行!想象中那是安縣的西南鄉,桑棗、秀水一帶的樣子,叫它回龍鎮。茶館定名‘其香居’,卻是綜合所見各種鄉鎮茶館的情形的。每人有每人的與身份相稱的茶座。尊貴的客人一進來,人人搶著喊‘看茶’。閉起眼睛也想得起來那種氛圍”。 其四,個人經歷的回憶是珍貴的口述歷史記錄。袍哥大爺蔡興華的回憶有相當的資料價值,但是我們也必須意識到其中存在的問題。首先是有些事情回憶者并不愿意講出來,所以我們所知道的這個袍哥的面貌,很可能是不完全的,而只是他愿意讓我們看到的面貌。另外,由于共產黨在取得政權后,一直以國家話語來解釋歷史,所以這些老人在回憶歷史的時候,難免落入這種話語的俗套,他們對自己歷史的回憶,難免用敵我分明的思維方式,盡管這種方式經常是無意識出現的。同時我們還應該意識到,由于年代久遠,其回憶的準確性一定會受到影響,因而不能僅僅依靠他們的回憶來看待歷史,還需要其他材料的補正。 其五,盡管本章引用文史資料所提供的事例具體生動,但這種政治化的表達影響了資料的價值。這類資料很顯然有著先入之見和政治傾向,這樣會影響其作為史料的價值,因為撰寫人難以持公允的態度。本章所引述的關于賀松的敘事便大量使用有傾向性的形容詞,諸如“專橫獨斷”“殘忍狡詐”“危害革命”“滔天罪行”“罄竹難書”“瘋狂地垂死掙扎”等,代表了1949年以后官方對所謂“反面”人物的評價。其實我們應該理解,一個地方文史資料的撰寫人很難置身于政治之外,因為地方政府、政策、人事、歷史、文化、習慣等因素,都會影響他們的寫作,地方文史資料的編寫體例留給他們自由發揮的空間并不多,因此不能對他們過于苛求。而且應該意識到,正是他們長期的努力,才搶救了大量的地方歷史,如果沒有他們,一些資料和故事就永遠消失了。他們的記述給我們提供了十分有用的信息。 五種文本所講述的故事有什么共同點呢?綜合這五種袍哥敘事,可以發現,這五種敘事至少在四個方面顯示了袍哥的共性。**,很多地方精英都加入了袍哥,如本章所提到的賀松是學校教師。但他們不是正統精英,而是以下層為主,所以袍哥難免被正統精英所歧視。袍哥的公開活動和影響引起一些正統精英的不安,雖然他們表示“對于任何幫會的正規活動”都不干涉,因為“我們是擁護結社結會自由的”,但擔心現在“幫會的活動已經達到極點了”。以成都為例,“哪一街莫有碼頭?哪一個茶鋪里莫有袍哥?現在的地方自治人員,不通袍的究有幾人?甚至在機關里,在議會里,也有不少人以什么公社社員的姿態出現”。他們指出幫會之所以這樣活躍,是由于“政治低能、法律失效、社會秩序紊亂所引起的”。他們支持政府“重申前令”,加強控制,不準學生加入幫會,凡參加者予以開除,校長亦須受管教不嚴的處分。 第二,袍哥在20世紀上半葉的劇烈擴張其實是和中國現代國家形成及現代化過程緊密聯系的。過去四川地方社會有著各種民間組織,在地方治安、經濟、日常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如清醮會、土地會等。但是晚清民國時期的現代化摧毀了這些組織,政府又無力填補留下的權力真空,從而給袍哥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第三,袍哥滲透進入了地方政權,特別是低級政權,上面提到的雷明遠和賀松都是極好的例子。他們甚至通過地方選舉,進入地方議政機構。我們還看到,雖然袍哥是政府所宣布的非法組織,但是他們在相當的程度上為政府服務,地方上許多事務都要依靠他們來實行,如抗戰中賀松成為修機場的民工大隊長。甚至有些袍哥從秘密社會組織的首領,搖身變為合法政黨組織的負責人,賀松成為青年黨縣黨部主席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就是說,袍哥在四川鄉村權力結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第四,不同文本都參與了袍哥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到,雖然各種敘事各有不同,但是1949年前后的敘述也是界限分明。“袍哥”這個詞在1949年以前,雖然存在不少的消極因素,但并不總是一個消極的概念,他們也經常被視為和政府對抗的好漢。但是政府和精英卻有完全不同的評價,并建立了其具有決定意義的話語權。我們現在對袍哥的認識,在相當程度上是傳統社會精英和現代革命話語長期影響的結果。從清初到民國,袍哥為非法的、政府明令查禁的組織。晚清地方改良精英把袍哥與江湖盜賊等列在一起,有其政治動機,與官方關于袍哥的話語一致。不過他們始料未及的是,不過幾年之后,袍哥成為傾覆清朝的主要力量之一,并在辛亥革命后一度得以公開活動。民國時期,雖然政府壓制袍哥的活動,但是這個組織卻不斷壯大。在1949年后共產黨的革命政治話語中,袍哥變成了和土匪一樣的集團。 袍哥的覆滅固然是共產黨國家機器打擊的結果,但也是這個組織傳統與國家機器對抗的必然結果。雖然在民國時期,這個組織試圖與地方權力結合,并由此擴張了組織的規模和影響,不過共產黨政權絕對不允許與國家機器相對抗的這樣一個組織的繼續存在。這個組織被摧毀了,但是它所留下的許多問題,今天仍然值得我們去認真回答。 出自第九章《文本解讀:鄉村秘密社會的多種敘事——1940年代四川袍哥的文本解讀》
鳴沙從計量.敘事到文本解讀:社會史實證研究的方法轉向 作者簡介
王笛 出生于四川成都。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博士,歷史學家。曾擔任美國得克薩斯A & M大學歷史系教授。現為澳門大學杰出教授、歷史系主任。主要關注中國社會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觀史的研究。成果豐碩,著有《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茶館: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與復興(1950~2000》《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等。相關作品榮獲美國城市史研究學會最佳著作獎、呂梁文學獎等多個圖書獎。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朝聞道
- >
羅曼·羅蘭讀書隨筆-精裝
- >
新文學天穹兩巨星--魯迅與胡適/紅燭學術叢書(紅燭學術叢書)
- >
月亮與六便士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裝共3冊
- >
經典常談
- >
二體千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