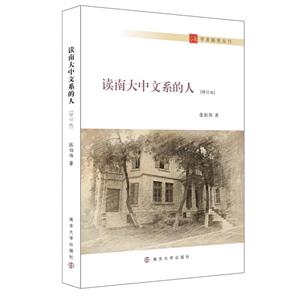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讀南大中文系的人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5231407
- 條形碼:9787305231407 ; 978-7-305-23140-7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讀南大中文系的人 本書特色
本書是對2014年初版的修訂。以散文的筆調,深情地記載了作者40多年來在南大中文系(文學院)學習、工作,以及在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地開展研究、工作所經歷的人和事,既有對自己崇敬的老師、同事的追憶,也有對學生諄諄教導的記載,還有對學術著作、學術生涯的評論和記憶等。
讀南大中文系的人 內容簡介
《詩經》有言:“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古人謂谷風為東風,隨春化雨,潤物無聲。又謂谷風為生長之風,翼彼新苗,花葉茂成。此套學人隨筆,作者多來自上庠,以隨心、率真的筆墨,透出才情與職志,故而取“谷風”冠之,期與讀者相呼應。
讀南大中文系的人 目錄
輯 人來人往
繞溪師的“藏”與“默”
管雄先生小傳
“行道救世,保存國粹”——程千帆先生的精神遺產
一件化俗為雅的小事
程千帆先生的治學與教學
老師,我舍不得您!
說先師閑堂贈潘石禪先生詩兼述往事
天真的浪漫詩人——趙瑞蕻先生
有思想的頑童——許志英先生
癡雁——嚴迪昌先生
暉弟已矣,雖萬人何贖
六十年間幾來往——我與《文學遺產》
齋名變遷與進德修業——從“日不知”“適其適”到“百一硯齋”
韓國文化散記
日本京都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室印象略記
憶南洋
第二輯 書前書后
《隋唐詩歌史論》讀后
《三思齋文叢》編后記
南京大學檔案館藏《程千帆友朋詩札輯存》題記
《桑榆憶往》題記
《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韓文版序
寫在《嘉定錢大聽全集》出版之后
《悔鄙遺稿》《石山遺稿》跋
略說《東坡禪喜集》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發刊詞
《域外漢籍研究叢書》總序
題《道在瓦甓》
《春天種一顆樹》序
《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序
《明末清初杜詩學研究》序
《漢魏六朝書法理論與文學理論關系探微》序
《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研究》序
閑堂師批語輯錄
第三輯 獨言獨語
書紳錄
首屆文科強化班開學典禮致辭
南京大學1992級學生畢業典禮致辭
南京大學1996級學生畢業典禮致辭
文學院2009級研究生開學典禮致辭
文學院2013級新生開學典禮致辭
2006年“趙安中講座教授”受聘儀式講話
“皇帝·單于·士人:中古中國與周邊世界” 青年學者工作坊致辭
第二屆中韓歷史學家論壇致辭
“三國志曼陀羅:三國時代的思想、學術與文學” 學術工作坊致辭
第二屆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 學術研討會致辭
“素心會”發起詞
“靜悄悄地”立德——《莫礪鋒文集》新書發布研討會致辭
讀古典文學的人
讀南大中文系的人 節選
讀古典文學的人,貴在有聰明而不恃聰明,貴在天分與功力的結合。當其下工夫之時,外人只見其笨拙、遲鈍,殊不知聰明正在其中矣。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1939年11月10日記:“午后過貞晦翁,談某君才太高,能太多,而不能守窮耐淡泊,恐不能成家。又謂:三十以前說聰明說天分,三十以后恃功力。”記得夏先生自己也說過,“笨”字從竹從本,故“笨”乃治學之本。古典文學的產生時代在數百年乃至數千年之前,歷史背景、典章制度、社會風俗、思維習慣與現代都有著很大差別,文獻汗牛充棟,真偽混雜,其用以表達的媒介又是文言,要能夠從中發現問題,并調動各種手段去加以解決,這需要多么強的理解力,多么豐富的想象力,多么敏銳的感受力,多么嚴密的思考力,這絕不是一個缺乏聰明的人所能夠承擔的。但在古典文學的研究傳統中,首先強調的從來就是一個“笨”字。 古典文學的研究,若就其性質而言,可大而化之地分為資料工作和理論工作兩大方面,所以,有一些學者往往具有某一方面的特長,偏于做某一方面的工作,將其特長發揮到極致,當然也能取得很高的成績。但理想的狀況是將這兩方面結合,也就是先師晚年提出的“文藝學與文獻學相結合”的“兩點論”。大概讀古典文學的人,都不應輕視文獻資料工作。以蓋房子為喻,資料即為地基。以做生意為喻,資料即是本錢。“長袖善舞,多財善賈。”每個人在研究生涯中,都會或多或少、或長或短從事過資料工作。資料工作本身,無非是查閱目錄,閱讀圖書,抄錄文獻,整理編排。這也許不需要很高的智力,但必須不辭辛勞,耐得住寂寞。這在外人看來,或不免于沉悶、枯燥,但這就是研究工作的基礎。有的人不耐煩這類工作,熱衷于使用別人編好的資料,甚至熱衷于利用他人研究著作中引用的資料。這就好比做菜,到超市里買來經過加工的原料,自然可以做出一道菜,但絕不會是高明的。一輩子這樣做菜,終究成不了廚師。真正的廚師必然從原料的選擇開始,去粗取精,整理安排,才能做出一道道上品的菜肴。 這還是就其常態而言。如果遇到社會的或人生的巨變,在困境中堅持不懈地從事資料的整理與研究,其工作就能顯現出一種意志力的美。這里,我要舉任半塘先生為例。1918年,任氏考取北京大學國文系,遇到詞曲大師吳瞿庵(梅)先生,受其影響而決定了他一生的學術研究方向。畢業后,他留居吳先生“奢摩他室”書齋,用兩年時間盡讀吳先生精心收藏的詞曲典籍。此后在從政和辦學之馀,仍不廢研究。1949年,他從桂林到成都,沒有工作,只能以賣薰豆、代人刻印、寫字為生。1951年,55歲的任先生在四川大學得到教職,但隨之而來的是政治運動,肅反、打右派、抓歷史反革命,不得不接受行政管制等等。在1980年以前近三十年時間里,他居住在一處陰暗狹小的房間,白天背著裝有熱水瓶、舊日歷紙片的背簍到圖書館讀書,晚上整理所抄錄的資料,凌晨即起伏案寫作。在人們難以想象的困境之中,他先后完成并出版了《敦煌曲校錄》、《敦煌曲初探》兩書,將敦煌曲的分類、收集、校訂、研究合為一個系統。又以右派分子和歷史反革命分子的身份,撰就了《唐戲弄》、《教坊記箋訂》、《唐聲詩》和《優語集》。這些著作,基本上都是文獻資料的整理和研究。1956年在其花甲誕辰日,他寫了一篇《唐代音樂文藝研究發凡》,敘述了他畢生學術事業的理想,對唐代結合音樂的詞章和伎藝作一全面研究。而其基礎就是由《教坊記箋訂》和《唐聲詩》奠定的。他的學生曾這樣評價其工作:“他全力以赴從事資料工作,于是使這種零度風格的工作充滿熱情,成為富于理論意義和人格力量的工作。”“他的學術具有堅實而強健的品格:總是按‘大禹治水’的方式設計學術工作,在他所研究的每一個課題范圍內,細大不捐地梳理全部問題;總是用‘竭澤而漁’的方式收集資料,‘上窮碧落下黃泉’,不放過有關研究對象的蛛絲馬跡。就像一個義無反顧的行路人,他不斷追求對于極限的超越,追求對于自己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的超越。”(王小盾、李昌集《任中敏和他所建立的散曲學、唐代文藝學》)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發憤著書”的傳統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后的又一個典型。 學者貴在有個性,假如我們詢問一下任先生,讀古典文學的人應該是什么樣的,他會如何回答呢?任先生已經在十一年前去世,我們不能起九原而問之。不過,從他對于學生的訓誡中,也許便寄寓了某一方面的期望,即“聰明正直,至大至剛”。這八個字都有出處,“聰明正直”出于《左傳》,“至大至剛”出于《孟子》。前者涉及學者的資質和品格,后者涉及學術的精神和氣象。其實,在古典文學的研究隊伍里,本是不乏聰明人的。但聰明而不正直,就往往會為了達到追求個人名利的目的,不擇手段。小者投機取巧,攘善掠美,大者背叛誣陷,落井下石。上世紀災難深重的中國,有內戰,有外侮,有動亂,有浩劫,雖然是極少數,但仍有一些學者或迫于外在壓力,或出于內在需求,其所作所為令人不齒。“至大至剛”一方面是學術氣象的博大剛健,一方面是學術精神的正大剛直。這可以說是一個很高的學術境界。而學術精神的正大剛直,實際上又貫通到其為人的“正直”。《孟子》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學者應該堅持真理,獨立思考,敢于挑戰權威,特立獨行。任先生指導博士論文,其精神就是兩句話:“要敢于爭鳴——槍對槍,刀對刀,兩刀相撞,鏗然有聲。”又說要“震撼讀者的意志和心靈”。總之,學者首先要做一個正直的人。聰明固然需要,但讀古典文學尤須以愚自守,以勤補拙。并且,聰明只有以浩然之氣來運作,才能發揮為至大至剛的氣象。 現在,我要談談先師的意見。先師也是吳瞿庵的學生,因此和任先生可以說是前后同學。但他們的風格顯然不同,而在不同之中又有其同者。我*近找到一份二十多年前大學時代的課堂筆記,內容是先師講授的“古代詩選”。大概是*后一堂課吧,先師講起了他對于做人和做學問的基本想法——“首先要做一個正直、真誠的人”。我的學問距離老師的要求相差太遠,但在“做一個正直、真誠的人”方面,自問還算基本合格。先師在遺囑中也有對學生的話,其中說到:“望在我身后仍能恪守‘敬業、樂群、勤奮、謙虛’之教,不墜宗風。”這其中的八個字,可以代表先師對讀古典文學的人的希望,是敬業的、樂群的、勤奮的、謙虛的。 我在做大學生的時候,就知道先師對他的研究生要求很嚴格,其中一條是,任何作業及任何字條,都不允許寫任何錯別字和潦草字,也不許寫不規范的簡體字,一旦出現,就用紅筆打一個大大的叉。我當時覺得有些不理解,一是認為寫字不一定非要楷體,二是認為這樣的要求對研究生似乎太低。當然,我自己還是遵守這項要求的。后來讀到宋儒的講法,才恍然大悟其用心所在。程明道說:“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河南程氏遺書》卷三)在老師要求的八個字中,敬業居其首,古人認為“蓄道德而后能文章”,“敬”正是一種道德修養上的要求。但這種要求實際上也是貫串于道德活動和知識活動之中的共同的精神狀態。黃勉齋說:“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性理大全書》卷四十一)在學術研究中,具有“敬”的精神狀態,就能面對研究對象,保持清明的智性,從而發現客觀材料中的意義。否則,就容易掉以輕心,信口開河,使學術研究走上虛浮不實之路。我的理解,由寫字而逐步使學生認識到治學之難,并逐步培養起對學術研究的“敬”的態度,是先師這一要求的用心及意義所在。所以,我也認為,在這八個字中,實際上應該以“敬業”為統帥。因為敬業,就會懂得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學術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探尋真理,在探尋真理的道路上,“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于是就必然會樂群;因為敬業,就會懂得學術研究的意義在于“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擔負著文化傳承的使命,而要完成這一任務,又要靠錙銖積累而成,于是就必然會勤奮;因為敬業,就會懂得“吾生也有涯,而知無涯”,面對知識世界,自己永遠都是一個小學生,于是就必然會謙虛。老師生前曾聽到我的這番議論,頗為贊許,認為我發展了他的思想。“發展”二字我不敢承當,但至少可以說,這沒有違背老師的立言宗旨。 關于謙虛,是先師強調得比較多的一個方面。他說:“人總是有點驕傲的,我回想起自己過去也很狂妄。狂妄或驕傲也意味著自信,問題是怎么把它們區別開來,是不是可以謙虛,同時又有自信,這個分寸比較難于掌握……你謙虛到什么主見也沒有,自己什么意見也不敢拿出來,那就成學術界的鄉愿。什么東西拿出來都四平八穩,是沒法子使科學發展的。所以既要謙虛,又要自信。”這個關系應該如何理解?我是這樣認識的:首先,謙虛的反義詞是自滿,《周易》上面說“滿招損,謙受益”,就是這樣相對來講的。驕傲的人也許同時就是一個不自滿的人,因為毛主席說“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所以現在講到一個人驕傲,就一定會說他不謙虛。其實未必然。十年前,我在日本見到京都大學的興膳宏教授,他應該是現在日本中國文學研究界學術成就和地位*高的學者了。他跟我講:“貴國毛澤東先生說:‘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我認為,驕傲使人進步。”這又如何來理解呢?我是這樣看的,因為驕傲,所以他對自己就有無限的期待,渴望今日之我超越昨日之我,于是就會永不滿足,永遠進取。先師曾勉勵我在學術上要“自致隆高”,我想也是這個意思,絕非要人自高自大。黃季剛先生是一個驕傲的人,但他又是一個多么努力的人。直到臨死之前還要堅持把沒有點完的一部書的*后一卷點完,真正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先師就曾經挖掘出季剛先生性格中非常謙虛的一面。其次,謙虛是面對知識本身的心理狀態,而不是對人的點頭哈腰、稱兄道弟。我們現在常常把一些對人和氣、措辭恭敬的人看成是一個謙虛的人,如果他同時也是一個勤奮努力、不斷吸收新知的人,我同意他是一個謙虛的人。反之,如果他非常懶惰,既不看書也不研究,我就認為他是一個自滿的、同時也就是不謙虛的人。他的表面上的“謙虛”,我只能認為這是“虛謙”。我們需要的是做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謙虛的人。程伊川說:“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道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道不尊。”(《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五)在今日的學術界,據我看來,學術之于學者,不患其不親,惟患其不尊。 任先生和先師對于讀古典文學的人的要求,應該說都是屬于儒家的,不過一近于孟子,一近于孔子。我再舉一個近于道家的例子。日本漢學家入矢義高先生1998年去世,他生前研究中國的小說、元曲、中古詞匯、敦煌學、禪宗語錄以及日本的漢文學,他是以一篇關于鄧之誠《東京夢華錄注》的書評震撼中國學術界的。他在敦煌文獻、口語文獻、佛教文獻的研究方面,被國際學術界推許為“*大權威”。傳說他對于治中國學的人提出了三項條件:一是要有錢;二是要能喝酒;三是要有閑情。這大概是有些開玩笑,不過,諧語中也有莊語的味道。**點說明學術不能“為錢作”;第二點有他的個人特色,入矢先生很愛酒,十年前我聽說他每天抽兩包煙,喝十瓶啤酒。而第三點所體現出的更是一種為學術而學術的精神。“學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常常有人問我,研究古典文學有什么用?問話的人顯然隱含著沒有用的答案。我常常也不愿意作回答,不過今天我想回答這個問題。首先,中國學術中*缺乏為學術而學術的精神。難道學術本身不足以成為研究的目的嗎?為學術而學術,不是一種消極的治學態度,它意味著學術研究不是為名、為利、為職稱、為學位,也不是為了迎合時尚、響應號召、配合政策、證明指示,學術有其自身的紀律、規范、意義、目的。按照《莊子·天下篇》的說法,每一門學科都是“方術”,而在其背后都有一個“道術”,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真理。學術研究就是要由“技”進“道”,發現真理,真理是沒有大小貴賤之分的。在這個意義上,胡適之說發現一個古文字的意思和發現一顆衛星,其價值是一樣的。其次,一個真正有著現代感的研究者,無論其研究對象是多么的古老,都會在他的研究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現代意義,所以克羅齊說:一切歷史,只要它是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都會對當代社會產生影響。我前幾天偶然發現自己1989年6月14日博士論文答辯時的答辯陳詞,其中有這樣一段話,轉述于下:“我寫這篇博士論文,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方法,之所以要將它納入文學思想史的范圍,是因為其內篇三章,歸根結底,所希望加以探討的不只是有關文學理論的問題。在‘以意逆志論’中,我抓住這一方法的人性論基礎,并指出在今后的發展中必須堅持人文主義的原則,是希望人們能保持住只有人才具有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使這顆心不被權力、名利所侵染,因而異化乃至非人化。在‘推源溯流論’中,我提出這一方法導源于中國學術傳統中因革損益的大法則,是希望人們對傳統采取創造性轉換的方式以推動社會的發展,使人民能以*小的損失而獲取社會*大的進步。在‘意象批評論’中,我強調其思想的內核是莊子的體道方式,是希望人們在從事創造性的文化勞動時,能夠吸取莊學的精髓,以虛靈不昧之心去觀照、揭示事物的本來面目,而不要使這顆像明鏡般透亮的心被一切世故的、狡詐的東西所蒙蔽。”我想,如果我的書能夠達到以上的目的,就是對現代社會產生了作用。第三,有用無用的問題的討論,是沒有意義的。為了某種“用”而作的研究,都是應時的、短命的,無用之用,是為大用。
讀南大中文系的人 作者簡介
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文學院)是南大最古老的系科之一,至今早已過了百歲。中文系的存在不僅為南大云集了一批鴻儒俊彥,培養了萬千學子,更為南大增添了人文的光芒。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張伯偉,嗜書、好酒、愛清談。機緣湊泊,偶涉隨筆,追求融合思想、學問、性情的文字風格。曾任日本京都大學、韓國外國語大學、臺灣大學、香港科技大學、浸會大學客座教授。
- >
經典常談
- >
伯納黛特,你要去哪(2021新版)
- >
朝聞道
- >
史學評論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裝共3冊
- >
隨園食單
- >
苦雨齋序跋文-周作人自編集
- >
李白與唐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