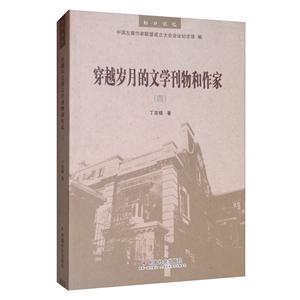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穿越歲月的文學刊物和作家.四 版權信息
- ISBN:9787508762586
- 條形碼:9787508762586 ; 978-7-5087-6258-6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穿越歲月的文學刊物和作家.四 內容簡介
本書為《虹口記憶叢書》第四本, 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左聯刊物和左聯解散后左翼進步文學期刊, 述評的對象也是左聯進步作家及文學作品。本書延續比較新的思維、觀點和角度去撰寫, 反映他們與進步作家攜手擔負起抗日救亡的歷史使命。左翼、進步作家和辦刊者以各種方式鮮明地體現在辦刊宗旨和發表的文學作品里, 其中有許多動人故事。
穿越歲月的文學刊物和作家.四 目錄
研究空白:魯迅主編的《文藝研究》創刊號
魯迅“遠離”的左聯文化刊物《世界文化》
潘漢年代表“文委”主編《文化斗爭》
左聯成立周年問世的《文學生活》
馮雪峰與《文化月報》和《世界文化》第2期
“蘇聯之友社”與《今日之蘇聯》周刊
廣州《戲劇集納》;上海《文藝新聞》“牽手”
《光明》“跨界”綜合性,高擎“國防文學”旗幟(上)
“五大劇社”春季聯合公演(“戲劇專號”之一)
“千載難逢”的劇壇前輩座談會(“戲劇專號”之二)
中國現代劇壇兩個“**”(“戲劇專號”之三)
“雙胞胎”《賽金花》禁演后的“舌戰”(“戲劇專號”之四)
魯迅觀看王瑩等演戲(“戲劇專號”之五)
許幸之改編的《阿Q正傳》(“戲劇專號”之六)
郭沫若首倡的王茂蔭研究
說不盡的魯迅
“肝火正旺”的筆戰
左聯與中國著作者協會
丁景唐修訂補充《左聯名單》一文的10則來往信札
后記
穿越歲月的文學刊物和作家.四 節選
《穿越歲月的文學刊物和作家(四)》: 顧仲起頗有才華,著有短篇小說集《生活的血跡》《笑與死》《愛的病狂者》,中篇小說《殘骸》《墳的自供狀》《葬》和詩集《紅光》等。但是,錢杏邨不愿意過多點贊,冷冷地指出“他的取材以及描寫,仍然不外乎個人生、活的記錄,仍然有自傳的傾向。而不能取材于廣大的群眾,或者對于時代更有關切的題材。他所表現的,可以說完全是革命失敗后不徹底的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生活形態的反映。然而,我雖有這樣的不滿,但他的創作的時代色彩,以及時代意義,我們是不能否認的。他是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作家”。錢杏邨采用先抑后揚的手法,以濃厚的批判色彩掩蓋他內心的哀悼之情,這歸根結底還是與顧仲起的自殺有關。如果讓如今世人重新評價顧仲起這位“老革命”作家,語氣可能委婉得多了,畢竟拉開歷史距離觀審,可以多一些不同角度的反思和探索。 對于顧仲起的自殺,蔣光慈表示惋惜,同時認為除了繼續努力奮斗下去之外,第二條道路便是“既不能繼續反抗黑暗的勢力,又不能投降于敵人的營壘,那除了自殺,還有什么路可走呢?”*后指出:“我們的青年作家,是自殺了,這是誰的罪過呢?……若政治沒有光明的一天,那么這悲劇是永不會停止的。”(魏克特:《鳥籠室漫話》,載《海風周報》第4期) 1928年1月8日,茅盾發表了《歡迎(太陽)》(《文學周報》第5卷第23期),對于蔣光慈、錢杏邨等人的太陽社寄予厚望,同時對于蔣光慈寫的一篇宣言式的論文《現代中國文學與社會生活》提出批評,指出“惟有描寫第四階級的文學才是革命”的提法是錯誤的。 同年7月28日,被迫流亡于日本的茅盾撰寫了《從牯嶺到東京》論文,自我解剖了早期思想及創作,其中談到《幻滅》《動搖》《追求》的構思及創作經過,以及對于國內文壇的意見,這是針對太陽社、創造社存在的“革命文學和理論實踐方面的一些問題”,有感而發,結果引來了太陽社、創造社的“圍攻”,成為魯迅之外的又一個批判對象。 對此,錢杏邨曾寫過《從東京回到武漢》批評長文,分為5個部分,即《到了東京的茅盾》《纏綿幽戀,激憤昂法,迷亂人色的人生》《(幻滅)(動搖)的時代推動論》《所謂文論的天然對象》《從東京回到武漢》。但是,此長文“因種種的不得已的關系,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印將出來”。因此,錢杏邨將其中第三部分《(幻滅)(動搖)的時代推動論》發表于《海風周報》第14、15期合刊(1929年4月21日出版),并在文前作了有關說明。 錢杏邨為“標語口號文學”作了辯解,認為這是普羅文學創作初期的必然產物,“這一術語,雖是資產階級作家用為謾罵的工具,用來反應(映)普羅的‘宣傳文藝’一術語,在事實上只做了普羅文藝運動初期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不健全的技巧的創作的說明,事實上時(是)阻止不了普羅斗爭文藝的發展的。” 錢杏邨諷刺茅盾對于“標語口號文學”的批評,“他從普羅文藝立場退到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從認為必然的初期的普羅文藝的病態,而變為以這變態作為他的攻擊普羅文學對象,是(他)自己的進步!”*后6個字下面有粗黑點,以示重點,其意不言而喻了。 *后,錢杏邨還為郭沫若的文學是政治“留聲機”的觀點作辯護,認為“這個警語是非常正確的”。因此,“茅盾先生或許是物質的環境原(緣)故,根本不能了解留聲機器的奧意,而覺得是一種凌辱,那是當然的。至于茅盾先生要覺得有價值的,在革命文藝上不得不有反對的價值了”。“茅盾先生也許是要革命的,那么請你先要完全棄掉你自己階級的利益,努力獲得普羅的意識罷!” 錢杏邨自以為是堅決站在維護普羅文學的立場上,以此與蘇聯“拉普”某些文學觀點相接軌,把茅盾強行按在嚴厲批判的被告席上,此類似當初“圍攻”魯迅的遺風。以上談及錢杏邨對于曾“圍攻”魯迅有些悔意,同時繼續嚴厲批判茅盾,“舊事重提”(翻檢出昔日批判茅盾的文章),依然沿順著昔日“圍攻”魯迅的思維慣性。這“雙重標準”令人似乎不可理解,其實也很正常,不足為奇。 1932年10月,瞿秋白加入與胡秋原、蘇汶(杜衡)關于“文藝自由”論爭,在《現代》第1卷第6期發表了《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一方面為錢杏邨辯護,因錢杏邨的觀點被胡秋原抓住話柄;一方面批評錢杏邨,“要求文學家無條件的把政治論文抄進文藝作品里去,這固然是他不了解文藝的特殊任務在于‘用形象去思索’。錢杏邨的錯誤并不在于他提出文藝的政治化,而在于他實際上取消了文藝,放棄了文藝的特殊工具”。 ……
- >
詩經-先民的歌唱
- >
姑媽的寶刀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歷史與人類學概述
- >
人文閱讀與收藏·良友文學叢書:一天的工作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裝共3冊
- >
史學評論
- >
月亮與六便士
- >
莉莉和章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