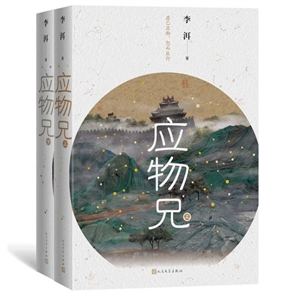-
>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茨威格短篇小說集
-
>
女人的勝利
-
>
崇禎皇帝【全三冊】
-
>
地下室手記
-
>
雪國
-
>
云邊有個小賣部(聲畫光影套裝)
-
>
播火記
應物兄-(上.下冊) 版權信息
- ISBN:9787020147465
- 條形碼:9787020147465 ; 978-7-02-014746-5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應物兄-(上.下冊) 本書特色
幾代作家向《紅樓夢》致敬的重要收獲。
新的觀察世界的方式,新的文學建構方式,新的文學道德,由此誕生。
應物兄-(上.下冊) 內容簡介
一部《應物兄》,李洱整整寫了十三年。
李洱借鑒經史子集的敘述方式,記敘了形形色色的當代人,尤其是知識者的言談和舉止。所有人,我們的父兄和姐妹,他們的命運都圍繞著主人公應物兄的生活而呈現。應物兄身上也由此積聚了那么多的灰塵和光芒,那么多的失敗和希望。
本書各篇章擷取首句的二三字作為標題,爾后或敘或議、或贊或諷,或歌或哭,從容自若地展開。各篇章之間又互相勾連,不斷被重新組合,產生出更加多樣化的形式與意義。它植根于傳統,實現的卻是新的詩學建構。
《應物兄》的出現,標志著一代作家知識主體與技術手段的超越。李洱啟動了對歷史和知識的合理想象,并將之妥帖地落實到每個敘事環節。于是那么多的人物、知識、言談、細節,都化為一個紛紜變幻的時代的形象,令人難以忘懷。小說*終構成了一幅浩瀚的時代星圖,日月之行出于其中,星漢燦爛出于其里。我們每個人,都會在本書中發現自己。
新的觀察世界的方式,新的文學建構方式,新的文學道德,由此誕生。
對于漢語長篇小說藝術而言,《應物兄》已經悄然挪動了中國當代文學地圖的坐標。
應物兄-(上.下冊)應物兄-(上.下冊) 前言
2005年春天,經過兩年多的準備,我動手寫這部小說。
當時我在北大西門的暢春園,每天寫作八個小時,進展非常順利。我清楚地記得,2006年4月29日,小說已完成了前兩章,計有十八萬字。我原來的設想是寫到二十五萬字。我覺得,這是一部長篇小說合適的篇幅——這也是《花腔》刪節之前的字數。偶爾會有朋友來聊天,看到貼在墻上的那幅字,他們都會笑起來。那幅字寫的是:寫長篇,迎奧運。我不喜歡運動,卻是個體育迷。我想,2008年到來之前,我肯定會完成這部小說,然后就可以專心看北京奧運會了。
那天晚上九點鐘左右,我完成當天的工作準備回家,突然被一輛奧迪轎車掀翻在地。昏迷中,我模模糊糊聽到了圍觀者的議論:“這個人剛才還喊了一聲完了。”那聲音非常遙遠,仿佛來自另一個星球。稍為清醒之后,我意識到自己還活著。后來,從車上下來兩個人。他們一句話也不說,硬要把我塞上車。那輛車沒有牌照,后排還坐著兩個人。我拒絕上車。我的直覺是,上了車可能就沒命了。
第二天上午,我接到弟弟的電話,說母親在醫院檢查身體,能否回來一趟?一種不祥的預感緊緊地攫住了我。當天,我立即回到鄭州。母親見到我的**句話是:“你的腿怎么了?”此后的兩年半時間里,我陪著父母無數次來往于濟源、鄭州、北京三地,輾轉于多家醫院,心中的哀痛無以言表。母親住院期間,我偶爾也會打開電腦,寫上幾頁。我做了很多筆記,寫下了很多片段。電腦中的字數越來越多,但結尾卻似乎遙遙無期。
母親病重期間,有一次委婉提到,你還是應該有個孩子。如今想來,我對病痛中的母親*大的安慰,就是讓母親看到了她的孫子。在隨后一年多時間里,我真切地體會到了,什么是生,什么叫死。世界徹底改變了。
母親去世后,這部小說又從頭寫起。幾十萬字的筆記和片段躺在那里,故事的起承轉合長在心里,寫起來卻極不順手。我曾多次想過放棄,開始另一部小說的創作,但它卻命定般地緊抓著我,使我難以逃脫。母親三周年祭奠活動結束后,在返回北京的火車上,我打開電腦,再次從頭寫起。這一次,我似乎得到了母親的護佑,寫得意外順暢。
在后來的幾年時間里,我常常以為很快就要寫完了,但它卻仿佛有著自己的意志,不斷地生長著,頑強地生長著。電腦顯示出的字數,一度竟達到了二百萬字之多,讓人惶惑。這期間,它寫壞了三部電腦。但是,當朋友們問起小說的進展,除了深感自己的無能,我只能沉默。
事實上,我每天都與書中人物生活在一起,如影隨形。我有時候想,這部書大概永遠完成不了。我甚至想過,是否就此經歷寫一部小說,題目就叫《我為什么寫不完一部小說》。也有的時候,我會這樣安慰自己,完不成也挺好:它只在我這兒成長,只屬于我本人,這仿佛也是一件美妙的事。
如果沒有朋友們的催促,如果不是意識到它也需要見到它的讀者,這部小說可能真的無法完成。今天,當我終于把它帶到讀者面前的時候,我心中有安慰,也有感激。
母親也一定想知道它是否完成了。在此,我也把它獻給母親。
十三年過去了。我想,我盡了力。
李洱
2018年11月27日 北京
應物兄-(上.下冊) 相關資料
13年潛心寫作,醞釀出一部標志著一代作家知識主體與技術手段的超越之作。“應物兄”!這個似真似假的名字,這個也真誠也虛偽的人物,串連起三十多年來知識分子群體活色生香的生活經歷,勾勒出他們的精神軌跡,并*終構成了一幅浩瀚的時代星圖。
——2018收獲文學排行榜長篇榜榜首頒獎辭
《花腔》用三段不同故事來展示個人在歷史中的細微感受,其方法、視野和思辨力令人望塵莫及,德國作家也不具備此種能力。倘若我如李洱一般年輕,我會妒忌他。
——德國著名作家馬丁·瓦爾澤
《應物兄》里的知識是讓讀者產生信任感的,小說家不是帶來新的知識,而是把默認的知識用他的方式表現出來,從而帶來真實世界的新鮮感。
——批評家張定浩
《應物兄》是今年濃度*的作品,我很久沒有看到具有如此總體性的文本了,當代小說更多是碎片化、現代性、后現代氣質特征,但李洱的文本特征席卷了理論視野。《應物兄》延續了李洱之前*好的東西,但又不是當年的李洱——《花腔》成為一種題材,《石榴樹上結櫻桃》成為他的語法,《應物兄》文本激活出很多副文本,體現了作家巨大的野心,以及被野心激活實現的文本。
——作家毛尖
李洱是歷史上以才學進入小說創作的第三人,前二位是寫《鏡花緣》的李汝珍和寫《圍城》的錢鍾書。
——復旦大學教授郜元寶
《應物兄》里有一句話:“一代人正在撤離現場》。”這對于生于1960年代的李洱同齡人來說,《應物兄》隱藏著秘密的代際知識圖譜,或者說“成長遺址”,引發了同代人強烈的共鳴。
——南京師范大學教授、評論家何平
一腳門內,一腳門外——評《應物兄》
王鴻生
敘事的“當下”性,小說的“移步換景、隨物賦形”,畢竟與詩、畫存在一定差異。詩、畫的視角,就是作者的視角,作者與對象之間的關系是直接的;而小說的書寫對象與作者之間,則夾著一個敘述人,小說的視角即敘述人的視角,哪怕這個敘述人是個隱含的作者。
《應物兄》需要一個特別的敘述人,這個敘述人就是應物兄。作為敘述人的應物兄之所以顯得特別,主要是因為:它既是作品里的一個人物,也是作者化入作品人物的“分身”之一;它既是一個非主人公的主人公,又是一個創造了隱含作者的作者;雖然小說的一切描寫、對話、事件,或見或聞,或印象或記憶,或思索或感覺,都嚴格出自應物兄“在場”的有限視角,但這個敘述人卻又具備在有限與無限之間收視返聽的能力。既然敘事時空是臨界的,敘述人在邏輯上必然也是臨界的。一個臨界的敘述人,只能是半個“局外人”,一腳門內,一腳門外,它必須學會在門檻上生存。此之奇謬,蓋因講述世道人心,只有臨界者才能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于是,仿佛游走在時間與空間、夢境與現實、已知與未知相互接引的界面上,它(他)邊講邊看,邊聽邊想,從而獲得了一種“究天人,通古今”的超越性的自由。
應物兄本名應物,只是出書交稿時忘了署名,出版商季宗慈交待編輯說,這是應物兄的稿子,小編隨手填上“應物兄”三字,這名字就流行開來了。一般來講,作家起書名、人名往往非常講究,除了上述“特別”的理由,李洱的小心思還在于,防止讀者把應物兄完全當作他本人。就像在馬路上立了一排有空隙的隔離帶,李洱不用翻越路障,就能自由來回,穿梭而過。你們可以說我是應物兄,我也可以說我不是應物兄,一個人總不能稱自己為“兄”吧?寫到這里,我仿佛都看見了李洱那種帶著狡黠表情的嘎嘎大笑。要知道,應物兄額上的三道深皺,無意識地把別人的打火機裝入自己口袋的積習,沖澡時用腳洗衣服,喜歡看“雙腳交替著抬起、落下,就像棒槌搗衣”,實在與生活里的李洱嚴絲合縫啊。
還是讓我們對“應物”二字做點釋義吧。應,有順應、適應、響應、應對、應變、應付、照應等義。物,復雜一些:《周易.序卦》云“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指具體實物;《荀子.正名》曰“物也者大共名也”,指事物之共名;而《老子》的“道之為物,惟恍惟忽”,則將物視為道一般的客觀存在;《中庸》以己、物對舉,《孟子》以心、物對舉,王陽明《傳習錄》的“物即事”、“心外無物”,干脆認為,物就是心事。由此可見,“應物”一詞,在中國哲學傳統中大有來頭。如:“應物隨心、應物通變”講的是內在自由,小說中數度出現的“應物而無累于物”講的是在世俗中超越世俗,“無常以應物為功,有常以執道為本”(歐陽修《道無常名說》),應物其實應的是“有無”之道。不管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否被物化,應物其實也是應人,而按*初給應物兄起名的鄉村教師朱三根用典,應物還體現了“圣人之情”。應物,亦應人、應世、應事、應道、應己、應心,凡此皆說明,作者將書名、敘述者名、主要人物名統一于“應物”,實有深意寄托焉。以一部書鉤沉一個被埋在歷史深處的詞語,拂拭、擦亮,再將其所蘊含的古老思想之光折射于熱鬧而蒼涼的現代社會,當代漢語長篇中我不記得有第二部了。
此話題且打住。從討論敘述人的角度,《晉書》里“虛己應物,恕而后行”這句話,似乎更讓人在意。虛己應物的待人處世之道,恕而后行的仁者行為準則(即恕道,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實也是小說的敘事之道。充分主體化的敘述人,是傲慢的、自以為是的敘述人,它往往會依憑自己的意志和主觀的好惡,來決定故事的走向,支配人物的形態、行為、命運,并指派一些有名、無名的人物來襯托主要人物。《應物兄》無疑提供了一個公正的敘述者,一個讓事物自行自在的敘述者,一個內斂的、仁慈的、不對口中事物輕易臧否的敘述者。凡人凡物,無論尊卑、大小、長短,在《應物兄》中皆有其名。在它的講述過程中,眾聲喧嘩、眾生平等,不僅體現于讓人物按自己的身份、性格說話辦事,讓動植物以自己的姿態、色調活躍于大千,而且也體現在所述事物該占有的篇幅、位置,甚至還包括諸多人物、動物、植物、食物、器物的比重、出場頻次。
應物亦尊物。亦周到地照應和善待物。以恕道對待每一個人,每一件事物,這個敘述人實在非常地儒家。人到中年,與李洱早先寫知識分子的中短篇小說相比,應物兄的自我姿態和聲調顯然都低了下來,作為敘述人,它不再那么自得、饒舌,像個精力充沛、無所不知的話澇。與李洱著名的長篇小說《花腔》相比,作者的注意力也不再執拗于尋找和探索個人(葛任)的存在。記得李洱曾說過,自己的寫作是“泡咸肉”,是鹽與鹽的對話:“釋放一點點自己,以激活更多的他人”。當敘述人同時也是故事人物的時候,虛己即及時地移位、讓位、側身,以便接納更多的他者,釋放更多的聲音,這一弱化主體而不是突出或取消主體的方式,應看作當代中國思想對西方啟蒙哲學和后現代哲學之緊張關系的疏解。虛己應物,具有特殊的敘事倫理意義,從這種敘事倫理意識的實踐效果來看,作者已深諳敘述的德性。而創造出這樣一個公正的、悲天憫人的敘述者,可謂當代中國小說一再向《紅樓夢》致敬的重大收獲之一。
相應地,作為書中的一個具體人物,應物兄雖然對全書至關緊要,但在作品中并不占有中心位置。他有思想、有學問但沒有權力,有追求、有向往卻無力遂愿,他不能把控任何事情,連僅有的兩次”偷情“也是被動的、懊悔不已的。在結構上,他只是一個多功能的樞紐、通道——“他有三部手機,分別是華為、三星和蘋果,應對著不同的人”,說明他時刻保持著與世界各方的聯線;“喬木先生與別人談話的時候,應物兄有時會充當潤滑油,有時候會充當消防栓,有時候會充當垃圾筒或者痰盂,還有的時候會充當發電機”,這是他在使用各種功能性的“招數”保證著話語活動的持續進行——這也是我將應物兄定義為“非主人公之主人公”的一大緣由。
除了抽象的敘述人和敘事功能上的樞紐、通道、潤滑油、消防栓、發電機,應物兄當然也是書中的一個活人,一個當事者,一個有血有肉的觀察者,謙抑、寬容的傾聽者。應世、應事、應人、應己,他雖然內在反應極度活躍、靈敏,甚至忍不住腹誹,但在領導面前“諾諾”,在前輩面前“弟子服其勞”,在鑄下大錯的學生面前發個火卻“把自己下了一跳”,該忍不該忍的一切都“忍”了,這種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呢?儒學修養自是一個方面,創傷記憶則是另一個方面。“知識分子的一個臭毛病就是逞口舌之快”,為此應物兄差一點付出慘痛代價。小說在開卷第2節就提出了一個吃緊問題:如何管住舌頭又不使精神黯啞?導師、岳父喬木先生早年告誡他:“記住,除了上課,要少說話。能講不算什么本事。善講也不算什么功夫。孔夫子*討厭哪些人?討厭的就是那些話多的人。孔子*喜歡哪些人?半天放不出一個屁來的悶葫蘆。顏回就是個悶葫蘆。.......日發千言,不損自傷。”一旦遵從師教,他的思維卻變得遲鈍起來,一度還陷入了恐懼:自己真的變成一個傻子了?是不是提前患上了老年癡呆癥?
但是有一天,在鏡湖邊散步的時候,他感到腦子又突然好使了。他發現,自己雖然并沒有開口說話,腦子卻在飛快地轉動。那是初春,鏡湖里的冰塊正在融化,一小塊,一小塊的,浮光躍金,.......自己好像無師自通地找到了一個妥協的辦法:我可以把一句話說出來,但又不讓別人聽到;舌頭痛快了,腦子也飛快地轉起來了;說話思考兩不誤。
伴隨著只有他自己才能夠聽見的滔滔不絕,在以后的幾天時間里,他又對這個現象進行了長驅直入的思考:只有說出來,只有感受到語言在舌面上的跳動,在唇齒之間出入,他才能夠知道它的意思,他才能夠在這句話和那句話之間建立起語義和邏輯上的關系。他還進一步發現,周圍的人,那些原來把當他成刺頭的人,慢慢地認為他不僅慎言,而且慎思。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一句也沒有少說。
在“自己跟自己下棋”的相互博弈里,應物兄學會了與世界和平相處的獨特方式:間距。記憶中的那段“冰舞”,使應物兄理解了舞蹈者之間的間距:欲拒還迎。拒、迎之間形成了奇特的張力,這種“張力”或應有更具體、確切的命名?正如在誠實與撒謊之間,是否還有另一個詞?在冷眼旁觀與相擁而眠之間,有沒有另一種狀態?在清醒透徹與暈暈乎乎之間,會否夾著別樣的思維?在*人稱、第二人稱、第三人稱之間,是否還藏著更有意思的奧妙?“之間”,這個同時確證了存在之親密與疏離的“之間”,揭示了某種非距離的距離感,敘述者與被敘述者,應物兄和自己,乃至書中所有師生同事、上級下級、父女母子、朋友熟人,其交互關系多少都會透出這種奇異的間距性。這種“間距性”幾乎遍布于敘述的每一處夾層,使《應物兄》讀起來,似乎每個局部都是踏實的、精準的,但整體感卻是恍惚的、迷蒙的。李洱喜歡法國作家加繆,不是個秘密,但他用“間距”的世界來置換加繆“脫節”的世界,把“局外人”莫爾索變成“半個局外人”應物兄,則意味深長:“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紅樓夢》的荒唐感與西方存在主義的荒誕感,區別恰在于一個“情”字。一如書中程濟世先生所言:一個儒家可以節欲、寡欲,但不能寡情、絕情,更不能無情。
“我們的應物兄”,小說里反復出現的這一稱謂,體現了這種既親密又疏離的間距特征,也提示出一種三層嵌入式的敘述視角:敘述者隱身在人物背后,隱含作者隱身在敘述人背后,還有一個觀察者,則隱身在隱含作者的背后。這個觀察者意味著他者的目光?還是文德能死前提到的那個奇怪單詞Thirdxelf”(第三自我)?究竟是一個莫名的“他”在看,抑或是一個更神秘的“我”在看,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設置了這一視點外的視點,我們就無法再自戀,再自欺了。
舉頭三尺有神明。知白守黑。《應物兄》的敘述人,當是一個懂敬畏、知進退、有情義的敘述人。
應物兄-(上.下冊) 作者簡介
李洱,中國先鋒文學之后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1966年生于河南濟源,1987年畢業于上海華東師范大學。曾在高校任教多年,后為河南省專業作家,現任職于中國現代文學館。著有長篇小說《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等,出版有《李洱作品集》(八卷)。《花腔》2003年入圍第六屆茅盾文學獎,2010年被評為“新時期文學三十年”(1979—2009)中國十佳長篇小說。主要作品被譯為英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韓語等在海外出版。
《應物兄》為其最新長篇小說,獲2018《收獲》文學排行榜長篇小說第一名。
- 主題:也許是我不夠,實在看不下去
此書一共兩冊,上冊只看了三分之二,實在是看不下去了,平淡的升過一杯白開水。有人說作者是在效仿《紅樓夢》,也許是我的文學功底差,或是那人抬舉了李洱,我讀下來只覺得煩,就是一盤嫩綠的蔬菜一點鹽味沒有一樣。看似漂亮嚼之無味。
- >
二體千字文
- >
中國歷史的瞬間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
- >
我從未如此眷戀人間
- >
經典常談
- >
煙與鏡
- >
姑媽的寶刀
- >
自卑與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