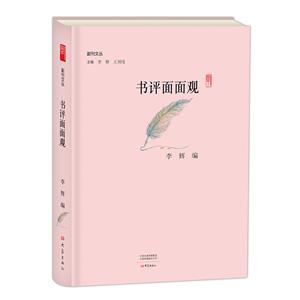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書評面面觀/副刊文叢 版權信息
- ISBN:9787534795572
- 條形碼:9787534795572 ; 978-7-5347-9557-2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書評面面觀/副刊文叢 本書特色
在編選諸多書評時,我有意側重收入帶有批評性的書評,我們可以從中看到當時書評是如何爭取保持客觀性,對于當前書評界一味地贊譽之風,也許不失為一面鏡子,一貼清醒劑。為了讀者閱讀的便利,我將各文標題規范化,對原題多有改動。 此書有它的新的意義,舊夢的追尋,也能給人新的回味。但人絕不是夢的依戀者,需要的是從夢中走出來,將昔日的夢化為今日的現實。在這個意義上說,我絕不是對蕭乾舊夢的偏愛,而是設想著這本書的問世,會使更多的人,用踏踏實實的工作和豐碩的果實,來充實、來完成前輩們所未完成的“夢”——書評。 ——李輝
書評面面觀/副刊文叢 內容簡介
書評如今已成為許多報紙的重點版塊。蕭乾先生三十年代就讀燕京大學期間,研究書評,畢業論文《書評研究》193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同年,他接替沈從文編輯《大公報》副刊,約請朱光潛、巴金、葉圣陶、沈從文等諸多名家和書評家,談什么是好的書評。與此同時,蕭乾在副刊于1936、1937兩年間,發表各類書評多篇。
李輝編的《書評面面觀(精)》從《大公報》副刊上精選名家談書評文章,以及所刊發的部分書評,可供當下書評作者參考,推動書評寫作的多樣化。
書評面面觀/副刊文叢 目錄
《書評面面觀》新版前記?
**輯? 蕭乾:一個未完成的夢
未完成的夢?
書評與批評?
平衡心?
知識與品位
書評和做人?
美
藝術與道德?
書評與出版商?
書評與書評家?
第二輯? 大家談書評
談書評?
我對于書評的感想?
我如果是一個作者?
我只有苦笑?
假如我是?
書評家即讀者?
批評家的路?
書評家的限制?
批評與探險?
讀者?書評?書評家?
書評的內容?
掌握那條繩索的?
沖出狹窄的風氣?
一個圖書館員論書評??
我們的書評家?
“集評”更理想些?
書評和讀者?
?通俗化些?
一位良師?
不要武斷?
我們得到了些什么
第三輯? 書評精選
徐懋庸的《打雜集》 ?
郁達夫的《出奔》
卞之琳的《魚目集》 ??
顧一樵、顧青海的《〈西施〉及其他》 ?
何谷天的《分》 ?
蹇先艾的《城下集》 ?
李廣田的《畫廊集》 ?
蘆焚的《谷》 ?
朱光潛的《孟實文鈔》 ?
畢奐午的《掘金記》 ?
鄧以蟄的《西班牙游記》 ?
李廣田的《銀狐集》 ?
艾蕪的《南行記》《夜景》 ?
蘆焚的《里門拾記》 ??
編后記?
書評面面觀/副刊文叢 節選
未完成的夢 蕭? 乾 人到老年,一種悲哀,一件憾事,是夢少了,偶爾腦海里冒出點什么,也一晃而過。不知是做夢的機器生了銹,還是由于幻滅得太頻繁而干脆罷了工。年輕時,我曾經是個夢想很多的小伙子。那時釘子碰得還不多,往往不問國情,不顧現實,就讓自己的夢盡情馳騁。 距今 50 多個春秋,也即 1934—1935 年。我忽然心血來潮,對書評感起興趣。恰好那時我正需要交一篇畢業論文。身在新聞系而心在文學系的我,就找了個跨在兩系之間的邊緣題目:書評研究。開頭,我挑上它還只不過是為過關。可是鉆進去之后,我發現它并不僅僅是報刊上偶爾設置的一個欄目,而是現代文化這巨廈一根不可或缺的梁柱。當時我曾預言:“隨著讀者層的擴大,新聞紙銷路的飛增,這勢力對于著作界、出版界、讀書界,都將具有相當的權威。……終有一天它將像塞克斯機一樣會在這古國國土上飛翔起來。” 我有多么樂觀,又多么天真啊! 1935 年 7 月,用那論文(就是這里重印的)換到一紙文憑后,我就走馬上任去編天津《大公報》的文藝副刊了。近年來李輝同志為了尋覓我過去的足跡,時常鉆到北京圖書館舊報刊部故紙堆里,從而發現那些年月里我曾怎樣不遺余力地提倡過書評。除了這本小書,我確實還曾充分利用了《大公報》那塊園地,聲嘶力竭地為書評而吶喊過。我宣告職業化的書評家終將誕生,并且還嚷著:“我們需要兩個批評學者、六個批評家、五十個書評家。” 我組織起一支書評隊伍:楊剛、宗玨、常風、李影心、劉榮恩等。有的還健在,有的已作古;有的移居海外,有的仍在我們中間。我對廣告向來懷有成見,甚至有意識地抵制,總不甘讓它左右我的選擇。在牙膏、鞋油上是如此,在看什么、買什么書上,我更不愿受它的操縱擺布。當時我認為書評就是為了讓讀者對書能有比廣告來得客觀的評價。所以我的一個原則是:堅持自己花錢買書來評,不評贈書。在上海時,我頂著大太陽,冒著溽暑,去四馬路買回一疊疊值得一評的書,然后打包分頭寄給我那十來位書評家,請他們評論。 在天津編刊物時,我還只是在自己寫的那些“答辭”中鼓吹書評。到了上海,除了刊物上經常保持書評專欄,我還編了幾個討論書評的特輯。謝謝上海《書訊報》的葛昆元同志,前年他在選登我這老掉牙的《書評研究》時,還特意把那幾個特輯復制出來見贈。這樣它們也同新時期的讀者見面了。記得盧溝橋已經開了火,我還在為書評奔走!有一個特輯好像就是在“八一三”那天刊出的。不幾天,由于報紙縮張,文藝版取消,我這個編者也隨之而失業了。 半個多世紀后,書評并沒在讀書界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也還沒見到有人像當年的宗玨、李影心那樣以寫書評為職業。書評更算不上一種文學品種,它依然以“聊備一格”偶爾出現在報刊上。 為什么說當年那樣提倡書評、鼓吹書評的重要性是天真呢?請聽聽一個奔 80 的糟老頭子說幾句世故話吧。老早我就懂得了在中國想干點什么,說點什么,都得先問問國情。國情是無形的,因為它既沒有明文規定,也找不到哪一位來坦率指出。它,只能心領而不可言傳。只有在碰了硬釘子之后,你才會恍然大悟:原來這使不得!可那時候多半已悔之晚矣。 旨在為讀者當讀書咨詢者的書評之所以樹立不起來,就是因為中國寫書的人大都只允許你褒,容不得你貶,即便你貶得蠻有道理。一本書出來,如果誰也不吭一聲,寫書的人倒并不在乎。說上點子好話,自然就不勝感激;倘若你歷數一本書的七分好,同時也指出它的三分差,麻煩就來了。正面申辯,甚至抗議,本無不可。然而不,他會在另外場合挑眼找茬,為幾個字竟然能結下多年深仇,在你料想不到的時刻和場合,大做起文章。倘若能發明出一種足以洞察積怨的顯微鏡,并用它來照照歷次運動中的發言,大批判欄上的聲討,那必然會觸目驚心。 年初在香港,讀了臺灣龍應臺的兩本書——《野火集》和《龍應臺評小說》。這位血氣方剛的女性大概看不慣那里一些不痛不癢的文藝批評和社會批評,想靠個人的一股勇氣,冒犯一下,闖出個新局面。她自稱要做的是“不戴面具,不裹糖衣”。她反對“四平八穩,溫柔敦厚”的批評,也不喜歡“點到為止”的批評,更不耐煩戴著面具看事情,談問題。 結果,她發現對一個健康人,你擰擰他的手臂,掐掐他的腿,他不會起激烈的反應。可一個皮膚有病的——不管是蜜蜂叮咬的紅腫,還是病菌感染的毒瘤,只要用手輕輕一觸,就可能引起他全身痙攣。所以人們寧肯寫引經據典、長篇大論的文學批評,很少人愿干開門見山、短兵相接的書評這一行。 然而為什么時至 80 年代,我對書評這個夢還依然鍥而不舍呢? 30 年代我曾提倡書評,可比起今天來,那時有幾本書可評!今天出版物成百倍地增加,有哪位一目十行的奇才能把(比如說文藝)書全看了呢?今天不是比中國文化史上任何時期更該有一批仁人志士,自愿當文化咨詢者,幫助廣大讀者選一選書嗎?眼下時興搞咨詢站,保險業設立咨詢站,計劃生育設立咨詢站。難道為廣大群眾提供精神食糧的出版業,不也該設些咨詢站嗎? 我之所以讓這本書同新時代讀者見面,是表示我對當今“雙百”方針的信念。我相信不至有“先進”的捍衛者用 80 年代的尺度來衡量這本半個多世紀前寫的小書。然而我對自己尚有冷靜的估計。以此書來說,就寫得十分粗糙,觀點更談不上準確。尤其書中所舉的例子又大多出自西方報刊,因為我當時身在燕京那個洋學堂,找不到多少東方資料。我衷心希望拋出這塊 50 多年前的老磚,能在新時代引出思路更透徹、立論更正確、例子更生動具體的玉來,更希望書評在咱們這里,能成為一個具有吸引力的文字行當。 1987 年 10 月 3 日
書評面面觀/副刊文叢 作者簡介
李輝,著名人文學者,傳記散文作家。先后發表論著《巴金論稿》 《蕭乾傳》 《沈從文與丁玲》 《胡風集團冤案始末》 《黃苗子與郁風》等長篇傳記以及《滄桑看云》 《陳跡殘影》等隨筆集,《福斯特散文選》 《走進中國》等譯著。1994年起,先后在《收獲》雜志開設文化隨筆專欄“滄桑看云” “陳跡殘影”,隨筆集《秋白茫茫》獲首屆魯迅文學獎(散文類)。1998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李輝文集》(五卷本),2001年起在大象出版社出版圖文系列“大象人物聚焦書系”,后來進一步合作,主編“大象人物自述文叢” “大象人物日記文叢” “大象人物書簡文叢” “大象名家收藏” “印象閱讀” “名家文化小叢書”等幾個系列套書。
- >
中國歷史的瞬間
- >
月亮虎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裝共3冊
- >
詩經-先民的歌唱
- >
姑媽的寶刀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歷史與人類學概述
- >
隨園食單